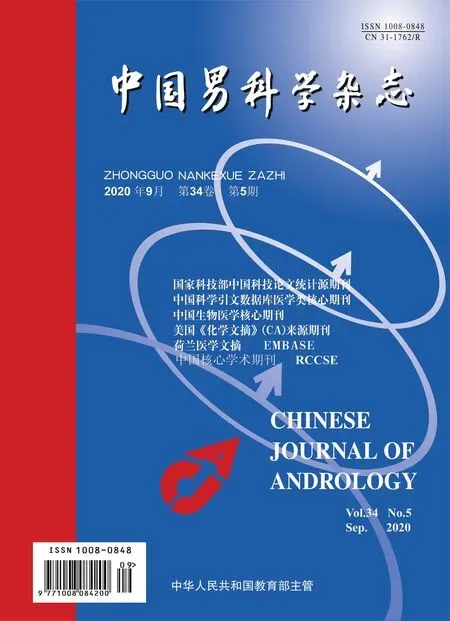男男性行為者中尖銳濕疣臨床治愈后人乳頭瘤病毒清除時限及其相關因素研究
倪禮楠 陸 晟 鄒丹陽 周平玉,*
同濟大學附屬上海市皮膚病醫院 上海市皮膚病醫院(上海 200443)
尖銳濕疣(condylomata acuminata,CA)是由人乳頭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感染導致的性傳播疾病。研究顯示性活躍人群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存在HPV感染[2],約4%的HPV感染可引起細胞學的變異[3]。HPV具有高度傳染性,但通常情況下其在基底細胞中的潛伏感染DNA拷貝數較低故而無法進行傳播,而在亞臨床感染時其拷貝數增高但無任何臨床癥狀,這使得HPV的傳播較為隱匿[4]。HPV的持續存在,不僅是CA的高復發率的根源,高危型HPV的長期存在更是宮頸癌、外陰癌、肛門癌、陰莖癌等的發病基礎[5]。
宮頸癌是全球女性第四大惡性腫瘤,近90%的宮頸癌是由高危型HPV感染引起的[6]。因此對這一已成為全球性女性健康的公共衛生問題的病原體在女性中的轉歸已經有了大量的研究。研究顯示HPV感染女性后,2年內的自然清除率約85%[7-8]。而HPV在男性中的感染情況及其導致的后果相較于女性遠遠沒有受到足夠重視。事實上HPV對男性造成的傷害并不亞于女性,尤其在男男性行為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人群中。由于MSM性交方式以肛交為主,而肛管內以單層柱狀上皮為主,容易在肛交過程中受損,故這一人群為性傳播疾病的易感人群,全球范圍內的報道都提示在MSM中HPV有著較高的感染率[9-11],且大部分的肛門癌均由致癌性的HPV導致,主要集中于MSM[12-13]。因此了解這一人群中的HPV感染和自然清除情況十分有必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患有尖銳濕疣的MSM人群中在尖銳濕疣臨床治愈后HPV的清除時限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以期為今后規劃這一人群的HPV感染的隨訪時間提供理論依據。
材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選擇于2018年2月至2018年6月就診于上海市皮膚病醫院性病門診的CA患者。符合如下標準的納入研究:1.通過臨床及核酸檢測明確診斷為的CA;2男男性行為者;3.經過治療后3個月不復發;4.完成隨訪至HPV轉陰,或者完成尖銳濕疣臨床治愈后為期2年的隨訪。5.具有完整的病史資料。
二、客觀指標
通過問診的方式獲得患者的婚姻狀況、文化程度、性伴類型、安全套使用情況、治療以及隨訪期間的性生活情況、梅毒和/或HIV合并感染情況、既往治療方法以及皮損的部位的信息。其中病程指的是確診CA直至HPV消失的這段時間,梅毒的確診依靠初次就診或病歷中梅毒螺旋體明膠顆粒凝集試驗 (Treponema pallidum particle agglutination,TPPA)的檢測結果,陽性即為患有或患過梅毒。HIV感染的診斷標準為結合流行病學史,且符合下列一項者:(1)HIV抗體篩查試驗陽性和HIV補0充試驗陽性 (抗體補充試驗陽性或核酸定性檢測陽性或核酸定量大于 5000拷貝/ml);(2)HIV分離試驗陽性。
三、治療后隨訪及HPV檢測
醫師分別于初診及隨后5次隨訪中對患者的CA部位用專門的拭子進行采樣。每次隨訪距離上次就診時間至少間隔3個月但在6個月以內。而后用人乳頭瘤病毒核酸分型檢測試劑盒 (流式熒光雜交法)(透景TELLGEN)進行樣本處理,PCR擴增以及雜交檢測。最后用LuminexTM 200進行HPV型別的檢測。可檢測出的型別有HPV6,HPV11,HPV16,HPV18,HPV26,HPV31,HPV33,HPV35,HPV39,HPV40,HPV42,HPV43,HPV44,HPV45,HPV51,HPV52,HPV53,HPV55,HPV56,HPV58,HPV59,HPV61,HPV66,HPV68,HPV81,HPV82以及HPV83。
四、統計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21.0進行數據分析,由于總樣本數量過少,分類資料僅能采用Fisher確切概率檢驗,以P<0.05定義為具有統計學差異。
結 果
一、一般資料
本研究總共收集32位患者的信息。這32位患者均符合我們所列出的納入標準。其一般資料如表1所示。

表1 32例尖銳濕疣患者的一般資料
二、患者隨訪期間HPV檢測情況
本研究對32位CA患者清除感染灶后進行了密切隨訪,在局部尖銳濕疣3個月未復發的人群中觀察其的自然清除和HPV型別變化。隨訪中的HPV檢測率的情況詳見表2。

表2 患者隨訪中的HPV檢測情況n(%)
而后我們運用了卡方檢驗探究HPV的復發是否與時間的推移有關,結果詳見表3。可以發現HPV在隨訪期間的陽性率呈現波浪形,在完成治療后3個月和距離隨訪第二次檢測均出現HPV陽性率高峰。這可能是由于在臨床隨訪的過程中患者復查HPV陽性即會進行治療干預有關。

表3 患者隨訪中的HPV檢測情況與隨訪時間的關系

表4 20位患者初診以及隨訪中的HPV型別
在32名患者中有12人(12/32,37.50%)隨訪期間從未測出HPV,即初診經過治療后HPV型別全部清除。(包含前幾次對方未如約復診,但后幾次隨訪均未出測出HPV)其余20人在隨訪期間的任意一次HPV檢測均檢測出陽性。表4為這20位患者初診和隨訪時測得的具體HPV型別。其中,有10(10/20,50.00%)人出現了和初診檢測出的HPV型別不一樣的新型別。從表4中我們可以看出新型別出現的高峰在第三次檢測的時候(7/10,70.00%)。 而有 5(5/20,25.00%)人經初診治療轉陰后又再次能檢測出HPV,其中有3(3/5,60.00%)人感染的依舊是原先的型別,另外2(2/5,40.00%)人出現了新的型別。在這20位患者中,分別有1人(1/32,3.13%)、5 人(5/32,15.63%)、4 人(4/32,12.50%)于隨訪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檢測后未測得HPV,即在隨訪過程中HPV型別全部清除。而仍有10人(10/32,31.25%)于初次治療經過2年仍能測得HPV。
三、患者初次治療后HPV清除的相關因素
從上文我們已經得知有12人隨訪期間從未測出HPV,即已在初次治療后就實現了HPV的清除。為了探究隨訪期間HPV復發與哪些因素相關,我們將患者按初次治療后的HPV清除情況分成了兩組:即已清除組和未清除組,并對收集到的相關資料進行了卡方檢驗遙如表5所示,我們可以發現HPV的清除與有無性生活、是否患有梅毒和HIV感染、性伴情況、病程、治療方式、CA部位和初診時是否含高危型別均無相關性。

表5 患者隨訪中的HPV清除的相關因素分析n(%)
四、患者隨訪期間HPV清除的相關因素
為了探究隨訪期間HPV清除的相關因素,我們每一次隨訪后未測得HPV的患者進行分組,并將其收集的數據進行了卡方檢驗。如表6所示,我們發現HPV的清除時限與HIV感染、性伴類型、CA部位、病程、治療方式、有無性生活以及是否含有高危HPV型別均無關系。而CA的復發也與隨訪期間的HPV檢測的陰性率并無關系。

表6 患者隨訪中的HPV檢測情況的相關因素分析n(%)
五、患者隨訪期間HPV新型別出現的相關因素
我們發現在患者隨訪的過程中有不同于初次就診時的新HPV型別出現,新型別的出現可能是由于再感染,也有可能是由于初診是HPV DNA載量并未到達檢測上限。表7所示,隨訪中新HPV型別的出現與有無性生活、是否患HIV以及性伴情況無關。

表7 患者隨訪中的HPV新型別出現的相關因素分析n(%)
討 論
HPV的持續感染可導致尖銳濕疣復發[15]和肛門直腸癌的發生[16],前者會對患者造成極大的心理負擔以及高額的經濟支出,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后者可以危及生命。因此了解男男性行為人群中HPV的自然清除情況有十分重要的公共衛生安全意義。
本文首次對我國MSM人群中尖銳濕疣臨床治愈后HPV清除率開展長達2年甚至更久時間的臨床觀察研究。國外有關研究男性CA的文章中提到,約有2/3的男性CA患者可以實現HPV清除[17]。本文中的MSM中2年內HPV總清除率為68.75%(22/32),與男性群體對照并無差異。國外的一項隨訪時間長達兩年的研究顯示:雖然MSM的HPV患病率和發病率高于非MSM人群,但HPV的清除率相似[18]。本文沒有對我國非MSM尖銳濕疣的人群進行觀察,但與已有的國外研究比較,我國MSM的HPV總清除率與國外非MSM人群相比并無差異。
在本文中,我們并沒有發現隨訪中新HPV型別的出現與有無性生活、是否患HIV以及性伴情況有關。我們無法得知新出現的HPV型別是本來就存在于原先病灶部位,只是由于未達到目前的檢測閾值而未檢測出,還是確實是新出現的HPV感染但由于大多數人(70.00%)的新型別出現于第三次檢測,且隨訪中性生活次數相較于治療中和治療隨訪期間都大大增加;另外我們發現在初診治療轉陰后再次檢測出HPV,并且出現了新型別的2人均僅在隨訪期間發生過性行為。限于研究人群的樣本量,雖然得不出有無統計學意義的結果,但我們推測新型別的出現仍可能與隨訪期間性行為引起的再感染有關。
與大多數病毒不同,HPV的整個生命周期均存在于上皮細胞中。有研究表明HPV清除之后會部分或者完全的獲得免疫[19]。但是急性感染高危型別時,只有約50%的患者會發生血清轉化,且平均需要12個月[20-21]。這導致大多數人依舊會被同一型別感染。而亦有文獻提示HPV6抗體會在治療后消失[22-23]。在本文中初診治療轉陰后再次于隨訪中出現了原先的型別的有3人,而其中有2人原先的型別是HPV6,這似乎印證了這種說法。而另一人的原先型別是HPV31,屬于高危型別。經過查閱,這3人中有2人在隨訪期間有性行為發生。根據以上這些我們可以推測,即使復發的是同一型別,仍然與再感染相關的可能性更大。但不可排除初診治療后HPV DNA載量下降至檢測閾值以下這種可能。
機體的免疫狀態在病原體的清除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由于HIV感染主要破壞機體的細胞免疫系統,因此HIV對于HPV感染的影響巨大,無論是HPV的感染還是復發,HIV陽性都是重要的危險因素[24]。研究指出患有CA的MSM如果合并HIV則會使尖銳濕疣的復發率增高[25]。而在本文中我們并沒有得出這樣的結論,其可能的原因其一是由于入組患者的選擇有關,本研究納入的人群為治療后至少3個月未復發的人群;其二樣本量較少,其三可能是本文中的所納入的患者抗病毒治療有效,AIDS控制情況良好,抗HIV治療后免疫重建良好。由于本文為回顧性研究,故我們無法再得到患者的CD4+T淋巴細胞計數的數據,這是本研究的一大缺陷。
研究顯示,婚姻狀態依舊是HPV感染的相關因素[26-27]。但本文中的MSM的婚姻狀態絕大多數(93.75%)都是未婚,我們無法得知婚姻狀況是否為HPV復發的相關因素。但是未婚意味著沒有法律的束縛,很可能導致性伴侶的波動和性伴侶數量的增多。而后者是HPV感染的危險因素[28]。本研究絕大多數MSM(96.88%)在性行為時經常使用避孕套,未得出安全套在阻止HPV傳播中的作用。而Pragna Patel等人所做的研究發現無套肛交是感染HPV的危險因素[18]。我們推測盡管患者主訴“經常”用避孕套,但未能堅持在每次高危性行為中應用,因此無套肛交也混雜在這一人群中,從而使他們感染HPV。
在本文中任何時段的性生活有無都與CA的復發沒有統計學上的相關性。Hernandez AL等的研究提示性交的頻率越高,發生感染的風險越高[29]。結合本文的結論提示,HPV的清除率或許仍與治療完成之后的性生活頻率相關,無論在治療完成后的哪個時段。而有文獻報道,暴露于多個伴侶能夠增加CA復發和發病的風險[18]。而在本文中,我們僅僅對性伴類型進行分析,并沒有統計學意義。這提示無論是固定性伴還是非固定性伴,性伴數量上的增加才是降低HPV清除率的相關因素。
有關于年齡、文化程度等因素,不同的文獻給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國外的文獻有報道,發現年齡和受教育時間短的HIV陽性的MSM,肛門高危型HPV感染的風險更高[30-31]。而國內有文獻報道,HPV感染與復發和文化程度無關,而和年齡、初次性行為等有關[32]。在本文中,我們統計的一般情況如年齡、文化程度等均與HPV的復發無關。這或許也和我們納入的患者年齡(集中于20-40歲之間)和文化程度(大學學歷占總人數的65.63%)較為集中有關。
本研究的理想狀態雖然是受試者需要在隨訪期間固定的時間點進行復查,受限于回顧性研究,很多患者只是在自覺有新生物的情況下才來復查。這也導致本文隨訪期間的HPV檢測的資料缺如。盡管受限于本文的樣本量,可能導致結果的偏移,然而本文首次在國內以2年為隨訪時間探討HPV的清除率及其的相關因素,一定程度上明確了CA患者需要長時間隨訪的必要性,為臨床指導MSM的尖銳濕疣患者的隨訪提供了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