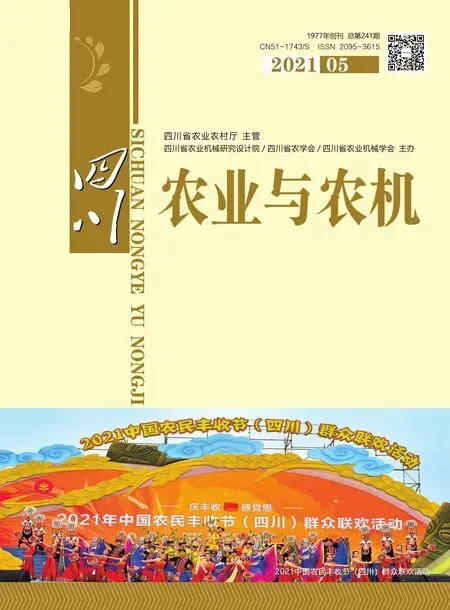科技助力涼山彝族自治州葡萄產業高質量發展*
四川水果創新團隊
水果創新團隊成員:呂秀蘭、馬暉、梁東、王進、劉偉、林立金、夏惠、劉磊、熊亮、張颯、李紅春、冷敏、袁敬勇、余斌文、邱乾光、徐堃富、祝進、萬勇、胡榮平、陳安均、李慶。
涼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簡稱“涼山州”)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干濕分明,冬春半年日照充足,少雨干暖;夏秋半年云雨較多,氣候涼爽。西昌市作為典型代表,素有“小春城”之稱,年均溫17.5℃,年降雨量1 000 mm左右,年日照時數2 400 h左右,空氣年平均濕度65%,是我國乃至世界最優晚熟葡萄生態區。
葡萄產業已成為涼山州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主導產業之一,常規普通種植效益可達45.0萬~75.0萬元/hm2,典型效益可達100.0萬~120.0萬元/hm2,在高額回報的吸引下,當地許多農戶和其他行業人員紛紛借錢、貸款或融資種植葡萄,租金高達4.5萬~7.5萬元/hm2,且“一地難求”,建園成本高達60.0萬~75.0萬元/hm2,個別高達90.0萬~120.0萬元/hm2。葡萄產業無序擴張和盲目追新種植,增加了產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因此,必需對葡萄產業的適度發展、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提質增效等有較清楚的認識,協同創新科技,助力涼山州葡萄產業高質量發展。
1 2016~2020年涼山州葡萄生產變化及趨勢
由圖1可知,涼山州葡萄在2017~2019年種植面積、產量和產值都有迅猛發展。2016年種植面積僅0.18萬hm2、產量3.99萬t、產值3.10億元,到2020年種植面積達0.77萬hm2、產量21.25萬t、產值19.09億元。全州17個縣市中有14個種植葡萄,近5年面積、產量和產值分別增長了3.2倍、4.3倍和5.1倍。

圖1 涼山州2016~2020年葡萄種植面積、產量、產值變化趨勢
由表1和圖2可知,涼山州除西昌市以外的13個葡萄種植縣5年間葡萄產業發展相對緩慢。西昌市是“中國晚熟葡萄之鄉”,也是涼山州葡萄種植面積最大的產區,葡萄種植面積、產量和產值分別占涼山州的86.55%、89.51%和89.63%,是種植葡萄產量和效益最優地區的典型代表。西昌葡萄產業變化趨勢與涼山州一致:2016年種植面積0.13萬hm2、產量2.53萬t、產值2.18億元,到2020年種植面積達0.66萬hm2、產量19.02萬t、產值17.11億元。全市25個鄉鎮中20個種植有葡萄,近5年面積、產量、產值分別增長了4.0倍、6.5倍和6.8倍。西昌市種植的葡萄普通品種包含了早熟、中熟和晚熟品種,其中,晚熟葡萄品種克瑞森面積達0.60萬hm2,占西昌葡萄種植面積的90.91%,占全國該品種種植面積的18.00%,是全國種植克瑞森葡萄規模最大的基地,亦是最火熱、最受關注的葡萄產區之一。

圖2 西昌市2016~2020年葡萄種植面積、產量、產值變化趨勢

表1 涼山州葡萄主產縣產業情況
西昌市葡萄規模化、規范化、標準化、特色化、優質化和品牌化種植已成為全川乃至全國示范樣板和行業引領標桿,近5年接待全國葡萄學會及省內外種植者參觀學習,產品銷往北上廣深及出口東南亞地區,極大推動了大小涼山彝區葡萄種植行業的科技進步,促進了區域經濟高質量協調發展,為鄉村振興、產業興旺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2 多方助力出成效
2.1 優良品種保產業
涼山州適宜早中晚熟葡萄種植,在國家葡萄產業技術體系創新團隊和四川省創新團隊等專家、科技人員的大力支持下,西昌市率先精準選擇了晚熟、質脆、無核、高產、耐貯運、適應性強的克瑞森(克倫生)葡萄作為主栽品種。目前,該品種種植面積已達0.65萬hm2,占涼山州葡萄種植面積的84.42%。
隨著消費需求的多元化以及新興品種的出現,涼山州已進行了葡萄優良品種的優化和布局。陽光玫瑰標準化示范基地已超過70.00 hm2,涌現了四川月城明珠農業有限責任公司等大、中型基地代表。此外,2021年還試種了大粒、色艷、嫩脆、優質、抗逆性強、早期豐產性高的“妮娜皇后”超過200.00 hm2,中型核心示范區達7.50 hm2,為葡萄品種的更新優化和布局奠定了良好的示范基礎和科技支撐。
2.2 提質增效保品質
全域均采用規范化、標準化表土起壟、高畦深溝雙行適度密植(0.8~1.2 m/株),鋼架避雨大棚加裝防雨槽,“雙層天膜+地膜”三膜覆蓋,高光效整形修剪,精準肥水一體化,實現了節水、節肥、節藥、省工、機械化和避風,解決了因避雨設施受損而造成葡萄果園病害發生及果實品質受損等嚴重生產問題,實現了提質增效保品質。
2.3 創建、維護品牌促效益
涼山彝族自治州和西昌市人民政府通過大力支持葡萄核心示范基地的標準化建設和引領,加大了對品牌的創建和維護。2011年,川興、西鄉“葡萄萬畝示范區”被認定為首批“四川省現代農業萬畝示范區”;2015年,“西昌葡萄”入選全國名特優新農產品目錄;2017年,巨玫瑰、陽光玫瑰被認定為綠色食品A級產品;2018年,“西昌葡萄”被認定為農產品地理標志產品;2019年,西昌市獲得了“中國晚熟葡萄之鄉”稱號,西昌葡萄從全國各地選送的80個果樣中脫穎而出,榮獲金獎17個、優秀獎25個,占總授獎數的87.00%;2020年,西昌市因葡萄成為四川省特色農產品優勢區。串串葡萄,已成為帶動總產值超20.00億元的大產業,西昌已成為全國晚熟葡萄產業版圖上最耀眼的明珠。
2.4 長效機制謀未來
國家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四川水果創新團隊和農業農村部農業重大技術協同推廣計劃“葡萄優質安全高效生產關鍵技術示范推廣”項目落地涼山州,從品種優化選擇、土壤修復改良、建園快速成苗成花、早結優質豐產、避雨設施結構優化設計、機械化省力化操作、精準肥水一體化和病蟲害綠色防控及品牌打造等方面為涼山州葡萄產業提供全方位的服務與技術支撐,協同創新長效機制,助力涼山州葡萄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未來。
3 需防范隱患風險
3.1 避免種植大戶盲目追新
近年來,一些種植戶對如“甜蜜藍寶石”等葡萄新品種的特性知之甚少,卻盲目追新,一方面抬高了種苗成本,另一方面在大量資金投入兩年后,出現了損失超60.0萬~75.0萬元/hm2的情況,給種植者和產業造成了極大傷害。因此,種植戶一定要在當地農業及科研部門對品種特性及配套技術研發清楚的情況下進行產業化應用。
3.2 適度限產提質
目前,西昌克瑞森產量高達60.0萬~75.0 t/hm2,收益達45.0萬~105.0萬元/hm2,但產品質量良莠不齊,有的著色不均、色澤亮度不夠、風味偏淡,產品僅能走低端市場,效益偏低。如能適度限產至37.5~52.5 t/hm2,產品質量將大幅度提升,同時,土壤承載能力將有所緩沖,適度限產提質十分有利于社會、經濟和生態效益的和諧發展。
3.3 科學種植技術有待進一步普及和提升
葡萄品種特性千差萬別,種植者大部分缺乏科學文化素質和先進規范的種植技術,在品種引入、土肥水管理、整形修剪、保花保果和病蟲害防治方面均以模仿為主,沒有系統的科學理論、實踐基礎相結合的先進技術支撐。十分有必要在關鍵技術環節加大對種植者科學技術的普及力度,以及技能提升的培訓力度,促進產業更加規范化、標準化、優質化、綠色化、品牌化發展。
3.4 增強市場開拓能力建設和加大品牌創建
培養專業營銷隊伍,做好線上線下相結合的葡萄銷售活動,大力開拓國內外市場,發展自主經營對內對外貿易企業,加強與省內外、國際知名會展商合作,多渠道、全方位展示、推介,提高國內外知名度和市場競爭力。樹立品牌形象和質量信譽,全力推進果品質量提升工程,以品質促品牌,以品牌開拓市場,以市場助力品牌增值,統一打造,著力提升產品銷售檔次,創建農旅融合的區域品牌,促進產品深度開發和增值。
4 保障措施抓落實
4.1 加強組織和制度保障
葡萄產業作為涼山州的農業支柱產業之一,葡萄產業興旺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路徑,應建立州、縣(市)、鄉(鎮)、村四級聯動的長效機制,上下齊抓共管、真抓實干;充分發揮財政資金投入的引領作用,引導社會和金融資金集聚,各級農業部門要會同相關部門積極出臺配套政策,破除行業壁壘;制定出臺本地葡萄產業建設推進方案,明確目標任務,強化后續管護,加強績效考評,確保各項任務做實做牢。

4.2 搞好核心園區標準化安全生產示范建設
優先支持園區農業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和創新,針對葡萄的發展特點與趨勢,實現種苗優質化、全程標準化、基本機械化、可追溯、信息化、經營規模化、銷售品牌化,保鮮、儲藏、加工、銷售一體化經營。開發具有民族傳統、地域優勢、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深加工產品,延長農業產業鏈,提高農業與二、三產業的融合程度,實現葡萄產業增值增效。
4.3 壯大新型經營主體
實施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工程,提升農民專業合作社規范化水平,鼓勵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社;不斷壯大產業化龍頭企業,鼓勵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加快建立新型經營主體支持政策體系和信用評價體系,落實財政、稅收、土地、信貸、保險等支持政策,擴大新型經營主體承擔涉農項目規模。
4.4 加強質量提升工程建設
構建“六統一分”(統一栽培管理、統一植保防治、統一配方施肥、統一農資配送、統一分級包裝、統一品牌營銷、分戶種植)全程關鍵點質量控制標準化管理模式,建立重質量、守信譽的專業聯盟,確保避雨設施材料優質、工程質量優良,肥藥安全放心,充分保障技術的可靠性與安全性,促進產品質量提升。
4.5 加強科技培訓
培養建立肥水管理、有害生物綠色防控、整形修剪與花果管理、農資供給保障、產品營銷與市場拓展等專業隊伍,培養高素質、現代化農民;關鍵技術環節建立“專家團隊+縣級技術人員+鄉鎮技術能手(田秀才)+村土專家”四級聯動技術推廣聯動機制,使技術落實,不留盲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