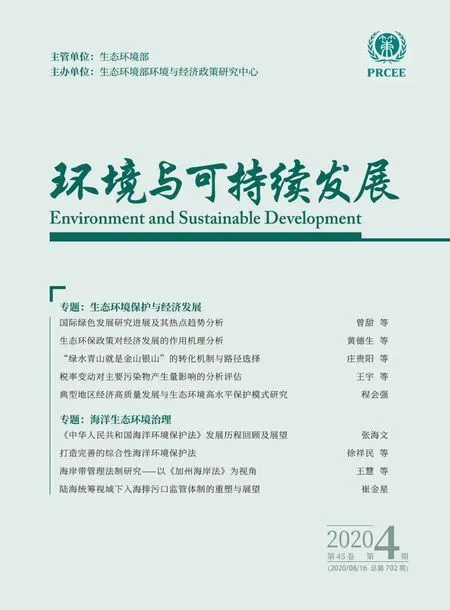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的政策演進、激勵約束與效果分析
馬本,孫藝丹,劉海江,孫聰
(1.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北京 100872;2.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北京 100029)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生態文明建設邁入了新階段。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將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一起,列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2017年11月,黨的十九大報告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了“千年大計”的高度;2018年5月,在第八次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生態文明建設被定位為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并確立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導地位。隨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進入了新時代,生態環境保護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加強生態保護、加大污染治理力度成為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建設美麗中國的必然要求。
2018年3月,國務院行政機構改革,組建了生態環境部,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在管理體制上加強了對生態保護的監管。由于生態保護具有跨區、跨時的正外部效益,地方政府、個人、企業都沒有足夠的激勵在生態環境保護上投入“足夠”的資金。從這個角度看,在宏觀層面建立力度適當的生態補償制度是確保生態保護外部效益內部化、促進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一致、實現生態環境可持續的必要條件。2010年,國務院頒布《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劃定了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作為重點生態功能區最重要的配套政策,2008年開始試點,我國建立起了重點生態功能區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作為一項國家層面的生態補償項目,隨著資金投入量的增加,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生態補償項目之一。就政府項目而言,我國的生態保護補償已成為最大的生態保護資金支持項目(Ouyang et al.,2016),其中的“退耕還林”被一度認為是我國乃至發展中國家最大的生態補償項目(Chen,K?nig,Matzdorf和Zhen,2015;R.Yin,Liu,Zhao,Yao和 Liu,2014);至2016年,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以570億元的資金投入,居我國各類生態補償項目之首(吳樂,孔德帥,靳樂山,2019)。此外,從資金總量來看,截至2015年底,第一輪“退耕還林”中央財政累計投入4056.6億元;第二輪“退耕還林”從2014年啟動,到2018年累計投入391.1億元,兩輪累計投入4447.7億元。而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自2008年至2019年共計5241億元,已成為我國乃至全球最大的政府生態保護補償計劃。
關于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的研究多集中在轉移支付制度的設計、監督考核、激勵約束機制等方面(何立環,劉海江,李寶林和王業耀,2014;盧洪友和祁毓,2014;張文彬和馬藝鳴,2018),對轉移支付的分配機制和資金使用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李國平,李瀟和汪海洲,2013;李國平和李瀟,2014,2017;劉政磐,2014;鐘大能,2014;劉璨,陳珂,劉浩,陳同峰和何丹,2017)。隨著政策實施時間的推移,一些研究也開始關注轉移支付制度的政策效應,如生態環境改善效果、空間溢出效應以及地方政府行為與官員晉升等(李國平,劉倩和張文彬,2014;李國平,汪海洲和劉倩,2014;劉炯,2015;呂凱波,2014)。考慮到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對中國生態保護的重要性,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針對該項政策的新動向、新趨勢,本文梳理和分析了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制度的形成過程、體制安排以及政策演變,著重對政策力度、激勵約束與效果進行討論,歸納了已有研究的發現,為該政策的改進與完善提供相關政策建議。
1 政策總體情況
1.1 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制度
1.1.1 制度介紹
2010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印發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的通知》,將國土按開發方式劃分為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禁止開發區。重點生態功能區和農產品主產區同屬于限制開發區。國家層面限制開發的重點生態功能區是指生態系統十分重要,關系全國或較大范圍區域的生態安全,目前生態系統有所退化,需要在國土空間開發中限制進行大規模高強度工業化城鎮化開發,以保持并提高生態產品供給能力的區域。2010年劃定的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包括25個區域,總面積約386萬平方千米,占全國陸地國土面積的40.2%;涉域面積2008年底總人口約1.1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8.5%。2016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報國務院批準,新增了240個縣域,使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增加到676個(1)2016國務院關于同意新增部分縣(市、區、旗)納入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批復。
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分為水源涵養型、水土保持型、防風固沙型和生物多樣性維護型四種類型,不同類型的功能區有不同的發展方向。整體而言,重點生態功能區規劃的目標包括:生態服務功能增強,生態環境質量改善;形成點狀開發、面上保護的空間結構;形成環境友好型的產業結構;人口總量下降,人口質量提高;公共服務水平顯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改善。對于重點生態功能區要嚴格控制開發強度,原則上不再新建各類開發區和擴大現有工業開發區的面積,逐步改造已有工業開發區,使其成為生態型工業區。在一系列嚴格的開發限制下,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考核也有相應的調整,實行生態保護優先的績效評價,不再考核地區生產總值、財政收入和城鎮化率等指標。
1.1.2 與轉移支付制度的區別和聯系
轉移支付試點先于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劃定,說明轉移支付并不完全以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為基礎;2010年436個國家生態功能區縣域劃定后,2016年新增240個縣域。同時,轉移支付縣域自2008—2017年逐年擴大,從2008年的230個增加到2017年的818個縣域,與重點生態功能區覆蓋的縣域并不完全一致。這種不一致可能來自轉移支付縣域與重點功能區縣域的確定在程序、周期、管理部門等方面的差異。重點生態功能區范圍的劃定由國家發展改革委負責,須報國務院批準,而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范圍由財政部確定,財政部對生態轉移支付的政策每年或隔年調整一次。當然,在實際操作中,生態環境部對生態環境質量狀況進行監測評估,認定獲得轉移支付的區縣即為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
重點生態功能區的劃定是通過國土空間管控的方式保護生態,其主要手段是限制社會經濟開發活動。2016年后,享受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的區縣均制定了比國家公布的產業目錄更為嚴格的產業準入負面清單,從某種意義上看,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是對由于生態保護限制當地經濟發展的一種經濟補償。當然,從嚴格意義上講,是否是一種對機會成本的補償,還需要進一步考察該項轉移支付的測算依據。
1.2 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制度
1.2.1 依據
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制度的實施依據主要為歷年財政部印發的政策文件。2009年,財政部研究制定了《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試點)辦法》(財預〔2009〕433號);2011年印發《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辦法》(財預〔2011〕428號);之后每年或隔年,均出臺了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辦法以指導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政策的實施。頻發的政策文件一方面體現出該政策備受重視,相關部門對該政策進行不斷的動態優化和調整,另一方面也意味著該政策的預期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1.2.2 體制
合理的管理體制是政策實施的重要保障,在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的體制安排中,生態環境部負責組織實施縣域生態環境質量監測評價與考核,財政部對考核的全過程進行指導和監督(2)2011關于印發《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生態環境質量考核辦法》的通知。考核的內容包括技術指標和監管指標兩部分,技術指標由自然生態指標和環境狀況指標組成,且考慮到不同類型生態功能區的差異性。具體指標設置(3)2017年環辦監測函《關于加強"十三五"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生態環境質量監測評價與考核工作的通知》如表1所示。
1.2.3 目標
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制度的試點始于2008年。為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引導地方政府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力度、提高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所在地政府基本公共服務保障能力、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中央財政在均衡性轉移支付項下設立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4)2009關于印發《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試點)辦法》的通知。歷年來政策目標如表2所示,可以發現,早期的政策目標中體現出了環境保護和改善民生的“雙重目標”特點(2009、2011年),這一特點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地方政府在資金使用方面弱化了生態環境保護的用途,出現一些文獻研究中提到的生態環境保護支出被擠占的現象(李國平,劉倩和張文彬,2014;李國平,汪海洲和劉倩,2014;何偉軍,秦弢和安敏,2015)。之后年份的目標中更多地突出了“生態文明建設”“生態環境保護”的政策導向。

表1 “十三五”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生態環境質量監測評價與考核指標

表2 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政策目標
1.2.4 屬性
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轉移支付,不規定特定用途,在使用上有較大的自主性;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屬于大口徑的均衡性轉移支付,亦歸為一般性轉移支付(與專項轉移支付對應)。換句話說,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是介于小口徑均衡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之間的一種轉移支付類型(5)財政部《2017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決算表》;縣政府的資金使用效果取決于具體用途,支出的對象可能是企業、個人和公共項目。因此,即便政策目標導向上強調引導對于生態環境的保護,但其均衡性轉移支付的資金性質仍決定了地方政府對資金使用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多大比例投入到生態環境保護中并沒有明確的標準。李國平和汪海洲等(2014)、何偉軍和秦弢等(2015)均提出生態環境保護與改善民生“雙重目標”相互沖突且與績效考核體系不匹配的問題,劉璨等(2017)也指出環境保護支出與公共服務的支出分配比例缺乏科學性。因而從這個角度看,基于生態環境質量的促進效果,對該項資金的使用情況進行嚴謹的績效評估,對于引導地方政府更好地使用資金、更好地發揮資金在生態保護上的效益具有重要意義。
2 政策力度: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的資金分析
2.1 均衡性轉移支付的測算辦法
根據歷年《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辦法》的文件規定,將不同年份的分配辦法整理如表3所示。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應補助數額的計算方法逐年有所變動。

表3 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分配辦法
從資金的測算方法來看,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并不是嚴格的生態補償項目。生態補償通常基于三個補償標準,一是生態服務本身的外溢價值,二是生態保護的工程建設及人力等支出,三是由于限制高耗能產業等發展而產生的生態保護的機會成本。而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是基于地方標準財政收支缺口進行測算補償,跟生態保護的需求關聯性較弱。這一問題在相關研究中也有所體現,如李國平和李瀟(2014)、何偉軍和秦弢等(2015)均認為以“標準財政收支缺口”為核心的轉移支付分配機制沒有體現向財力較弱和生態環境較差地區的傾斜,盧洪友和余錦亮(2018)提出在支付標準的確定中應加大生態自然與環境保護等因素的權重。
在支付類型上,2017年重點補助、禁止開發補助、引導性補助、生態護林員補助、考核激勵和考核扣減的地方合計額度分別為436.82億元、55億元、113.67億元、24億元、1.92億元和-4.41億元;2018年五種補助及 地方合計額度分別為519.13億元、55億元、121.68億元、34億元、2.03億元和-4.14億元。重點補助始終是轉移支付中占比最大的支付類型,其次是引導性補助和禁止開發補助,新增的生態護林員補助、考核獎勵和考核扣減數額相對較少,尤其是考核獎懲資金數額較少,該政策的激勵約束力度存在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2.2 總額年度變化
享受轉移支付政策的縣的個數從2008年的230個增加到2019年的818個(表4)。到2016年,轉移支付區縣占國土面積超過50%。資金投入從2008年的60億元擴大到2019年的811億元,累計投入資金達5241億元。在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退牧還草、退耕還濕等國家級生態補償項目中,重點生態功能區投入轉移支付在資金數量上是最大的。比如,2016年生態補償投入的資金總量約為1776億元(吳樂,孔德帥和靳樂山,2019),重點生態功能區投入資金為570億元,占總量的32.1%,該項資金對生態環境保護的促進作用尤其值得關注。

表4 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縣個數與轉移支付金額
歷年來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縣域的平均補償額、占均衡性轉移支付的比重以及與節能環保支出的比率變化如圖1所示。在2014年及以前,平均補貼額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且增長幅度較大,2014年至2017年有所下降。該項轉移支付在均衡性轉移支付中的占比在3%上下波動,在縣域財政收入中也一直占據重要的地位,2010年縣域平均轉移支付在平均財政收入中的占比接近30%。轉移支付金額與節能環保支出的比率由2008年的4.1%上升到2017年的11.2%。整體而言,特別是在近年財政吃緊的背景下,該項轉移支付無論從資金總額還是資金占比來看,都是政策力度較大的一項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補償政策,體現了國家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視。

數據來源:依據歷年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文件和決算表、中國縣域統計年鑒(縣市卷)整理。圖1 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政策力度
2.3 各省區市年度變化
自2008年以來,各省區市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情況隨年度有所改變,如圖2所示。從各省區市轉移支付總額來看,基本都呈現出轉移支付金額隨年份增長的趨勢,其中甘肅、貴州為轉移支付總額數量較大的兩個省。到2017年,甘肅轉移支付金額達50.33億元,貴州轉移支付金額達45.35億元,湖南省緊隨其后,2017年轉移支付金額也近40億元。根據享受政策縣的個數計算各省區市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支付縣平均轉移支付金額,貴州、重慶、河南、安徽的縣域平均轉移支付金額量大,2017年,重慶的縣域平均轉移支付金額達到2.04億元,河南的縣域平均轉移支付金額達到1.58億元。

數據來源:財政部信息依申請公開。圖2 各省區市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數量
3 激勵約束機制:生態環境質量考核制度分析
3.1 依據
2011年,原環境保護部與財政部印發《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生態環境質量考核辦法》,明確考核內容及指標,規范對政策縣域生態環境質量的考核。此后2014年、2017年,兩次修訂完善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生態環境質量監測評價和考核指標體系,目前使用的指標體系為2017年發布的“十三五”期間考核指標體系,作為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生態環境質量考核制度的實施依據。
3.2 激勵約束
原環境保護部于2009年開始啟動了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生態環境質量考核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和試點考核,2011年起正式考核,歷年來激勵約束的變化如表5所示。從2012年起對享受轉移支付的縣域優先進行生態環境保護績效評估,評估結果直接用于每年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資金調節(何立環,劉海江,李寶林和王業耀,2014)。

表5 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生態環境質量激勵約束
3.3 考核指標
考核指標的變化如表6所示。2012年的《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辦法》不再將“基本公共服務”指標考慮進來,縣域生態環境指標(EI)成為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考核激勵機制的核心依據(孔德帥,李銘碩和靳樂山,2017)。在生態環境指標部分,依據《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生態環境質量考核辦法》(環發〔2011〕18號)對2010年數據進行試點考核,對2011年之后的數據進行正式考核評價。自然生態指標包括林地覆蓋率、草地覆蓋率、水域濕地覆蓋率、耕地和建設用地比例指標;環境狀況指標包括SO2排放強度、COD排放強度、固廢排放強度、工業污染源排放達標率、Ⅲ類或優于Ⅲ類水質達標率、優良以上空氣質量達標率指標。此后考核指標體系處于不斷的調整豐富中,側重點也有所變化,如《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生態環境質量監測評價與考核指標體系》(環發〔2014〕32號)考核評價的主要污染物排放強度包括,SO2、COD、氨氮、氮氧化物之和,調節指標包括生態環境保護與管理,涵蓋生態環境監管能力;《關于加強“十三五”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生態環境質量監測評價與考核工作的通知》(環辦監測函〔2017〕279號)補齊環境空氣質量指標,新增土壤環境指標,并將污染源排放達標率、主要污染物排放強度、城鎮污水集中處理率調整為監管指標。

表6 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考核指標
考核指標的變化趨勢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一是從環境保護和公共服務的雙重考核轉變為以縣域生態環境質量為核心的考核;二是豐富了監測與考核的指標體系,形成了以縣域生態環境保護結果評價和保護過程評價相結合的指標體系,如進一步豐富監管能力指標,重點體現縣域生態環境保護開展的工作和成效,涉及生態保護狀況、生態環境保護投入、產業結構綠色化、農村環境整治、主要污染物排放、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等;三是引入資金使用情況的績效考核,有利于加強對資金用途和使用效率的監督和引導。
4 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的政策效果
4.1 部門分析結果
首先,從生態環境質量本身的情況來看,2017年818個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中,生態環境質量“良好”的縣域有458個,占56.0%,“一般”的有247個,占30.2%,“脆弱”的有113個,占13.8%(6)參見《生態環境部就2018年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生態環境質量考核工作有關問題答記者問》。不同類型生態功能區的生態環境質量存在差異性,其考核結果匯總如表7。比較不同等級占比可以發現,水源涵養型生態功能區縣域的生態環境質量整體較好,防風固沙型生態功能區縣域的生態環境質量整體情況較差。
從生態環境質量的變化角度來看,將歷年考核結果中不同程度“變好”“變差”“基本穩定”的縣域占比統計為表8。生態環境質量“變好”的縣域占比波動較大,每年也有一定比例考核結果為“變差”的縣,此外大部分縣域的生態環境質量在歷年考核中被評價為“基本穩定”,即沒有明顯變化。

表7 2017年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生態環境質量狀況

表8 2012—2019年考核情況
基于考核結果,從全國范圍看,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政策并沒有使生態環境質量顯著地提高,少數縣域的生態環境質量變好或變壞,而多數縣域的生態環境質量保持穩定。這樣的考核結果一方面是政策覆蓋縣域實際的生態環境質量情況的體現,另一方面也與上文所述考核指標體系的設置密不可分。考核指標中,自然生態指標的權重相對較高,而自然生態指標多為土地類型的面積或覆蓋率指標,這些指標本身就具備年度變化程度小的特征,因而考核結果中體現出較強的穩定性。
4.2 相關研究結果
相關文獻針對特定區域開展研究,評估了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對生態環境質量的影響,其促進作用得到較多學者的認同。張文彬和李國平(2015)基于動態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中央政府和縣級政府在生態保護中的行為選擇,認為轉移支付制度能有效激勵縣級政府在生態環境質量提高方面做出努力,從而對生態環境質量起到顯著改善作用。徐鴻翔和張文彬(2017)以陜西省33個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為研究樣本,按財政收入高低進行分組回歸,得出轉移支付對生態環境質量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的結論。侯鵬和翟俊等(2018)研究了海南島中部山區熱帶雨林重點生態功能區,發現2013年功能區森林面積占比顯著高于海南島平均水平,且水源涵養服務功能和土壤保持服務功能也明顯優于功能區外部。林云杉(2018)以南嶺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區中的4個國家重點生態功能縣為研究樣本,發現2015年至2016年4個功能縣中有3個功能縣的生態狀況和環境狀況呈現變好的趨勢。繆小林和趙一心(2019)利用2006—2016年我國省級面板數據、采用雙重差分模型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對生態環境改善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轉移支付總體上改善了以水質為代表的生態環境質量,且地方政府環保支出占比越高,轉移支付的政策效應就越明顯。
同時,也有研究認為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對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的作用微弱。李國平和劉倩等(2014)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基于陜西省2009—2011年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認為增加轉移支付可以改善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生態環境質量,但是影響較微弱。李國平和楊雷等(2016)采用空間計量模型研究陜西省秦巴山區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的生態環境質量空間溢出效應,認為轉移支付對生態環境質量只有相對有限的促進作用。
總體而言,相關文獻對轉移支付效果的評價以定性和理論分析為主,少數的定量分析以案例或某個省區市的數據為主,缺少在宏觀層面對轉移支付政策的生態環境改善效果的全面評估,尤其是結合地區異質性、功能區異質性、政策效果動態變化的評估還有待進一步深化。總體評估依賴于數據的支撐,然而當前的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生態環境指標的數據存在生態數據不全、連續性不夠等問題,為嚴謹的評估帶來了困難。從方法論看,所采用的實證方法多數不能很好地解決轉移支付政策對生態環境質量影響的內生性問題,在政策評估方法論上也有改進的空間。此外,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政策會從多個維度影響享受轉移支付的縣域,政策效果不僅體現在生態改善、環境質量改善上,還會影響地方的減貧與經濟發展,而此類研究尚顯不足,有待進一步深化。
5 結論與政策建議
梳理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制度的形成過程、體制安排以及歷年的政策變化,研究發現,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大力推進,重點生態功能區制度及其配套的重點生態功能區財政轉移支付受到了國家的高度重視:政策目標上增強了“生態文明建設”“生態環境保護”導向,從環境保護和公共服務的雙重考核轉變為以生態環境為核心的考核;逐年豐富和完善了監測與考核的指標體系;引入資金使用情況的績效考核,加強對資金用途和使用效率的監督和引導。在政策效果方面,多數文獻研究認為部分地區的生態環境質量有所改善,但官方考核結果表明大部分政策縣域的生態環境質量變化不明顯。考慮到該項轉移支付資金屬于均衡性轉移支付,為更好地引導地方政府將資金投入到生態環境保護領域,政策的激勵約束機制有進一步強化的空間和必要。本文為該政策的改進提供如下建議:
第一,逐步完善轉移支付資金的分配與使用。由于資金分配的測算方法不符合嚴格的生態補償標準,轉移支付數額與地方實際生態環境保護的需求不成比例;為達到更好的生態環境保護效果,資金測算應體現與生態服務價值、生態保護支出及機會成本等因素掛鉤;在資金使用方面,要加強對地方政府資金使用的引導,引導其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提高生態環境治理效率,避免出現生態環境保護支出被擠占從而偏離了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政策初衷或者資金使用效率低下無法有效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的情況。
第二,增加生態環境質量考核制度激勵約束的作用。考核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激勵縣域加大生態環境保護力度,當前基于考核結果的獎懲資金數額較少,所發揮的激勵約束作用有限。建議加大針對考核結果的獎懲力度,通過更完善的激勵約束機制促進提升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的政策效果。
第三,動態完善生態環境質量考核指標體系。當前考核指標體系中,自然生態指標多為不同類型土地面積及覆蓋率指標,而此類指標數據通常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年度變化較小,難以體現出縣域自然生態方面更詳細的變化情況,且覆蓋面積通常僅能體現數量差異、難以體現質量差異。因此建議在自然生態考核中增設可進一步表征生態質量的指標,不斷提高生態和環境質量監測水平,為開展評估提供數據支撐,完善對自然生態情況的考核。
最后,建議開展對轉移支付政策效果的全面評估。從試點開始算起,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政策已經實施12年。從生態環境質量改善角度,政策的促進作用有多大,隨著時間的推移促進作用是增大了還是減小了,不同功能區類型的生態環境效益是否有顯著差異,回答這些問題對于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益、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在評估過程中除了縱向對比外,引入縱向和橫向對比相結合的維度,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分析轉移支付政策本身對縣域生態環境質量促進的凈效應,仍有待進一步深入、客觀和嚴謹的定量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