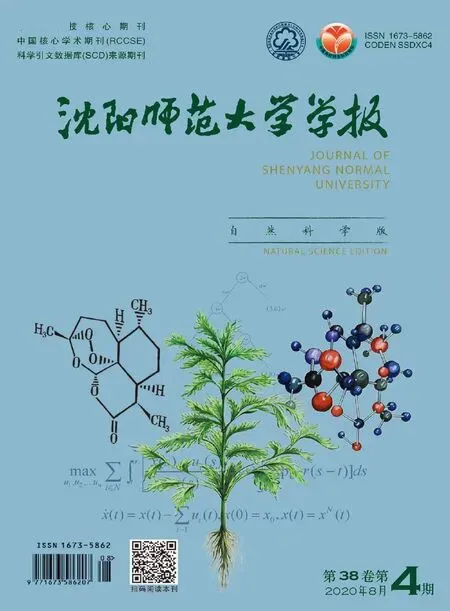南京國民政府鹽稅治理對財政的影響與啟示
韓 毅, 韓興國,2
(1. 遼寧大學 經濟學院, 沈陽 110036; 2. 遼寧金融職業學院 會計學院, 沈陽 110036)
0 引 言
鹽是百味之祖,是調味的必需品,鹽的壟斷專營是極易實現的,誰掌握了鹽誰就掌握了財富,因此,鹽稅從產生之日起就起到了富國強兵的作用。諾斯指出“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1],南京政府成立初期人們對制度變遷存在強烈的要求,政府作為制度變遷的供給者,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具有主導地位,同民眾一樣,南京政府期盼制度變遷能夠帶來新的收益以緩解財政壓力。
1 南京國民政府鹽稅改革的背景
1.1 政府財政窘急
1912年1月2日,南京臨時政府公布的大總統宣告中第一項是“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為有效,至于條約期滿為止,其締結于革命起事后者則否。”可以說自中華民國成立之始就繼承了清末的財政困局。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面臨著數額巨大的積欠外債,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28年6月底,北洋政府共遺留外債合計金額2 105 692 957.88元[2]。在外債償還問題上南京國民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同時百廢待舉,各方面建設都需要大量的資金,而與各派軍閥的戰爭使其軍費也不斷攀升,巨額的財政支出所引致的財政赤字,使得南京國民政府急于尋找到一個簡單快捷的財政增收途徑,而鹽稅恰恰符合這種要求。

表1 南京政府初期外債統計Table 1 External debt statistics of Nanjing Goverment 元
1.2 專商引岸制度弊端累累
民初鹽稅承清制,中國鹽稅經過2 000多年的發展到清末形成了獨特的專商引岸制,其特點是: 購鹽有定場, 行鹽有定額, 運鹽有定商, 銷鹽有定岸[3];其主要做法是政府頒發鹽引給特許專商,商人交稅后在指定的鹽場按規定數量購鹽,然后起運至固定引岸銷售。引案制是指劃定行鹽地界,商人各按地界售鹽互不侵犯,鹽商跨引岸銷鹽視為販私鹽處理。專商引岸制限制了民族制鹽工業以及自由貿易的發展,同時鹽商與鹽官關系異常復雜,時人稱“官以商之富也,而脧之;商以官之可以護己也,而豢之”,官商勾結尋租謀利比比皆是。北洋政府時期,在英國人丁恩的主持下對專商引岸制進行了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至南京政府初期全國仍有近半地區實行鹽商專賣制,鹽商仍然擁有雄厚的實力,它們壟斷著全國許多重要省份的食鹽貿易,繼續影響著鹽稅的改革進程。

表2 鹽務稽核所一覽表(1913—1918)Table 2 List of Salt Audit Institutions(1913-1918)
1.3 鹽稅主權喪失
北洋政府時期為緩解財政危機于1913年4月同五國銀行團簽署了《善后大借款》合同,其中合同第五款規定了將引進外國人幫助中國治理鹽稅,同時在北京設立鹽務稽核總所,由中國人任稽核總所總辦,外國人任會辦,稅款存入銀行團指定銀行,非經洋會辦簽字不準挪作他用,中國之鹽稅至此權操于洋人。截至1916年財政部除在北京設立稽核總所外,在鹽產區和銷區分別設立了稽核支所和稽核處十五處。南京政府北伐開始后,所到之處稽核事務也一律停止,英國駐華公使藍普森由此感到了稽核機關的巨大危機,一方面,通過稽核總所洋會辦英國人斐立克與南京政府內部當權派特別是財政部要員頻頻接觸,試圖恢復南京政府統治區稽核機關及其職權,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也以在國際上發布不利于南京政府信息為要挾持續向南京政府施壓。1928年1月,宋子文出任財政部長后,認為原有人員都“久于任事,富于經驗,為整頓稅收計,不得不實行恢復稽核,為恢復稽核計,不得不起用原有人員”[4]。
1.4 稅法混亂、稅率不一
民國時期的鹽稅稅率紊雜,各地稅率輕重不一,“百斤稅率最重者至五元而強,最輕者僅一元而弱”,各省之間稅率不統一,就是在同一省內不同縣市之間稅率也高低不同,以上海為例,租界內每擔鹽賦不過3.05元,而同在上海的南匯川沙每擔鹽賦高達7.10元。傳統征收鹽稅系從量征收,故權量之單位對稅收關系重大,各個鹽區的引目不一致,斤量輕重不一,每引800斤至235斤不等,收稅放鹽,雖各地用“擔”為單位,而所用的衡器很不一致導致各地實際稅率不一,如山東每擔合133.33磅;而兩淮用壩秤每擔合152.5磅。各地稅率不一衡量各異,使低稅地區鹽向高稅率地區走私,增加了稅收征收成本。

表3 不同稅率地區銷量占比(1931)
2 南京政府鹽稅改革
鹽稅巨大的增收潛力成為國民政府改革鹽稅的首要動力,宋子文十分看重鹽稅收入,在1928年7月召開的全國財政會議上,他提出以就場征稅來治理鹽稅,宋子文希望廢除專商制度實行食鹽自由買賣,來增進食鹽消費擴大生產,增加稅基進而增加鹽稅收入。
2.1 從廢引到護商謀取收益
早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孫中山就曾邀請張謇到南京臨時政府任職改革鹽稅,取消專商引岸制度實行自由貿易。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政府中鹽稅改革者,又把廢除引岸、就場征稅、實行自由貿易的建議提上日程。1929年9月,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各省鹽稅只有60%解繳中央,軍需急迫使南京政府放棄廢引向鹽商直接謀取“收益”。南京政府第一屆財長古應芬提交中央政治會議的呈文中這樣寫道:“現在軍用浩繁,財政方針貴先謀各種收入之分別增多,再圖稅制之根本整理,方不至影響稅收,牽動軍事。鹽務一項積弊尤深,徹底改革頗需時日,整理順序似應從清查鹽票入手。”[5]呈文直陳了驗票護商的理由:第一,軍需浩大,為保政權之穩固必以增收為先,第二,財政窘急,鹽稅涉及面廣,徹底改革費時較多,第三,鹽商食鹽利已久,引權出租坐收鹽利,財政增收不如從審驗鹽商手中的鹽票入手。
1928年1月,國民黨政府以政令形式向兩淮、兩浙、松江等鹽產區以軍用鹽斤加價為名,計劃全年新加價收入約有305萬元。又因為軍需急迫,以全年鹽斤加價為抵押強制向銀行及鹽商借款300萬元。從1928—1930年,國民黨南京政府以同樣的方式手段籌款4 100萬元,緩解了政府的財政危機。鹽商為挽回損失極力要求南京政府保護引岸專商制,1929年“鹽商以軍人之破壞引岸及精鹽之廣銷,遂呈財政部維持原案。宋子文乃乘機邀鹽商持舊票注冊”。國民黨政府通過查驗和換發鹽商的鹽照給予了承認和保護,同時又從鹽商那里獲得了13 322 080.00元的驗票費,新驗票憑證注明了“永遠照舊環運,裨資保障,附發司諭、載明條件,安心營業,以堅信用”。
2.2 收回鹽務主權實現鹽稅提用自主
在鹽政主權方面絕對不可再任由列強把持,1928年2月20日宋子文發表關于鹽務稽核所的政見:“財政部將任各種專才管理財政部所轄各機關事務所,鹽務稽核所華洋人員,財政部將概予任用,使其專司鹽務稽核事務”;“鹽務稽核所不能有支配何種款項以為償還何種外債之權,清理外債,系財政部專責,或另設機關專理其事則可”;“國民政府未嘗否認且將不否認中國所有正當債務,大部分以鹽務擔保之債款,現正由國民政府下之關稅償還,其非由關款償還者,財部正謀所以處置之方,以昭信用”[4]。改革恢復了鹽務稽核所的稅收稽核職權,但取消了鹽務稽核所對償還外債的審批簽字權限,對外償還外債統一由財政部負責,改革使得鹽稅收入存入外國銀行團指定銀行,提用經洋會辦批準失去了現實基礎。宋子文于1929年1月主持頒布了新訂鹽務稽核總分所章程,令北京稽核總所南遷改組,直隸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裁撤原在鹽務署下設的稽核處,仍將鹽稅征收職責交由稽核機關辦理。11月,宋子文訓令各地鹽務機關,“鹽款為國家稅收大宗支持,自應慎重。凡由稽核機關簽發款項支票,應送經各該處運使運副榷運等局長會簽,向本部指定收款之銀行提取”[4]。鹽務稽核機關專管稅收,取消了決定鹽稅支款次序的權力,也不再對外國債權人負責。
2.3 統一收入防鹽稅截留強化中央稅權
1928年7月南京國民政府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通過了《統一全國鹽稅收入案》和《統一各省鹽務機關征收入員任免權案》,力求從征稅權限及人事任免上控制鹽稅。一年后中央政府向各地方政府及軍事機關發出訓令,各省鹽稅由中央統一征收,地方政府不得截留鹽稅,訓令發出后各省截留鹽稅的行為有所收斂且呈逐年下降趨勢。據統計,1925年各省截留鹽稅占中央鹽稅總收入81%,訓令發出3年后各省鹽稅截留占比下降到30%,到1936年已經查不到地方截留鹽稅數據。控制地方截留鹽稅的同時,國民政府于1929年下令各省鹽稅由中央統籌征收,整理、制止各省濫征鹽斤附加稅,1935年4月,以刑法和政令為約束改由中央統征鹽稅地方附加,對由此帶來的經費不足由中央財政彌補,秉此原則,除少數地方未能照辦外,各省附稅被陸續裁并,征稅集權化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果。

表4 1913—1925年鹽稅收入統計表Table 4 Statistics of Salt Tax Revenue From 1913 to 1925 千元
2.4 劃一提高稅率增加鹽稅
鹽稅征管權劃歸中央后,南京政府對鹽稅稅率以劃一提高、追補既往、鎊虧附加、改秤加斤為措施進行了治理。首先,劃一提高稅率,在鹽產區推行調整稅率的辦法,按“凡輕稅區域一律提高,重稅區域暫不議加”的原則調整稅率,從1932—1936年,全國鹽稅稅率已減至90余種,南京市稅率基本統一,稅率統一同時各地鹽稅均有0.1~1.45元不等的提高[6]。其次,追補既往,鹽稅追補政策就是對各鹽產區加稅以前庫存之鹽、已稅未放之鹽、出場在途之鹽、銷岸鹽商之存鹽、預繳稅款之鹽一律補納加稅,國民政府意欲增加收入的迫切心情,由此可窺一斑。第三,加征鎊虧附加,“鎊虧附加”是1931年國民政府為彌補償還外債時所發生的兌換損失而加征的場稅,1929年10月—1931年3月,世界銀價下跌,致使以銀價計算的還債兌換損失1 000萬元之多,為維持國信確保債務償還,財政部對每擔食鹽在產區一律加征附稅0.3元,專門用來補償由于銀價下跌導致的兌換損失。最后,改秤加斤直接提高鹽稅,1934年1月,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統一各地衡器,把原來通用的司馬秤(大秤)換成市秤(小秤),100斤司馬秤相當于127斤市秤,衡器變小稅率卻保持不變,即原來127市斤鹽的稅金現在由100市斤鹽承擔,直接加稅27%,為緩解輿論壓力,國民政府把所有稅賦在10元以上地區一律減為10元,看似高稅區實行了減稅措施,實際上降稅地區僅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而已,受益區域較小,并且降低部分被“改秤”增加部分所覆蓋,實際稅率未降反升。劃一衡器增稅范圍更廣,手段更具隱蔽性。

表5 1930—1937年食鹽平均稅率表Table 5 Average rate of salt tax from 1930 to 1937 元·擔-1
2.5 組建稅警團加大輯私力度
緝私是中國政府增加鹽稅的利器,為打擊販私歷代鹽法都非常嚴酷,1914年12月22日北洋政府公布《私鹽治罪法》,私鹽治罪法第一條規定“凡未經鹽務署之特許,而制造、販運、售賣或意圖販運而收藏者為私鹽”。即未經批準的制售運藏食鹽均為私鹽,私鹽界定范圍甚廣。然而由于食鹽價高,私鹽價低而食用者較多,據統計,1928年全國食用私鹽者約占半數,販私鹽對稅收影響巨大。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沿用了1914年的《私鹽治罪法》,1929年6—8月,又制定《海關緝私充賞辦法》《私鹽充公充賞暨處置辦法》,對緝私績優者進行超額累進獎勵,查獲私鹽由鹽務機關變賣,變賣及罰沒收入扣除緝私費用不足的由財政補足,如有剩余按3到8成不同比例作緝私人員、主管機關和報信人員獎勵。1931年,鑒于由于原來的緝私隊伍兵商勾結,甚至親自參與販私,宋子文招募有志青年親組新稅警團緝私,經軍校正規培訓后,戰斗力較強,執法嚴明。
3 南京民國政府鹽稅改革的績效與評價
3.1 鹽稅收入增加
南京國民政府經過劃一提高稅率,改秤加斤等十年鹽稅改革,鹽稅收入大幅增加,財政狀況得以緩解。據《中國鹽政實錄》《民國財政史》和《商業月報》統計,南京政府1936年鹽稅收入分別比1927年增加了82.06%、1 089.42%和243.8%,可見鹽稅改革對稅收影響較大。雖然由于統計口徑不盡相同三者統計數據并不一致,但鹽稅逐年上漲趨勢一致。

表6 1927—1936鹽稅收入統計Table 6 Statistics of salt tax revenue from 1927 to 1936 元

圖1 1927—1936年鹽稅收入變化趨勢Fig.1 Statistics of salt tax revenue from 1927 to 1936
3.2 食鹽銷量下降
財政增收的目的達到了,但是鹽稅收入增加鹽的產銷量卻在下降。美國經濟學家阿瑟·拉弗指出,高稅率能夠使政府稅收增加,但稅率的提高超過一定的限度時,企業的經營成本提高,投資需求、消費需求、社會產出減少,反而會導致政府的稅收減少,凱恩斯認為,在經濟蕭條時,政府應該降低稅賦水平并擴大政府支出,以此來擴大需求,加速經濟增長。與上述經濟理論相悖的是,南京國民政府在成立初期,經濟尚未恢復時急于加稅的后果是鹽的需求大大減少,按1933年加稅前鹽稅收入160 693 000元水平計算,加稅后1934年鹽稅收入應為200 866 250元,但1934年全國鹽稅實際收入只有177 461 000元,比預估的短收23 405 250元。按1933年和1934年平均稅率4.94元/擔和5.52元/擔計算,2年平均售鹽32 528 947擔和32 148 731擔,銷量下降了,同時根據鹽務稽核所年報所載放鹽量計算,1933年放鹽48 816 260市擔,而1934年為37 336 000市擔,食鹽銷量減少近四分之一。可見,南京政府的鹽稅治理是以犧牲社會產出為代價的涸轍而魚,事倍功半。
3.3 鹽稅主權收回不徹底
1928年到1930年南京政府取得了全國名義上的統一,新的鹽務機構效率低下,南京政府不得已恢復了原有的鹽務稽核所,并設立了鹽務署,統轄全國鹽政,主持稅收。新機構中由華洋員工組成,共同參與管理鹽務,外國會辦和各地區的洋員在管理方面處于領導地位的狀況結束了,但其影響依然很大。隨著中日戰爭的進行,中國經濟狀況惡化,洋員待遇及地位進一步降低,一些有經驗的洋員離開了中國鹽務系統,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鹽稅的半殖地化程度有了降低,但外國洋員的影響直到抗戰全面爆發才得以消除,這也充分體現了南京國民政府在對待國外勢力上既斗爭又妥協的兩面性。
3.4 輕民生而毀國計
經過治理,1929年以后鹽稅收入每年約占稅收總額的25%左右,最高達到31.26%,穩居關鹽統三稅中第2位。就“國計”而言,南京國民政府的鹽稅治理和改革表面上取得了成功,實現了增收的同時削弱了地方財權,但是中央稅收增收不是為了統籌發展改善民生,而是為了進一步消滅軍閥謀求更大的中央集權與統治。楊格認為,20世紀30年代當中,中國鹽稅總數平均占鹽的零售價格總額的3/4,比美國當時高2倍[7]。事實說明, 南京國民政府已拋棄了“三民主義”原則,高鹽稅致“苦我民眾,將無死所”,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強權、強征暴斂致民權喪失,沒有民權民生何來民族之獨立與國家富強。鹽稅治理使南京國民政府失去了民心, 動搖了其統治的穩固性,為生存動機而進行的鹽稅治理最終導致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生存危機。

表7 鹽稅收入占三稅收入百分比(1928/07/01—1937/06/30)Table 7 Percentage of salt tax revenue(1928/07/01—1937/06/30) 百萬元
4 幾點啟示
新制度經濟學繼承了斯密“經濟人”基本假設,諾斯國家理論認為統治者也是具有追求自身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經濟人”,“沒有國家辦不成的事,有了國家又有很多麻煩”[8],用制度經濟學國家理論分析南京政府鹽稅治理還是一次新的嘗試。
4.1 南京政府目標選擇上的偏差
國家最基本的目標有兩個,一是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即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所有權結構,這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個目標框架中降低交易費用,使社會產出最大化,使國家稅收增加[9]。統治者要實現福利最大化,只有在滿足了他生存要求之后,才會采取措施增加稅基。南京政府在成立初期財政窘急的情況下,采取了重新驗票的措施,延緩了專商引岸制的治理步伐,維護了舊鹽商的利益,雖然鹽商的“報效”短期內增加了財政收入,緩解了政府的生存壓力,但是過于強調增加短期財政收入的增加,使舊鹽稅制度得以延續。鹽商作為傳統的利益集團他們經濟付出必然要求高額的回報,必將政治獻金及驗票成本轉嫁與鹽民,鹽價高而食者少,私鹽盛行又導致了中央鹽稅短絀。在同鹽商謀租金的同時,又提高鹽稅以謀稅收收入增加,相悖的政策必將最終導致政府生存目標的難以實現,因此,政府在進行制度變遷時,一定要綜合考量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過度追求短期目標和財政增加無疑于飲鴆止渴。
4.2 超過了技術性生產邊界
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是一種長期的契約關系,按諾斯的理論:統治者在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時要受到生存問題、代理問題及度量成本問題等的限制,因而它所采用的征稅方法和建立起來的產權體系,很可能會引致經濟遠離他的技術性生產邊界[10]。南京國民政府鹽稅治理的技術性生產邊界即是民眾的承受能力,鹽稅改革雖然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但是過高的鹽稅稅率加重了民眾的負擔,超出了民眾的承受能力。北洋政府時期鹽稅稅率不過2~3元,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部分地區的稅率已高達十數元以上,涸澤而魚不如放水養魚,面對高鹽稅盤剝老百姓只能選擇食淡或食私,改革要使最廣大人民群眾受益,一項制度的推行不能遠離他的技術性生產邊界,所謂過猶不及。
4.3 過度集權與權力濫用
南京政府通過北伐取得了政權,1931年5月12日民國會議通過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加強了中央統治,按溫加特的理論:國家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夠有足夠的強制力去做他該做的事,即執行合同,但國家又不能過分強大,以致他不受約束,濫用自己的強制力,任意侵犯公民的財產和權力[11]。南京政府依靠強制力收回了鹽政主權,削弱了稽核所的職權和外國勢力的影響,同時有效的限制了地方政府對鹽稅收入的截留,使統一收入、提高劃一稅率、改秤加金等鹽稅治理措施能夠迅速在全國展開。但也正是南京政府過于集權導致權力濫用,使得千呼萬喚才出臺的《新鹽法》由于沒有制定實施日期而輪為空談,民眾期盼的食鹽自由貿易遙遙無期,限制了中國食鹽業的發展。
4.4 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
制度的變遷經常在不同群選民中分配財富、權力和收入,如果變遷中受損者得不到補償,他們將明確反對這一變遷。在廢除引岸制過程中,引商要求以恤金為補償,而改革者以商人欠交引額甚多,取消引岸,不追究既往,亦不必給以恤金,導致引商齊聚南京反對改革。在稅收治理過程中,整理、制止各省自行征收鹽斤附加稅,為應對地方政府的反對意見,對各省原來依靠鹽稅附加支付的款項,改由中央征稅后收入沒有來源的,改由中央財政撥補省款的辦法,降低了制度變遷的摩擦成本。如江西省鹽稅附加用于教育基金,中央征稅后財政部決定分十二月平均返還以補經費不足。因此,在改革的過程中,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對地方經濟受損嚴重且難以為繼者,要加大中央轉移支付和對地方的財政補助力度,要兼顧各地區財政的不平衡現狀,把地方經濟受損降到最低。
5 結 論
巴羅在《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多國經驗研究》論文中強調了制度的重要性,他的研究發現“法治對經濟增長的效果相當大,而民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則相當弱”。南京政府鹽稅治理短期內實現了財政增收的目標,但是卻忽略了民生與長期執政的基礎,要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快速推進改革,加強中央集權可以減少制度性摩擦成本,但是為防止權力濫用肆意侵害公民財產權利,建立健全法治與制度體系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