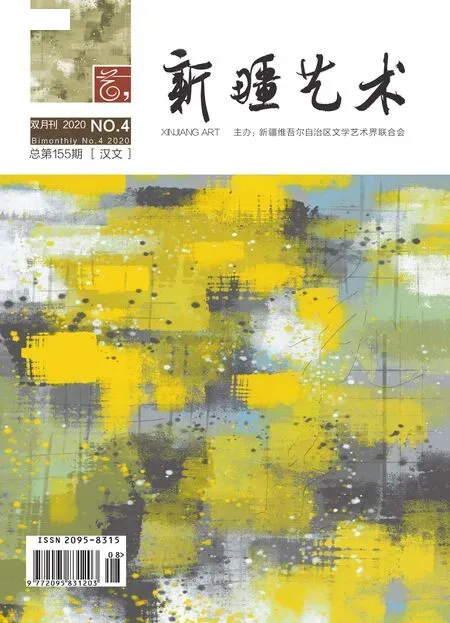民族舞蹈口述史傳承作用
——以新疆哈薩克族舞蹈為例
□ 謝雯雯
口述史研究用于民族舞蹈傳承發展方興未艾。相對來說,雖然作為一種較為小眾的研究方法,但其對于中國民族舞蹈的傳承發展均有獨特作用。本文以新疆哈薩克族舞蹈為例,簡單探析了其于民族舞蹈傳承發展中的作用及策略。
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通常需要傳承人進行積極的保護,并進行必要的信息收集、整理與分析,在此過程中,不可避免需要傳承人進行口述。[1]對于民族舞蹈傳承,在某種程度上來講,傳承人的口述甚至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如果能從口述史的角度研究民族舞蹈的傳承與發展,講方法、有步驟地進行口述,則口述于民族舞蹈的傳承更能發揮作用。

在口述史訪談時向舞蹈表演老前輩學習哈薩克族舞蹈
一、口述史
遠古時期,在沒有歷史文獻記錄之前,人們通常以口述的形式傳承歷史。從已發現的資料來看,被稱為東方“荷馬史詩”《格薩爾王傳》便以是以口述的形式傳承的。[2]無獨有偶,古希臘時期的《荷馬史詩》也是通過相同方式完成的。
確切地說,口述史作為一門學科,以及其不斷地發展成為一種研究歷史方法直至上世紀40年代才開始出現,當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成立了專門的口述史研究中心。[3]自此,作為一種流行方法用于史學研究。在我國,也有一些學者為開展相關研究工作而開展了口述史的研究,但通常把其作為一種輔助方法使用。不過,即使在國際上,關于口述史的規范以及可能產生的法律、倫理問題等,人們并未達成共識。進入21世紀,出于研究的需要,中央黨史研究室開始把其作為一種普遍方法研究黨史,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因為存有爭議,有些研究者對即使已在某些專業學術刊物發表的研究成果,還是持以嚴謹的態度,只作參考,但卻不予以使用。
二、口述傳承舞蹈必要性與可行性研究
把口述史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用以舞蹈藝術的傳承具有極大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這主要是因為在舞蹈藝術的傳承發展中,“言傳身教”是主要形式。[4]也因此,在現代社會,當人們在探討如何傳承民族舞蹈藝術時,通常提倡現代師徒制,倡導一對一言傳身教的形式。本文在此以新疆哈薩克族舞為例探究口述史于民族舞蹈傳承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必要性
國內外一些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者熱衷于“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缺乏足夠的文獻資料有關。因為有一些少數民族甚至沒有書面文字,所以其傳承只得以口述形式進行。這也在某些方面導致了民族舞蹈文獻資料的匱乏。也因此,對民族舞而言,以口述史的形式進行研究較為實用。再就文獻檔案記錄而言,其視角通常對準那些具有典型性的事件或政治活動,而對于舞蹈藝術等通常只能記錄下較少一個部分。

國家藝術基金新疆哈薩克族舞蹈教學傳承與編創研究研討會現場
也正是因為如此,直至在非物質遺產的保護下,新疆地區的一些哈薩克族舞蹈民間藝人才被人們發現。但關于他們舞蹈藝術的傳承卻又缺乏必要的資料。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他們如其他舞蹈藝術的傳承人一樣,不擅筆墨。對于他們而言,舞蹈實踐與表演是他們藝術活動的核心。在此情況下,運用口述史傳承他們的技藝顯得更為關鍵。
(二)可行性
首先,我國在以口述史研究舞蹈藝術傳承方面已經有過探索。例如,在本世紀初期,北京舞蹈學院的潘志濤便運用口述史研究方法編寫了一部民族舞蹈教材。其后,他又出版了相關專著,如比較有影響的《中國民族民間舞口述史》。再從地方民間舞的傳承來看,也有許多學者通過口述史的相關研究,開展民間舞的傳承與保護。例如,張璨通過口述史對江蘇民間舞進行的研究。雖然從所發現的資料來看,目前尚無學者專門針對新疆哈薩克族舞蹈進行口述史的研究,但這些為相關方面的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礎。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統一國家。少數民族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近年來,黨和國家極其重視少數民族優秀文化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明確表示黨中央非常重視支持少數民族文化發展,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更是給予了莫大的重視和支持。2019年10月,國家財政部向社會公布,為貫徹黨和國家支持少數民族文化的部署,將分別通過“轉付支付”、“部門預算”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人才啟動專項基金。
這些均為通過口述史研究哈薩克族舞蹈,進而使之得到傳承與保護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條件。
三、口述史傳承民族舞蹈的作用
(一)使民族舞蹈實現生態傳承
通過對哈薩克族舞蹈的傳承現狀研究發現,無論是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舞蹈,如“卡拉角勒哈”,還是其他一些并不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舞蹈,其傳承人或表演藝術均出現了老齡化現象。[5]而年輕一代從事舞蹈傳承或專業舞蹈表演的人較少,在此情況下,一方面要擴大舞蹈傳承表演群體人口。另一方面,則以通過不同形式為這些邁向老年的傳承人、表演藝人留下珍貴的資料,以便使其所承載的舞蹈藝術能原生態地保存下來。

2019年5月于薩代提家中口述史訪談時學習哈薩克族舞蹈
在此方面,口述史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不但在于通過這種方式,可以搜集一些緊密相關的資料。更主要的是,通過這種方式,也可以保存正要逝去的“聲音”。相對于其他研究方法,口述史更關注普通個體的聲音,由此獲得的史料可在很大程度上彌補文獻資料的不足。以此方式研究新疆哈薩克族舞蹈,其視角對準的當然是新疆地區的不同市縣的哈薩克族舞蹈。研究表明,通過口述史對哈薩克族舞蹈進行研究,口述人的生活經歷、舞蹈經歷以及其對舞蹈傳承發展的建議、觀點,可為人們提供一條文獻沒有記載的路徑去探究哈薩克族舞蹈的傳承、發展與保護。
(二)豐富民族舞蹈的研究方法
對于民族舞蹈的傳承與發展,人們一般較為青睞綜合使用某些方法,特別是文獻資料法與田野研究法。田野研究法通常需要一定的文獻資料作為輔助。而在某種程度上來講,文獻資料法并不利于民族舞蹈的生態傳承。因為即使有文獻記載,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理解,甚至有時會出現誤解。
如同所述,通過口述史的方法研究民族舞蹈的傳承與保護在我國并不常見。但如果有機地把其融于其他方法,則可能會實現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更可以豐富民族舞蹈的研究方法。從其在哈薩克族舞蹈研究中的現狀來看,研究者通常以錄音的形式以搜集口頭史料。從其實際運用來看,的確豐富了哈薩克族舞蹈的研究。但其實施遠未成為一種研究方法。其實,把其作為一種研究手段上升為一種研究方法對于包括中國民間舞蹈整體均有實際意義。而且,基于口述及田野研究法的運用,民族舞蹈可在借鑒人類學研究的方法研究之上,形成自己獨特的口述史研究方法。
(三)保存珍惜資料
實際上,近年來,口述史在世界各地的舞蹈非物質遺產的保護傳承研究中運用得轟轟烈烈。通過研究發現,這主要因為一些相關的訪談者通常根據個人親身的舞蹈經歷,基于個人對所從事舞蹈技藝、傳承、發展現狀深入思考,在此基礎上口述。
對于民族舞蹈而言,因為歷史發展的變遷,曾經的生存環境已發生了較大變化,特別是在網絡科技的影響下,新一代的傳承人、表演者對其認識較為膚淺。但隨著老一輩傳承人、表演者的離去,他們對舞蹈藝術的認識與思考也終將離去。具體到哈薩克族舞,例如,“卡拉角勒哈”當初的游牧環境早已不存在,即便現在的老一輩傳承人,他們也沒有經歷過曾經的游牧生活。對于“卡拉角勒哈”的理解與傳承是通過其上一輩人言傳身教獲得。而現在新一代傳承人面臨的舞蹈生存環境又與他們當初存有巨大差異。因此,通過對老一輩傳承人進行口述史的研究,可為當代、更為后代傳承者留下極其珍貴的資料。
四、口述傳承舞蹈策略
(一)確定口述對象
隨著民族舞蹈學科的不斷發展,相關的研究變得較為復雜。如以新疆哈薩克族舞為例,不但要關注舞蹈本身,而且要研究其生存發展的環境。例如,同一舞蹈的傳承人,在不同的年代其對舞蹈的思考、認識均有不同。而且,即使普通群體,并沒有被認定為某種舞蹈傳承人的普通表演者,其對于舞蹈技術、發展等也有自己的思考。再從某些方面來講,正是因為這些普通業內人士的存在,口述史研究才變得更有活力,更有底氣。

國家藝術基金新疆哈薩克族舞蹈的教學傳承與編創研究活動現場
因此,除分別確定不同年齡段的傳承人作為口述史的研究對象,普通參與者也應按一定比例融于其中。研究者在對哈薩克族舞進行口述史的研究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普通的哈薩克族舞者的口述不但可以拓展哈薩克族舞的研究領域,而且利于深入挖掘常為人忽視但卻不失為精彩的部分。
(二)明確規范與要求
口述史研究用于民族舞蹈傳承發展與其用于其他領域一樣,需要確定一定的原則與要求。除對口述人的基本信息進行記錄,更先確定口述的內容。在此方面,研究者與口述人最好能事先達成一致。但在口述未開始之前,研究者應深入了解口述內容。這樣,在其過程中,研究者才能敏銳地捕捉到口述者較感興趣的話題。在引發其興趣后,才可能就研究者更為關心的內容進行口述。
例如,在有關哈薩克族舞蹈的傳承中,如何在舞蹈過程中即興發揮始終是學界關心的問題。在此方面,可有意識引導口述人盡可能進行深度陳述。當然,口述民族舞蹈的研究更需要確定人物線索。在此方面,可以一人為主多人為輔,也可以傳承人為主非傳承人為輔。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方法應綜合運用。
(三)激發口述動力
確定了口述對象及原則,在對相關人士進行口述研究時,更要激發其口述動力。因為在口述研究中發現,有些人可能因為記憶原因,或出于主觀原因,結果在口述時刻意遺漏了曾經的經歷,甚至對其加以美化等。口述史受到質疑與此有很大關系。在此情況下,需要依據舞蹈本身,使之作為激發口述者動力的載體,以便其可充分地挖掘自己對舞蹈的記憶,便于根據動作經驗,并盡可能地為藝術生態傳承而從客觀的角度進行口述。
對舞蹈的風格傳承,這一點極其重要。例如,在“卡拉角勒哈”中,男性表演者如何通過自己的律動表現豪放、粗狂,而女性如何展現柔美、含蓄,均可通過口述人的語氣、表情,甚至微微的身體動作展現。
對于民族舞蹈的研究,以口述史的方式進行目前方興未艾,特別是其對哈薩克族舞蹈的傳承與保護來講更是如此。但無論其用于哈薩克族舞蹈,還是用于我國其他民族舞蹈,其可能發揮的作用及采取的策略遠非以上所述。例如,在運用策略方面,除此之后,更需要深度挖掘珍稀資料。這樣,口述史研究對于民族舞蹈的傳承與發展才具有廣度與深度。作為一種學科,民族舞蹈才會變得更加多元和具體。同時,作為一種藝術,其傳承、發展與保護才能得到持續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