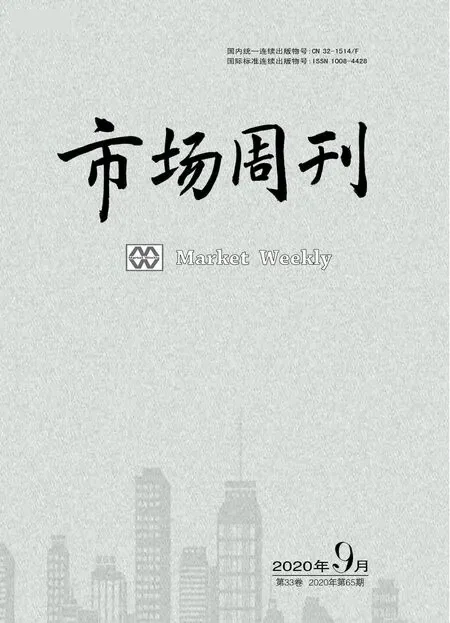教育對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影響
王慧英
(太原師范學院,山西 晉中030619)
一、 前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結構的轉變,新生代流動人口在流動人口中的比重持續提高。 在2017 年的流動人口中,新生代流動人口(1980 年以后出生)所占比重已達65.1%。 年輕血液的注入為流入地提供了城市建設和社會發展所必需的人力資源支持,為推快我國城市化進程做出巨大的貢獻。 但由于不同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新生代流動人口融入當地面臨著諸多困境。
受大學擴招政策的影響,新生代流動人口整體素質較高,存在一定比例高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流動人口。 現代教育的意義不僅在于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可以影響生活習慣、人生態度、思考方式。 那么,與受教育程度低的新生代流動人口相比,受教育程度高的新生代流動人口是否能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 我們是否應該增加對高素質流動人口的關注? 為此,文章將著眼于探索教育對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具體影響,考察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為政府采取有針對性的政策提供啟示。
二、 數據來源與變量設置
研究采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CGSS2012)。 根據流動人口定義和問卷設置,將同時滿足非自出生起一直就住在本地、戶口登記地為本區/縣/縣級市以外的樣本設定為流動人口,賦值為1。 其余樣本則為非流動人口,賦值為0。 同時,由于文章僅關注城市生活中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狀況,因此,僅保留居住在市/縣城的中心城區、邊緣城區、城鄉接合部的年齡在27~36 歲的樣本。
研究的因變量為社會融入狀況。 以全年總收入、工會參與度、選舉參與度和與鄰居社交頻繁程度來分別反映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經濟融入、社會組織參與、政治參與、文化適應情況。 全年總收入采用對數形式進行回歸,同時剔除全年總收入在50 萬元以上的極端值樣本。 工會參與度為二值變量,若樣本為工會會員,則賦值為1,否則為0。 選舉參與度指的是上次選舉是否投票,若投票賦值為1,否則為0。 與鄰居社交頻繁程度也為二值變量,與鄰居社交頻繁賦值為1,不頻繁為0。 為研究不同教育程度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情況,將受教育程度作為主要自變量,并將其劃分為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本科以下受教育程度。
需要注意的是,當以教育作為自變量,對各項社會融入指標進行回歸時,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內生性問題(豪斯曼檢驗的P值均小于5%)。 因為存在一些不可測變量,例如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既可能影響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同時也會影響其社會融入的程度。 為此,將是否受高校擴招政策影響作為受教育程度的工具變量,用以解決內生性問題。 把1999 年未滿18 周歲看作受高校擴招政策影響的等價條件,若符合該等價條件,則將工具變量賦值為1,若不符合符合該條件,則將工具變量賦值為0。
對控制變量的選擇主要根據各社會融入指標的影響因素、數據的可得性來綜合確定,具體包括:政治面貌、性別、戶口情況、婚姻狀況、房屋所有權、家庭經濟情況、社區類型、行業編碼、企業規模、企業所有制、雇主或雇員、工作時長、收入情況、社交觀、地域編碼。
由于篇幅限制,僅展示一部分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 所示。

表1 描述性統計結果
三、 基本模型
為了解決內生性,本文采用兩階段回歸模型,具體如下:

其中,Yi是因變量,即社會融入狀況的具體指標,包括年總收入、工會參與狀況、選舉參與狀況、與鄰居社交活動頻繁程度。 EDUi代表個人的受教育程度,EDUi等于1 代表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EDUi等于0 代表本科以下受教育程度。Fi是區分流動人口和非流動人口的身份變量,Fi等于1 代表流動人口,Fi等于0 代表非流動人口。Pi為工具變量,Pi等于1 代表受擴招政策的影響,Pi等于0 代表不受擴招政策的影響。
通過分析可知,α1度量的是教育對社會融入具體指標的普遍作用,即同時存在與流動人口和非流動人口中的作用。α2則代表在流動人口中,教育對社會融入具體指標的額外影響作用。
四、 結果與分析
由于篇幅限制,表2 只展示關鍵自變量的回歸結果。

表2 回歸結果
在經濟融入方面,教育對流動人口和非流動人口的年收入均有正向的影響,教育程度越高,年收入越高,這符合教育經濟回報的一般規律。 由于新生代流動人口選擇離開常住地到流入地生活、居住的主要訴求是來自經濟方面,流入地較之其原居住地經濟往往更發達,因此,新生代流動人口獲得越高的收入,說明其在經濟方面越趨同于當地人口,經濟融入水平越高。 因此,在經濟融入維度上,我們應該更多地關注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新生代流動人口。 同時,可以發現,交叉項前的系數為0.3898,且顯著為正。 這說明在流動人口中,教育對年收入的正向促進作用更大。 與非流動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動人口在缺乏社會資源的條件下,人力資源成為其增加經濟收入的重要因素。
在社會組織參與方面,回歸結果顯示,α1為-0.4502,顯著為負,α2為-0.1672,結果并不顯著。 這說明,無論是年輕流動人口中還是在年輕當地人口中,受教育程度為本科及以上的參與工會的概率低于受教育程度為本科以下的45.02%。 其原因主要源于以下兩點:第一,受教育程度越高,勞資關系越和諧,且其法律意識更強,對工會的維權訴求越低。 第二,政策傾斜。 全國總工會及地方分會近年來致力于不斷推進經濟收入低、生活貧困的勞動者加入工會,為其提供幫助。 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教育對工會參與率的負效應。 值得注意的是,流動人口較之非流動人口更需要加入工會組織,融入工作環境。 現代工會作為員工之家,為員工維權的同時,也是員工參與企業事務、相互溝通交流的平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員工在當地的社會融入。 因此高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工會參與情況需要我們格外的關注。
對于政治參與,回歸結果顯示,教育對選舉參與率的普遍作用為-0.6059,結果顯著。 即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選舉參與率低于受教育程度在本科以下的人口的60.59%,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第一,高受教育程度的人群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缺乏參與選舉的時間和精力。 同時,由于工資率較高,其參與選舉的時間成本更高。 第二,低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通常是社區幫扶的對象,由于與社區工作者的頻繁接觸,其獲得選舉信息更便捷、更全面。 同時,低教育程度的人口往往更容易受其他人影響,被發動去參加社區選舉。 此外,回歸結果顯示,在流動人口中,教育對選舉參與率的額外作用為0.2537,結果顯著。 由于其數值小于普遍作用的絕對值,因此,在流動人口中,教育對選舉參與率的影響仍為負,但其負效應小于非流動人口中的負效應。 其主要原因是,流動人口中受過高層次教育的人有著更為強烈的融入意愿,更愿意參與到社區、居委會的工作中去,保障自己的利益。
在文化適應方面,研究發現,教育對社交頻率的作用,在流動人口中和非流動人口中并無差異,且其影響均為負,即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社交頻繁度要低于本科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進行社交的頻率,具體數值為-47.03%。原因有:第一,高教育程度的人口,社交對象更難匹配。 高教育程度的人口更容易形成自己獨有的思想體系,感興趣的話題往往更具有技術性,在同樣的社區中,找到聊得來的人的概率更低,因而,與鄰居社交的頻率也更低。 第二,與選舉參與率不同,社交娛樂更多的基于情感基礎而不是利益基礎。因此,高受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較之低受教育程度流動人口更為強烈的流入意愿,只會促使其參與社區選舉等與其利益相關的活動,而與鄰居的社交娛樂活動則不會受影響。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當因變量是與鄰居社交的頻率時,教育的額外作用不顯著。
五、 結論
文章通過研究教育對社會融入各個維度的不同影響,對本科及以上、本科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情況進行了多層次多維度的剖析。 研究發現:
教育對新生代流動人口經濟融入有正向的促進作用。高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經濟整合更好,他們往往會獲得更高的收入、職業聲望以及福利待遇。 而經濟條件的提高是流動人口選擇繼續留在當地的基礎。 因此,在經濟層面,政府要繼續關注低教育程度流動人口經濟生活,定期組織職業技術培訓,提高其工作能力,同時開展就業指導和專項招聘會,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教育對新生代流動人口參與社會組織、參加政治選舉、文化適應有負向的抑制作用。 經濟轉型中的我國,市場經濟逐漸成熟,“能者多勞”較為普遍,高素質人才承擔著更多的社會責任,工作壓力大,時間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在工作中,參與當地社會事務的精力較少。 同時,高工資率意味著更高的參與成本。 此外,當下社會把較多的關注放在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的社會融入問題上,無論是社區還是工會的工作重點都忽視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從而導致此類流動人口信息獲取渠道不暢,加之工作和生活的雙重壓力,更少參與到社會事務中,容易導致其地理上和心理上的雙重隔離。 因此,政府也應該密切關注高教育程度流動人口的社會參與,生活中以社區為主體,工作中以工會為主體,定期對其進行走訪調查,了解其需求,給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