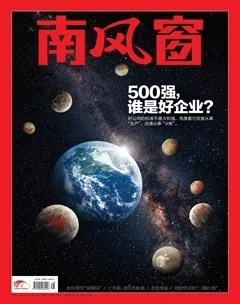美國增兵印太,戰略瓶頸何在?
于英紅

8月18日,美國空軍、海軍、海軍陸戰隊和日本航空自衛隊進行大型聯合軍演
2020年9—10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將與印度、澳大利亞、日本同僚舉行四方會談,探討印太地區的安全合作框架。盡管2017年四國因為基建投資而啟動這一四方高層會談,但該會談此后的目標指向非常明確,即從軍事和安全多個角度為區域內國家提供“中國以外的選項”。聯系數月來美國持續增兵印太,不難發現美國高調領跑印太競爭的決心。
而8月31日,印軍在中印邊界的西段班公湖以南地區以及熱欽山口附近再次非法越線,造成邊境局勢再度緊張,很難說背后沒有美國增兵印太的因素。
強化防御與增強威懾
大疫當前,美國不但沒有集中全部精力防疫,反而密集增兵印太:
7月28日,美國陸軍阿泰米斯偵察機抵達日本,配合美軍沖繩基地執行偵察任務。8月12日,美國空軍3架B-2轟炸機部署到印度洋中的迪戈加西亞島,2架B-1轟炸機從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飛往日本海。8月15—17日,美海軍累計派出7架電子偵察機前往中國臺灣周邊偵察。8月20日,美空軍派出B-1槍騎兵轟炸機,與日本同行在日本海舉行聯合軍演。
這些軍事行動的共同特點是,現代化、信息化,精準打擊、補給能力強。
8月18日,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部宣布,將“定期開展轟炸機特遣部隊行動,以顯示美國對印度﹣太平洋地區盟友和伙伴的承諾”。幾個月來,美國從軍事部署到國內政治議程兩個維度,加快推進2018年以來布局的印太戰略。美國防長埃斯珀對美軍新部署的解釋是:強化防御,無意挑起戰爭。
美軍增兵印太地區的同時,美國國內關于推進印太戰略的政策討論,也在密集進行。
7月初,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審議通過2021年國防授權法案。該法案提出“太平洋威懾倡議”(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批準撥付近70億美元作為支持基金。
太平洋威懾倡議是2014年歐洲威懾計劃的姊妹版,其核心內容是實現作戰平臺的現代化:一方面增強防御能力,另一方面從軍力部署到后勤供應等方面增強作戰能力,將該地區過去相對密集的軍力部署,轉化為更為靈活的分布式部署;同時,提升與盟友、伙伴協同作戰、情報共享等能力。
此外,總統軍控事務顧問馬歇爾·比林斯利透露,美國計劃研究在一些亞洲國家部署中程和中短程導彈的可能性。據比林斯利稱,美國正在研制的高超音速武器,將與目前部署在印太地區的陸基中短程導彈等穩定性防御能力一起,成為美國亞太盟友得到保護的某種保證。
特朗普政府對印太地區的密切關注,也體現在戰區司令部的調整上。2018年,美國將原太平洋司令部更名為印太司令部。即便在增兵印太之前,印太司令部也是美軍在全球的聯合作戰司令部中規模最大的一個;約37.5萬名美國軍人和文職人員配屬于印太司令部責任區,兵種覆蓋海陸空,并按照兵種設有海陸空和海軍陸戰隊4個指揮部。不過此前,美軍在該地區的兵力部署主要集中在幾個大型軍事基地,此次調整,將這些集中的力量分散到各個區域,機動性和靈活性得到加強。
據比林斯利稱,美國正在研制的高超音速武器,將與目前部署在印太地區的陸基中短程導彈等穩定性防御能力一起,成為美國亞太盟友得到保護的某種保證。
和奧巴馬時期確保美國在印太地區核心水域的優勢地位相比,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政策更傾向于從水、陸、空方向,全方位確立美國在該地區的絕對優勢。印太地區被布熱津斯基列為世界上“地緣政治最為瀕危的地區”之一,特朗普政府在強化防御的名義下增強威懾能力,或將成為損害地區穩定的關鍵外部誘因。
全球秩序重構的一環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既是美國此前亞太政策的延伸,也是特朗普面對大變局背景下的全球權力危機所做的回應。從“亞太”到“印太”的轉變,不僅僅是地緣意義上的調整,也包含著美國在地區戰略博弈以及全球秩序重構上的重大調整。
2017年11月5日,特朗普在日本橫田的美空軍基地發表演講,提出“建立一個本著自由、公正與互惠的印度﹣太平洋地區”。不久,美國《2018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宣布,印太地區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重要地區。此后,美國決策高層在各種場合闡述印太概念的內涵以及相關的行動計劃。2019年6月1日,國防部發布《印太戰略報告》,標志著美國正式將印太地區上升到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來看待。
經濟上的配套方案也在籌劃之中。由美國國會在1970年代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旨在促進美國在新興市場的投資,如今據稱將在亞洲和全球促進所謂“市場驅動、透明和財務持久”的基建發展。
美國高調介入印太地區,除了因為該地區良好的經濟前景和地緣優勢不容錯過外,還因為該地區的許多國家都在經歷深刻的變革,原有的均勢逐步讓位于新的力量架構。區域內大國擴大影響力的愿望和控制力,均有增加勢頭。
隨著印度洋﹣太平洋航線對經濟和安全戰略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地緣意義上的亞太逐漸被印太取代,其重要區別在于剝離區域內主要的美國競爭對手—中俄兩國。美國希望重構以美國為主導的地區秩序,確保經濟安全,反對除美國以外的地區霸權,確保軍事上建立起足夠的威懾力,建立網絡化地區安全框架。
從全球背景來看,在21世紀的頭十年,二戰結束后美國主導構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遭到前所未有的廣泛質疑。從發達國家、新興發展中國家到仍在貧弱境地掙扎的弱小國家,各方都可列舉出該秩序的缺陷,連美國自身對該秩序的可持續性也深表懷疑。
在全球權力分散的局面下,多邊關系和國際制度以及組織越來越不能滿足美國的愿望。美國期望建立起可謀求其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全球秩序。面對多力量中心的崛起,美國認為其倡導建立的秩序培植起一些修正主義國家,對自身的全球戰略利益和地位構成威脅和挑戰。因此,特朗普就任以來,在“美國優先”的旗幟下,相繼退出一些多邊協定,一度給各界造成美國戰略退卻的錯覺。實際上,美國是在醞釀深刻的戰略調整。
印太戰略的出籠,證明特朗普政府并沒有淡出全球霸主位置的打算,而是換了一種方式,將有限的資源用在更值得的地方。在世界秩序重構的大背景下,隨著多元力量中心的出現,冷戰后美國作為全球超級大國的地位和影響力難以為繼,要逐夢“美國優先”只能退而追求有限度的目標—確保美國在關鍵地區的優勢地位。而印太正是這樣的關鍵地區之一。
新一輪區域性帝權的角逐
就歷史經驗而言,大戰略的國內外政治基礎,對于大戰略的實施成效非常重要。大多數研究者,將國內決策機構間的齟齬、環印太國家對美國印太戰略存在疑慮,以及美國越洋部署難以為繼,視為印太戰略的瓶頸。
事實上,從國會研究部發布的一系列印太關系報告,到國防部發布的《印太戰略報告》,再到白宮高層在多個場合對印太戰略的解讀,以及軍方兵力部署,說明印太戰略經歷一個國內決策過程,體現為美國決策層針對印太地區新進展做出的戰略部署。
而環印太國家的疑慮,更多的是對細節的推敲而非對整體戰略的抵制。環印太國家大致可以分為四類:有抱負的區域內大國—日本和印度;與中國有邊界、島嶼爭議的國家;正在經歷社會轉型的國家;在東西方之間搖擺的國家—澳大利亞、新西蘭。
由于美國與印太地區盟友的利益契合點大于分歧,加上印太地區區域性大國希望提高自身地區競爭力乃至全球性影響的愿望,過去幾年里,環印太國家以各種方式對印太戰略表示支持和歡迎。因此,印太戰略將成為美國和印太地區盟友的聚合劑。
印太戰略最主要的安全風險是,體系內作為主導角色的美國,能否有效避免體系內其他國家為了自身利益而破壞和平。美國大規模的軍事投入與網絡化力量部署,從長遠看,勢必會鼓勵甚至固化已有的地區矛盾,導致現有矛盾擴大和深化。
二戰后,美國主導的亞太秩序之所以保持相當的穩定性,是因為日本在美國的扶持下,成為一個政治經濟發展相對穩定的國家。為了避免戰爭再起,美國也從內部和外部約束日本重建軍隊。
二戰后,美國主導的亞太秩序之所以保持相當的穩定性,是因為日本在美國的扶持下,成為一個政治經濟發展相對穩定的國家。為了避免戰爭再起,美國也從內部和外部約束日本重建軍隊。
近年來,為了實現所謂的均勢和制衡,印太戰略在演變出爐的過程中,降低了對日本的約束,而印度國內深受經濟發展不平衡以及由此而來的矛盾激化、宗教以及邊界爭端等矛盾困擾,具有地緣上的脆弱性。與中國有島嶼爭端的國家,也在借美國之力強化自身防務,其對島嶼主權的訴求和立場越發強硬。美國在自由與主權完整的名義下,支持與中國有島嶼和領土爭議的國家堅持自己的主權訴求,而以國際法與和平手段為旗幟,限制中國捍衛其領土完整的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印太戰略的后果或將是提供短期內的和平穩定,但從長遠看,醞釀和觸發地區不穩定。
印太戰略是美國重構全球秩序的一部分,也是“美國優先”指導下的新一輪美國霸權(卡贊斯坦稱之為“美國帝權”)的一部分。阿諾德·沃爾弗斯認為,強國塑造有利于其核心利益的地區秩序,是其發展過程中的必然,此為“環境目標”。國際關系學者卡贊斯坦認為,強國在塑造新秩序時,需要滿足以下條件:相對實力,成本與收益,加強防務,結盟,穩定的核心國家,制度以及意識形態引力。美國恰恰是在滿足上述條件的情形下,提出印太戰略的。
在衰落的西方與崛起的東方之間,美國在關鍵領域仍然占據優勢,而印太戰略的推行則是依托傳統的地區盟友,加強防務協作,由此解決遠程投送兵力所面臨的困境。在這個基礎上重建威懾,建立網絡化安全框架,可以有效縮減成本與收益之間可能出現的巨大缺口。
印太戰略同時也是門羅主義以來美國外交傳統的延續。美國建國以來融入現存國際秩序并在其中嶄露頭角乃至躍升到領導角色的經歷,證明美國奉行的準則一直是規則的歸規則,實力的歸實力。但是,如能在和平共贏的情況下實現地區秩序的重構,不僅是區域和平與穩定之幸,也是全球和平與發展之福祉;而不論何種秩序,作為其中發揮主導作用的國家,對區域內國家破壞地區的行為,如果缺乏有效的約束力,秩序的可持續性必將會因為地區穩定遭到破壞而付出代價。
責任編輯謝奕秋 xyq@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