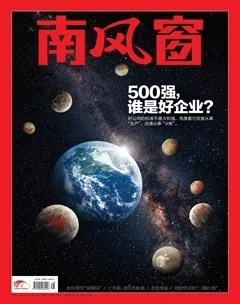500強里的“失語者”
榮智慧

8月2日,江蘇省泰州市南舍村,村民劃著菱桶采摘菱角
今年,中國(含香港、臺灣)共有133家企業入圍“世界500強”,歷史上第一次超過有121家企業上榜的美國。
大多數人的目光都盯在能源企業和互聯網企業上,這些來自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國企和民企有一種極大的象征性: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既有工業大國的重器“坐鎮”,又有科技大國的“先鋒”出征—而有著五千年歷史的“農業”,只是個毫不起眼的配角。
如果刨去致力于流通過程的中糧集團,再刨去屬于制造業的農業機械公司,與農業生產技術相關的公司,在“500強”榜單里只有兩家:中國中化集團和中國化工集團。前者滑落了21名;后者滑落了20名,虧損約12.5億美元,是中國虧損最多的企業。而且,農化技術只是它們眾多業務版塊中的一部,他們是化工企業,而不是農業企業。
其實,關注“500強”里中國農業技術公司的狀況,實際上關注的是中國農業現代化向何處去的問題。特別是在國際貿易博弈走向深化,并開始波及農業和糧食領域的時候,作為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以及人口大國,中國在農業領域的頂級企業“缺失”,已經到了必須引起關注的時候了。
頂級中國農業企業,有沒有?
無論是國企中化集團,還是央企中國化工集團,二者的農化版塊,自2018年中化集團董事長寧高寧兼任中國化工集團董事長以來,已經進行了整合。
其中,農化版塊的“拳頭”就是先正達。先正達是瑞士公司,被中國化工集團于2017年收購,交易對價430億美元。先正達總部位于瑞士,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擁有4.8萬名員工。2019年,先正達集團的總營收達到230億美元,超過拜耳集團作物科學單元的221億美元,是全球營收規模最大的農化集團。
另外在“500強”榜單上的農化巨頭還有巴斯夫公司、陶氏杜邦公司和拜耳集團。它們都在種子、除草劑、植物保護、數據科學等方面擁有高技術含量的成果。拜耳集團還收購了孟山都公司,合并后的前6年要投入160億美元用于種子研發。
比較來看,中國的農化技術,其實幾乎完全得益于收購而來的先正達,以及之前十年間收購的多間外國公司,本身是沒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家底”的。而且,在農業生產領域,考驗技術的地方,無非是種子、化肥和防疫。但是,對于吃了5000多年農業飯的中國人來說,好像只給歷史留下了邊際效益無限遞減的“內卷”,說起來“很沒有面子”。
無論是巴斯夫、陶氏杜邦還是拜耳,它們的客戶往往來自大型的、成規模的農業集團和農場,但在中國,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阻止了高新農化技術的迅速流通。
這絕不是因為中國人沒有能力研發農化技術,也不完全因為中國農化公司放棄了“追求”,而是由于地少人多的國情,導致中國的家庭農場的生命力持久而頑強,使新技術很難一瀉千里地推行下去。
人多到什么程度呢?中國農業的就業人口,在全世界依然高居榜首。由于中國城鎮化一直處在進行過程之中,那么,即使城鎮化比例在2030年增加到80%左右,中國還是會有大概1.6億人從事農業。在同樣人多地少的日本,農民只有250萬,在臺灣地區是77萬。
地少到什么程度呢?在今天,中國農業和皇朝時代一樣,依然以小農場為主,勞均耕地面積約10畝。這和美國人少地多的情況比不了,它的勞均面積將近2700畝。
正是因為人多地少,家庭小農場式的精耕細作才能獲取整個家庭糧食生產加消費的最大收益,同時,也正是因為人多地少的情況始終難以改變,中國農業的大農場化、“規模效益”并不現實—農業人口不可能憑空減少,而家庭農場式的“自雇”成本遠遠低于大公司的雇工成本。因此,家庭農場還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家庭農場規模小,范圍極其分散。在改革開放后,國家基本上退出了制度性的農業生產領域,除了儲備糧任務,已經沒有統一性的指導或分配下達給農戶。這種分散的情況對企業推廣技術來說,更是個很大的難題。無論是巴斯夫、陶氏杜邦還是拜耳,它們的客戶往往來自大型的、成規模的農業集團和農場,但在中國,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阻止了高新農化技術的迅速流通。
自耕農和大企業
當然,中國農業的發展模式分成三種,并不是可以一概而論的“鐵板一塊”、絲毫沒有新型農化技術的用武之地。
第一種叫“行政模式”,主要用于糧食生產。糧食生產是國家高度行政干預的領域,包括大規模存儲糧食,國家掌握著儲存糧食年產量約六分之一的現代化倉庫;施行穩定糧價的措施,比如設定最低價;利用行政手段建立集中的糧食生產基地;提供糧食加工和銷售服務;以及發放種糧補貼、獎勵、取消農業稅費等。
這樣的模式下,中小農場的農民能夠達到1000元/畝的凈收入,再加上國家提供的各種補貼和獎勵,生產是“可持續”的。不過,行政模式的最大受益者依然是“龍頭企業”、大家庭農場和大合作社,在得到更多政策利好的條件下,這些連片的土地也更有機會推廣新型農化技術,并能有效觀察技術應用后的效果。
第二種叫“新農業”。新農業主要包含肉、蛋、奶、菜等高附加值農產品領域(產值差不多是糧食的四倍),這一領域幾乎完全依賴于市場機制,國家較少提供技術指導和輔助,或只提供一些較為基礎性的“交易場所”。同時,從事新農業的更多是分散的家庭式農場,農戶們一直煩惱于市場價格的劇烈波動,還要自己去和層層的產地小販、小商人、批發商、銷售地批發商打交道。
新農業既受到物流上的限制,也由于地塊狹小、范圍分散,使新技術推行成本極高。新農業是資本和勞動雙密集的生產領域,但是,產品產值的絕大部分,都被各式各樣的“中間商”抽走。這也造成了“種菜賠、買菜貴”的局面—生產者和消費者“雙輸”。
第三種是近年來借鑒美國的“大合作社”模式。這種模式隱含了對“大田農業”的改造,而不是對三五畝地的大棚蔬菜、二三十畝魚塘果園的新農業的改造。“大合作社”想利用機器的耕—播—收,促成土地連片,既可以推動農業機械的大量使用,也可以促進新型農化技術的廣泛應用。
但是,“大合作社”模式的嘗試并不成功。其中大部分的“合作社”僅僅是個空殼,或者由企業“冒充”合作社來領取國家補貼和優惠。其實美國的農業合作社,是基于農業企業的組合,按投資額或銷售額分配利潤,而近年中國一些發達地區的農業合作社的“嘗試”,往往來自地方政府對被征用的土地增值的期待:將村莊公司化,將農民轉化為持有股權的員工,背后的動力則是要流轉、集中村莊內的土地。這樣的做法,與中央政府設想的合作社為農民服務、“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目的相去甚遠。
在三種農業發展模式中,其實隱含著現實和期待的“角力”。一方面,是地少人多的客觀限制下,無數小自耕農長期以來的精耕細作、自給自足;一方面,是政府希望推行的大農場、機械化。與其說分析三種發展模式哪一種更適合推行新型農化技術,不如說分析這三種模式應該如何根據難以改變的客觀現實而進行改進。
中國一些發達地區的農業合作社的“嘗試”,往往來自地方政府對被征用的土地增值的期待:將村莊公司化,將農民轉化為持有股權的員工,背后的動力則是要流轉、集中村莊內的土地。
相比人少地多的“豪放”美國模式,反而是日本的“東亞模式”更為適合中國的農業實際情況。東亞模式合作社的基礎一樣是小自耕農,通過社區農民合作組織,順著國家行政體系層層上延,這種合作社不僅可以集體購買生產資料,也可以集體加工和銷售農產品,還包含了信用社和金融服務,并形成了全國性的“農協”、國家級的全球化大銀行“農林中金”,甚至還有全國性的爭取農民利益的政治游說組織。
可以看到,日本這種國家參與領導、農民自愿參與的合作社模式,不僅能發揮農民的生產能力和生產積極性,還能節省流通環節的龐大成本,及時采用新技術來提高產品附加值,同時利用內在的金融機構實現投資,并形成代表農民利益的政治組織來影響政策的制定。
如果一味地推行大農場來使用新技術,比較糟糕的后果就是無產化的農民的出現。
技術不是目的
換句話說,提倡新型農化技術的應用,不是目的。通過應用新型農化技術,來提高中國農業產品的產值,這只是目的之一。更根本的目的是,在地少人多、勞動資本雙密集的基本條件下,在勞動力和資本的投入已經逼近極限的情況下,如今更需要發揮農化技術的效用,才能讓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成果,更多地被廣大農民和消費者享受到。
所以,中化集團和中國化工集團,收購先正達等國外公司以掌握先進的農化技術,無可厚非。但是如何更加有效地推行技術,實際上已經超出了“500強”等企業所能完全掌控的范圍。然而,政策的方向,又和這樣的巨無霸式的央企、國企有一定的內在聯系—對“越大越好”的規模效益的信賴,導致對農業的真正主體—小農戶的忽略。
以家庭為基本經濟單位的小農農場,仍然占全國農業的絕大比例,其在農場和務農人員總數、總耕地面積和總產值上,都遠超過雇工經營的大農業企業,也因此比后者具備更加強大的市場競爭力。很多大規模的涉農企業,都很少直接雇工經營,它們更愿意采取訂單、合同、協議等方式退出農業生產,將其轉包給小農家庭。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大多數的涉農企業主要以商業性活動為主,而不是產業性的農業企業。這也就導致了中國農業中的“資本”往往都是非產業性的商業資本。能夠積極介入生產的,比如種苗、防疫、飼料、化肥等,少之又少。更有甚者,是一些商業資本憑“賤買貴賣”來攫取農民收益,根本沒有生產技術、信息技術、物流技術的開拓和創新。

7月2日,在新疆伊犁特克斯縣境內的夏牧場里,牧民放牧
連續多年占據“世界500強”榜首的沃爾瑪公司,就是一個很好的比較例子。作為大型批發公司,沃爾瑪借助信息技術、現代化儲藏和運輸技術來提升物流效率。不要小看物流的成本,以及物流效率提升對農產品的重大意義:根據國家發改委公布的數據,中國的物流費用占GDP的16%,比美國的8%高一倍。特別是在生鮮領域,“損耗”是致命的問題。
雖然近年來因農藥濫用和轉基因備受爭議,但被拜耳收購的孟山都公司,是農業技術領域的巨頭。它擁有1700多項專利,掌握著全球90%轉基因種子專利權,占據了多種農作物種子70%~100%的市場份額。在美國本土,它的市場份額高達90%。一些消費者不免談轉基因而色變,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轉基因作物在消除饑餓和貧困、適應自然環境、加快生長速度和提升口感以及提高產品產值等方面,都有顯著貢獻。
被拜耳收購的孟山都公司,是農業技術領域的巨頭。它擁有1700多項專利,掌握著全球9 0%轉基因種子專利權,占據了多種農作物種子70%~100%的市場份額。
中國的涉農企業,更應該以沃爾瑪、孟山都等致力于產業性發展的企業為模板,關注相關技術的研發和創新,來激發農業產品本身的價值提升,而不必依賴舊式的、“雁過拔毛”型的商業資本模式。
而政策的傾向,也應該以小農戶自愿結合的農業合作社為基礎,為農民提供信貸服務和規模化的資源、技術采購,為農民組織加工和銷售,再依靠中央級別的全球化大銀行,為農民提供更廣闊的融資渠道和理財服務。
農業不僅僅意味著溫飽,也代表著中國人內心的“精神底色”。那里不僅有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的仁政理想,也有陶淵明“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的靈魂寄托。“500強”榜單里中國涉農企業的不受關注、本土農化技術的“落后”,顯示出農業的滿身“落伍感”,似乎已經要消失在工業大國的視野里。
實際上,自明清以來,農村和城鎮的畸形市場結構依然存在;億萬小農戶也依然在尋找新的發展機會。他們的收入能否進一步提高,是決定中國國內市場規模能否進一步擴大、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條件。
責任編輯譚保羅 tdb@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