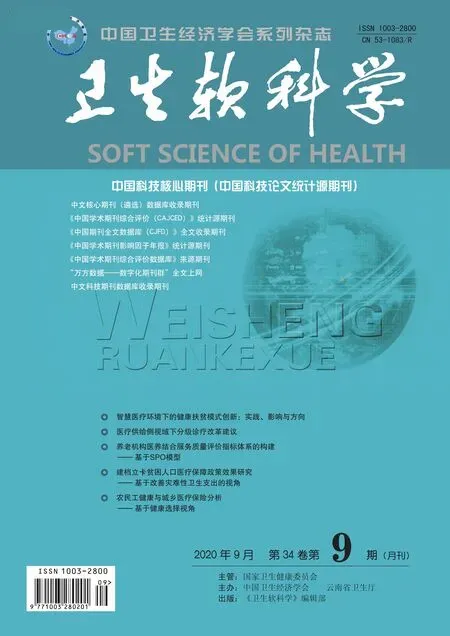我國人均衛生費用的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主成分回歸分析法
王衛紅,張 云,李 婧,侯積菲
(1.青島大學附屬醫院,山東 青島 266100;2.青島大學,山東 青島 266071)
國家衛健委發布的2018年《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衛生總費用已經達到51,598.8億元,人均衛生費用達到3,783.8元,而2008年人均衛生費用為1,094.5元,平均增長速度為14.78%。如何控制衛生費用的過快增長已經成為醫療衛生行業的焦點之一。而人均衛生費用控制了人口因素對衛生總費用的影響,是最常用的且具有說服力的指標[1]。關于人均衛生費用的影響因素研究已經廣泛存在。李麗清[2]等研究發現衛生費用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李長樂等[3]使用混合回歸和固定效應模型發現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65以上老年占總人口比重正向影響人均衛生費用。顏琰[4]通過主成分分析,認為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千人口執業醫師數和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正向影響人均衛生費用,城鎮化率、人口老齡化、嬰兒死亡率負向影響人均衛生費用。謝聰[5]等采用面板分位數回歸模型綜合分析社會人口指數對人均衛生費用的影響。
目前針對人均衛生費用的研究多是從國家經濟、人口等宏觀角度出發,認為經濟發展、人口結構變化等均影響人均衛生費用,選取的指標多為宏觀指標。本研究將人均衛生費用作為因變量,采用主成分回歸方法選取了國家層面的宏觀指標和醫院層面的微觀指標,結合起來綜合分析影響人均衛生費用的因素。此外,所選取的宏觀指標均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建設相關指標,旨在研究基層建設對于人均衛生費用產生的影響,從而為加強基層建設提供新的證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數據主要來源于2009-2013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14-2017年《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2018年《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
1.2 指標選擇
人均衛生費用是多個宏觀和微觀影響因素共同決定的。本次研究選取的指標分為國家層面的宏觀指標(基層建設指標)和醫院層面的微觀指標(醫院病床使用、工作效益及效率指標),具體選取的指標名稱以及說明見表1。

表1 人均衛生費用影響因素指標選取說明
1.3 研究方法
使用Excel 2016對2009-2017年人均衛生費用及其影響因素等相關數據進行整理。考慮到各指標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先運用SPSS 25.0進行主成分分析提取主成分,隨后進行多元線性回歸。
此外,由于人均衛生費用會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本文對名義人均衛生費用進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平移處理,即通過名義人均衛生費用除以定基CPI來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得到實際人均衛生費用,以此作為本次研究的因變量。
2 結果
2.1 主成分分析結果
為檢驗所選取的樣本數據是否符合做主成分分析的條件,本文首先對所選取的樣本數據進行了KMO檢驗和Bartlett’s檢驗。結果顯示,KMO值為0.588,大于0.5,可以進行主成分分析;Bartlett’s檢驗近似卡方值為104.825,P<0.01,具有顯著性水平,各變量間存在相關性。
利用SPSS 25.0對2009-2017年間的原始指標變量首先進行了標準化處理,主成分分析后得到各變量的特征值以及方差貢獻率,主成分1、2的特征值均大于1,且累積貢獻率達86.272%,即這2個主成分代表了原9個指標的86.272%的信息,可以認為主成分1和主成分2為本研究的主成分,見表2。兩個主成分分別代表了一個或多個不同指標的信息,其具體關系見表3。

表2 主成分分析的初始特征值、貢獻率

表3 2個主成分負荷矩陣
2.2 回歸結果
以主成分1和主成分2為自變量,實際人均衛生費用為因變量進行線性回歸。回歸模型的調整R2為0.897,方差檢驗F值為40.280,P<0.0001,具有統計學意義。
對各主成分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檢驗顯示,兩個主成分均有統計學意義,但常數項沒有統計學意義,考慮到常數項非常小,本研究忽略常數項,見表4。

表4 主成分回歸分析結果
由于主成分1和主成分2為本研究原變量的線性組合,可將主成分回歸結果還原成原變量的線性回歸模型。從表4中可分別得到主成分回歸的具體表達式:
Average Fee=-0.761F1+0.584F2
(式1)
由表2和表3可得到各主成分的回歸表達式:
F1=0.30X1+0.35X2+0.38X3+0.23X4+0.39X5-0.22X6+0.38X7-0.38X8-0.32X9(式2)
F2=-0.09X1+0.08X2+0.11X3+0.29X4-0.00X5+0.25X7+0.07X7+0.07X8+0.20X9(式3)
將式2和式3帶入式1中可得:
Average Fee=-0.28X1-0.22X2-0.22X3-0.01X4-0.30X5+0.32X6-0.25X7+0.33X8+0.36X9(式4)
從式4中可以看到,病床使用率(X6)、綜合醫院醫師日均擔負診療人次(X8)、綜合醫院醫師日均擔負住院床日(X9)均正向影響人均衛生費用。每萬人口擁有農村執業(助理)醫師數占比(X1)、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數占比(X2)、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占比(X3)、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數占比(X4)、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入院人數占比(X5)和平均住院日(X7)負向影響人均衛生費用。
3 討論與建議
3.1 基層醫療衛生建設對人均衛生費用的影響
影響人均衛生費用的因素較多,經濟發展、人口結構變化等對衛生費用的影響已經被多次證實,而本次研究多以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建設指標為因變量。由上述結果可知,每萬人口擁有農村執業(助理)醫師數占比(X1)、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數占比(X2)、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占比(X3)、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數占比(X4)、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入院人數占比(X5)的下降,均導致人均衛生費用的上升。
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無論是衛生服務供給還是利用程度,都處于不斷下降的趨勢,導致人均衛生費用的上升。究其原因,雖然我國總體的醫療設備、設施、人才隊伍建設等一直在提升,但整體對比來看,基層建設仍然不夠[6]。基層各占比指標均顯示:基層無論是在硬件還是軟件方面,占比均處于下降趨勢,我國城鄉發展的不均衡性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
由于基層建設的薄弱,居民無論大病小病均往大醫院跑,而國家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推行分級診療,不同等級醫院收費不同,加之醫保報銷比例的區別,也間接助推了人均衛生費用的上升[7]。我國城鄉發展的不均衡性已經嚴重影響到“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解決[8]。李華[9]等通過CFPS(2014)數據,實證分析了分級診療制度與家庭經濟負擔的關系,認為基層首診可顯著降低居民家庭醫療經濟負擔,對慢性病和有住院經歷患者尤其明顯。誠然,分級診療措施是應該和必須的,但是從加強基層建設的宏觀角度出發,必須首先強基層,逐步拉小城鄉之間的差距,保證城鄉醫療資源合理、公平、有效的分配[10,11]。此外,與基礎建設的薄弱相比,城市大型公立醫院不斷擴張,虹吸現象的背后不僅是利益驅使,誘導需求也導致衛生資源的大量浪費。
3.2 醫院層面的微觀因素對人均衛生費用的影響
本次研究不僅考慮國家層面的宏觀因素,同時也分析了醫院層面的微觀因素。結果顯示病床使用率(X6)、綜合醫院醫師日均擔負診療人次(X8)、綜合醫院醫師日均擔負住院床日(X9)的上升均導致了人均衛生費用的上升。其中,綜合醫院醫師日均擔負住院床日對人均衛生費用的影響最大。這三個指標主要反映了綜合醫院的服務效率,可見,隨著醫院工作效率的提升,病人流轉于醫院、病房的速度不斷加快,診治病人的總數固然也會上升,產生的醫療費用自然也是不斷累積。但服務效率的提升也有利于緩解綜合醫院“看病難”的問題。對于醫院的服務效率,我們不可能要求醫院降低效率。
進一步分析可知,大型綜合醫院病人總是源源不絕,醫務人員不得不加快工作效率,同時,病人的平均住院日也在不斷下降,一方面是因為醫療技術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病人數量過于集中的壓力[12]。于德志[13]等通過對居民就診流向和費用水平的變化分析,得出居民就診明顯向大醫院集中,而大醫院衛生費用水平遠高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不合理的就診流向是導致“看病難、看病貴”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須逐漸緩解大醫院“門庭若市”、小醫院“門可羅雀”的問題,改變大醫院的 “戰時狀態”,讓醫療資源被充分合理利用,使患者也能得到有序分流,以控制衛生費用的過快增長[14]。
3.3 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建設,緩解我國“看病難、看病貴問題”
2019年3月8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馬曉偉主任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次全體會議中就指出:我國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尤其是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建設比較弱,必須大力推進優質資源下沉、工作重心下移,要合理調整資源,合理分流病人。從降低醫療費用角度出發,我們也必須不斷加強基層建設,保障醫療費用合理增長。
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建設應主要從人、財、制度等方面去考慮和實施。首先,加大全科醫生隊伍建設,既要保證數量,也要確保質量。第二,提高對基層的財政投入,建立對基層的長效補償機制。第三,建立和完善相關配套制度,如基層的人事考核和薪酬待遇制度、基層用藥和醫保報銷制度、三級轉診制度等。
3.4 辯證看待各影響因素,調控人均衛生費用合理增長
城鄉二元結構對我國“看病難、看病貴”的影響一直是關注的焦點之一,本次研究為這一論點提出了新的實證分析證據。但人均衛生費用的增加是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各影響因素之間也存在錯綜復雜的關系,任何一次研究都很難涵蓋所有影響因素[4,15]。
且由于各研究之間選擇的指標、使用的方法、選取的年份數據等不同,也會得到各自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結論。但選取的這些指標對衛生費用的影響卻是不容置疑的,確定這些指標的影響程度能為政府及衛生行政部門控制過快增長的人均衛生費用提供決策依據,為進一步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和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提供策略指導。
建議未來的研究應結合新時代、新發展,選取不同的指標、不同方法等進行綜合研究。衛生管理部門要重視實證和理論分析的結果,結合改革現狀和經驗,辯證看待這些影響因素,積極調控人均衛生費用合理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