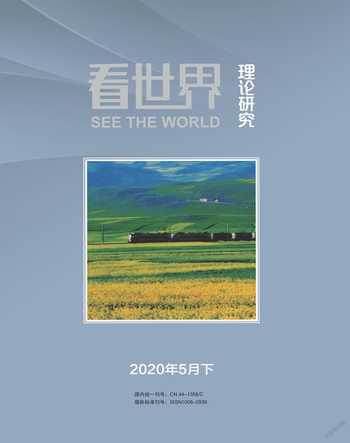第一人稱紀錄片的敘事與真實性建構
摘要:第一人稱紀錄片通過切割社會生活,對其中某一角落中典型環(huán)境、典型群體的情感進行挖掘與再現(xiàn),得以傳達第一人稱的視角所帶來個體化的、立足于私人空間的獨屬于“我”這一概念的情緒傳遞。對社會生活切片化的闡釋使第一人稱紀錄片區(qū)別于傳統(tǒng)紀錄片,以其獨特的敘事風格,建構出真實的情境;通過對人物欲求的深入挖掘、人物處境的多維呈現(xiàn),實現(xiàn)創(chuàng)作者蘊藏于情境之中的個人化表達。
關鍵詞:敘事與主體呈遞;客觀事件的真實性還原;人物行動的真實性探索;人物欲求的真實性追問;不同社會之社會意識共性與差異的真實性挖掘
一、第一人稱紀錄片的敘事分析
影視范疇所謂的敘事本質上包含作品內容的呈遞及對作品內容進行二度創(chuàng)作的建構,前者即物質層面對所選對象、事件的還原或再現(xiàn),而后者則在感官層面對客觀的“內容”進行演繹和呈現(xiàn)。紀錄片在作為一種在大眾認知里內容與表達相對契合的影視范疇,對于被攝內容的呈現(xiàn)往往會將其置于相對閉合的敘事空間,以旁觀者抑或講述者的視角將鏡頭對準內容,進而呈現(xiàn)出拍攝者與內容雙方相對單向的交互。這種狀態(tài)在本質上是順應內容自在發(fā)展模式敘事邏輯。第一人稱紀錄片見之于其本身涵蓋的個人化因素,在敘事層面一定程度脫離對自在事物的呈現(xiàn),而傾向于通過影像敘事技巧,揭露內容所包含的自為的矛盾、沖突乃至社會性本質。“作為一種個人化的行為,一種獨立的思想行為,它恰恰是排斥任何的模式化 [1]”。非模式化的紀實手段與追求主題精確表達的創(chuàng)作訴求相結合,使第一人稱紀錄片慣于使用精巧的敘事模式,打破事件發(fā)酵的冗長時序,由此實現(xiàn)受眾對主題的理解與共情。
以紀錄片《艾滋病人小路》為例,影片記錄了患有艾滋病的小路的求醫(yī)之路。其由最初對治愈疾病充滿希望到最終為困境所打倒,這一過程中充斥著對創(chuàng)作者對現(xiàn)實的質詢——社會對敏感疾病群體的審視、高價醫(yī)療問題、絕境中的愛情與親情、欺騙與愚昧……絕望之人小路在其求醫(yī)的過程中,原有的對家庭的責任感、對親人的承諾、對生活的熱情逐漸被疾病所消解,治愈疾病的希望因高額的費用與社會的排擠而漸漸異化;寄托其生命欲望的載體被現(xiàn)實錯置為非科學的“奇跡”。最終,愚昧的欺騙順理成章的成為壓垮小路的最后一根稻草。
影片按照小路的病情發(fā)展時序,以幾次重大的病情轉折為節(jié)點,呈現(xiàn)其在不同病情階段的心態(tài)。與小路初識的部分主要表現(xiàn)其最初向上、充滿希望的心態(tài),同時也呈現(xiàn)以兩位跟拍記者為代表的大眾立場對艾滋病人的刻板印象及這一印象的重構;此后小路病情的加劇,收入不足以支撐治療,使整個事件進入潛在的發(fā)展階段,原本向上的心態(tài)開始瓦解,恐懼、焦慮逐漸顯露,其與記者間的交流模式也發(fā)生了潛在的改變;當小路開始對按部就班的治療失去信心,試圖嘗試新藥并期許奇跡,最終卻以失敗告終,這一過程成為小路心理絕望的前夜;絕望之際,當小路提出要求記者陪同其去艾滋病關懷中心而遭到的拒絕,社會層面對艾滋病患者的偏見再次傷害了小路,此處成為其情緒爆發(fā)的節(jié)點,對自我、社會、醫(yī)療等因素的懷疑激發(fā)了其與記者的沖突;最終絕望且心灰意冷的小路選擇相信江湖“神醫(yī)”,在被欺騙的悲劇中死去。整個影片的敘事順序按照正向的事件發(fā)展順序,在不同時期展現(xiàn)當事人小路所面臨的困境與困境中的選擇,而小路與記者之間產生的交互通過事后采訪的形式實現(xiàn)敘議結合,以高維話語權對事件的評析達成對第一人稱內容的補證。
整個影片在拍攝與被攝層面本應界限分明的立場被打破,作為拍攝立場的記者涂俏、陳遠忠介入到小路的生活,會與之對話、寬慰,陪同其就醫(yī),乃至與其發(fā)生沖突,兩位記者在小路事件中所給出的信息相互映照,甚至有時相互矛盾——拍攝立場原本冷峻的、毫無傾向性且代表著理性中立的視角全然被打破,兩位記者本身作為事件的敘述者,常常會表達出恐懼、同情抑或憎惡等情緒。在這一過程中,影片的敘事空間并不拘于事件本體,而被加入了更多的話語、更多的聲音。敘事層面的外延同時推進著影片主題的擴張,拍攝者立場對當事人經(jīng)歷事件的參與,在一定程度上將整個事件所涉及的敘事范疇進行了進一步切分,拍攝者作為內容的呈遞一方,既代表事件的觀察立場,與此同時,亦代表著社會中大多數(shù)對艾滋病患者群體缺乏了解,帶有負面刻板的群體立場,群體立場與小路的個人立場之間的沖突,在敘事層面起到引申矛盾的作用,小路的“被傷害”并不止于單純的不被接納,同樣在于其因自身的敏感特質而在社會語境下卑處一隅。這部分深層價值的呈遞,實則便是通過第一人稱化的敘事對小范圍矛盾進行放大,在更高維度上通過敘事激引主題。
二、第一人稱紀錄片的真實性建構分析
第一人稱紀錄片相對于其它紀錄片類型,更注重個體化、個性化的價值表達,在價值傳輸與表達的過程中,抽象概念的價值與客觀概念上現(xiàn)實發(fā)生的事件之間產生連結,因而對于影片客觀真實性的建構更為必要,第一人稱紀錄片的真實性建構不僅在于對事件所進行的真實性還原,更指代對影片價值傳播噪聲的削弱——其整體的真實性,實則立足于客觀與主觀兩個層面的真實意義。“真實”在影像化的語境下一定程度上指代情境主義范疇的真實,其見之于被人為建構出的視聽空間,通過對從客觀世界獲得的影像進行結構而建立的表意情境。
“原生態(tài)的私密經(jīng)歷和體驗被看作是對于我們的生活的復雜性和缺乏連貫性的一種平衡 [2] ”。對復雜多變的生活進行的切片觀察,對規(guī)則社會中個體不馴順的自由意志進行的探索反思,絕大多數(shù)第一人稱紀錄片(除卻一部分以兜售痛苦、自由、私人經(jīng)歷等為商品價值的紀錄片)傾向于作為一種背離消費主義的,更強調個體真實思想的對真實社會的刻錄而存在。對客觀事件的真實性還原、人物行動的真實性探索、人物欲求的真實性追問、不同社會之社會意識共性與差異的真實性挖掘……第一人稱紀錄片通過視聽、敘事等元素致力于建構世界最為真實的存在狀態(tài)。
影片《尋找薇薇安· 邁爾》與影片《尋找小糖人》在內容特質上有著一定的共性,對有著多元評價、多重身份的話題性人物所進行的尋訪,以尋訪的過程為視角落點,在尋訪的過程中,基于不同人對主體的評述,探尋為相關人物所影響的社會意識、社會文化。以上兩部電影的聚焦點除卻對涉及主體本身的探討,亦包含著對涉及主體所在時期社會文化的撿拾、某一特定時期人們交往行為、話語模式的認知。對于影片內容外延的載體——無論是薇薇安·邁爾抑或羅德里格斯而言,將其從過去時空抽離,而置于當前時空的認知模式之下進行評價,本質上有著一定程度上不在場的“缺席審判”意味,故而,兩部影片在過往相關事件的表述上盡可能含蓄而克制,不同人對主體的評價,互相映照,勾勒出想象空間內的人物畫像,以《尋找小糖人》為例,大眾對歌手羅德里格斯的想象、民間流傳的其吊詭的自殺之謎……..無數(shù)的話語搭建出羅德里格斯神秘的剪影,而當想象空間中的影像與現(xiàn)實空間內本人的客觀狀態(tài)相重合時,原本交揉錯雜的刻板印象便得以被真實所消解,進而顯露出社會文化差異這一現(xiàn)實本質。第一人稱紀錄片的真實性建構,其一定程度上來源于充分調動各個層面的話語體系對單一事實的映照,進而與客觀維度形成對照,自此達成對影片內核的抽離分析。
參考文獻:
[1]沈倩.淺析吳文光“個人化”視角的建立——以紀錄片《流浪北京》為例[ J ].傳播力研究,2018,2(08):47
[2]孫紅云.公開的隱私:第一人稱紀錄片[ J ].電影藝術.2010
作者簡介:
宋昱明(1999—),男,山東濟南人,中國傳媒大學本科生,專業(yè):廣播電視編導(文藝編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