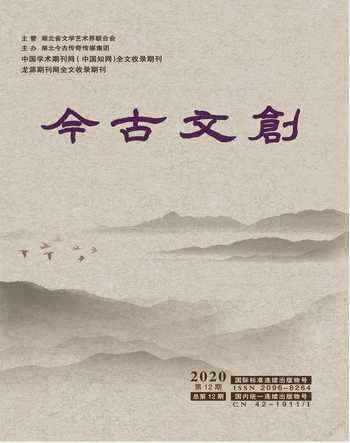廢名新詩探索之路

作者簡介
張吉兵,男,湖北蘄春人,教授,黃岡師范學院文學院教師,《黃岡師范學院學報》副主編,校學術委員會委員,鄂東文學研究所所長,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廢名研究方面,發(fā)表10多篇論文,出版專著兩部:《抗戰(zhàn)時期廢名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廢名研究札記》(臺北秀威資訊,2009年)。
【摘要】 廢名以創(chuàng)作“《嘗試集》派”白話新詩步入新文學詩壇,在新詩發(fā)展的背景下對何為新詩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tǒng)的思考探索,形成獨特的新詩觀,詩作風格面貌發(fā)生變化,創(chuàng)作出“廢名風”現代派詩歌。1931年是廢名詩歌風格、面貌發(fā)生新質改變的時期。
【關鍵詞】 廢名;新詩;現代派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12-0004-05
廢名詩是新詩中的觀念詩,觀照的是宇宙世界、生命、藝術、人生、生死、愛情、友情等這些一般性的命題,表達了流連而不執(zhí)著于人生的生命姿態(tài)。
一、1931年是廢名新詩創(chuàng)作的令人關注的節(jié)點
(一)三十而立與新詩創(chuàng)作
1931年是廢名的而立之年。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這是一個具有特殊意味的時間節(jié)點。不知是不是巧合,這一年也確實是廢名人生和文學創(chuàng)作發(fā)生轉折性變化的年份。
11月,廢名終于心想事成得到北京大學教職,成為講師。稱得起三十而立。
廢名1922年考入北大預科,本科進入英國文學系學習,留學英國回來的陳通伯(西瀅)、葉公超是他的老師,1929年7月畢業(yè)。經周作人推薦,得到聘任,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任教,講授散文寫作、現代文藝等課程。
文學事業(yè)上,由小說創(chuàng)作轉向現代詩寫作。
廢名在武昌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接受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影響,開始新文學創(chuàng)作,①并慕名給周作人寫信,將習作寄給周作人,得到周作人的肯定和指導。廢名是周作人的得意門生,他們的淵源開始于此時。②后來廢名考入北大,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很快嶄露頭角,作品發(fā)表于胡適編輯的《努力》周報③、魯迅編輯的《莽原》④、周作人編輯的《語絲》⑤等著名期刊,陸續(xù)出版小說集《竹林的故事》(1925)《桃園》(1928)《棗》(1931),長篇小說《橋(上卷)》(1932)《莫須有先生傳》(1932),成為一個具有自己鮮明創(chuàng)作風格的作家。兩部長篇小說出版于1932年,事實上寫作于1931年之前,其中《橋》的大部分章節(jié)以《無題》發(fā)表于《語絲》,《莫須有先生傳》的大部分章節(jié)發(fā)表于1930年廢名自己編輯的《駱駝草》周刊。可以說,至1931年,廢名寫完了他一生主要的小說作品。
1931年,廢名大寫其詩。這一年的兩頭他都并不在北平。一 二月廢名來到青島,試圖在青島大學謀得一學期教職,在青島呆到暑假,因為他對青島感覺很好,最終沒有如愿,于是三月初返回北平。下半年,重九(10月19日)過后,為了好友梁遇春的文集《淚與笑》南下上海尋找出版社出版,期間獲知到北大任教一事已成,年底回到北平。
廢名大寫其詩是三月初從青島返回北平以后,尤其是三月和五月。他自述:“那時是民國二十年,我忽然寫了許多詩,送給朋友們看。” ⑥他常常是一天內寫成好多首。僅三月一個月就成詩80余首,五月,又成40首。
廢名自述:“我于今年三月成詩集曰《天馬》,計詩八十余首,姑分三輯,內除第一輯末二首與第二輯第一首系去年舊作,其余俱是一時之所成:今年五月成《鏡》,計詩四十首。現在因方便之故,將此兩集合而刊之,唯《天馬》較原來刪去了幾首,所刪的有幾首是第三輯里的散文詩,以不并在這里為好。方其成功《天馬》時,曾作一序略略述及我對于新詩的意見,余之友人多見及之,茲則棄之,我想那意見或者是對的,然而我偶爾作詩,何曾立意到什么詩壇上去,那實在是一時的高興而寫了幾句枝葉話罷了。及其寫完《鏡》,我更覺得我尚有‘志’可言似的,那個志其實就庶幾乎無言之志。今日別無話要說,只是勉強這樣地想,惟人類有紀念之事,所以茫茫大塊,生者不忘死,尚憑一抔之土去想象,其平生無一面緣者直為過路之人而已,是曰墳;藝術則又給不相識者以一點認識,所謂旦暮遇之,斯道不廢,下余不可以已者殆沒有。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十七日,廢名記。” ⑦
廢名自述中提到的《天馬》《鏡》兩部詩集并沒有真正出版,編定的初稿本今天也無從尋得,但其中部分詩作留下了。
(二)現代詩
廢名1931年的詩是現代主義性質的詩。
其實,廢名最早發(fā)表的新文學作品是詩歌。1922年10月8日出版的《努力》周報第23期刊載有兩首新詩《冬夜》《小孩》,署名馮文炳。是為廢名處女作。接下來10年間,廢名以小說創(chuàng)作成為“京派”著名作家,但廢名也同時有新詩創(chuàng)作和發(fā)表。這時廢名的新詩可以稱之為“《嘗試集》派”新詩。
廢名遵循胡適白話詩理論創(chuàng)作新詩,卻又感受到胡適理論的局限性,陷入迷茫。
“我那時對于新詩很有興趣,我總朦朧的感覺著新詩前面的光明,然而朝著詩壇一望,左顧不是,右顧也不是。這個時候,我大約對于新詩以前的中國詩文學很有所懂得了,有一天我又偶然寫得一首新詩,我乃大有所觸發(fā),我發(fā)現了一個界線,如果要做新詩,一定要這個詩是詩的內容,而寫這個詩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 ⑧
引文中的“那時”指的是他沿著胡適道路行走之際。“有一天我又偶然寫得一首新詩”中具體詩作現在不可能考證了,但不應該是一首胡適體即“《嘗試集》派”的新詩,而是廢名風的新詩,那么就應該至遲是1931年3月的時候,從這時起,廢名新詩詩風大變,我稱之為廢名風新詩,也就是現代主義詩。
新詩濫觴于白話文運動,隨著新詩的發(fā)展,很多人都在探索新詩發(fā)展的道路。胡適提倡文學改良之際,他的白話詩理論“話怎么說,詩怎么寫”,得到廣泛認同,此后,則沒有任何一種理論、主張能夠“一統(tǒng)天下”“領袖群倫”。新詩理論、創(chuàng)作呈現多元化局面。這是新詩發(fā)展、繁榮的表現。這種情景,用廢名的話說,很多人都在那里“摸索”,都在那里“納悶”,像新月派這類與西洋文學稍微接近的人摸索到西洋詩里頭去,冰心模仿泰戈爾的小詩,等等,不一而足。⑨廢名也是新詩發(fā)展道理探索者之一。從廢名談新詩的論述看,他對新詩發(fā)展的動態(tài)是密切關注,并有著全面、準確的認識了解的。但他又并不認同、趨向哪一家。他的心中有個新詩雛形。只是還不是十分明晰,正如尚不足月的孕育中的胎兒。經過全面深入考察各家新詩人為建構新詩所做的探索,并且從新詩以前的詩文學的更宏闊的背景上加以觀照,同時融合自己新詩創(chuàng)作體驗,經過這些努力,廢名終于獲得關于新詩的理性直觀,建立了新詩格式塔。即“新詩應該是自由詩”。⑩所謂“自由”,指向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內容上,表現當下時代、現實給詩人的感受、體驗,此即“詩的內容”,杜甫的盛唐氣象,李商隱的晚唐色彩,對他們的詩來說是“詩的內容”,如果原封不動拿到現在,則是鸚鵡學舌的“腔調”。廢名對“詩的內容”的闡發(fā)賦予了新詩“現代性”特質。形式的自由就是“散文的文字”,也就是胡適所說的“話怎么說,詩怎么寫”,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
廢名因一些詩作發(fā)表于施蟄存編輯的大型文學刊物《現代》,以及卞之琳編輯的《水星》,而被“命名”為“現代派”,而事實上,從審美屬性上看,他的詩確鑿的是現代詩。他這個“現代派”不是“誤讀”。1931年廢名確立其“現代派”詩人之前,新詩壇現代主義詩潮已蓄勢、涌動,李金發(fā)以新怪的詩風引人矚目,北大名教授葉公超傾力介紹英國象征主義詩歌。然而現代派詩歌本身就是個多元化的存在,不同于創(chuàng)造社、新月派、“左聯”具有相對一致的理論主張;臺灣現代派詩人痖弦將廢名與李金發(fā)對舉,稱二人“先后輝映”,?然而廢名與李金發(fā)的差異決不小于與其他任何詩人,如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李金發(fā)、葉公超的象征主義是直接移植于法國、英國,廢名的“現代”性則是根植于他對于佛學唯識論“悟道”后的創(chuàng)發(fā)。
二、“廢名風”新詩是廢名“悟理證道”的方式
(一)廢名的“悟理證道”
廢名完成《橋》《莫須有先生傳》的創(chuàng)作后,興趣轉移到“悟道”方面去了。這是朱光潛說的。他在談論廢名寫作《橋》的過程時說:“他近來的興趣已逐漸由文藝創(chuàng)作轉變到他自己所認為更重要的悟理證道一方面去……” ?這段話寫于1937年,實際上是“追敘”,所敘是1931年前后的廢名。
1933年,朱光潛結束八年的留學生活回國,住在地安門里的慈慧殿三號,發(fā)起并組織“讀詩會”,至1937年7月止。“讀詩會”每月舉行一至兩次,其目的是研究新詩應該怎么做,研究“誦詩”的藝術。廢名是“讀詩會”的常客。參加過“讀詩會”的沈從文記敘過這件事。
“這個集會在北平后門慈慧殿三號朱光潛先生家中按時舉行,參加的人實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馮至、孫大雨、羅念生、周作人、葉公超、廢名、卞之琳、何其芳諸先生,清華有朱光潛、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華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熙良先生等等。這些人或曾在讀詩會上做過有關于詩的談話,或者曾把新詩、舊詩、外國詩當眾誦過、讀過、說過、哼過。大家興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詩在誦讀上,究竟有無成功可能?新詩在誦讀上已經得到多少成功?新詩究竟能否誦讀?差不多集所有北方新詩作者和關心者于一處,這個集會可以說是極難得的。” ?
19世紀80年代中期,法國象征主義大詩人馬拉美在他巴黎羅馬街寓所舉行“星期二茶話會”,影響巨大,逐漸成為象征主義文學運動的中心。馬拉美經常在聚會上闡發(fā)他“純詩”的詩歌理論。不知朱光潛發(fā)起“讀詩會”是否是效法馬拉美。又,上文提到卞之琳等編輯《水星》,是具有鮮明現代主義風格的詩歌期刊,巧合的是19世紀90年代,也就是馬拉美詩名鼎盛,成為各國詩人朝見的偶像之際,法國象征主義文學的機關刊物刊名就是《法國水星》——原名《北斗星》? (或《七星》),1890年改名為《法國水星》。?插敘這兩則象征主義詩歌史上的故實,與本文論題或許有關聯,也或許沒有。
由朱光潛這篇評論《橋》的敘述文字看,他對廢名創(chuàng)作動態(tài)和心理狀態(tài)非常了解。因此,朱光潛說廢名的興趣轉移到“悟道”方面,是信史。
廢名自己曾多次敘說他1930年前后研習佛學的情況:
“熊先生(熊十力——引者注)最初在北京大學將唯識,屢勸我學佛,其時我則攻西洋文學,能在莎士比亞塞萬提斯的創(chuàng)造里發(fā)現我自己,自以為不可一世,學什么佛呢?……民國十九年以后,我能讀佛書,龍樹《中論》于此時讀之,較《智度論》讀之為先,讀《智度論》時則已讀《涅槃經》,已真能信有佛矣……” ?
廢名自述更印證了朱光潛所言不虛。
(二)悟理證道與創(chuàng)作現代詩的重合
廢名悟理證道與創(chuàng)作現代詩在時間上是重合的,重合于1931年。這不是偶然,二者之間存在內在聯系。作家的敘述方式就是他的感受方式。正是悟道啟發(fā)廢名創(chuàng)發(fā)了其獨特的抒發(fā)方式。也因此,同為現代詩,廢名與李金發(fā),以及后來的穆旦,等等,有根本性差別。當他寫作胡適體新詩之際,他有迷茫,朦朧感覺到前面的光明,卻又找不到明確的道路;到他修習佛學中觀論、唯識論——他并不是為了新詩發(fā)展道理而修習佛學,竟然曲徑通幽,豁然開朗,走出了一條新路。當然,是一條窄路、僻路,長期只有廢名自己一個人走,但正如朱光潛所說,這也恰是它的可貴之處。
三、作為觀念詩的廢名詩
(一)“禪家與道人的風味” ?
朱光潛1933年7月結束8年的留德生活回來,進入清華大學任教,這時候廢名的文學創(chuàng)作基本上已告結束。但是朱光潛非常欣賞廢名的作品,他對廢名創(chuàng)作動態(tài)和心理狀態(tài)非常了解,只有非常關注關心對方才能做到這樣。朱光潛見證了廢名的現代詩創(chuàng)作,他從而成為廢名的知音、解人。他是第一個對廢名詩做出肯定評價、高度評價、深刻透徹評價的評論家。他的觀點今天還有影響。朱光潛評論廢名詩最有代表性的一段話轉引如下:
“廢名先生的詩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后,你也許要驚嘆它真好。有些詩可以從文字本身去了解,有些詩非先了解作者不可。廢名先生富敏感而好苦思,有禪家與道人的風味。他的詩有一個深玄的背景,難懂的是這背景。他自己說,他生平只做三首好詩,一首是《文學季刊》發(fā)表的《掐花》,一首是在《新詩》月刊發(fā)表的《飛塵》,再一首就是本期發(fā)表的《宇宙的衣裳》。希望讀者不要輕易放過。無疑地,廢名所走的是一條窄路,但是每人都各走各的窄路,結果必有許多新奇的發(fā)現。最怕的是大家都走上同一條窄路。” ?
劉半農曾留下對廢名詩的看法:“廢名即馮文炳,有短詩數首,(按:指《亞當》《海》《掐花》《妝臺》和《壁》五首),無一首可解,而此人為知堂所賞識,殊不可解。” ?劉半農的意見有一定的代表性,卞之琳、艾青都與劉半農相若。這是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在志趣相投的好友圈子里,大家互相品評新作,賞心樂事,他的詩也成為品鑒對象,受到過推崇,但沒有留下具有建設性意義的見解。而朱光潛作為一個美學大家、文藝評論家,他的批評就顯得尤其難能可貴。
朱光潛所說“有禪家與道人的風味”,寬泛地說,“禪家”與“道人”泛指佛家,然而朱光潛沒有料到的是,今天的研究者把“禪家”理解為“禪學”“禪宗”,進而從這兒出發(fā)去解讀廢名詩。其實根據廢名實際,他與禪學、禪宗沒有任何關系,他修習的古印度大乘空宗的學說,即提婆《百論》,龍樹《中論》,并據此而悟唯識論。
(二)“真能信有佛矣” ?
這所謂“佛”不是如來、菩薩等佛教偶像,而是指佛學,“信”不是世俗相信佛法靈驗法力廣大有求必應的迷信心理。“信有佛”即服膺佛教思想學說,又主要是古印度大乘空宗著名思想家提婆、龍樹的思想學說,以及唯識論種子觀。1920年代,熊十力翁在北京大學講唯識論,廢名與之交游,熊翁屢勸廢名學佛學,并與之談論種子論,廢名當時正沉醉于文學世界,對熊翁的教誨不以為然,但“種子”論還是給他留下印象。1930年,廢名竟真的研習佛學了,他集中閱讀了多種佛學經典,其中提婆的《百論》、龍樹的《中論》則是給他打下基本的深厚佛學學養(yǎng)根底的著作。這時,先前熊翁給他灌輸的“種子”論也激活了,他依據《百論》《中論》對種子說做出自己的穎悟。也就是說,廢名的唯識觀不是承續(xù)從玄奘窺基至熊十力的中國法相唯識宗的法系,而是他竟然仿佛重走古印度從空宗中觀學派進至瑜伽行派的思想歷程,契得圣人之同心!當然這其中熊翁的啟迪有著無法估量的意義。
具體來說,就是(一)認同識(種子)是世界萬有(相)的本源,內識生起外相,這是唯識觀;(二)外相假有真空,是非是非虛的,這是中觀論。
這即是廢名“觀念詩”的核心“觀念”。它一方面構成廢名詩的內容,更主要的方面是構成廢名觀照方式,和藝術表現方式。
所謂構成廢名詩的內容有兩重含義,一重是說與他此前的小說相比,超越性地拓展了藝術表現的境界,把宇宙世界、生命、人生、藝術等納入視野;另一重是一些詩寫的就是唯識觀、中觀論的觀念。
廢名的觀照方式是直探“識”體,從事物、現象形成的本體、本源,解釋、表現事物、現象;而不是從表象出發(fā),層層深入抵達本質。
廢名詩最主要的藝術表現方法就是“示現”。建構具有映現特質的意象,如夢、鏡、燈、日、月、池水,等等,通過特定意象示現,生成境相世界,特定意象與境相世界共同構成詩境,其中,具有映現特質的特定意象是“識”的譬擬,境相為“識”“示現”而有。
(三)“我的詩是天然的……”
廢名詩觀念的意味濃郁。廢名自己對此有認識,他說:“詩是應該訴之于感官的,我的詩太沒有世間的色與香了。這是世人說它難懂之故。” ?但廢名詩卻又克服了一般觀念詩沒有詩味的審美缺陷。觀念詩之所以常被詬病藝術性不足,是因為一般觀念詩往往是運用理性思維觀照事物,詩作帶有主觀認識的色彩或觀念化的痕跡,觀念大于形象,統(tǒng)攝形象,形象是扁平的,是一種點綴,比喻、類比、象征等本質上是為理性認知思維所支配的修辭,而不是詩性運思。廢名的觀念詩,甚至從積極的意義上說,融貫于詩中的觀念使廢名詩更富于完足感,正如他所說:“他們(卞之琳、林庚、馮至等)的詩都寫得很好,我是萬不能及的,但我的詩也有他們所不能及的地方,即我的詩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個的不是零星的,不寫而還是詩的……就詩的完全性說,任何人的詩都不及它。” ?其所以如此,個中奧妙值得深入探究。廢名觀念詩訴諸我們審美接受的是某種境界,境界呈現為整體觀照,具有審美意味。
注釋:
①廢名自述:“大約是民國六七年的時候,我在武昌第一師范學校里念書,有一天我們新來了一位國文教師(按:指劉賾),我們只知道他是從北京大學畢業(yè)回來的,又知道他是黃季剛的弟子,別的什么都不知道,至于什么叫做新文學什么叫做舊文學,那時北京大學已經有了新文學這么一回事,更是不知道了,這位新來的教師第一次上課堂,我們眼巴巴地望著他,他卻以一個咄咄怪事的神氣,拿了粉筆首先向黑板上寫‘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給我們看,意若曰,‘你們看,這是什么話!現在居然有大學教員做這樣的詩!提倡新文學!’他接著又向黑板上寫著‘胡適’兩個字,告訴我們《蝴蝶》便是這個人做的。我記得我當時只感受到這位教師一個‘不屑于’的神氣,別的沒有什么感覺,對于‘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沒有好感,亦沒有惡感,不覺得這件事情好玩,亦不覺得可笑,倒是覺得‘胡適’這個名字起得很新鮮罷了。”(《廢名講詩》,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頁。)
②周作人述:“在他來北京之前,我早已接到他的幾封信,其時當然只是簡單的叫馮文炳,在武昌當小學教師,現在原信存在故紙堆中,日記查找也很費事,所以時日難以確知,不過推想起來這大概總是民九民十之交吧……”(周作人:《懷廢名》,《談新詩》,第111頁。)
③廢名第一部小說集《竹林的故事》中的作品主要發(fā)表于《努力》周刊,少數幾篇,該刊不久停刊后,發(fā)表于其他刊物,或入集前未曾發(fā)表。
④短篇小說《河上柳》載《莽原》周刊第3期,1925年5月8日出版,后收入《竹林的故事》。
⑤長篇小說《橋》始以《無題》名分章節(jié)陸續(xù)發(fā)表于《語絲》周刊不同期數上。
⑥《廢名講詩》,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頁。
⑦《廢名講詩》,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頁。
⑧ 《廢名講詩》,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頁。
⑨《廢名講詩》,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頁。
⑩《廢名講詩》,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頁。
?(臺灣)痖弦:《禪趣詩人廢名》,原刊于《創(chuàng)世紀》(詩雜志)1966年1月第23期,這里轉引自《廢名詩集》轉載的同題文章。《廢名詩集》,陳建軍,馮思純編訂,(臺灣)新視野2007年出版。
?《橋》,《文學雜志》1937年7月1日第1卷第3期。
?《談朗誦詩(一點歷史的回溯)》、《沈從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51頁。
?袁可嘉:《象征主義(上)》,《外國文學研究》1985年第3期,第90-97頁。
?廢名:《阿賴耶識論》,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頁。
?朱光潛:《文學雜志·編輯后記》,《文學雜志》,1937年6月1日,第一卷,第二期。
?同?。
?(《劉半農日記》,《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1期)。
?同?。
?《廢名講詩》,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頁。
?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