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王圣教序》的歷史意義與藝術特征
——以《尊右軍以翼圣教》專著為中心
(意)畢 羅(Pietro De Laurentis)
《集王圣教序》是一幅書法愛好者非常熟悉的書法作品。無論是大書店還是小攤位,只要有書法字帖,基本上都會有一本《集王圣教序》。我相信,就書圣王羲之(303—361)的作品而言,除了《蘭亭序》以外,恐怕最受書法愛好者歡迎的一幅就是《集王圣教序》。特別是學習行書的人,總會有一天都要關注《集王圣教序》。主要的原因是《集王圣教序》的字比任何王羲之作品的字還要多。
一般書法愛好者都知道弘福寺僧人懷仁(7 世紀下半葉在世)用王羲之行書字形拼貼了648 年夏天太宗李世民(599—649)《圣教序》和當時尚未登基的皇太子——高宗李治(625—683)撰寫的《述圣記》,還附上著名的《心經》。顯然,這不僅僅是跟佛教有關的石碑,也是跟唐代政壇關系非常密切的文物。不過,筆者認為,雖然《集王圣教序》是一幅赫赫有名的作品,大部分愛好者都臨過不知道幾遍,一般人不但對它的文本內容未必有充分的了解,而且對它的歷史含義也不是非常清楚。我們看待書法作品或整個書法史的時候,雖然表面上還可以停留在字面上的審美欣賞層次,但是也不要以為所看到的這些作品也只有字面美觀這個層次了。《蘭亭序》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大家比較熟悉它的內容,心目中一定對王羲之、蘭亭以及對當時參加曲水流觴的士大夫會有一個形象,并不會覺得《蘭亭序》只有它的字好看而已。顯然,在某種程度上,任何書法作品都是其書寫時代的一面鏡子,要么屬于文學、檔案、個人記錄和宗教這四大類內容。但是,一旦認可書法作品是更廣的一種文化背景的產物,為了更準確地了解和理解它們,我們必須把這些書法作品與其他的文化產物聯系起來。筆者認為,《集王圣教序》說不定就是歷史上這種“文化網絡”緊密相關聯的最典型一個例子。
俞豐先生《經典碑帖釋文譯注》和王玉池先生《古代碑帖譯注》是兩部講解書法作品文本內容的工具書,在書法界和文史界已相當受歡迎,書本都一直在重印。[1]這一現象證明,書法作品的文本內容對書法愛好者準確理解、欣賞和研究書法史非常關鍵。任何書法作品——再好看的書法作品也不例外——都是某人記錄一定文本的載體。即便書寫者起初的出發點是寫一幅漂亮的字,或多或少,所記錄的文本和當時的文化和社會環境有著一定的關聯。王羲之現存的若干“帖”原來是他當時的人際網絡的一個部分反映,因此,當
《集王圣教序》是筆者近幾年的主要研究課題。經過若干年的文獻梳理和實地考察,筆者對它的書法特質和歷史含義做了系統的研究,終于發表了一部《尊右軍以翼圣教》的漢語專著[2]和三篇漢語的學術論文,并且準備明年在德國出一部英文專著。[3]在本篇論文中,筆者以剛剛問世的拙著為中心,對《集王圣教序》的基本情況作出綜合的介紹。
一、《集王圣教序》碑石和碑文的基本情況
通稱《集王圣教序》是一方碑,按照考古學學術規范應該把它叫“《集王圣教序》碑”,但是因為一般所指的不是碑本身而是歷代碑上拓下來的拓本和拓片,實際上碑石載體的《集王圣教序》不如平面紙張的《集王圣教序》有名。盡管如此,為了真正了解作為書法作品的《集王圣教序》我們絕對不可以忽略作為文物的《集王圣教序》的方方面面問題。
《集王圣教序》碑現藏著名的西安碑林博物館,雖然現在安放地點與原來的地點尚有一定的距離,從立碑年代到現在一直沒離開過西安。全碑是399 cm x 127 cm,只有碑身碑陽帶有文字和七個小佛像(圖1)。西安碑林存放著3000多方刻石,而《集王圣教序》是其中的一方國寶級的石碑,已經不允許再打拓片。

圖1 《集王圣教序》碑陽
絕大多數提及《集王圣教序》立碑年代的論文,根據《集王圣教序》的題記有這樣的提法:“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八日。”據筆者所知,只有翻譯玄奘(卒于664 年)傳記《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德國學者Alexander Mayer 才把具體日期從中歷轉換成西歷,結果是673 年1 月1 日。[4]雖然咸亨三年確實大部分相當于西歷672 年,[5]表面上看并不是嚴重的遺漏,但是從歷史研究的方法來看,某件事在年底還是在年末發生對了解這件事的真相還能提供重要的證據。
據考證,《集王圣教序》進今天西安碑林前身的西安府文廟也不晚于12 世紀中期。[6]在此之前的將近500 年期間,《集王圣教序》最早立于挨著長安宮城的弘福寺,在當時長安的修德坊內,相當于今天西安市的蓮湖區。弘福寺705 年改名興福寺,845 年武宗李炎(814—846)滅佛時寺廟被廢,846 年6 月2 日繼位的皇帝,即宣宗李忱(797—859),又恢復了16 座寺院,其中沒有位于修德坊的興福寺,可是有位于鄰接安定坊的千福寺,結果在846—847 年間《集王圣教序》就移到了千福寺。[7]因此,基于《集王圣教序》作為王羲之書法傳統的典型作品,很可能是因為北宋文人喜愛書法導致原石從千福寺(北宋時叫興元寺)或其他安放的地點轉移到文廟中,或許也考慮到經營拓片買賣的需要。
《集王圣教序》一共30 行字,1903 字。1957 年著名的日本學者中田勇次郎在《書道全集》提出1904 個字總數的說法以后,好像學術界普遍認可中田氏的說法。[8]因為準確的數目是1903 個字,這意味著學者們都沒有一個字一個字地分析過此碑的實際內容。[9]筆者提出數字的準確性并不帶有任何學究氣。書法作品與其他藝術品非常關鍵的區別在于,書法是以漢字為基本單位的藝術,反而我們在繪畫等雕塑創作中都無法找出類似的基本單位。也就是說,凡是書法作品所謂的風格、筆意等描寫審美趣味的單詞,都必須基于其作品的具體單字情況。筆者從2015 年中期一直到2017 年年底將現存王羲之行書草書的摹本、《集王圣教序》、以及唐代其他最有代表性的集字碑《興福寺斷截碑》(721 年)和《新集金剛經》(832 年)的單字都剪出,并且把重復字歸入在一起,終于得知王羲之行書字庫的基本狀況。結果是,雖然《新集金剛經》是字數最多的一方石碑(5264 個比1903 個),其實就單字而言不如《集王圣教序》多(717個比755 個)。通過這種電腦處理圖片的方式才可以系統地比較王羲之的作品,把它們的常見的和不常見的字形統計起來之后,才能有效地講出筆法、結構等具體形態和技法問題。當筆者在二十幾年前向文字學專家田樹生先生請教古代漢語時,他就說:“漢語必須一字一個字地讀和翻譯,不準大概。”過了幾年以后筆者開始研究書法作品,果然悟到了田先生那天講的真理。
《集王圣教序》除了收錄唐太宗給玄奘翻譯佛經的序言《圣教序》和唐高宗為父親序言寫的《述圣記》以外,還收錄了赫赫有名的佛教經典《心經》和太宗和高宗給玄奘致謝書信的兩封答復,加上立碑題記想為如下的內容:
1)《大唐三藏圣教序》題名,29 個字(第1-2 行);
2)《圣教序》正文,781 個字(第3-12 行);
3)太宗給玄奘致謝答復,63 個字(第13 行);
4)《述圣記》題名,10 個字(第14 行) ;
5)《述圣記》正文,579 字(第15-22 行);
6)高宗給玄奘致謝答復,61 個字(第23 行);
7)《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題名(加以玄奘詔譯提及),15 個字(第24 行);
8)《心經》正文,265 個字(篇末重題簡寫題名),(第25-28 行);
9)佛經翻譯潤色官員姓名,68 個字(第29 行);
10)題記,32 個字(第30 行)。
唐太宗撰寫的《圣教序》一文,其根本意義在于贊揚玄奘和佛教,[10]《心經》又是非常流行的一篇佛經,顯然這方碑的政教色彩非常濃。因此,我們要精確地了解這方碑的始末,必須關注當時佛教與宮廷的關系。
二、《集王圣教序》的歷史含義
《集王圣教序》碑在673 年1 月1 日立于弘福寺時,《圣教序》《述圣記》和《心經》已經刊于石刻。《圣教序》和《述圣記》刻成石碑,在《集王圣教序》前有過三次。第一次是長安大慈恩寺大雁塔竣工,褚遂良(596—658)書丹的兩方對稱的石碑,右側的《圣教序》于653 年11 月10 日完成(永徽四年十月十五日),左側的《述圣記》于654 年1 月3 日完成(永徽四年十二月十日),即所謂的《雁塔圣教序》(今兩座碑石尚在原處)。第二次是王行滿(生卒年不詳)書丹的《大唐二帝圣教序碑》,在658 年1 月24 日立于偃師招提寺(現藏偃師商城博物館)(圖2)。第三次是所謂的《同州圣教序》,663 年8 月3 日(龍朔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立于同州,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有學者提出它是重刻了《雁塔圣教序》的字,至少是非常熟悉這方碑書法風格的高手所作。關于《心經》的編譯過程,說法不一,不過目前中外學者支持《心經》的梵文本其實是玄奘從漢文翻譯過來的,原文就是漢語。從文獻角度來看,目前只能肯定佛教文獻記載《心經》是玄奘649 年7 月8 日(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翻譯的,而其最早的全文記錄是楊社生(生卒年不詳)661 年3 月3 日在房山云居寺(在今北京市房山區)敬造的一件石刻(圖3)。[11]
那么,既然當時長安和洛陽寺院已有刊刻《圣教序》和《述圣記》的石碑,為什么673 年1 月1 日又要立一方呢?一般學者認為立《集王圣教序》的念頭,與《雁塔圣教序》《大唐二帝圣教序碑》和《同洲圣教序》三方石刻相比實際上是最早的,在撰寫兩篇文章后不久就啟動了,但是因為其工程既復雜又費時,用了二十幾年時間才完成。這是北宋文人周越在11 世紀中葉最早提到的觀點,[12]一直延續到清朝金石學家王昶(1724—1806)。[13]筆者認為,所謂的“25 年之說”不可信。從當時收藏王羲之真跡的情況來看,雖然我們不能排斥民間甚至寺院還藏有幾件王羲之書法原作或摹本,必須承認絕大多數自己都藏在宮廷里面。因此,兩文《圣教序》《述圣記》刻成石碑是一件相當隆重的事情,不難發現一定需要通過皇帝的認可。所以,一旦宮廷允許懷仁查閱宮廷書法作品或者還愿意借出所需的幾件,一定是明確要求這項工程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完成,不可能耽誤25 年之久。筆者通過對唐代若干文獻的梳理找出了關于復制書法藏品和刊刻石碑的數據,并且說明了建立像《集王圣教序》如此碑石的工作進度不會太緩慢。[14]
因此,筆者認為《集王圣教序》的立碑念頭比唐太宗撰寫《圣教序》的648 年更靠近最終立碑的673 年1 月1 日。顯然,這兩個年代相差這么長時間的原因并不是這方碑的實現計劃有多大的難度,而跟640 年代末和670 年代初不同的歷史背景有關。
為了準確理解《集王圣教序》的文化含義應該把它放入當時佛教經典的抄寫和流布大環境里面。首先,648 年夏天完成的《圣教序》和《述圣記》只有在唐太宗逝世5 年以后才立了《雁塔圣教序》。佛教史料表明,只要符合玄奘的宣教的需要,他還會主動請求皇帝立碑,所以他648 年并沒有立即促成《圣教序》和《述圣記》刻成碑是有一定原因的。[15]玄奘648 年夏天剛獲得《圣教序》和《述圣記》的時候所需要的并不是把這兩篇文章刻立成碑,而是通過宮廷的力量把它們夾在抄寫他翻譯的佛經的寫本之中,這樣才會對佛教在整個大唐帝國鞏固它的政治地位起最有效的作用。幸虧,當時帶有《圣教序》和《述圣記》的寫本尚見于現存敦煌文獻之中,[16]這表明皇帝兩篇文章確實附在佛經漢文寫本之首,并且由國家行政機構負責流布到各個地區。這無疑是648 年玄奘最關心的一個實際效果。
可是在唐高宗649 年即位以后宮廷對佛教的支持越來越少,皇帝本來也只是因為父親的命令才敷衍寫了《述圣記》,可以說不僅僅對佛教沒有太大興趣,而且對玄奘并沒有像他父親那樣的熱情。另外,高宗明顯重視道教,因此,在整個650—660 年代里,曾經受到宮廷推崇的長安佛教僧團不得不發現皇帝的喜愛明顯轉到與他們有著激烈的競爭關系的道教團體。[17]
道宣在661 年編寫了《古今佛道論衡》,確實證明當時佛、道之間存在著深深的矛盾。劉餗8 世紀中葉撰寫的《隋唐嘉話》中,保留了一則特別有意思的記載,是提到6 世紀初,南方著名畫家張僧繇所畫的《醉僧圖》,有道士用來諷刺僧人,結果是僧人“聚錢數十萬”請閻立本(卒于673 年)作《醉道士圖》。[18]我們不知道這種記載是否可信,不過可以肯定在8 世紀中葉佛、道之間的關系應該有極大的沖突。同時,這篇記載還表明僧人為了反駁道教的攻擊毫不吝惜金錢。筆者認為,這點與《集王圣教序》的立碑情景有一定的關系。
在這種不利的情況下,僧人會采取何等措施呢?《圣教序》和《述圣記》畢竟是李世民和李治撰寫的文章,是皇帝贊賞佛教的最顯赫的象征,對僧侶來講一定有可用之處。可是重新把它們刻成碑還不夠新穎,僧人當時首先需要強調兩位皇帝與佛教和玄奘的關系。對長安僧侶來說,648—649 年宮廷與佛教的默契才是理想的相處模式,因此他們在設想立碑款式又加了兩封答復的書信,刻于碑上公布于世,足以證明李世民和李治對佛教的重視程度和對玄奘本人的尊重。而最初宮廷把玄奘安排在弘福寺翻譯佛經,那刊刻《集王圣教序》的地點應該就是在弘福寺。其他相關的記載,像“貞觀廿二年八月三日內出”和“潤色”官員的出現僅僅是為了強調宮廷、官方對佛教的支持,這在道教影響越來越大的660 年代和670 年代具有很大的意義。
于是,即便唐高宗反對佛教,他不好拒絕僧人提出用他和他父親喜愛的王羲之的字來“抄寫”他和他去親自己寫的文章的要求。用王羲之的字來拼貼皇帝的文章,實際上并不是迎合唐高宗的樂趣。王羲之一方面是唐朝崇拜的“書圣”,另一方面他是道教信徒。筆者認為當時長安佛教僧團一定考慮到用《集王圣教序》可以讓王羲之脫去他道教的身份為佛教抄寫皇帝文章和佛經的《心經》。[19]
三、《集王圣教序》的藝術價值
筆者認為,只有從上述的歷史背景才能精確理解《集王圣教序》如此復雜的立碑過程。一旦我們考慮到當時對佛教趨勢不利的背景,不難發現對懷仁等僧人來說,立這方碑是一項要命的工程,它的意義不在于書法本身而是用書法來維護佛法。因此它的出發點并不是保護和繼承王羲之的書法,正好相反,它是利用王羲之來獲取自己利益的一種“佛教藝術品”。那么,雖然佛教美術是中國藝術史非常重要的領域,但是基本上它以繪畫和石刻造像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很少關注書法作品。《集王圣教序》正好是佛教美術利用最高端的書法境界——王羲之的字形——來達到與其他佛教藝術手段相似的目標。為了充分地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了解書寫對佛教的一些基本情況。
其一,對中國流行的大乘佛教來說,佛經的抄寫是一件能夠做出功德(梵文gua)的活動。可是,在不太重視書寫的印度文化,大乘佛教雖然也重視抄寫的活動,但是往往不如中國“漢字帝國”那么重要。所以,當大乘佛教進入中國的東漢末年的時候,中國不但已經有好幾百年的抄寫書籍和檔案的傳統,而且在2 世紀初也剛剛興起了獨特的書法藝術。因此,中國文人信徒一旦接觸了這種以功德造福為目標的抄寫活動——我們可以推測——當然與印度信徒心理感受截然不同,同時也發現了抄經在審美上的龐大發揮余地。[20]
我們看待《集王圣教序》一定需要考慮這些特殊的文化背景才能理解它的書法價值所在。于是,對當時佛教信徒來說,佛經并不是一般應該尊重的正規文本而已,實際上它是必須崇拜的佛法載體。因此,在當時濃厚的佛教信仰的社會里,具體負責抄寫某經的人不僅僅是復制佛經文本的人員而已,書寫者也是直接參與造福功德的活動,何況由王羲之書圣來抄寫《心經》以及附于其前面的《圣教序》和《述圣記》!換句話說,當時觀看《集王圣教序》或其拓片的佛教徒跟我們今天的人看它有精神上的極大區別。對佛教僧團來說,集王羲之的字等于是讓召喚王羲之“復活”來書寫佛教經典。所以,雖然《集王圣教序》是一項集字拼貼工程,但是它效果與真人自然書寫非常像。我認為,《集王圣教序》的集字并不是在保護和復制王羲之字庫里面的字形,其實它主要需要通過王羲之的不同字形和書寫風格——在保持整體風格的條件下——表現出一個在世活人在書寫的視覺效果。
筆者也對《集王圣教序》字形問題做了總體研究,包括對不同拓本的比較,得出東京三井紀念美術館藏劉鐵云本是最能夠表現原來石碑刻字的審美一件拓本(圖4)。另外,筆者根據文獻的記載也設想了懷仁如何搜集、設計和調整《集王圣教序》文本內容的字形的工作步驟。[21]通過對現存作品中的字形的比較,筆者還探索了《集王圣教序》字形的來源,得出的結果是大部分字形來自當今現存以外的作品。由于沒有保存下來我們無法看到這些作品面貌,但是從褚遂良編的《右軍書目》和張彥遠《右軍書記》等文獻可知,[22]7 世紀中葉因為唐太宗酷愛王羲之作品而收藏的王羲之真跡——其中未必都是王羲之原作,毫無疑問也包括大量后人的臨本——就行書而言,應該有一萬字左右,這與我們今天能看到的不滿1000 個字的王羲之行書作品相比,確實是個完全不同的情況。也就是說,當時可查的宮廷王羲之真跡藏品有的是,懷仁要選字并不存在非常要緊的缺字問題。筆者認為最典型的例子是赫赫有名“永和九年”的“永”字。《集王圣教序》有兩個字形一樣的“永”字(第12 行第11 個字和第16 行第55 個字),但是都不是《蘭亭序》的“永”。顯然,雖然《集王圣教序》“天”字、“群”字、“趣”字等字形都是與《蘭亭序》的字形非常相似,但是《蘭亭序》這赫赫有名的作品的開頭第一個字,懷仁并沒有收進去,這無疑是這個“永”字的字形不符合他對碑石的整體審美效果(圖5)。[23]因此,《集王圣教序》是一幅總結初唐對王羲之行書字形的作品,一方面保留了好多早就無法看得到的字形,另一方面表現了初唐人對王羲之書法的理解。就是因為唐太宗在貞觀年間搜集了大量六朝流傳下來的真跡,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出這個結論:《集王圣教序》是一件總結整個以王羲之為中心的六朝書法傳統的作品。《集王圣教序》問世以后,唐宋時期還出現了二十幾方王羲之集字碑,但是因為從8 世紀開始宮廷收藏品受到了極大的損失,大部分初唐尚能看到的王羲之真跡卻都遺失了。因此,盡管《集王圣教序》并不能作為王羲之書法原貌的直接再現,但是無疑是窺見王羲之書法的寶藏。

圖4 劉鐵云本《集王圣教序》

圖5 永-《蘭亭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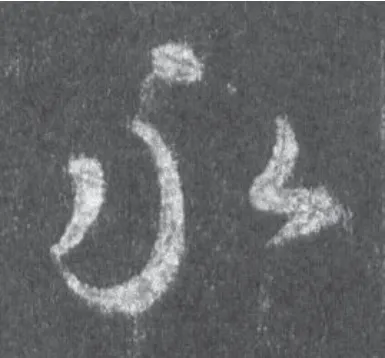
圖5 永-《集王圣教序》
最后,從《集王圣教序》這方背景錯綜復雜的石碑還可以看出古代書法與當時社會各個階層的緊密關系,充分表明任何藝術現象除了內在的藝術含量以外,首先是一項文化現象,具有一定的時代性、社會性和特殊性。這也是書法史能夠讓我們更準確了解中國古代文明的極大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