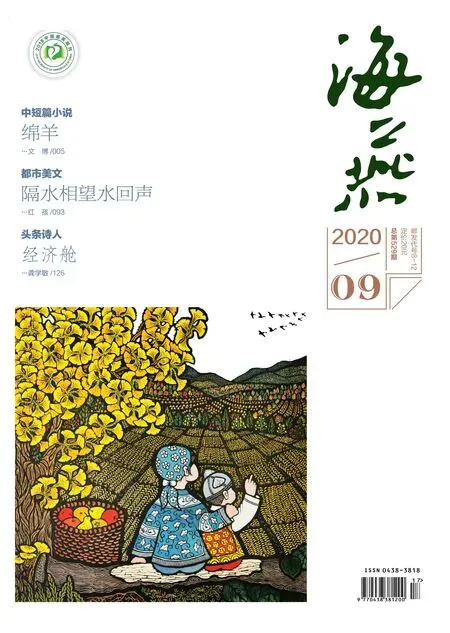經濟艙
龔學敏
在柳州柳宗元衣冠冢前讀《江雪》
一出聲
我才知道曠世的孤寂被你釘在此處。
飛絕的紙鳥,我只是撕了個小口
面具們便紛紛轉世。草地在跑調
從唐朝奔跑到此時的雪
已經覆蓋不了他們卑微。
我不想讀第二句
受傷的山巒和藥店,比比皆是。
在南京西善橋讀乾隆《新林浦》
乾隆用筆把江山攬了一攬
譯成白話的風,被江上鐵船的紐扣絆住
跌了教科書那么遠,起身
已然忘記自己就是時間。
西善橋把一條大江女人樣的腰
隨手一緊,江鷗成為萬里河山的叫聲。
牛首山像是硌在歷史被窩里的一句
慢性病,詩歌的處方再好
雪花當真是浩蕩的鵝毛
也比不過一陣陣遲鈍的鐘聲,手術刀
一樣,成為歷史。
趁著夜色,我把詩歌趕緊合上
大地用古墓的耳朵偷聽時間的秘密。
出租車把行人下在金陵,建康,江寧
農田里長熟的高樓,一轉眼
和我一起被江風吹得遍體鱗傷。
甘蔗甜得低頭
鴨子們朝著高處曲頸
紙越新鮮,越不可相信,如同機器
生產的字,像是贗品。
在西善橋,更多的人像地名一樣誠實
像江水一樣,知曉一首詩可以走得那么
遙遠。
題武功山古祭臺
不要輕易與這些石頭說話,它們是風
的根,聚集在此,時間才沒被刮走。
不要輕易與這些風說話,它們是石頭
伸出的枝,是時間的化身,是白鷴。
眾草靜穆,風在目送遠去的云朵
而儺戲是神靈降臨時,遺贈給我們的
花朵,一年開一季。
在天水訪東柯草堂
出租車的秦腔車禍了現在唐詩的
十字路口
勒死槐樹的柳家河,用村名
鋪成肥腴的斑馬線
唐朝在高速公路的筆畫中
成為一條河的服務區。
教科書在洋芋中
與磷肥一同起床。
發涼的月亮咳出茅草的血跡
試紙在化驗餓瘦的詩
能否懷孕
用蜀葵納涼的杜甫,在風中
取鹽。螞蟻把字鋪成
床單
釘死在鸚鵡跌落的舌影上。
影子越來越瘦。豐滿的墻上
寄居著駛進唐朝的卡車。
瘦地翻宜粟
陽坡可種瓜。
在西安雁塔南路吃油潑辣子面
塔影的面湯一直添到九寨溝,一碗
一碗地,養活洋芋疙瘩中的戲文
河水把辣味切細,在遠處爬山
譯過的風一吹,萬壑似魚
世俗在塔頂上抽刀。
海碗中的秦腔
被滾油逼到高處,掠過玄奘的法號。
啤酒打白馬夜行,來世幾兩面?
經書雕成銅像,氣喘吁吁的梵文
在翻譯剩下的水深。
身著便衣的飛機在渭水邊乘涼
龍王被海碗的魚餌
渴死在黃土的切面刀上。
風鎖住時間,在琵琶上練習潛逃
名何需見經傳,只是味道
整個西域旱在弦上,大雁讀經
把唳聲一群群鋪開成水
女人們用衣衫遠去。
一片吃面的葉子,被雁塔豐腴
起來,直到面一樣地慢慢老去。
梓潼七曲山大廟文昌星祖庭遇雨
想要成為星宿的人,掉下來
成了雨滴。
在梓潼,拖拉機的白發與天空隔壁
古柏的古字空洞
我把雨滴碼成古字的鄰居,天旱時
請他們從紙里出來,走走。
種下的書用雨滴的耳朵穿墻
柏,把一個朝代寫得沒落
再把人心寫偏一點,與古字不重。
烏鴉邊抽煙,邊清潔人們說話的路線
把柏油路卷成軸。
汽車喇叭聲的農藥,假裝給歷史除病害
壯膽。
雨落得越多,淋得柏的身子越沉
人們越是夠不著星宿。
內江梅家山成渝鐵路筑路民工紀念堂
青石上發芽的句子,長成最春天的
一瓣鐵路。
從成都到重慶,最后一段鐵軌
鋪在內江
一朵叫做民工紀念堂的梅花上。
照片的火車,黑白的年齡兌換成,煤
的重量,和姓氏。
汽笛把天空的虛空塞滿,麻雀
如同紙片,繪滿工業時代的門楣
直到這些名字的石子
踏實,像是沒來過。又如是朝陽。
1953年的十萬粒石子,團結成
一棵石頭的樹。
沱江毛體的水寫字
一棵鋼鐵的樹正在引領煤,鐵
米,鹽,和糖生長。
民工十萬次走過梅花
春天已然
紀念堂只需在梅家山紀念自己便是。
在云南澄江縣撫仙湖
攥成拳頭的藍,把神仙說話的口氣
捶成天空。
人世騎馬而過
恣意的馬鞭草一誤再誤,把來路
和歸途,一概抽打成路標中
油漆冬天的鷗,死給
在風中懷孕的孤島。
神仙在玉米地中發育
陽光里滾落的黃色南瓜,絆倒在
女人的邊疆。一碗粗糙的藍
用喝酒的方法,生兒育女。
單車死去三回,我才把一株女人
種活
不停梳頭的鐵皮船
用救生衣的頭皮屑一遍遍說謊,直到
夜幕三合。遺一合
像是天空下腹的細軟,說實話
而后,后世無人敢以霾為名。
宜賓李莊梁思成林徽因舊居
建筑,在即將成型的圖冊中相互指證
小青瓦的船,呵護番茄們的野心
和院落在秋日里饑餓的平衡。
在李莊,種植月亮的田壩像是紙上的
疤痕,揚子江蛻掉的皮
一節翠屏成船,泊在戰火中
重新長。一節,扶不起來
在橋下識一些被江水泡軟的字。
李莊的箭里趴著喘著柴油粗氣的
鐵船。地圖上浸濕的鋼盔
像是第一城正在萌動的羽毛。
哲學成為鳥分類的籬笆
長衫與江水互不往來,大詞們被種在
書中,槐的刨花一直呼吁廢除筆直
和雨水的膚淺。
隔壁的假照片,已經在田中長成荷花
淤泥中睡眠的李莊,開一次花
就被紀錄片在遠處轟炸一次,而后
沉穩一次
直到土豆一樣,在淀粉的
純白中,慢慢化渣,沉實。
陳子昂讀書臺
蜀地的口音把唐風逼到幽州,一只雁
噙著天空的幕布,給愴然取暖。
蟬鳴的刀,被夕陽妥協在秦嶺的酒色中
男人們用疼痛,平衡水稻和小麥
川腔攀巖而上
像群山綿綿不絕的狗,在空中
無處下口
寫詩的人,開始懷抱時間痛哭。
高速公路的耳朵聽見涕下還在涕
直到,在酒中傾城
在紙上,哭痛鉛筆的叢林中長出的國。
嵌在書中的鐘,摳出來,讀出一聲
朝代就茁壯一里
十聲過后,山河豐沛
唐詩即為鼎盛,為悠悠,為不見。
汽車和我,都是唐詩的路讀過的字
被拾遺種在陳年的讀書臺
鐘敲過的風中
前也不得
后又不敢。
在輞川王維手植銀杏處
薺菜茂盛成月光,被軍工的刀
一棵棵挖走,春天空懷秦腔。
土里的佛號用薺菜說話
餃子們修行,直到煮斷石上的清泉。
壓路機一刀刀地壓薄月光
高速路的面塊把辣子疊好,一車車
給老邁的蜀祛濕
松在高處吸煙
我用哪一棵的灰燼白了頭。
砌磚的農民給詩歌抹灰,保持水分
用來吸引烏鴉的巢
和欲言又止的春色。
捆住山水的高速路,用隧道咳嗽
老痰的汽車,潑墨
漢字破損,草頭隨薺菜涼拌
陪我飲素酒,醉一地的山川。
贗品的空氣在文件袋里閱讀銀杏樹的
標題。唐在蛻皮
我在唐過的河灘,賣農家樂的膏藥。
在邯鄲永年區廣武古城
把自己薦成一則成語
趴在城外的衣冠冢上,用《史記》的
一個噴嚏
毛遂在飛,昏鴉們布滿平原。
把鐘聲薦給鐘,用舊的姓氏,敲一次
塵埃就活一次
酥魚坐在城頭用醋施令
城池中潛伏的水,被店鋪的書法
聚攏在口音中。
壓塌弘濟橋的稻草和我飲酒,抬花桌。
在灌腸中說話的驢,把成語馱在天上
城池茂盛,天氣和磚的生長被預報在
生銹的縣衙。
致力于天空的香椿,用手勢給庭院施肥
大雁的太極把城墻揉軟。
成語身著水的新裝在石板路上騎自行車
我用散裝的柳絮給他們讓道
避開一滴叫做楊露蟬的水。
在宜興陽羨貢茶院遇雨
天上寫過茶字的雨,停在書拐彎的燈光處
看路,看一枚叫做宜興的茶葉,如何
把江南的高速公路伸到唐朝。
我是蜀水中制茶的魚,竹林的餌
像是書中疾行的月色。
圣旨一道,陽羨便生一片好茶,皇帝的
聲音,是所有茶的種子。
所有潛伏的湯色被我從縣志中活捉出來
一滴滴,用雨聲,打成一把老壺。
手機是我新種的茶,專醫眼鏡們瘋長的
無聊。陶色的網,把魚養在茶中
敲一些鐘聲,數到哪枚,那枚
便進門來,讓我讀完
貼在汽車的尾聲里,等著天亮。
茶葉在鋼鐵的屋檐上廣義
我把竹馬養在蜀報廢的筆畫中
把院落里所有男人的睡眠,泡軟
當做那盞陶制的燈
一直朝前走的草料。
在雁江臨江寺豆瓣廠
井從唐代的寺院中發芽,長到清朝
成一枚蠶豆,一瓣已經菩提
一瓣還在迦葉的手勢中發酵。
辣椒的紅繩把井系在臨江寺
空洞的地名上
坐在江邊的農業標簽,練習飛翔
被卡車印刷到指示牌的青春期里
在地名上種辣椒的人
拿豆瓣們發酵出來的高速公路擦汗。
白鷺被迦葉的樹蔭隔在缸
世俗的外面。
給一座手寫的寺院加鹽,加水,加香油
加一河的陽光,再添一船書寫過的月光
加早醒的木門剛開啟時的露,清晨
必是清朝的清。
最后,減去鹽,減去水,減去香油
減去陽光,月光,減去露,只留下
用臨江寺的地名,煮熟的一碗干飯。
在雁江蜀原廣場觀八段錦
把一條江最美的一段獻給大雁
— —題記
藍楹花把天空搬到低處,直到大雁的
舉止在八段錦中飲水,下棋
說江面打盹的是船只的年齡。
用八段錦說話的大雁,在資陽人
的洞中,打印3D的火苗。
樹是風的年齡。高鐵用第二節車廂
給年老的風打電話
大雁成為藥粒,醫治痛風的高樓。
大雁從地上長出的姿勢
結出話筒的種子
被觀光車載到風口處
一段貯藏資陽羽毛制成的秘籍,七段
隨風去,吐出的魚
掛在塔頂,晾曬鰓上的白發
和語錄的樹。大雁偶爾也棲。
給大雁施八段錦的肥料
一條江的經歷恰到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