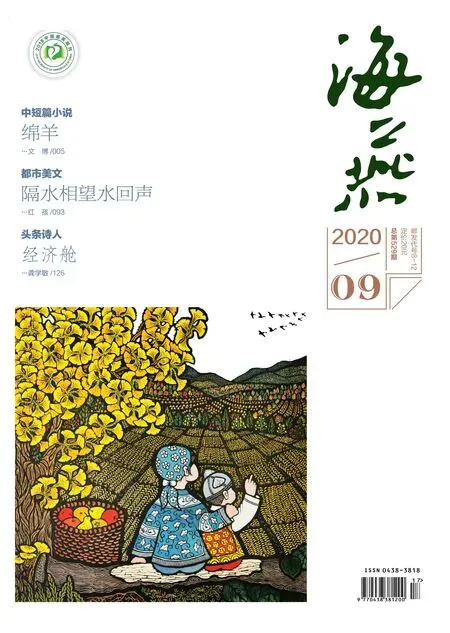讀詩記(三)
劉向東
生命本體最直接的感受
卡瓦菲斯,希臘詩人。讀其詩感受最深的是他的心靈與語言的最大限度和接近與無遮礙的狀態,是對詩的一種直接的到達。詩所表現的,是生命本體的最直接的感受,是說出來的心里要說的話,其中自然有經驗的成分,但卻不是常理的經驗、推理的經驗,而是一種精確的領域的擴張與再造,虛虛實實,真切而又縹緲,呈現一種靈魂的獨特的姿態與感悟。
埃利蒂斯稱:“另一個極點是卡瓦菲斯,他與艾略特并駕齊驅,從詩歌中消除所有華而不實的東西,達到結構簡練和詞語精確的完善境界。”
卡瓦菲斯的詩的不可模仿,其本質和神秘性,來自他的獨一無二的語調。語調之中似乎沒有具體的指向,只是一種懸浮的空間,一種無法兌現的可能。
詩人這獨特的語調,可能來源于其生存狀態,生命的悲觀。日子百無聊賴,“同樣的事情/在我們面前一次又一次發生,/同樣的時刻來了又去。/一個月過去了,另一個月又來,”“我能在哪里過得好些?下面是出賣皮肉的妓院;那邊是原諒罪犯的教堂;另一邊是供我們死亡的醫院。”
卡瓦菲斯還以一種獨特的視野來看世界,這種獨特的視野使得他無論用哪種方式來寫,都能把平凡的場面提升至哲學的高度,賦予不平凡的意義。
《墻》只寫一種精神的隔離,一點聲音也沒有,沒有筑墻的人,他們卻將自己與世界隔開,寫一種絕望的情緒:
沒有考慮,沒有憐憫,沒有羞恥,
他們已經在我的周圍筑起一道道墻,既高且厚。
此刻我坐在這里感到絕望。
我什么也不能想:這個命運啃著我的心——
因為在外面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做。
當他們在筑這些墻,我怎么會沒有注意到!
但我不曾聽見那些筑墻的人,一點聲音也沒有。
不知不覺地,他們已經把我與外面的世界隔離。
(黃燦然 譯)
《召喚陰影》只寫一種情調、氛圍:
一支蠟燭已經足夠。它的柔光
會更為合適,更為雅致,
當陰影降臨,愛情的陰影。
一支蠟燭已經足夠。今夜房里
光不能過多。在沉思冥想中,
全部是接納,并且,伴著這柔光——
在這沉思冥想中我將組織視力
召喚陰影,愛情的陰影。
(黃燦然 譯)
詩單純得只寫一支蠟燭所帶來的陰影,這種情調的需要,也是一種直接的述說。沒有委婉,沒有暗喻,明白如話卻充溢著一種朦朧的情境和獨有的心理狀態。
如此敏銳,如此憂傷,達到了如此簡捷的高度,遠遠超越了他的語言和他的時代。
你說:“我將去另一片土地,我將去另一片海洋。
另一個比這個城市還好的城市將被找到。
我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命運的一次判決;
而我的心靈——像一具尸體——被埋葬。
我的思想將在這片荒原上停留多久?
無論我把目光轉向何處,無論我可能會看何處,
我都在這里看見我的生活的黑色廢墟。
我在這里毀滅而荒廢地度過了那么多年。”
你不會找到新的土地,你不會找到別的海洋。
這個城市將跟隨你。你將漫游相同的
街道。你將在相同的鄰里變成老人;
你將在相同的房子里頭發灰白。
不要再抱任何希望——
沒有載渡你的船只,沒有道路。
正如你在這里的這個小小角落里
摧毀了你的生活,你在整個世界上毀滅了它。
《城市》
(喻楊、董繼平 譯)
卡瓦菲斯的《城市》是對現代城市生活經驗的高度概括。這首詩的前一節是“你”說的話,后一節是針對性的回答,這兩節詩暗暗地形成了一種潛在的對稱。
從第一節詩來看,“你”已經對這個城市產生了厭棄情緒,并認為它已經失去了改造的可能,因而試圖擺脫它,去找“另一個比這個城市還好的城市”。接下來的句子頗為警策,“我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命運的一次判決”,這表明,“我”的每一次努力能否成功將最終取決于命運的判決。命運讓“我”成功,無論誰也阻擋不住;命運讓“我”失敗,無論怎么努力也無濟于事。事實上,人與城市的恩怨未必是城市撩撥的結果,大多是由人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當一個人感覺失意時,它會無端地歸咎于他生活的城市,并天真地以為換個城市就能使問題得以輕松解決。
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不僅“你不會找到新的土地”,更要命的是,“這個城市將跟隨你”,從而使你所到之處一切照舊:“……你將漫游相同的/街道。你將在相同的鄰里變成老人;/你將在相同的房子里頭發灰白。”
實際上,千篇一律的城市并不具備轉換心境的作用。在這方面,它根本不具備自然造化的魅力。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城市固然都是雷同的,但它僅止于雷同,而人的心情卻會由于這種雷同而變得更糟,因為人常常借助變化來“改善”自己的生活。然而,當他發現這樣做全然于事無補之后,一個人將在所有不同的城市里看到“生活的黑色廢墟”。事實就是這樣,當人厭倦了一個城市之后,所有的城市都變得不宜居住。因為厭棄一個城市就意味著毀滅了在所有城市重新開始生活的可能性:“正如你在這里的這個小小角落里/摧毀了你的生活,你在整個世界上毀滅了它。”
從他位于市郊附近的村子
那小販來了,渾身上下
仍滿是旅塵。他“香油!”“樹膠!”
“最好的橄欖油!”“頭發香水!”
沿街叫個不停。但到處是喧囂、
音樂、游行,誰聽得見他?
人群推他,扯他,撞他。
他完全被弄糊涂了,他問,“這里發生什么事呀?”
有一個人也向他講那個宮廷大笑話:
安東尼在希臘打勝仗了。
《公元前31年在亞歷山大》
(黃燦然 譯)
通過一首詩,卡瓦菲斯把一個同樣不起眼的小販,置于一個重大歷史事件中。
許多人都知道一點安東尼的故事,喜歡卡瓦菲斯詩歌的人還可以從他的《安東尼的結局》《天神放棄安東尼》等詩知道這個故事(卡瓦菲斯總是善于從不同角度寫同一題材),但是安東尼“勝利”的消息傳來時,人們到底是怎樣反應的呢?卡瓦菲斯透過亞歷山大郊區一個小販進城來觀看這件事。值得注意的是臨結尾那兩行“有一個人也向他講那個宮廷大笑話:安東尼在希臘打勝仗了。”這里的“大笑話”,并不是指那個人真的向人講笑話,那個人是在高興地告訴他安東尼打勝仗了,自己并不知道這是個大笑話、大騙局,“大笑話”是從作者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的評論。這個句子是非常概括的,充滿挖苦,也是典型的卡瓦菲斯式寫法。
叫人上當的樸素
羅伯特·弗羅斯特是美國詩歌史上最受人們尊崇的詩人之一。即使在八十五歲高齡,弗羅斯特仍能用顫抖和模糊的聲音,充滿激情地誦讀自己的詩歌,仍然有成千上萬的聽眾聚集在他的身旁,聚精會神地聆聽并分享。就在他去世前不久,他還應邀在肯尼迪總統的就職典禮上朗誦詩作。
弗羅斯特詩歌的魅力在于它貌似自然、直接和簡單,而實際上并非如此。他曾說:“我是一個十分難以捉摸的人……當我想要講真話的時候,我的話往往最具有欺騙性。”在弗羅斯特看來,詩歌的最高價值在于其意義的“隱秘性”。
他的詩歌觀察敏銳、情感真切、語言簡潔,每每能夠變平淡無奇的思想為令人難忘的詩行。他生活在19世紀美國詩歌向20世紀現代主義詩歌過渡的時期,他的詩蘊含著一種意象派詩人稱之為“直接處理事物”的直接感。牛津大學教授、詩人羅伯特·格雷夫斯認為:“弗羅斯特是第一位真正可以用世界標準來衡量的美國著名詩人……他的詩歌創作沒有依托古老的歐洲詩歌傳統,也不靠模仿前人的成功之作,而是通過自己辛勤的實踐,直至最終找到了一條既適應‘美國氣候’又符合美國語言的詩歌創作之路。”
弗羅斯特的詩具有親切、自然的對話感和素描似的真實感,他將人們使用的活的話語變成了詩歌,在別的詩人筆下只能是日常瑣事的故事素材到了弗羅斯特的詩中都因為它們變得樸實無華、真摯生動而具有了普遍意義。
弗羅斯特說:“獨創性與首創精神是我對我們國家詩歌創作的希望。”但是,他不像大多數同時代詩人那樣為了表現新內容,而瘋狂地去追求種種新的形式。弗羅斯特認為獨創性并不意味著“詩歌可以不用標點符號……不用大寫字母……不要格律……不要意象……不要戲劇性的語氣……不要內容……”在《一首詩的形跡》中,弗羅斯特指出:“一首詩以喜悅開篇,以智慧作結。”在他看來,每一首詩歌都有其形象的運動軌跡:“它始于喜悅,喜歡情不自禁;隨著詩人寫下的第一行詩,它就有了方向,然后經歷了一連串幸運的事,最后澄清了生命。”這不僅是詩歌運動的形象軌跡,而且勾勒了他詩歌創作的思維和想象模式。弗羅斯特的想象經歷了從對自然的觀察到對觀察的沉思這樣一個過程。因此,“一首詩的形跡”始于對某一自然事物、自然景象或日常事件的觀察給人們帶來的“喜悅”,而終于觀察給人們帶來的對生命意義更加深刻理解的“智慧”。
“詩始于普通的隱喻、巧妙的隱喻和‘高雅’的隱喻,適合于我們所擁有的最深刻的思想。” 弗羅斯特說。
弗羅斯特堅信他的詩歌語言“簡單到了運用日常用語的程度……就連華茲華斯的語言也比我的更難。”他說:“我不喜歡故弄玄虛的晦澀,但卻非常喜歡我必須花時間去弄懂的微言大義。”他認為“只要用詞生動,作品就不會令人生厭”。雖然日常談話可能只要“八十個或一百個字眼”,但“字字都能提供有聲的意義”,字字都“有血管”“有生命”。《牧場》就是極好佐證:
我去清理牧場的水泉,
我只是把落葉撩干凈。
(可能要等泉水澄清)
不用太久的——你跟我來。
我還要到母牛身邊
把小牛犢抱來。它太小,
母牛舐一下都要跌倒,
不用太久的——你跟我來。
(趙毅衡 譯)
一看就明白,就有可能把他當成一首平平常常的鄉土詩放過去,事實上它風韻殊絕,無論是對美國詩歌,還是對弗羅斯特個人,都非常重要。
這首詩看似獨白,近乎自言自語。從結構上看,“我”和“水泉”(以及落葉、母牛、牛犢)是實的兩端,與“你”(指向虛的一端)形成了三角關系,三者之間微妙關聯:“我”是時間性的,是稍稍的蒼老,但是此刻,“我”的內心是何等的柔嫩;水泉、落葉、母牛和牛犢是寫實的,錯落的,給愛溫潤地撫摸著的;“你”,聆聽者。
詩很短,卻充滿豐富的戲劇性,語言平實卻內涵豐富,詩人運用隱喻的象征把讀者帶進了深邃的藝術空間。有的批評家把它看成詩人詩歌創作思想的具體體現,認為“落葉”象征著詩人要放棄十九世紀陳舊的詩歌創作手法,而掙扎著要自己站起來的牛犢似乎象征著詩人所追求的新的詩歌創作風格。
弗羅斯特對詩歌堅定的追求,使我們看到了一種本質的詩歌精神。他的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農場勞動,他干那些最具體、最粗重的農活,這可以從他很多詩中讀出來。他不是那種為文學史寫作的人,在形式上,他并不求新,但就是這種真實和淳樸,這種對時尚的不顧及,使得他的詩有占據更多時間的可能。
《停馬在雪夜的林邊》,也是弗羅斯特的名篇之一:
這是誰家的林子,我想我知道,
雖說他的農舍卻在村子那一頭;
他不會看到我停留在這兒,
望著他的林子積雪有多厚。
我那小馬一定會感到奇怪:
停留在這兒?又沒村舍在鄰近——
夾在一座森林和一片冰湖之間,
在這一年中最昏暗的黃昏。
他搖了搖胸前的掛鈴,
想問問到底有沒有弄錯。
此外只聽得一陣微風吹過,
和一陣鵝毛似的雪片卷過。
樹林真可愛,幽暗而深遠。
可是我還得趕赴一個約會,
還得趕好多里路才能安睡,
還得趕好多里路才能安睡。
(方平 譯)
樸實無華并不能說明弗羅斯特詩的風格。他的詩表面一目了然,但再讀就會覺出那是一種“叫人上當的樸素”。
這是一首表面平靜而內心焦灼的詩,如果只是讀出了一種平靜,那就有可能讀丟了這首詩的神髓。
不僅是弗羅斯特,每一個人的一生中總會有那種在岔路口猶豫的經歷。對愛或事業的猶豫,對生死的詢問,總要進入我們的生活。人生最關鍵、最不知所措、最宿命的時刻,常常就是在這些岔口上。這首詩,在你讀過幾遍后,對最后兩句中“安睡”這個詞,就會有所警覺。它并不僅僅是一個雪夜趕路人所向往的那種在溫暖房舍中的尋常睡眠,它暗示出了永遠的睡眠。
找到了這把鑰匙,我們來理解這首詩就容易些。林子和林子那頭的農舍,以及農舍中的“他”都會找到相應的暗示對象。那里也許就是天堂和神居住的地方,“他不會看到我停留在這兒/望著他的林子積雪有多厚”。弗羅斯特沒有把天堂想在高高的頭頂,也沒有把神想得必須仰望。他們就像是一個鄰居;生和死的距離大概就是要穿過一片林子,去串一個門的感覺。這樣的寫法,有著一種舉重若輕的效果。他把生死、天地神這樣大的問題當作最為日常的事件來寫了,這才是不動聲色的大氣魄。
關于“質樸”這一點,中國古詩中也有種理論——無一句是詩,無一句不是詩。弗羅斯特這樣的大師,把全部的心思放在對整首詩的詩意經營上去了,對表面形式感的句子反而回避。他可以使得整首詩的語言了無痕跡,不需要精彩,避免引人注意。但在一首詩總體的經營上卻是大下功夫,他要使詩不僅有情,更要有神。中國古代詩歌理論中也有“練詞不如練句,練句不如練意”之說。用這話來理解弗羅斯特的質樸應該更準確。
這樣的詩需要細讀、深讀、反復讀,乍讀,會被那種輕松感所籠罩,甚至輕松得有點活潑。比如那匹“小馬”,如果就真的把它想成是一匹馬,那勢必要對這首詩有所減弱。但它象征什么?有人說,多讀幾遍后,會覺出那是詩人的另一個自己,詩人的不安、焦灼都從小馬的問中表現出來了。“他搖了搖胸前的掛鈴,想問問到底有沒有弄錯。”這都是詩人的自問。詩人把焦灼埋得很深,甚至用了一種輕松來掩藏,這也是這首詩的魅力所在。猶如賈島的“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也是一首表面平靜的詩,但對后兩句你再深想時,就會覺出一種曠世的疑慮——它就在那兒,可你無法知道。這幾乎道出了我們面對這個世界時的惆悵。
弗羅斯特在這首詩中,表現了一個對生死的決斷過程,“樹林真可愛,幽暗而深遠。”我們能夠從反面讀出生活的艱辛來,同時我們也能讀出詩人對生的理解,對生的責任的理解。這使我們感到了這首詩中可貴的真實和積極。
《未選擇的路》是弗羅斯特特別具有象征意義的一首詩:
黃色的樹林里分出兩條路,
可惜我不能同時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佇立,
我向著一條路極目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叢林深處。
但我卻選了另外一條路,
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
顯得更誘人、更美麗;
雖然在這兩條小路上,
都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跡;
雖然那天清晨落葉滿地,
兩條路都未經腳印污染。
呵,留下一條路等改日再見!
但我知道路徑延綿無盡頭,
恐怕我難以再回返。
也許多少年后在某個地方,
我將輕聲嘆息把往事回顧:
一片樹林里分出兩條路,
而我選了人跡更少的一條,
從而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顧子欣 譯)
詩中的叢林無疑代表著人類自己的內心,而分出了兩條路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的選擇。當然不同的選擇肯定會有著不同的結果。
詩的起句把我們帶到一個充滿象征意味的情境,面對樹林里的兩條道路,意味著必須做出選擇。這個情境也讓我們聯想到但丁《神曲》的開頭:“就在我們人生旅程中途,我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之中醒悟過來,因為我在里面迷失了正確的道路。”
兩條路可供“我”自由選擇,暗示著“我”所面對的可能性和“我”選擇的主動性。然而,一旦選擇的行為發生,主動性將決定可能性的方向。
這兩條路有差別,但不是對立的,沒有引申出兩條路的好壞或選擇的對錯,選與不選都差不多,即使不做選擇也是一個答案。不像但丁詩中提及的,存在某種“正確道路”,弗羅斯特在這里只提示了客觀的可能性。
據說弗羅斯特在英國時,結識一批英國詩人,其中,愛德華·托馬斯成為他親密的朋友和他早期詩歌的權威闡釋者。弗羅斯特和托馬斯常常一起到林中散步,有一次在散步途中,托馬斯懊悔沒有走另一條路,好讓他的美國朋友見識某種稀有植物或某處美景。就此,佛羅斯特寫了這首詩,不過,當弗羅斯特將這首詩寄給托馬斯時,托馬斯卻沒有看出來。
在弗羅斯特的諸多杰作中,最讓人難以捉摸和富有戲劇性的,要數這首《家葬》了:
他從樓梯下向上看見了她,
在她看見他之前。她開始下樓梯,
卻又回頭望向一個可怕的東西。
她猶豫地邁出一步,卻收住了腳,
她又站高了些,再一次地張望。
他一邊說一邊向她走來:“你看見了什么,
總在上面張望?——我倒是想知道。”
她轉過身來,癱坐在裙子上,
她的表情從害怕變成了呆滯。
他搶時間說道:“你看見了什么?”
他向上爬,直到她蜷縮在他的腳下。
“我要答案——你得告訴我,親愛的。”
她獨自站著,拒絕給他幫助,
稍稍梗了梗脖子,保持沉默。
她讓他看,但她確信他看不見,
瞎眼的家伙,他根本看不見。
但最后他低聲說了“哦”,又說了聲“哦”。
“那是什么?是什么?”她說。
“是我看見的東西。”
“你沒看到,”她挑戰道,“告訴我那是什么。”
“奇怪的是,我沒有馬上看見。
我以前從未在這里注意到它。
我大概是看習慣它了——就是這個原因。
這小小的墓地埋著我們的親人!
真小,從這窗框中可以看見它的全貌。
它還沒有一間臥室大呢,不是嗎?
那里有三塊青石和一塊大理石,
還有寬肩膀的小石板躺在陽光下,
在山坡上。我們對這些不必介意。
但是我知道:那不是一些石頭,
而是孩子的墳墓——”
“不,不,不,不,”她哭喊著。
她向后退縮,從他擱在扶手上的胳膊下
退縮出來,然后滑下樓去。
她用令人膽怯的目光直盯著他,
他連說兩遍才明白自己的意思:
“難道男人就不能提他死去的孩子?”
“你不能!——哦,我的帽子呢?
哦,我并不需要它!我要出門。我要透口氣。
我不知道哪個男人有這個權利。”
“艾米!這個時候別去別人那里。
聽我說。我不會下樓的。”
他坐下來,用兩個拳頭托著腮。
“有件事我想問問你,親愛的。”
“你才不知該如何問。”
“那你就幫幫我。”
她伸手推動門閂作為全部回答。
“我的話好像總是讓你討厭。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么樣的話
能讓你開心。但是你可以教我,
我想。我得說我不明白該怎么做。
一個男人得部分放棄做個男人,
面對女人。我們可以達成協議,
我發誓往后決不去碰一碰
你講明了你會介意的任何東西。
雖然我并不喜歡愛人之間這樣行事。
不愛的人缺了這些無法生活在一起。
相愛的人有了這些倒無法相守。”
她稍稍移動了門閂。“不——別走。
這一次別再去跟別人說了。
跟我說吧,只要是心里的東西。
讓我分擔你的痛苦。我與其他人
沒什么兩樣,可你卻站在那里,
離我遠遠的。給我一個機會。
我覺得,你也稍稍過分了一點。
是什么使你老是想不開呢?
一個母親失去了第一個孩子,
就永遠痛苦——即使在愛情面前?
你認為這樣才是對他的懷念——”
“你在嘲笑我!”
“我沒有,我沒有!
你讓我生氣。我要下到你那里去。
上帝啊,這女人!到了這個地步,
一個男人不能提他死去的孩子。”
“你就是不能,你根本不懂怎樣提起。
如果你也有感情,你怎么能
親手去挖他的小墳;怎么能?
我從那個窗口看見你在那里,
見你揚起沙土,揚向空中。
揚啊揚,就像這樣,土輕輕地
滾回來,落在坑邊的土堆上。
我想,那男人是誰?我不知是你。
我走下樓梯,又爬上樓梯去,
再看一遍,見你還在揮鍬揚土。
然后你進來了。我聽見你的低音
在廚房外響起,我不知道為什么,
但我走過去,要親眼看一看,
你正坐在那兒,鞋上污跡斑斑,
那是你孩子墳墓上的新泥,
然后你又講起你那些瑣碎事情。
你把鐵鍬靠在外面的墻壁上,
就在門口,我也看見了。”
“我想笑,笑出有生以來最苦的笑。
我真苦!上帝,我真不信我的苦命。”
“我能重復你那時說的每一個字:
‘三個多霧的早晨和一個陰雨天,
建得最好的柵欄也會爛掉。’
想一想,這個時候還這樣談話!
一根樺木腐爛需要多長時間,
這與昏暗客廳里的東西有什么關系?
你根本不在乎!親友們可以
陪伴任何一個人共赴黃泉路,但卻言行不一如斯,
他們還是不要陪的好。
不,當一個人要死的時候,
他孤獨,他死的時候更孤獨。
朋友們假裝都來到他的墓地,
可棺木尚未入土,他們的想法已變,
想他們如何返回自己的生活,
和活人一起,辦他們熟悉的事情。
世界邪惡。如果我能改變世界,
我就不會這么悲傷。唉,如果,如果!”
“瞧,你說出來了,你會好受些的。
你現在不會走了。你在哭。關上門!
你的心已飛走,身體何必還要追隨?
艾米!大路上走來了一個人!”
“你——哦,你認為我說說就了事了。
我要走,離開這個家。我怎能讓你——”
“你——敢!”她把門開得更大了。
“你要去哪里?先得告訴我。
我會跟著你,把你拉回來。我會的!”
(劉文飛譯)
這是一首杰出的詩篇,也是一部杰出的電影腳本,圍繞一對夫妻關于他們的已經夭折的被掩埋了的孩子的心理活動和對話,把整個舞臺壓縮在一個樓梯和一個窗口。第一行詩向我們介紹了“演員”的位置以及他們所扮演的角色。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幾個連續的鏡頭。“她開始下樓梯”是一個畫面,“卻又回頭望向一個可怕的東西”是另一個畫面,這也是一個特寫鏡頭,一個側面像——呈現她的面部表情。“她猶豫地邁出一步,卻收住了腳”是第三個畫面,也是又一個特寫——腳部的特寫,直到她“站高了些,再一次地張望”,這是第四個特寫,一個全身的特寫。后面還有很多,“她轉過身來,癱坐在裙子上,”后面緊跟著一個特寫,“她的表情從害怕變成了呆滯。”
透過窗口,她看見了他沒看見的東西,而他不知道或假裝不知道她看見了什么。
他們的每一句話幾乎都在繞圈子。她不愿正面面對。“東西”,她將自己死去的孩子說成是“東西”,而不是“人”,她把小小的墳墓說成“昏暗客廳”。他說怎么就到了這個地步,一個男人就不能提他死去的孩子?她說你不能,你知道為什么你不能,你根本就不知道怎樣提起!
在一個吸引人的故事線索下,許多人都會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誘惑,將其視為一出關于人與人之間無法溝通的悲劇,一首關于語言之無能的詩。可是情況可能正相反,在這里,詩人所探求的是悲傷與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