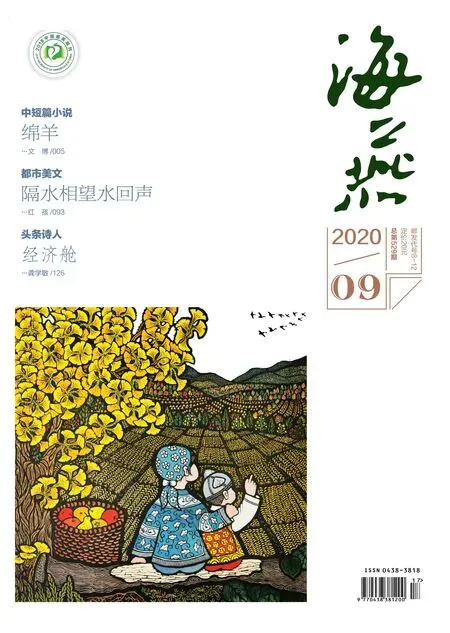“做客”壟上堂(外一篇)
李 成

大約是上個世紀80年代,我到家鄉桐城的著名詩人陳所巨先生家拜訪。不記得是在他家的客廳抑或書房的墻壁間,看到掛有一幅中堂,畫的是古干遒枝的老梅,著上了點點白花,兩邊還有對聯:“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那字當然也寫得古樸典雅,一派大家風范。我看見其落款“唐大笠”,乃記起在《安徽文學》上讀過他的散文,印象里他是一位很有古典文學修養的作家。我很欽慕陳所巨老師能得到老杜對李白一般的贊許。后來我又一次去陳所巨先生那里,再見到這件書畫,仍止不住凝視久之,心里有了一點了解唐先生的愿望,便問他在何處高就。陳先生答:“他還在安慶。”此前我大概也已知唐先生是在離我家鄉不遠的安慶工作(但不知在什么部門),說真話,我覺得安慶城的分量都因此在我心中重了許多。
此后,我從各種途徑的“風絲雨片”得知,唐先生是有名的畫家,曾師從書畫大師林散之先生,便不再驚異他的詩文功底不凡(我不懂畫,不好評價唐先生的畫)。他的散文從古雅當中透出新氣息,入情入理,雋永有味,我是很愛讀的,可惜的是我視野有限,所見不多,難以魘足。沒想到,我因近期喜好在舊書網上搜書,無意間,竟有一冊標明“唐大笠著”的《壟上堂散集》跳入眼簾,不禁為之一喜,連忙下單訂購。不幾日,書在我翹首以盼中送到,我便忙不迭地閱讀起來,而且是逐篇逐句讀完的。這些篇什,都是三十年前的作品了,但是,我仍覺得像是新近才來到“壟上堂”做了一次客,不僅聽了一番主人的娓娓傾談,而且品嘗到了主人從壟頭山野采來的山蔬野果,暢飲到清澈甘冽的山泉,其心情是十分愉悅的。
我由此知道了唐先生的生平遭際,“我與書畫結緣,是遭受五十年代后期那場政治風暴襲擊之后的事”,也就是被錯劃為“右派”,失去了發表文章的資格(此前他在《安徽日報》當記者)不得已而改習繪事。始師時居合肥的著名畫僧懶悟,“隨后由已故陳雪塵教授的引薦,從1964年與散之老人開始了書信往來”。后成為林的入室弟子。這是唐一生的關鍵,得到了“真師”的教誨、指引,所以他在《真師林散之》一文中將此記述分明,而且飽含深情。在黯淡、苦難的歲月,文人友朋師弟間的交往有一種相濡以沫的色彩,讀來著實感人。文中這個細節是多么的令人感到溫暖:
(林老想先看看唐的作品,唐鼓足勇氣寄去了。)不數日,意外地收到林老的一封長信,給我鼓勵與指導,并附狂草婁山關詞一幅。再過幾天又收到山水橫卷《太湖紀游圖》,筆墨淋漓,蒼雄古秀。我當即送懶悟法師,懶師見之把玩不忍釋手,并風趣地開了一句玩笑:“此老當死矣!”問其故,答曰:“畫得這么好,還不該死么?”說完哈哈大笑,笑畢,令我珍藏起來。
文字的曲折有致,讀來真有一番“云破月來花弄影”之感慨。唐先生在文章中進一步回憶道:“這些年來,出入林老門下,每有請益,老人必諄諄教誨。除了動亂歲月特殊困難外,幾乎每年總要千方百計地尋找機會看望老人。每一次見面,老人必口傳手授,獲益良多;每一次見面,總是依依不舍地離去。”說來唐子何其有幸,在人生低谷,得遇這樣的良師。但“文革”大動亂中,林老連遭不幸,先是被車撞,后又不慎跌入浴池湯鍋,右手致殘。他還用僅剩的三指執筆畫畫,不久便給唐寄來一幅山水,上題“何事湯池去又還,死生早作夢中看,病回留得半殘手,來寫人間可愛山”。可見對晚輩的誼深情切。終于,師弟們守到云開日出之時,唐先生將歷年來林老送他的畫作裝裱成冊,帶去江上草堂林老家,老人重檢舊作,仿佛回憶往日行蹤,看得很認真。而同在現場的邵子退先生后來為這本特殊的寫生畫冊題跋,其中有“大笠攜來散之昔年為其所作山水小幀十四頁,邀予觀賞,展讀三四,未忍釋手,其用筆圓潤剛柔有力,不同于古人。所寫皆經歷游蹤,反映山川真面目,其筆墨在蹊徑之外”之句,詠讀再三,對藝術家們的“俊彩風流”嘆賞不置。
而唐大笠對懶悟和尚的記述,也讓我們得以銘記一代名畫僧的超逸性格與苦難命運。《人間懶和尚》中有一段文字,可看作他的精彩小傳——
懶悟,河南潢川人,自幼披剃于潢川遠鐸庵。壯游吳越,就讀于閩南僧學院。在杭州學畫,初畫粉蝶,繼習山水,間或寫梅。其時因得中國佛教會遴選東渡日本習法相,五年歸國,演教四方,頗獲禪林重望。1931年由滬溯江而上,擬周游祖國西南諸勝跡,行至皖江安慶,客迎江禪寺,迎江寺心堅、竺庵兩僧重其才,執意挽留,寄寓大士閣,以“西堂”待之。抗戰軍興,懶悟避亂于肥西紫蓬山西廬寺,勝利后復歸安慶……
這位以“懶”著稱的名僧,常年不更衣,長夏不沐浴,一心浸淫于書畫,可謂是一藝癡,故造詣精深。唐大笠記述其言:“平生無所好,山川寄我情。”其作多師古人與造化,不愿隨人俯仰。時人對他的畫褒貶不一,但他常說:“人褒之,我一笑,人貶之,我亦笑。”從中可揣摩真正的大家對藝事的體認堅定性。可惜這樣一位無爭于世的名畫僧,在“文革”中橫遭迫害,紙墨筆硯文房四寶及所藏歷代書畫珍品,均洗劫一空,甚至被逐出山門,攆到肥城南隅一座小廟月潭庵,與僧尼道士和天主教徒等居于一處,不久病逝,斯時人間何世!難得的是,唐先生還去月潭庵探望他的“懶師”:“在一間沒有天花頂棚的房間里,懶師閉目枯坐于榻上……斯景斯情,令我凄苦倍生,師察之,報之以一陣爽朗大笑,說:‘這樣很好,他們徹底幫我卸下終年為書畫所累的包袱,身外之物,盡皆破除,真正做到“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了’……”這也可以算看作一種名士的曠達吧,然而讀來叫人不免淚目。
與兩位大師的結識,可謂一種非常的際遇,由此也可見唐先生的學識與人品。今天讀到這樣的回憶性文字,也可謂沁人心脾。
作為書畫家、散文家的唐大笠對山水風景、花草樹木、人倫物理俱覺有情,有情遂有細致入微的觀察,遂有自己體味出來的獨特感受。在本書的第一篇《家在江南》中,就飽含著他對家鄉的熱愛:
我常用一枚閑印,二寸左右見方,印文曰:“家在江南四峰五溪六泉九華之間”……巍巍佛地九華山如九曲屏風,穩穩地排列于東南角,朝陽天天從那里探出山口,夕陽最后從那里抹去,與之遙遙相對的四峰尖像一位慈母,攜兒挈女,把西北面大大小小的群山手牽手地拉在一起……
家事、身世在這篇文章里都有記述,甚至對自己書齋“壟上堂”命名之得來亦有透露:實是源于對這片故土的深情。三十多年前我就讀過的《梅花三章》,以“憶梅”“畫梅”“望梅”三部曲寫盡了自己與梅的神交向往,其中情感的跌宕起伏,回環往折,令人隨之婉轉入迷。《我家小麻貓》寫得樸實無華,卻處處洋溢著奇趣,端的是“平中見奇”,其中一個“細節”尤可注目:因耳濡目染,這只小麻貓竟然在大畫家的案頭養成了喝洗筆墨水的習慣,這還不算,有一天乘主人不注意,竟躍上書案,將臟了的天足踩在雪白的水宣上,主人接受妻子建議,就著這貓的足跡加以補筆,畫面竟獲得意外的生動。主人還吟詩兩首,以志其趣。這樣的文章讀來,不僅生意盎然,而且處處峰回路轉,如屏風九疊,確乎引人入勝。
為本書作序的袁鷹先生作為同行,對書中的《漫談副刊文化》一文擊節欣賞:
他對副刊文化的主張,我都是贊同的,也深受啟迪。他從宿州傳統小吃,從全國最小的園林“個園”,從歷史上最有名的東岳泰山這三個絕不相干的比喻,論證副刊的特性和個性,“多味而不單調”,寓教于樂,揭示生活的美,鞭撻生活的丑,兼顧各階層讀者的知識結構,讓他們都能在小小的“個園”中找到各自喜愛的東西,這些都是有深刻見地的經驗之談,寫得又趣味橫生,引人入勝。
的確,唐大笠的文章寫得“趣味橫生,引人入勝”,常能化抽象為具象可感,寓議論于敘事之中,娓娓傾談,聽者愜心入理,頗覺豁然洞開。可以看出,他不是為作文而作文,而是生活中有獨到感受,使之不得借筆傾吐出心中的情與思,這樣的文章當然值得讓人細思細品。他勤于汲取、體悟,日積月累,使他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寫起文章來,從容有度,舉重若輕,我覺得他的這些文章躋身于他的同行如錢君匋、黃永玉、吳冠中諸大家文叢中一點也不遜色。我雖然不懂繪畫,也很少欣賞到唐的畫作,即據其文章亦可推斷,他的畫品亦當不凡。
可惜余生也晚,當年沒有機會去壟上堂拜訪唐先生,所以我讀先生的《小樓夜談》,更覺別有一番吸引人之處。他說:
我的寓所先前叫“一梅軒”,繼而更名“望江樓”。名曰“望江樓”,實際當時并沒有樓,只因寓所地處號稱“九頭十三坡”的古城制高點,就是平房也在低處五六層樓房之上,待到我家真的修建二樓,可以憑欄鳥瞰長江,數點風帆,成為名實相符的“望江樓”時,我卻又將齋號改了,改名“隴上堂”……
白天忙于上班,客人來訪大多擱在夜晚進行。因而就有夜談之舉。這種夜談,尤其對于闊別多年的老朋友來說,簡直是生活中一大快事。
作者還從聊天中發現許多生活尤其是人際關系的哲理。“如果不是個中人,沒有深刻地體驗,恐怕不易真切地領略它的真實內涵。”
于是我想,如果我當年就去拜訪,以我其時的學養,大約也談不出什么,恐陷兩人于無話可說的尷尬境地;而今,我對人世,對讀書、藝術也算略有所知,當有許多可向這位鄉賢請益,可惜先生已歸道山……我們就這樣“失之交臂”,對于先生當然沒有什么,對于我卻是永久的遺憾。
那么,讀先生文章,就權當做客壟上堂,在在如聞謦欬,我認為便不虛此行,獲益良多。
方瑋德:新月下的流星
最近一段時間,我一直沉浸在閱讀和追懷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新月派詩人方瑋德的作品與逸聞當中,常常是嘆賞不置。我贊嘆其才之俊,其風采之美,感慨其命運之淹騫,更嘆天不永其年。我從諸多懷念他的文字里感受到仿佛有那么一位瀟灑出塵的謫仙,在春風中詠歌一番,就回到天上,給世人留下了永久的懷念與想象。因此,他的死也就并不是悲劇,而只是一個美的化身的消失。
我大約十幾歲就知道早在三十年代我的家鄉就出過這么一位有現代氣派的青年大學生。那是我從《方令孺散文選集》里讀到《悼瑋德》一文,這篇浸透著血淚的文字卻優美如詩,飽含著一位姑母對英年早逝的侄兒不可抑制的無限的哀憐與痛惜,任誰讀來都不由生出深深的同情。九姑方令孺不僅把一個秀逸的青年才子的形象描繪在我們眼前,而且讓我們感到他幾近完美的人格品性。“瑋德那可愛的人格,若大家能多知道他些,我相信人人都要惋惜。瑋德有的是一個美麗純潔的靈魂。”“瑋德多么似一潭清水的溫柔,光明照徹人心呢!”“瑋德的信心是人所難得的,忠懇,崇之如神明,是瑋德對他朋友的態度……”這樣的贊語恐怕不是能輕易就下得的吧?哪怕是他的姑母。從方令孺的悼文中,我們也隱約知道一點他的愛情故事,他怎么喜愛上了一個女孩,中間又有誤會與暌違,最后在病榻上又如何得這女子的照拂。方令孺在另一篇《信》中,一開頭也提到她的侄兒:“瑋德已在醫院里呻吟多日,我帶著愁悶的心在烈日下來去。”其中摘錄的一個信片,我疑心就是寫給瑋德臨終時仍陪伴在側的那個女子:“今年初夏,在玄武湖上看見你同瑋德,都像春花一般的盛年在金色的黃昏中微笑”,并贊許她,“這因為你有詩人的溫存的性質,當你在那樣憂苦不安的時候,寫出的話仍是那樣的蘊藉。”我很驚訝,我的家鄉在半個世紀前竟然也出過如此超逸脫俗的知識青年,但我那時似乎并不知道方瑋德還是個優秀的詩人,直到我上了大學,從學校圖書館里借到一冊《新月詩選》,陳夢家先生選編的,還是豎排版(不知是否為影印本),見到上面赫然選錄方瑋德的詩,我才知道這位才子曾經是在中國的詩壇上活躍過的。但那時,我正為如潮流般涌進來的外國詩歌而目眩心迷,對于新月派這樣一些似乎跼蹐于一己之天地里喁喁私語的作品是不太喜歡的,甚至認為它們帶有一點“灰色調”,有些“澀”口感,所以只是翻了翻,又擱下了。
直到來北方讀書,所在大學的出版社出了一本新選的《新月派詩選》,選編者是我們系的老師,我輾轉得到一冊,見到上面仍然選有方瑋德詩作多首,便予以格外的注意,同時也感覺到,在現代中國新詩的發展進程中,有我家鄉的一兩位詩人(《新月派詩選》里也選有方令孺的詩作)身影,我不僅為之驚異,更為之驕傲。桐城,那是一個多么崇仰古文化的地方,沒想到它也能“新變”!這時我已經得知,方瑋德與著名學者舒蕪先生(我與他有一面之緣)是堂兄弟關系。他們都出自桐城有名的書香門第:魯谼方家。我甚至還知道,他們并非是“桐城派”創立者方苞的后人,但他們一族也出過方東樹這樣的大學問家(我買過一本他的《昭昧詹言》),而方瑋德、舒蕪的曾祖父方宗誠也是著名的桐城派作家,曾入曾國藩的幕府(我甚至疑心,曾國藩之服膺桐城派是否與方宗誠有一定關系),他們的“九姑”方令孺其文、其行倍受著名作家如巴金、丁玲、趙清閣的稱贊,這樣的一個文化“世家”真的令人欽敬。再后來,我就讀到舒蕪對他的這位英年早逝的大哥方瑋德的記述文字,首先是《舒蕪口述自傳》中的:
方瑋德是我大伯父的兒子,大排行是老大,我叫他“大哥”。他比我這個老三大14歲。1932年他在南京中央大學畢業時,我才10歲,正在家里讀私塾。那時我對他崇拜得不得了,常常聽到大人們提到他,評論他,都是贊美的話,如何如何才華出眾;如何如何用白話文做出了漂亮的新詩,在南京、上海、北平著名報刊上發表;如何如何風度翩翩,讓女孩子們提起他的名字就臉紅。親友中一些美麗的大姐姐們都注意他,有一位還說:“方瑋德是最好的情人,最壞的丈夫。”別的姐姐們似乎也同意。這當然不是說瑋德大哥生活作風怎么不好,不過是強調他對女性太有吸引力,做他的妻子總歸不太放心。
這些回憶多么有意思,讓我隱約地想象到三十年代住在縣城里的桐城大家族的生活情景,甚至覺得桐城似乎也不是那么閉塞,大家子弟也不是整體只知“子曰詩云”的了。
舒蕪在“自傳”中還回憶到方瑋德放假回家對他文學上的啟發,他走后給舒蕪留下的一個小書柜,這都對舒蕪后來走上文學寫作、研究之路有很大的影響。現在我們不妨看看這個小書柜的“內容”。舒蕪說:
書柜里放的都是新文學一類書籍,各個流派代表的主要作品差不多都有,像魯迅、周作人、茅盾、巴金、郭沫若、徐志摩、冰心、葉圣陶、梁實秋、陳夢家、陳衡哲、宗白華、朱光潛等等,都有作品,我可以隨便翻看。魯迅的《彷徨》《朝花夕拾》《偽自由書》,周作人的《自己的園地》《談龍集》,郭沫若的《落葉》和他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還有他和宗白華、田漢三人的《三葉集》,徐志摩的《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陳夢家選編的《新月詩選》,冰心的《寄小讀者》《繁星》《春水》,陳衡哲的《小雨點》,梁實秋譯的《潘彼得》和他的論文集《浪漫的與古典的》,朱光潛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等等作品,都是我在小書柜里讀到的。
他還說到,“書之外,還有三四期《新月》雜志和二十來期《小說月報》,這同大哥“新月派’詩人的身份是相符合的。”我相信,舒蕪的記憶不會有太大的誤差。我很驚訝,同時也確實很自豪,新文學之風,這么早就吹到了我家鄉的縣城,這個以“程朱理學”為精神皈依的“桐城派”發源地。這當然主要還在于方氏子弟有家學淵源,這個家族很早就有人接受現代高等教育,包括“九姑”方令孺,但方瑋德所取得的成就更與他對新人生新文學有自覺的執著追求分不開。方令孺在《悼瑋德》中提到他不顧體弱,毅然步行近百里山路到安慶然后轉赴南京考大學,可見其求學之切。另外,舒蕪在懷念其老師的文章中提到,當年“先兄方瑋德,已與家庭所訂的未婚妻解約”,還遭到“親戚社會間”的非議與不滿,也可見其追求新生活的勇氣。
從舒蕪的懷念文章《白色的飄飏》中,我得知那個后來與方瑋德訂婚,并一直在病榻前照料他的女子是黎憲初。他們在北平的一次聚會上一見鐘情,但后來黎女士為避兵禍,回到了家鄉湖南。雖兩地相隔,但是鴻雁不斷,情感日益升溫。他們的“兩地書”竟有二百多通,而且通篇充滿詩情畫意,十分的旖旎浪漫。得益于現代網絡技術的發達,我很快就從網上搜閱到了黎女士的“生平事跡”,原來她的父親就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著名的語言學家黎錦熙,而湘潭黎氏,何其了得,可謂俊杰輩出!黎錦熙曾是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時的老師,畢業后毛澤東還曾去信向他求教。而黎憲初本人更是1932年畢業于清華西洋語言文學系的才女校花。如果不是天不假年,方、黎是一對多么令人稱羨的神仙眷侶!可惜,倒真應了那句古語“世間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玻璃脆”,怎么不令人扼腕嘆息!
瑋德之死,主要還是由于他生來體弱,他十歲即喪母,由祖父親自帶大并啟蒙;當然也跟他后來勤奮學習而又才情奔放,未加珍攝有關,所以到廈門集美任教后,不服其水土、氣候,引發舊疾,遂至不可收拾。他于1934年底由堂弟護送來北平,獲允與黎女士訂婚,雖藥石不斷,仍常常談笑風生,語驚四座,并與伴侶游賞風景,終因體力不支,一病不起,而且病得十分痛苦。看到這些回憶文學,我也不由感慨:老天對于這樣一位英才、這樣一對璧人真是太苛刻了!殘酷啊,造化!
知其人,不讀其詩可乎?我首先是從書櫥中取出藍棣之先生編選的《新月派詩選》,翻到方瑋德部分,將所收14首逐一讀過,覺得真的寫得不錯,許多作品在今天看來也沒有“過時”,每首詩意境不僅是圓融的,而且是輕快、靈動的,尤其是當我讀到《我愛赤道》時,更不禁暗自吃驚。
我愛赤道。我愛赤道上
燒熱的砂子;我愛椰子,大橡樹,
長藤蘿,古怪的松林;我愛
金錢豹過水,大鱷魚決斗,
響尾蛇爬;我愛百足蟲,
大蜥蜴的巢穴,我愛
黑斑虎,犰狳,駱馬,駝羊,
無知的相聚,我愛猿猴
攀登千仞的山巖;我愛
老鷹在寂寥的蒼空里
雄飛;我也愛火山口噴灰,
我愛堅硬的鋼石變成鐵水流。
我愛赤道。我愛赤道上光身子的野人,
樹皮是他們的衣服,
葉子是他們的寶章;
我愛他們勇敢的流血,隨便地
截去一只大拇指,或是左腿上一塊
大皮;我愛他們容易
跳過一個地里的缺口,天真的飛;
我愛他們頑皮的口吻
手臂交著手臂,腿交著腿,
在大海的邊沿,他們放肆的
擺下一付熱情的十字架;
我愛他們星子下的笑,水上的吐沫,
我愛他們敲下一付牙齒,
從血嘴里說出他們的真情;
我也愛他們在黑林里的幽怨,
他們的太息,他們落下幾滴
堅強的淚水;我更愛他們
溫柔的暗殺,我愛他們割過
野花也割過女人的喉頭的刀子;
我愛他們的搖頭,他們像忘掉的死。
我愛赤道我愛赤道
在你的心里;我愛
你燒紅的眼睛,炙熱的嘴,
我愛你說不出的荒唐,
好,去吧,我的愛,
我們在赤道上相見。
我覺得這首寫于1932年的詩接跡完美,它應該是新詩史上的一首杰作。我驚奇于作者綺麗的想象,把我們帶到赤道上去感受熱帶風光;我驚嘆作者能把如此繽紛的意象并置于筆下,讓它成為一幅廣闊而又細密(細節處處閃光)的風俗畫,這在三十年代的詩壇幾乎是絕無僅有!第一段寫自然界,那么多動物(當然也有植物)絡繹而至,生動可愛;第二段寫人類生活,寫赤道部落的率直、自然、質樸、野蠻,在在都吸引人。有些句子不僅優美,還令人震撼(如“敲下一付牙齒”——讓我想起古人有“雕題鑿齒”之說;又如“他們割過野花也割過女人喉頭的刀子”),頗有鋪張揚厲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全詩意象明麗,主題朗健,甚至有一些現代色彩(因為全詩沒有習用的古詞古典),總之是讓人感覺耳目一新,即便置于當今作者的詩集,仍然是光彩熠熠,這多么難得。
這是偶然的嗎?我把目光移向方瑋德其他的詩,又讀到一首讓人擊節欣賞的《“他們說——”》:
他們說我曾經愛過哀綠綺思,
是的,哀綠綺思在春天給過我的吻;
他們說我有一次喜歡過莎菲亞,
我認得,不錯,我喊過莎菲亞我的情人;
他們說伊凡瓊思也很和我要好,
這孩子,我承認,我教會她許多聰明;
他們又說我至今不會忘記恩艷,
我也明白,恩艷對我是十分鐘情;
(到底這件故事是白白地便宜了她,
她如今還說她是我國度里惟一的臣民)
他們到后說我和赫浪蒂思,瑪利赫倫,藍花威思,浴金,
(這婦人!)齊通過音訊:
彭卡爾的太太,拉菲,——杜先生的情人——
鋈金伯爵的寡婦,和格塞教堂的小清道士,
華令茲小姐同我也有過往來,眉目上做過情;
連那隔屋童克森老太太的女兒,
也是,我誤著她,他們說,誤著她的青春;
他們有許多證據,許多咬著牙齒的傳說,
指摘我,說我的愛情上曾沒有過忠貞!
只有一個人他們一點不曾知道,
連名字也沒有人喊過這是分明。
我早想找出一位最知己的朋友,
告訴他,我一來心里就只有這一個人,
可是誰相信?誰都要說這是美麗的謊。
我發誓,用我父母的名字,那可不成?
僅正這件心事我就不希罕人知道,
他們說的,罵的,我一齊承擔。
天下雨,葉子上的水不就道出這秘密,
夜里的星子不也教過露水閃出它們的聲音,
你聽這一滴一滴的——永遠在我心里——
(這一個人,這一個人!)
這也是一首迷人的詩。它的立意是在否定別人的指摘:“說我的愛情上曾沒有過忠貞。”但作者沒有直接去否認流言,而似是承認了自己與其他女性的交往乃至感情,并一一列舉出來,但我們看到的卻是純真的美好的感情,最后道出他在心里“只有這一個人”——真正的愛的對象是“秘而不宣”的,可又是“魂牽夢縈”的,何以見得?因為連“雨水”“露水”,一滴一滴“在我心里”敲響的,也是這個人的“名字”!這是何等深切、雋永的愛情,有了這樣的愛情,那么一切謠言便不攻自破。這首詩的曲折幽婉于此可見,可說一讀即“膾炙人口”。第一段列出的許多人都有著外國人的名字,作者是把自己設想成一個外國人,也使詩作有了現代派的浪漫色彩,給詩增添了詼諧的情調(當然也能夠看出整體受到英國詩歌的影響)。這首詩的由來大約是有所本的,那就是方瑋德與黎憲初戀愛過程中,確實經歷過一些流言蜚語和謠諑(謂方移情別戀于某才貌雙全的新月派詩人)的干擾,而瑋德拿出這樣一首別致的情詩,當然會讓自己的戀人心中疑團盡釋,并更生愛意!
讀到以上兩首詩,我不由對我這位同鄉詩人“刮目相看”。在那么早年,他就寫出如此成熟的,在今天看來仍十分有魅力的好詩,端的是不容易。難怪他病逝后,那么多人寫詩作文悼念他,林徽因、劉夢家、宗白華(宗是瑋德的表兄)……難怪連性格有些“怪異”的吳宓也與他成為知交。我想起我曾替外地的好友買過一冊《吳宓詩集》,當年粗粗翻閱,就讀到他懷瑋德、挽瑋德的詩、聯,并把它抄下來。寫本文時我趕忙找來抄件,首先看到的是《過背陰胡同有懷方瑋德》:
舊巷重經景已非,生偷死寄等無歸。
網遮淺水魚群泣,風急寒林鳥倦飛。
求愛千程知病苦,論詩片語入精微。
桌頭尚看遺容在,玉柱間憑對夕暉。
第一句下,作者自注:“方瑋德君,于本年五月九日病歿北平西單背陰胡同北平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宓數往視疾,并送喪。近日西單大街新建屋宇,街市全非舊觀矣。”可見,這位眼高額頂的吳宓教授對比他年輕14歲的青年詩人瑋德是何等推許(“論詩片語入精微”,想亦不是吳宓能輕易許人的)。從網上獲知,瑋德逝后,吳宓教授多年一直將瑋德的遺照放在桌頭,正如這首詩第七句所言(此句后亦有注:“遺照系民間二十二年秋,在廈門大學攝寄者。”)。我也從網上看到了這張照片,一著長衫的青年在廊沿柱間,凝望夕陽,長身玉立,若有所思;而收入《舒蕪口述自傳》中的瑋德的正面頭像更是秀逸如“婦人好女”,一雙眼睛清澈如黑琉璃。
閱讀至此,我決定要搜羅到一本《瑋德詩文集》。仍然是借助網絡,我訂下一冊由“上海書店出版社”于2015年1月“原貌影印”的“現代文學名著原版珍藏”本。不日,書送我,我逐一讀來,仍然興致盎然,書之“代序”即“九姑”方令孺的《悼瑋德》。“詩卷一(十八年至二十年)”收詩25首;“詩卷《二十一年以后》”收詩12首,附譯詩4首;“文一卷”收自作文4篇、譯文一篇;“古詩文一卷”收詩文五題。翻閱這本詩文集,一方面感覺到方瑋德在創作上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績,幾乎每一首詩都成立,沒有半成品或廢品,每篇文章都可讀,顯示出一個從“文學世家”出來的“青年才子”很不一般的功底;另一方面,也再次為他的英年早逝扼腕嘆息。《瑋德詩文集》在現代文學史的著作之林里自有其不朽的地位,但畢竟還不是最頂級的,而如果假以時日,我相信他完全有實力登上文學的頂峰的。我為中國現代文學可惜,我更為我家鄉桐城在現代文學史上本應該有一位更大的作家出世卻因其早逝而缺如感到可惜。
因此,今天看來,方瑋德在文學的天空上,仍然是一顆流星;他如一彎新月般劃過,劃出了燦爛的光芒,在一瞬間,我覺得其亮度甚至不亞于整個新月。宗白華在《曇花一現》中說:“提起他的白話詩,真是新文學里的粒粒珍珠……反對白話詩的人,如果肯虛心讀它,恐怕也可以改變他們的頑固成見。”但畢竟,他很快就墜落到茫茫夜天,留給人的除了不盡的回味、想象,還應該有遺憾與悵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