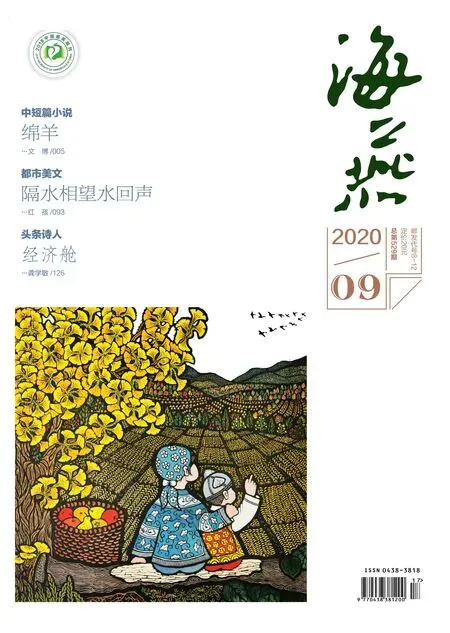娘給的
雷從俊

起初,我們常到她那里買東西。不僅因為在這方圓幾十公里的荒郊野外,她的小賣店離我們臨時駐地最近,更由于她不嫌麻煩。有的剛買根火腿腸,又想換成松花蛋,她沒二話,隨時調換。有的白天出了大力,三更半夜餓了,敲門買包方便面在她那里煮著吃,她像隨時恭候似的,很快把火生上,往往還放幾根小青菜滴幾滴香油,煮面用的煤、搭上的東西和花費的工夫,都不另收錢。
那年頭,大家差不多都是兜子比臉還干凈,那些津貼費隨發隨光的家伙,買煙往往只要幾根,她也樂于把一包煙拆開零售。有時一根兩根確實不值得把一包煙拆開,她干脆從懷里掏出自己的煙給人抽,你要是不好意思接,她準會說:“我都五十多了,給你當娘還不行嗎?接著吧,娘給的!”
那口氣,比親娘還親。
但有一陣子,大家寧可多走點路,也不再到她店里去了。
那天中午,班長買一包花生米,又買了個打火機,她找回一毛錢,班長說趕著算吧,下次買東西再說。推來推去,班長也沒接,徑直從店里住外走,她追趕不上,一著急“嘰哩呱啦”連說帶比劃,聽起來很像是日語,班長立即警覺起來。
回到連里,班長在第一時間向上級報告了這件事。上級指示說,在事情沒調查清楚之前,暫時不要到她的小賣店買東西。大家伙兒私底下議論紛紛,有人說她可能是特務,也有人說她是軍屬。總之大家開始有意識地遠離她,尤其是半夜三更胃里缺東西時,我們寧可到炊事班找個干饅頭啃也不到她那里去了。
就這樣過了半個多月,班長到離駐地二里開外的小店買東西回來,被她攔住,她一臉焦急地問:“你們怎么都不來了呢?我做錯什么了嗎?”
班長無言以對,只能落荒而逃。
后來,調查有了結果。原來她是朝鮮族的,“嘰哩呱啦”說的是朝鮮語,她很小就沒了爹娘,是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長大的,故對我們這些人民子弟兵格外有感情。
調查結果出來的當晚,班長在班務會上講評完一天的工作生活后,鄭重其事地說:“以后咱們買東西再也不用舍近求遠了!”
第二天,班長正寫信時圓珠筆沒水了,兩分鐘就跑到她店里買了一支,接著跟女朋友紙上談兵。從那以后,去小店買東西的多了起來。她似乎更熱情了,有時誰去買東西趕上她吃飯,她總會盛一些讓你嘗嘗。你若推辭,她就會故意斂起笑容,裝作不高興地說:“吃點不行嗎?就當娘給的!”
這樣,任誰也無法拒絕,連隊那幫家伙好多人在她那里吃過餃子、面條、湯圓,只是誰也沒叫過一聲“娘”,跟她說話只用一個“您”。她似乎從不介意,只要看到大家都熱情得像家里來了遠客。
有一次我們野外作業,離她的店子不遠,她端來滿滿一大盆毛桃給大家吃。來連隊采訪的攝影干事給大家照合影,連長禮貌地請她一起照相,她被大家擁在中間,高興得像個孩子。
大半年過去了,大家和她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親情。湖南兵弄了罐臭豆腐,放哪哪臭,誰見誰罵,實在沒辦法就拿去放她哪兒,周末沒事了過去抿兩口。四川兵家里寄來了臘腸,也偷偷到她那里煮,然后和她一起邊吃邊聊。有時她也講自己小時候的事,煙抽得很深,語速很快,偶爾也會“嘰哩呱啦”蹦出幾句。
國防光纜施工結束后,連隊馬上就要回撤歸建了。天不亮,駐地車隊轟鳴,隊伍準備開拔。借著車燈的亮光,大家看到她蹣跚地走來了,懷里抱著幾條煙。她邊上車邊拆煙,每人一盒。那些不會抽煙的只是說著感謝,并不接煙。有的說車里不讓抽煙,三番五次推辭,她急了,又一陣“嘰哩呱啦”,接著把煙往每個人手里塞,理直氣壯地連連說:“娘給的還不行嗎?娘給的還不行嗎!”
煙發完最后一輛車,大家跟她揮手再見,有的還說:“將來有時間再回來看您。”
聽到這話她臉上的皺紋如菊花綻放,欣慰而又驕傲地說:“好嘞,娘永遠在這里等著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