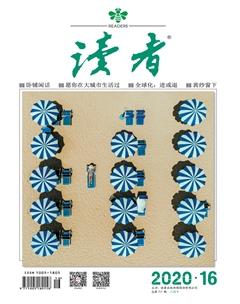守護(hù)莫高窟的年輕人
王雙興

陸佳瑜為參觀者講解
上山
來莫高窟工作之前,陸佳瑜在一個(gè)地質(zhì)公園當(dāng)導(dǎo)游,每天站在通往景點(diǎn)的大巴上,“覺得每天都很閑,不會(huì)有提升空間”。生活節(jié)奏被改變,是在2016年,她看到莫高窟招聘講解員,考慮到“它背后的東西非常厚實(shí),應(yīng)該可以獲得成長”,便來了莫高窟。
入職是在那一年的4月5日,莫高窟的旅游旺季馬上就要來了。陸佳瑜有兩個(gè)月的培訓(xùn)時(shí)間,白天聽研究者、講解員上課,晚上看書、整理自己的解說詞,凌晨3點(diǎn)入睡,早晨6點(diǎn)起床復(fù)習(xí),然后上洞窟,練習(xí)講解。兩個(gè)月時(shí)間看完8本書,筆記寫滿兩個(gè)A4筆記本,陸佳瑜發(fā)現(xiàn):“歷史的、文化的、宗教的、美術(shù)的……莫高窟的知識(shí)根本學(xué)不完,感覺自己來對了。”
不過,并非每個(gè)人都像陸佳瑜一樣主動(dòng)選擇莫高窟,也有人是畢業(yè)季找工作,無心插柳地來了。2005年,俞天秀從蘭州交通大學(xué)畢業(yè),聽說敦煌研究院在招人,便投了簡歷,心里還納悶:“莫高窟招計(jì)算機(jī)專業(yè)的干嗎?”進(jìn)入數(shù)字化研究所那一年,只有辦公的電腦配有一根網(wǎng)線。俞天秀耐不住寂寞,只能自娛自樂,去洞窟旁邊的水渠里撈魚,去沙丘上燒烤……
有位老院長評(píng)價(jià)那些年輕人:“有的人,肚子里憋著一股氣,晚上抱著吉他,爬到房頂,對著月亮一聲怪叫……”
和俞天秀一個(gè)部門的安慧莉2009年入職,這個(gè)學(xué)工業(yè)設(shè)計(jì)出身的姑娘,此前對莫高窟的全部認(rèn)知,是8點(diǎn)檔電視劇開始前,那個(gè)緩緩飄落的“飛天”圖標(biāo)。剛到敦煌時(shí),安慧莉發(fā)現(xiàn)整座城市只有一家超市,買了一瓶綠茶,看上去和普通的康師傅綠茶一模一樣,但商標(biāo)處寫的是“小二黑”。這個(gè)女生有點(diǎn)沮喪,覺得“待兩年,肯定是要走的”。
這種想法在剛來莫高窟的年輕人中并不罕見。五湖四海的年輕人離開故鄉(xiāng),在甘肅省省會(huì)蘭州中轉(zhuǎn),然后沿著河西走廊抵達(dá)敦煌,沿路看著窗外的山越來越禿,心里都猜測自己“肯定待不住”。
壁畫臨摹師彭文佳,來敦煌是因?yàn)閷δ呖咚囆g(shù)的向往。同窗同學(xué)大多去了沿海城市,那里有更多的畫廊和工作機(jī)會(huì)。而她想要和外界聯(lián)系,只能在每周三或者周日,乘班車去25公里外城里的網(wǎng)吧。登錄QQ,收到老同學(xué)發(fā)來的消息:“你們在敦煌是不是要騎駱駝上班啊?”
“1擋掛到5擋”
現(xiàn)在,陸佳瑜的生活漸漸和工作融為一體。以前看《解憂雜貨鋪》,現(xiàn)在看《敦煌石窟藝術(shù)簡史》;以前最熟悉的作家是郭敬明公司的,現(xiàn)在變成了趙聲良、王惠民,去書店都是直奔專業(yè)類的書籍。她不能忍受每次進(jìn)一個(gè)洞窟都講同樣的內(nèi)容,“覺得是在退步”。
每天,當(dāng)陸佳瑜帶游客在開放洞窟參觀時(shí),另一群人正在非開放洞窟“面壁”。四五月天氣回暖,利于材料黏結(jié),壁畫修復(fù)師們對231窟的“治療”開始了。他們爬上腳手架,用毛筆除塵,用注射劑黏結(jié),隔著一層鏡頭紙,用修復(fù)刀修復(fù)壁畫……
這支隊(duì)伍中,“80后”是主力。張瑞瑞是231窟修復(fù)師中唯一的“90后”,也是唯一的女生,前幾年大學(xué)畢業(yè)后來到莫高窟工作。她學(xué)的是文物保護(hù)專業(yè),專業(yè)對口,但依然不能立刻接觸壁畫修復(fù)工作。和每個(gè)修復(fù)師一樣,工作的前幾年,她的主要任務(wù)是幫師父和泥、遞材料,以及站在一旁學(xué)習(xí)、提問。
曾經(jīng)確信自己一定會(huì)很快離開莫高窟的人,在幾年、十幾年后,掰著手指列舉留下來的理由:工作環(huán)境單純,個(gè)人成長空間大,職業(yè)成就感強(qiáng)。
耐不住寂寞的俞天秀,在前幾個(gè)月的“動(dòng)搖期”過后,慢慢發(fā)現(xiàn)了莫高窟的魅力。他和同事的任務(wù)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建模莫高窟,將莫高窟的影像數(shù)字化,保存起來。
2008年,“盛世和光——敦煌藝術(shù)大展”在北京舉辦,出自數(shù)字化研究所的展品是莫高窟第61窟的壁畫影像。40多平方米的《五臺(tái)山圖》,是敦煌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跡畫,采用鳥瞰式的透視法,把五臺(tái)山全景記錄下來,從山西太原到河北鎮(zhèn)州(今正定縣)的山川道路,以及旅行、送供、拜佛者,全都出現(xiàn)在畫面里。“以前我們的成果都被存到檔案里,你拼完只有自己見過,其他人無法得見。那是第一次,整面墻的內(nèi)容展現(xiàn)在大家面前。看到時(shí)確實(shí)覺得自豪:哇,這是我做的。”俞天秀說。
到如今,俞天秀已經(jīng)在莫高窟待了15年。那個(gè)跑去城里上網(wǎng)的畫師彭文佳則度過了16年,在她看來,莫高窟就像一個(gè)烏托邦,不僅有永遠(yuǎn)汲取不完的藝術(shù)養(yǎng)分,還有世外桃源一樣的環(huán)境。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沒有太多誘惑,也沒有太多功利的東西,非常純粹”。
陸佳瑜的同事邊磊在莫高窟工作了12年,他記得,有前輩講自己的經(jīng)歷:剛來的時(shí)候愛夸夸其談,聲稱要做出一番事業(yè),當(dāng)時(shí)的研究院院長段文杰在一旁聽著,不吭聲,最后說了句:“好好吃飯,好好睡覺,10年后再說。”邊磊也沒想到自己一晃已在莫高窟走完了第一個(gè)10年,他說:“1擋掛到5擋,就一直往前跑了。”

已辭世的老一輩守護(hù)人,被安葬在莫高窟對面的沙丘上
接力
年輕人也樂于講起“上上輩、上上上輩莫高人”的故事。在莫高窟對面,是嶙峋的三危山,沿著山腳的戈壁灘一直朝南,在“九層樓”正對著的沙丘上,是一個(gè)墓園,安葬在那里的,是來莫高窟的第一批年輕人。
1935年,留學(xué)法國的青年畫家常書鴻在舊書攤遇到《敦煌石窟圖錄》,后來回國,四處逃難,8年后去了敦煌。1944年,重慶國立藝專國畫系學(xué)生段文杰遇到張大千的“敦煌壁畫臨摹展”,在完成學(xué)業(yè)一年后來到莫高窟。從1947年開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到洞窟里“面壁”,歐陽琳、史葦湘、李其瓊、竇占奎……
曾經(jīng)的絲路重鎮(zhèn),在那時(shí)已經(jīng)變成了邊陲小城,被沙漠和戈壁包圍著,日光熾烈。因?yàn)槿彼荒芟丛瑁荒堋安猎琛保聊槨⒉辽怼⑾茨_,水用完還要留著派其他用場;夜里,為了看守駱駝和羊群,需要派人值班,拿著獵槍防狼;天亮后,用鏡子和白紙當(dāng)反光板,就著反射進(jìn)洞窟的陽光臨摹壁畫、修復(fù)雕塑……
現(xiàn)在,曾經(jīng)的青年已經(jīng)進(jìn)入暮年,其中一些人已然辭世。20余座墓碑端立在沙丘上,隔著佛塔、戈壁、干枯的河道,和莫高窟對望。
“沒有可以永久保存的東西,莫高窟的最終結(jié)局是不斷毀損。我們這些人畢生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與毀滅抗?fàn)帲屇呖弑4娴瞄L久一些,再長久一些。”敦煌研究院名譽(yù)院長樊錦詩曾說。
現(xiàn)在,幫助莫高窟對抗時(shí)間的接力棒被后輩年輕人拿起來。和前輩們相比,這些年輕人身上少了歷史氣質(zhì),鮮少把“奉獻(xiàn)”“一切為了國家”掛在嘴邊,更多關(guān)注個(gè)性和自我價(jià)值的實(shí)現(xiàn)。講解員陸佳瑜說:“這里工作待遇算不上優(yōu)越,工作環(huán)境也不那么舒服,愿意留下來的,大多是熱愛莫高窟的。人選擇喜歡的職業(yè),職業(yè)也在篩選適合它的人。”
(林 冬摘自微信公眾號(hào)“剝洋蔥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