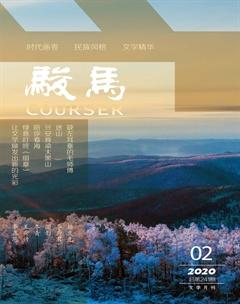故鄉的山
梁新英
在故鄉,我家的東邊,隔著一條道就是山。山的形狀像饅頭,線條柔美,從不危峰兀立,鄉親們稱這樣的山為饅頭山。饅頭山連在一起,像輕柔的波浪,綿延數十里。這樣的山在北方隨處可見,沒有泰山的雄偉,沒有華山的險峻,沒有黃山的奇秀,它平淡無奇,普通到不能再普通,卻如母親一樣乳養著村莊里的人們。
春季的山給予美。杏花為春山代言,一開口便是嫣紅的詩句。花蕾點點紅,枝頭春意鬧。花瓣初綻,像少女羞紅的臉頰。折一枝含苞的杏花插進罐頭瓶,今天開一朵,明天開兩三朵,一室生輝,一座山,一個春天全在這里了。
杏花落了,結出杏子。老樹葉子少,青杏擠擠挨挨布滿枝頭。發了新枝的杏樹葉子蔥蘢,零星著幾個杏子,個個肥嫩。山杏酸澀,兩三個下肚,牙便倒了。去了杏仁,母親加糖把杏煮熟,涼下來,酸酸甜甜的味道像山楂罐頭。采的杏子或做的罐頭,總要送一些給鄰居,山里人家很少獨享什么。
山是愛美的姑娘,發間簪滿各色的野花。春天是一座開滿詩歌的城,耗子花詩一束,雞爪花詩一冊,老頭兒花詩一扎。野花的名字接地氣,花朵透著樸素的可愛。女孩子最喜歡這時在山上瘋跑,野花是自己的,山也自己的,便覺得世間再沒有一個人如我這般富足。
夏日的山給予希望。每到暑假,我們去山上挖藥材,賣的錢買學習用品。柴胡、黃芩是草,是藥材,也是花;桔梗、卷蓮是藥材,是花,也是食材。柴胡黃色的花朵細細碎碎,極像滿天星。桔梗扎堆在碎石遍布的小丘,它的花蕾像僧帽,喇叭似的藍花吹奏著山林之歌。黃芩的花在遙遙招手,一排排紫藍的琴鍵叮叮咚咚,日復一日,彈奏出悅耳的音韻。挖藥材時,露水打濕了鞋和褲腿,鞋面糊了泥巴,泥猴似的,鞋里泥水一走一“噗嗤”,到中午才漚干。頂著太陽暴曬,不停地彎腰蹬藥叉子,一天下來渾身酸疼。
偶爾發現藏在草叢的卷蓮,中大獎一般高興,那艷紅撣去了身心的勞累。卷蓮又名山丹丹,植株高三四十厘米,細葉纖弱,又叫細葉百合。花骨朵兒交錯向上,由綠逐漸粗長變紅,粲然一笑。花下垂,花瓣向外反卷,像紅燈籠,花朵由下而上次第綻開,像窮苦日子里的希望,一盞落了,一盞亮起。風一吹,紅燈籠輕輕搖曳,花蕊像被撓了癢癢似的顫著。摘一朵,插在發辮,美美的。卷蓮的根似沒分瓣兒的蒜頭,甜味兒極淡,黏乎乎的,喜悅從味蕾漫溢開來。
人靠山吃山,牲畜亦然。牲畜散養禍害莊稼,由牛倌豬倌趕到山上去放養。牛角聲當街響起,大人、孩子放出自家牲畜,吆喝著入群。被囚禁的牲畜一旦獲得自由,有些小興奮。哞哞聲,咩咩聲,吭吭聲,雜織在一起,形成夏日的交響樂。畜群浩浩蕩蕩,向東山開拔。遠處的山像綠色的國畫,牛羊悠然地走入,畫卷的色彩不再單調,山生動起來。
上初中那會兒,我喜歡到山上早讀。東方染上微微的紅暈,炊煙裊裊,村子寧靜安詳。一冊在手,輕聲誦讀,山默默地望著,聽著。鳥語入書,花香入書,古文著了山的靈氣,背誦不再艱澀。多年后,村里的同學說:“那時的你,像山上盛開的一朵百合。”我讀書,山讀我,別人讀我和山,生命中的一切那么美好。
冬天的山給予溫暖。沉靜下來的山陷入沉思。我們到山上用大耙摟柴火,寒風里走得通身是汗,柴草一簾子一簾子攢起來。我們以腳步丈量山的高度,丈量冬天的溫度,丈量生活的寬度。暮色中,疲乏的身體平躺在草車上,夕陽搖晃,意識也晃動起來。后院,柴火漸漸長起一座小山,家人一年的生活暖烘烘的。
故鄉的山樣貌平凡,看過難以留下深刻印象。它安靜地站在那,默默地給予人們美、希望和溫暖,與我血脈相連。
如今,故鄉成為遠方,在菜攤上看到綠瑩瑩的山杏,總要買一碗,吃幾顆;在草原上看到紅艷艷的山丹丹,總要欣賞一番。在青杏的酸澀里,在山丹丹的艷紅里,思念洶涌而來,濕了眼眶。
朦朧的霧氣里故鄉的山清晰可見,饅頭一樣沒有棱角,卻不憂不懼,從容挺立在天地之間。故鄉山的能量不僅流注到我的物質生命中,也流注到我的精神生命里,我的呼吸里落滿了杏花和卷蓮淺淺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