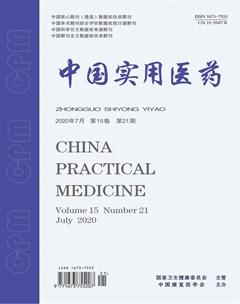缺氧誘導因子-1α與缺氧誘導因子-2α在宮頸癌組織中的表達與相關性分析
黃平 陳光元 鐘細妹 李日紅

【摘要】 目的 探析缺氧誘導因子-1α(HIF-1α)與缺氧誘導因子-2α(HIF-2α)在宮頸癌組織中的表達與相關性。方法 選取160例在本院實施手術切除的宮頸鱗狀細胞癌的患者宮頸腫瘤組織, 進行免疫組織的化學染色處理, 比較HIF-1α、HIF-2α在宮頸浸潤癌組中的免疫組化染色得分以及在宮頸浸潤癌、原位癌中的表達率, 分析宮頸浸潤癌中HIF-1α蛋白、HIF-2α蛋白表達相關性。
結果 HIF-1α在宮頸浸潤癌組中免疫組化染色得分為(1.55±1.61)分, 低于HIF-2α的(4.50±1.05)分,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HIF-1α蛋白宮頸的浸潤癌、原位癌中陽性表達率分別為78.6%、57.7%, HIF-2α蛋白分別為85.7%、65.4%。宮頸癌級別越高HIF-1α、HIF-2α蛋白表達率則越高。浸潤癌中HIF-1α蛋白、HIF-2α蛋白表達呈正相關,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r=0.854, P<0.05)。結論 HIF-1α、HIF-2α在浸潤癌、原發癌中表達和臨床宮頸癌病理的特征間關系密切, 且二者表達呈正相關, 在宮頸癌發生、發展、浸潤轉移期間二者可能存在協同效果。
【關鍵詞】 浸潤癌組;原位癌;缺氧誘導因子-1α;相關性
DOI:10.14163/j.cnki.11-5547/r.2020.21.089
HIF-1α在人體及動物腫瘤多類細胞中的存在性相對廣泛, 其活性對于腫瘤細胞能量的代謝可起到維持效果, 有助于生成新血管, 對腫瘤的轉移和增殖起到十分關鍵的推動作用[1]。據相關研究表明[2], 在多種腫瘤的組織中HIF-1α可對其生物學行為進行表達和調節, 如腦腫瘤、宮頸癌、乳腺癌、肝癌等。最近幾年, HIF-2α被臨床發現, 與HIF-1α間屬蛋白的同系物, 因此, HIF-2α也具備核轉錄的活性, 二者間DNA識別位點相似[3]。本文針對HIF-1α、HIF-2α早宮頸癌組織中的表達進行檢測, 探析二者與宮頸癌間關系和相關性, 有利于后期臨床的診治。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2018年1月~2019年12月160例在本院實施手術切除的宮頸鱗狀細胞癌患者的宮頸腫瘤組織, 其中原位癌104例、浸潤癌56例, 浸潤癌中例淋巴結存在轉移24, 無轉移32例, 患者年齡40~82歲, 中位年齡為61歲, 未在術前接受任何治療, 如放化療等, 無炎癥性相關疾病, 術后病理進行證實, 納入標準:160例患者的組織病理學結果與宮頸癌符合, 確診為宮頸癌;未接受術前的免疫治療和放化療;年齡>18周歲[4]。排除標準:診斷結果未明確為宮頸癌或未診斷組織病理學者排除;其他系統存在惡性腫瘤者排除[5]。
1. 2 方法
1. 2. 1 組織處理 切除患者組織后以福爾馬林100 g/L對其進行處理并固定, 以石蠟包埋, 連續切片4 μm厚備用。
1. 2. 2 免疫組織的化學染色 取切片完成脫蠟去水, 為修復其抗原, 給予其0.1%的檸檬酸進行微波處理, 以3%的H2O2做封閉處理。4℃孵育過夜為一抗, 室溫孵育0.5 h為二抗, 通過二氨基聯苯胺(DAB)完成顯色, 復染脫水使借助蘇木精, 在透明的封片上以光鏡對其實施觀察。一抗代替由硫酸緩沖鹽溶液(PBS)控制陰性質量, 陽性質量由已知陽性片控制[6]。
1. 3 觀察指標及判定標準 比較HIF-1α、HIF-2α在宮頸浸潤癌組中的免疫組化染色得分以及在宮頸浸潤癌、原位癌中的表達率, 分析宮頸浸潤癌中HIF-1α蛋白、HIF-2α蛋白表達相關性。染色細胞漿或胞核至棕黃色、淺黃色、黃褐色的顆粒即為HIF-1α、HIF-2α陽性的表達, 以細胞的陽性率評分+染色強度之和判定HIF-1α、HIF-2α的表達。隨機選取五個高倍鏡視野展開判斷:0分表示無染色, 淺黃色(弱染色)為1分, 棕黃色(中等染色)為2分, 黃褐色(強染色)為3分。細胞的陽性率≤5%則視為0分, 1分表示細胞陽性率為6%~25%, 2分表示陽性率為26%~50%, 3分表示陽性率為>50%[7]。上述兩項之和若為0分則表示陰性(-), 結果在1~2分間為(+), 結果在3~4分間為(++),?結果在5~6分間則為(+++)。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2.0統計學軟件處理數據。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相關性檢驗采用應用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法。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 1 HIF-1α、HIF-2α在宮頸浸潤癌組中免疫組化染色得分比較 HIF-1α在宮頸浸潤癌組免疫組化染色得分中為(1.55±1.61)分, 低于HIF-2α的(4.50±1.05)分,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 2 HIF-1α和HIF-2α在宮頸的浸潤癌、原位癌中的相應的表達率分析 HIF-1α在宮頸浸潤癌、原位癌中陽性表達率分別為78.6%(44/56)、57.7%(60/104), HIF-2α分別為85.7%(48/56)、65.4%(68/104)。宮頸癌級別越高HIF-1α、HIF-2α蛋白表達率則越高。
2. 3 宮頸浸潤癌中HIF-1α蛋白、HIF-2α蛋白表達相關性分析 據Spearman相關性分析得出, 浸潤癌中HIF-1α蛋白、HIF-2α蛋白表達呈正相關,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r=0.854, P<0.05)。見表1。
3 討論
在全球女性惡性腫瘤中宮頸癌較為常見, 其發生率在乳腺癌之后, 位居第二位。而發展中國家的婦女宮頸癌發生率位居第一, 給女性生殖的健康帶來嚴重的影響[8]。伴隨著迅猛發展的細胞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 以及不斷提升和完善的檢測基因技術及診斷技術, 現證實多因素、多基因的作用結果與該疾病的發生、發展關系密切, 且在宮頸癌演進期間它們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9]。
宮頸癌常因異常的血管功能和結構、組織氧耗量不同等原因, 組織出現程度不一的缺氧區域, 此現象與其他的實體腫瘤相同[10]。而決定細胞生存與否的關鍵環節即為細胞耐受缺氧的能力。相關文獻治療指出[11], 腫瘤細胞耐受缺氧的能力與化療、放療、是否轉移、惡性的程度等存在相關性。氧在眾多基質中較為關鍵, 不論是信號的傳導, 還是細胞的代謝, 其作用均十分重要, 多細胞生物生理正常的功能及存活與氧關系密切。缺氧在病理及生理的過程中屬基本體征的一種, 氧穩態之所以得以維持, 其分子機制的關鍵點在于經HIF誘導相關基因的表達, 介導細胞逐步對缺氧反應開始適應[12]。Semenza和Wang于1992年首先發現了HIF, 其家族主要亞型可分為以下幾種, 即HIF-1、HIF-2、HIF-3, 在細胞適應性的缺氧中前兩者會參與調解[13]。上述三種HIF均為異源二聚體的轉錄因子, 其組成包括β亞基和獨特的α亞基, 含有的HIF-1β亞基均相同, HIF-1、HIF-2、HIF-3、HIF-1β均屬Bhlh-PAS家族。HIFα亞基、β亞基分別具有活性、功能性和結構性, 前者受氧調解, 后者不受, HIF在氧濃度正常的條件下, 其降解、表達會持續進行, 維持其細胞或組織內的表達量在較低的水平, 而缺氧條件下水平才會穩定[14]。HIF在常氧狀態下的降解主要取決于PHD(脯氨酰羥化酶), 其可羥基化α亞基中的脯氨酸殘基, 借助泛素連接酶、pVHL使復合物形成, 并以泛素途徑完成α亞基的降解, 機體內含氧濃度一旦下降, 未能完成α亞單位的降解, 進入核內, 在內部和HIF-1β產生作用異源二聚體形成, 激活轉錄目的基因, 讓其生物活性充分得以發揮。
機體的細胞、組織在生理狀況下氧濃度在所在條件下若降低, 可加大HIF-1α、HIF-2α的表達, 缺氧發生后, 介導細胞的反應為適應性反應, 進而維持內部環境基本的穩態[15]。且在惡性腫瘤細胞缺氧性的適應中HIF-1α、HIF-2α發揮的生物學作用同樣十分關鍵, 因腫瘤組織生長期間過快的增生, 致使缺氧現象在局部組織內狀況較為嚴重, 為將腫瘤細胞對缺氧的適應性實現, HIF可對生成腫瘤血管起到誘導效果, 進而更改相關的基因表達, 如能量的代謝等。文獻大量資料表明[16], HIF-1α、HIF-2α的表達在大部分的實體瘤組織中較高, 如神經膠質瘤、乳腺癌、膀胱癌、宮頸癌、腎癌等, 且經調控血管的生成等, 讓腫瘤組織對因過度生長的細胞而出現的微環境逐漸適應, 對于腫瘤的侵襲、生長作用十分關鍵。在腫瘤的發展中HIF-1α、HIF-2α的作用雖然十分關鍵, 但有關研究表明[17], 而二者具體作用的機制存在差異。現階段臨床逐漸以抗血管生成靶向對腫瘤站開展相應的治療, 而HIF-1α、HIF-2α作為調控實體瘤血管生成的參與分子, 其作用十分關鍵, 因而明確二者與癌癥組織間的表達及相關性的意義十分關鍵。HIF-2α在結腸癌中表達率降低, 而HIF-1α在結腸癌中表達率不變, 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與結腸癌的發展變化間相關性較高, 在治療結腸癌中需對HIF-1α、HIF-2α等特異性予以考慮。
綜上所述, HIF-1α、HIF-2α在子宮頸鱗癌的組織中有表達存在, 而在浸潤癌中HIF-1α、HIF-2α的表達呈正相關, 且在宮頸浸潤癌中HIF-2α免疫組化染色得分高于HIF-1α, 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宮頸癌級別越高, HIF-1α、HIF-2α蛋白表達率則越高, 表明在宮頸癌發生、發展、浸潤轉移期間, HIF-1α、HIF-2α可能有協同作用存在。
參考文獻
[1] 高雁榮, 郭玉. 老年宮頸癌組織中轉化生長因子-β1、叉頭框蛋白P3、程序性死亡蛋白1及其受體的表達及意義. 中國老年學雜志, 2018, 38(10):2350-2353.
[2] 李娜, 熊嬌, 史明媚, 等. 宮頸癌組織中組織因子途徑抑制物-2表達變化及其與VEGF表達、微血管密度的相關性. 山東醫藥, 2018, 58(3):59-61.
[3] 郭麗梅, 戴守勇. 宮頸癌組織FoxM1蛋白的表達特點及其與病理學特征、預后的相關性. 癌癥進展, 2018, 16(5):640-642.
[4] 許振, 劉志強, 孟瑋, 等. 宮頸癌組織中maspin、AKT、p-AKT表達變化及其與腫瘤微淋巴管密度的相關性. 山東醫藥, 2017, 57(27):23-26.
[5] 李秀福, 賈世峰, 耿彤瑤, 等. 宮頸癌組織中miRNA-125a、STAT3、 IL-10的表達變化及意義. 山東醫藥, 2018, 58(13):1-4.
[6] 劉東伯, 楊麗, 周洋媚, 等. HMGB1、Notch1、PCNA在宮頸癌組織的表達及臨床意義. 中國計劃生育學雜志, 2018, 26(9):
793-797.
[7] 王慶西. 老年宮頸癌組織中人乳頭狀瘤病毒16-E6、p53 mRNA表達及其與放療敏感性的相關性. 中國老年學雜志, 2017,
37(22):5622-5624.
[8] 張華, 路喜安. 宮頸癌組織中受體相互作用絲氨酸/蘇氨酸蛋白激酶4高表達與宮頸癌預后的相關性分析. 山西醫藥雜志, 2018, 47(8):865-867.
[9] 張少娟, 嚴莉, 曲洪濱, 等. 宮頸癌組織miR-135a-5p、GATA3、
STAT3表達變化及其臨床意義. 山東醫藥, 2019, 59(31):61-63, 67.
[10] 遲龍青, 楊薇薇, 劉宇, 等. 宮頸癌組織中人乳頭瘤病毒16-E6基因整合/整合率與臨床病理資料相關性分析. 國際免疫學雜志, 2018, 41(1):19-22.
[11] 李娜, 熊嬌, 史明媚, 等. 宮頸癌組織中組織因子途徑抑制物-2表達變化及其與VEGF表達、微血管密度的相關性. 山東醫藥, 2018, 58(3):59-61.
[12] 李秀艷, 郭麗, 卜琦等. 宮頸癌組織lncRNA GAS5、miR-205表達變化及其與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山東醫藥, 2019, 59(31):70-73.
[13] Semenza GL, Wang GL.A unclear factor induced by hypoxiavia de novo protein synthesis binds to the human erythro-poietin gene enhancer at a site required for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Mol Cell Biol, 1992, 12(12):5447-5454.
[14] 周玉飛, 岳青芬. miRNA-21、miRNA-34a在宮頸癌、CIN、正常組織中的差異性表達及對宮頸癌早期診斷價值. 實用醫學雜志, 2018, 34(17):2888-2891, 2920.
[15] 黃志軍, 王遙, 崔國英, 等. 宮頸癌組織人類白細胞抗原F表達變化及其與患者臨床病理參數的關系. 山東醫藥, 2018, 58(16):
89-91.
[16] 黃麗鳳, 梁夯, 張立峽, 等. HPV16E7在宮頸癌組織中表達升高并促進宮頸癌細胞系HeLa和C33A的增殖. 基礎醫學與臨床, 2019, 39(11):1537-1542.
[17] 宋曉環. 宮頸癌患者癌組織中內皮特異性分子-1和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蛋白的表達及意義. 中國老年學雜志, 2018, 38(13):3233-3235.
[收稿日期:2020-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