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的花紋
黃昱寧
毫無疑問,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是我的翻譯生涯里遭遇的最難啃的骨頭之一。《螺絲在擰緊》(The Turn of the Screw)之后,我再次面對他的中篇小說《地毯上的花紋》(The Figure in the Carpet),既躍躍欲試,又一籌莫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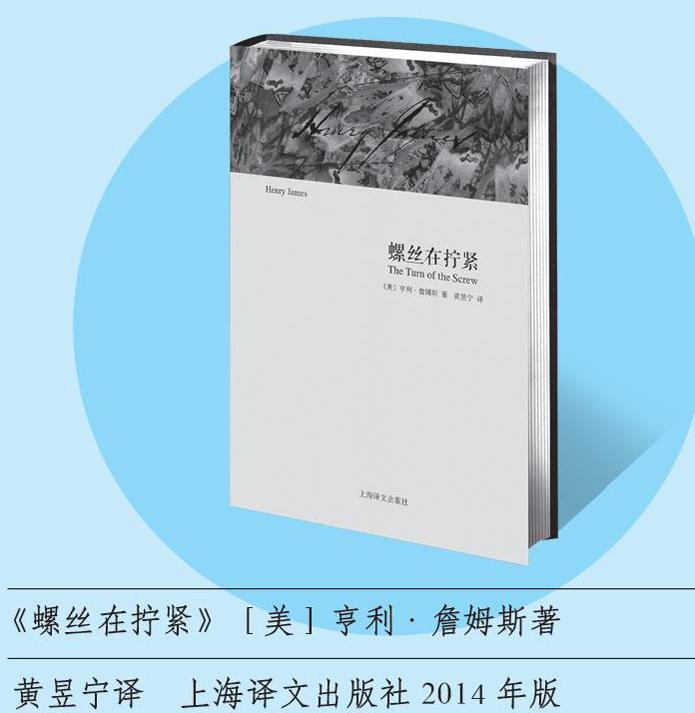
一籌莫展是因為,詹姆斯的文本,無論是對其語法的理解層面,還是對其意義的闡釋層面,都有著讓人深感受挫的難度。第一遍讀下來,小說里的情節和人物都如鬼魅般忽明忽滅,躲開一切明確的結論—你橫豎抓不住什么。十九世紀末英美文學圈的生態,隱約在小說中現出輪廓,有時細節纖毫畢現,有時又仿佛置身于半透明的罩子里,被看不見的手夸張而劇烈地搖晃。顯然,這不是一部以古典現實主義準則構建的小說,它具有某種詹姆斯筆下特有的迂回而不安的現代性。
躍躍欲試是因為,這一篇雖然譯成中文后僅三萬字,卻在詹姆斯的寫作生涯中具有非常獨特的風格和相當特殊的地位。小說首次發表于一八九六年一月號的《大都會》月刊(Cosmopolis),這本雜志雖然只存在了三年,卻有過不小的排場:總部在倫敦,且在柏林、巴黎和圣彼得堡同時發行當地的版本,很吻合小說中描述的當時報刊日益“國際化”的風潮。同年,這篇小說被收入詹姆斯的中短篇小說集《尷尬種種》(Embarrassments),英國版與美國版同時面市。回過頭來看,《地毯上的花紋》是這本書里影響最大的篇目,而標題“地毯上的花紋”也漸漸成了一個被后世頻繁引用的文學典故。英國小說家、評論家福特·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曾經說過,自從這篇小說出版之后,詹姆斯的同齡人就開始追求“地毯上的花紋”,希望能將原本復雜難辨的“花紋”變成清晰可鑒的物質實體。在發表于一九四一年的散文中,T. S.艾略特幾乎把同樣的話又說了一遍:“如今,我們都在尋找‘地毯上的花紋。”
小說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是個賺過一點稿費卻苦于在圈里寂寂無聞的寫手。明顯比他更為資深,主要以寫評論為主的考威克因為來不及完成著名作家維雷克新作的書評,把這個機會轉給了“我”。“我”以為抓到了在文學圈里進階的機會,不料卻像是一頭撞進了一座迷宮。維雷克對于這篇評論不屑一顧,并且拋出了一系列炫目的名詞和意象,引誘“我”追逐對于其作品的終極破解:
在他本人看來,毫無疑問,那個讓我們不勝迷惘的東西,明明是清晰可見的。那玩意,我猜想,就藏在最初的規劃中;宛若波斯地毯上的一個復雜的紋樣。當我使用這個意象時,他表示高度贊賞,而他自己則用了另一種說法。“它就是那根線,”他說,“把我的珍珠串起來的那根!”
此后的情節發展就進入了詹姆斯最善于營造的詭異瘋狂的敘事鏈。“我”對于維雷克(毋寧說是小說這種文體)的“整體意圖”的追尋,注定要像《螺絲在擰緊》中那個關于“莊園里有沒有鬼”的命題那樣,經受百般折磨,經受“真諦”在眼前閃現又幻滅的海市蜃樓般的瞬間。洞悉維雷克的秘密的人(或者說“我”以為洞悉秘密之人)一個接一個遭遇不測。詹姆斯得心應手地折磨著讀者的耐心,在人物細節和對話里嵌入可以引發多重理解/誤解的隱喻。熟悉詹姆斯套路的讀者,幾乎在小說進行到一半時就能判斷:直到結尾,我們也得不到答案。
但我們還是會一口氣讀完它。我們知道,像很多具有元小說特質的現代主義作品一樣,這是一部闡述小說觀念的小說。小說里的小說家和評論家的關系,是一種近乎貓捉老鼠的關系。小說文本的“整體意圖”被層層包裹,被繁復衍生,被漸漸失去節制地神秘化。批評家瘋狂地追逐它,而小說家則似乎一直在使用各種障眼法躲開這種追逐,這樣的關系越來越具有奇特的儀式感。地毯上到底有沒有花紋,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批評家和讀者的興趣和精力,在這個過程中被刺激、被撩撥,同時也被消解、被損耗—像表演、像愛情、像生死。作為由古典主義向現代主義過渡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對于時代風氣的觀察,對于小說作為一種敘事游戲的深層思考,都滲透在文本的肌理中。
在這篇小說里先后出現的幾個命運多舛的人物,我們無法確認哪一個更能讓詹姆斯產生代入感;我們同樣無法確認詹姆斯是否要通過《地毯上的花紋》表達現代小說家和批評家的使命和宿命。(是使命多一點,還是宿命多一點?)可以確定的是,詹姆斯之后的寫作者,越來越深切地體驗到他在這篇小說里所傳達的那種時而狂喜、時而虛無的復雜感受。“二戰”結束之后陸續涌現的文學名詞和小說流派,可能比此前的總和都多。對于普通讀者而言,弄清現代主義究竟在哪個時間點進入后現代主義,“后殖民”與“新歷史”分別代表什么意思,或者推理小說究竟分出多少亞類型,并沒有太明顯的意義。社會現實的動蕩和傳播方式的劇變,使得小說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信任感漸趨微妙。敘事套路仿佛已經窮盡,連“生活比小說更精彩”都成了老生常談。小說家進退兩難,時而希望勇往直前,沿著文體實驗的道路越走越遠;時而又希望重溫現實主義的榮光,回歸古老的故事傳統。
在現代文學的語境中,小說家與批評家,作品的創造者和詮釋者,他們之間究竟有沒有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默契,密碼有沒有可能被完美破解?我們從這個既抽象又具體,甚至有時候頗具哥特風格的故事里,看不到詹姆斯對此有任何樂觀的表示。故事的荒誕走向甚至讓人聯想到那個著名的思想實驗:A和B兩位將軍,各自盤踞在兩座山頂,需要同時攻擊山谷處的敵人,但他們之間的通訊只能穿過敵方陣線進行。A給B發了個信息:“明天出擊?” B回答:“可以。”但B不知道自己的回復有沒有到達,而A必須給B發送另外一條信息來確認已經收到了B之前的信息,從而確保B會行動—實際上,為了達成完美的共識,他們需要發送無窮無盡的信息。
《地毯上的花紋》就在這種看不見盡頭的努力溝通中戛然而止。然而,也許,無論是密碼被(簡化地)破解,還是因為無法破解而失去對破解的渴望,都會使小說的魔法黯然失色。這真是個繞不出去的悖論,但敘事藝術的奇跡和榮光,也恰恰蘊含在這悖論中。畢竟,詹姆斯狡黠地在絕境中也留著一星微暗的火:
如果說,她的秘密(按照她的說法)便是她的生命—這一點,從她越來越容光煥發的樣子就能窺見端倪,她那因為意識到自己享有特權而流露的優越感,被她優美而仁厚的舉止巧妙化解,使得她的容貌教人過目難忘—那么,迄今為止,它并未對她的作品產生直接影響。那只是讓人—一切都只不過讓人—越發覬覦它,只是用某種更美好更微妙的神秘感將它打磨得圓潤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