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人
劉墨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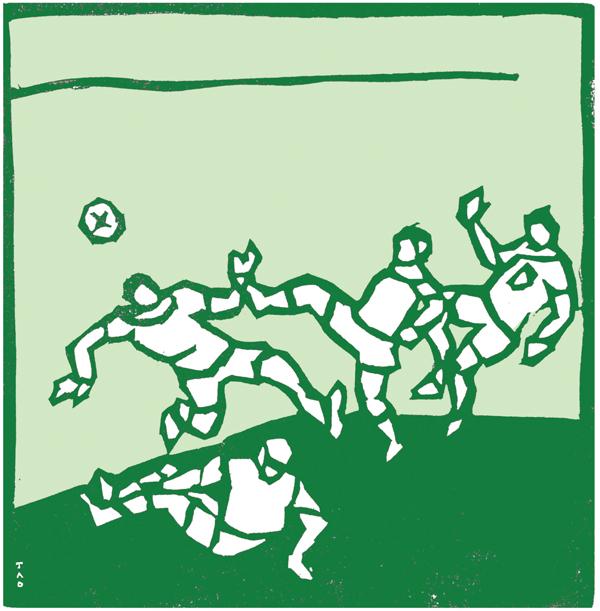
1
老王曾經(jīng)是個職業(yè)球員,巔峰時期與國家隊擦肩而過,后來頻繁更換東家以證明自己的剩余價值。退下來后,他到我們高中當體育老師,兼職球隊教練。
老王的兒子小王從生下來就看爸爸比賽,跟著爸爸東奔西走,連帶著享受了不少賽場的刺激和歡呼。小王從小就渴望能像他爸爸一樣馳騁在賽場上。
但是,這條路太難走,老王并不想讓自己的兒子在三十多歲時就像自己一樣,如此艱難地謀生。他希望自己的兒子能考上大學,念法律或者經(jīng)濟,有一份穿著西裝的工作,資歷與年紀成正比,不怕衰老,不用控制飲食和保持體能,沒有傷病。
但小王過早地展示出自己的執(zhí)念。在初中的賽場上就聲名鵲起的小王,如愿進入重點高中,就是老王所在的學校。開學沒多久,他就參加了校隊的選拔,但是一去就被老王送了回來。他們父子在那段時間頻繁地吵架,互不相讓。
后來,小王的媽媽從中調解,最終在小王不耽誤學習的情況下,老王同意他加入校隊。就這樣,每天下午三點,小王和其他隊員一樣,開始在操場上折返跑熱身,參加校隊的訓練。但是,他始終得不到正賽的上場機會。
球員的場上狀態(tài),是需要大量的比賽去鍛煉的。如果上場的時間越來越少,他的競技狀態(tài)和運動敏感度都會大大下降,所以對一個球員來說,長期不讓他比賽,無異于斷送他的運動生涯。
我們要去廣州比賽的消息傳到隊里時,每個人都很興奮。小王也很高興,他訓練越來越積極,并開始調整作息。
但是,最后公布的大名單里并沒有他的名字,老王又一次把他留在了學校。那天,小王脫下隊服,回到教室,從此,下午三點的訓練,他再也沒有來過。
退隊的小王像換了個人一樣,不說話,很孤僻。有時候,我們在學校比賽時偶爾會看見他,他遠遠地站在操場邊的花壇附近觀戰(zhàn),看一會兒就走。
2
日子匆匆而過,市里比賽的日子越來越近,隊里的人員進進出出都有調整。我們隊的中鋒和后腰人才濟濟,但前鋒只有一個。這讓老王很憂心。
我鼓起勇氣建議老王召小王入隊集訓。老王表情復雜地問我:“你覺得他能行?”
小王就這樣回來了,前提是老王答應了給他出場的機會。像得到爵位的騎士一樣,小王忘乎所以地馳騁在賽場上。
正式比賽的日子很快就來了,我們排隊,隨著裁判走進場地,同學和家長們在空曠的觀眾席上搖旗吶喊。那天,小王的媽媽也來了。盡管如此,小王也沒有首發(fā)出場。
上半場,我們踢得很拘謹,讓對方抓住機會先入一球。中場休息,我們灰頭土臉地下來。下半場要加強進攻,爭取扳平。這時,隊長提出讓小王上,我們都同意隊長的提議,老王卻猶豫不決。
終于在下半時開場前,老王才吐出一句:“王宏斌,你上吧,我們打雙前鋒。”
小王等這個機會太久了,他先是頓了一會兒,然后迫不及待地開始熱身,動作大得有些變形,微微有些顫抖。
下半場雙方拼得很猛,都有破門的機會,卻都錯過了。直到我們抓住一次防守反擊的機會——對方在中場附近丟了球。隊長一眼看見在左路奔跑的小王,他大腳開出,將球長傳出去。小王跑得太快了,把對方的后衛(wèi)遠遠地甩在后面。反越位成功后,他接住傳球帶入禁區(qū),然后故意將身體傾斜至一邊,晃開守門員的撲救,最后將球狠狠地射向遠角——教科書般的進球。
進球后的小王撲向場邊,他沖父親大聲咆哮:“這才是我,你看見了嗎?這才是真正的我,你看見了吧!”
坐在教練席后面的小王媽媽緊張地看著發(fā)生的一切。他們父子又針鋒相對地彼此對視了一會兒,直到小王被前來慶祝的隊友撲倒在地,這場對峙才有了一個不那么尷尬的收尾。
我們依靠小王的進球扳平了比分,但是下半場我們的體力出現(xiàn)了問題,對方抓住機會又入一球。最終,我們還是輸?shù)袅吮荣悺?/p>
走下球場的小王發(fā)現(xiàn)父親教練席的位置空了,他在父親的位置左右尋了一會兒,然后問看臺上的媽媽:“我剛才是不是太大聲了?是不是又惹我爸生氣了?”
一絲欣喜居然掛在他媽媽的臉上,她激動地說:“沒有,你爸沒生氣。你慶祝完跑開后,他開心地大笑起來,然后什么都沒說就笑著走了。”
小王如愿以償?shù)貐⒓油旰竺嫠械谋荣悺D悄辏覀冏罱K排名第八,不是很理想,但我們盡力了。
3
高中畢業(yè)后,小王離開家,去了南京上大學。他如愿以償?shù)卦趯W校里踢球,也進了校隊。
小王大二那年,老王去南京看他。小王帶著老王在學校里逛,帶他去圖書館、教學樓、文體中心,當然還有綠茵場。小王讓老王觀摩自己訓練,大學的教練走過來親切地向老王問好,老王害羞地回應著。
小王一只手搭在父親的肩膀上說:“您那套過時了,讓您看看現(xiàn)代體育是怎么訓練的。”
從前鋒到后衛(wèi),每個位置的訓練方法都不一樣,從有氧功能到訓練負荷等都有新的訓練方式。助教在小王身上來來回回地繞上許多皮筋,然后小王有規(guī)律地運動起來,練習身體的協(xié)調性。老王一邊看一邊記,好像是想能了解多少就了解多少。
走的時候,老王對小王說自己是真的落后了,再干幾年也想卸任了。小王沒想嘲諷爸爸落后,他只想讓老王為他高興,這始料不及的陰差陽錯讓小王久久不能釋懷。
大學畢業(yè)后,小王沒有繼續(xù)踢球,而是回來在一家私企做培訓。平日里,他在各個城市之間來回奔波,到了周末,就和中學同學組個球隊繼續(xù)踢球。
那年五月,老王正在學校的食堂里打飯,不知怎么就暈倒了。被人送到醫(yī)院后,大夫確診為腦血栓。
剛剛五十六歲的老王,完全沒有想到自己會得這個病,還沒到退休的年紀就不得不顫顫巍巍地端著手,口齒不清,需要人照顧。
4
小王從球隊里退出來,他再也沒有時間踢球了。工作的忙碌、家庭的壓力,讓小王老得很快。他開始迅速發(fā)胖、脫發(fā)。短短一年光景,他居然有了早衰的前兆。
有一天,球隊里的老同學告訴小王,母校快到校慶了,屆時他們要回學校去踢友誼賽,許多老朋友都會去,讓他也去,算為校慶獻禮。小王非常想去,但是想了想父親的情況,他還是拒絕了。
回到家后,老王不知道從哪兒知道了這個消息,他顫抖著指揮小王,讓他回母校去比賽。不僅要小王去,他也要回去看看。
比賽那天,老王穿回自己任教時常穿的灰藍色運動服,在妻子和兒子的攙扶下,走過操場,走到看臺邊坐下。不時有人過去打招呼,有人喊:“教練。”“王頭兒。”也有人喊:“王老師。”
老王僵硬地笑著點頭,大家適當?shù)睾眩蛛x開,保全老王的自尊。小王在一旁安靜地看著,他已經(jīng)很久沒有像這天這樣放松了。
小王拼命地把腰間的贅肉往衣服里塞了塞,我們毫不留情地彼此嘲笑,然后笨拙地奔到球場上。
比賽開始前,裁判跑到觀眾席,將哨子遞給老王,說請王老師吹開場哨。老王深吸一口長氣,吹了一個連續(xù)哨,斷斷續(xù)續(xù)的哨聲緩緩入場,友誼賽就這樣開始了。
我們先開球,隊友倒了幾腳后就把球塞給我。我沿著邊線過了一個人,遠遠地看見小王笨重又努力地往前奔著。我忽然鼻子一酸,毫不猶豫地把球大面積轉移給他。
小王迎著球的方向跑,他一邊跑,一邊用余光盯著場邊的老王。他看見患腦血栓的父親拄著拐杖堅定地站在那里,哆哆嗦嗦地揮手喊著:“加油,兒子加油!”
這幾個字從老王嘴里吐出來時,根本聽不清是什么,但是父親奮力想說的樣子,讓小王哭得像個丟了玩具的孩子。
口水不斷地從老王的嘴里流出來,身邊的妻子一邊幫丈夫擦,一邊替兒子加油。小王就這樣義無反顧地跑著,好像身上的贅肉都認真起來,身上的年輪也緊繃著做最后的沖鋒,眼淚也被他狠狠地甩在身后。
他跑,好像十六歲時第一次被換上場一樣;他跑,好像他在人生賽場上替換下的,是自己的父親。
(張秋偉摘自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特別不浪漫》一書,本刊節(jié)選,張伯濤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