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醫生變得更好
依靠個人“抗性”永遠不夠,醫療衛生系統必須有所改變。
如今苦惱的醫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1,無論年齡、專業、性別、種族、資歷如何,抑或是隸屬于公立還是私立的衛生系統,都是如此。應當由臨床醫生個人還是他們所在的衛生系統著手解決這個問題?這值得我們思考。
受精神疾病、情緒疲憊和焦慮影響的醫療衛生專業人員的比例正在增加2-3。世界各地的原因基本相同,包括:與患者接觸時間短、喪失連續性、值班室等便利設施的撤銷、傳統的同輩幫助和上級支持因輪班制而弱化、公眾對醫學的期待過高而不切實際、醫療衛生服務的產業化將醫療轉變為生產線、管理負擔日益增加,以及對以更少資源消耗提供更多醫療衛生服務的期待。
責備文化
醫生們在越來越多的訴訟和責備中工作,承擔著全部責任卻失去了權威和自主。如果無法提供患者應得的高質量醫療服務,他們就會苦惱4,可能認為必須始終保證自己無可指責。有評論者指出,醫生常常為了維持良好職業人格而苦苦掙扎。為了維持良好的職業人格,他們需要做到很多,包括具備自我犧牲精神和否認自己存在弱點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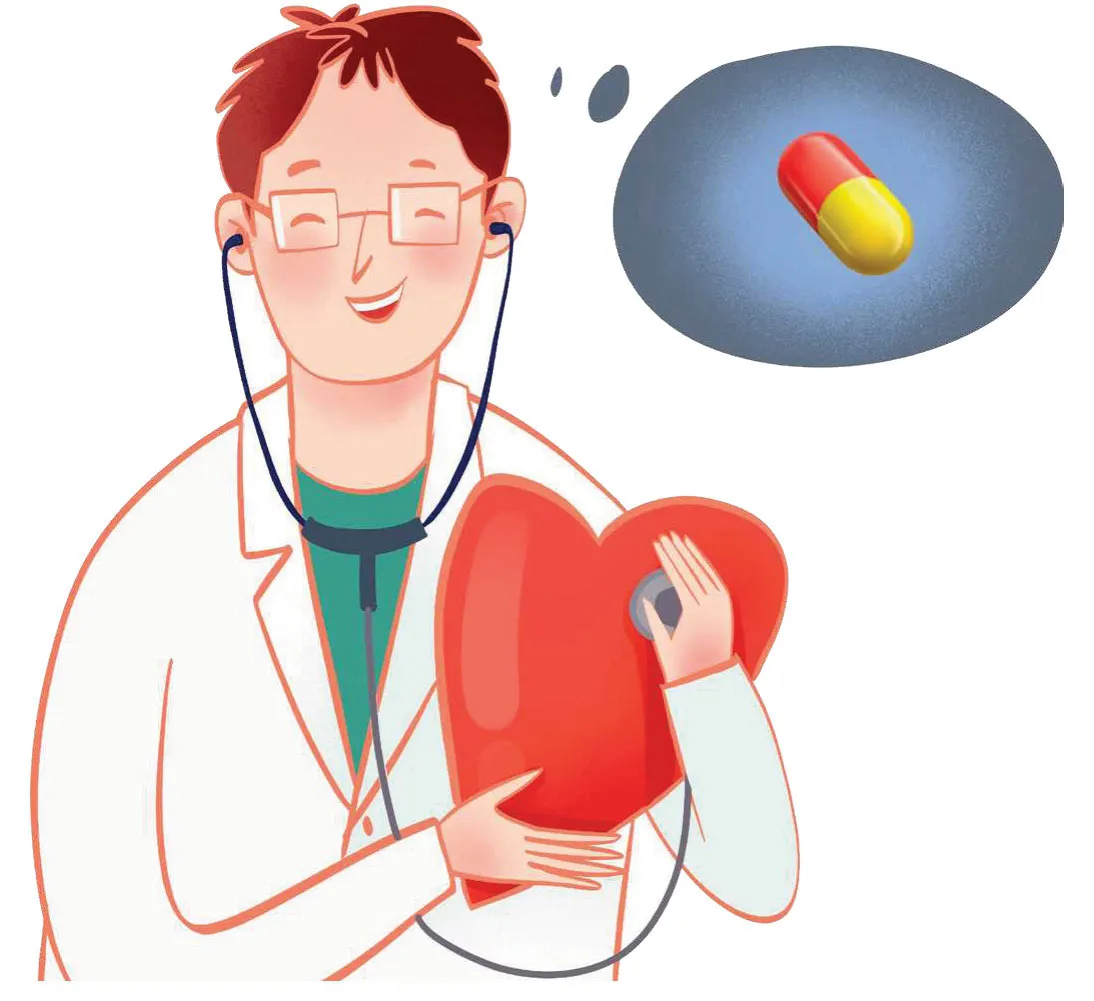
為向患者提供最安全和最優質的照護,保持臨床醫生的身心健康至關重要。
許多醫生覺得自己被醫療衛生專業人員的角色給“定義”了。這種“醫療自我”的誕生,被認為是來自醫療培訓期間職業身份和個人身份的融合6。“醫療自我”可以用于掩蓋痛苦并保護醫生免受內疚、恐懼和絕望的困擾。然而,如果“醫療自我”的職業側面占主導地位,醫生可能會忽視其健康和福祉所必需的個人角色,包括他們生病時作為患者的角色。
因此,“醫療自我”必須得到平衡,手段包括健康的工作環境、為醫生提供的支持和業余愛好。然而,旨在提高臨床醫生福祉的舉措大多效果有限,因為它們側重于對醫生個體的支持而忽視了更廣泛的環境。對醫生個人的支持如正念訓練、壓力管理和小組討論可以緩解醫生的職業倦怠,但是對有精神健康問題的臨床醫生影響不明顯7-8。過去大都采用抗性訓練(resilience training)來幫助醫生抵抗衛生系統帶來的壓力因素,而最近,這種方法遭到了臨床醫生的質疑甚至拒絕9-10。
要培養臨床團隊,使醫生產生歸屬感,并同時做好“基于循證醫學的臨床實踐”和“醫生自主權”之間的平衡(有時二者相互沖突),重構工作模式、縮短值班時間十分重要,但醫療衛生機構可以改善之處遠不止于此3,7,11。
只有涵蓋整個衛生系統的方法能使臨床醫生、患者和公眾之間就醫學及從業者的局限性進行坦率的討論。例如蘇格蘭有一個“現實醫學”(Realistic Medicine)的概念,旨在配合宏大的國家改進計劃,在全社會的層面滿足公眾期望12;“改變醫學面目”(Changing Face of Medicine)項目,鼓勵醫生思考其傳統角色的變化,并考慮如何重新設計自己的角色和任務以保證患者的最大利益13。但另一方面,諸多事實,特別是Bawa-Garba案例[1]使我們必須改變由來已久的責備文化,這種文化使醫生恐懼,迫使其自衛14。
最后,我們需要在醫務人員和患者之間達成一種新的共識,允許醫生作為有缺陷的人而存在,并且能夠說“我已經盡力了”。我們需要恢復基于團隊的醫療培訓,而不是繼續相信輪班制度和毫無感情的電子檔案中增添的個人反思可以替代共同學習的同志情誼。因此必須為Schwartz查房[2]和巴林特小組(Balint Group)[3]等基于團隊的反思活動創造空間。我們應該恢復專門用于開會、思考和交流的場所,但最重要的是整理醫生的職業生活,給他們時間和空間來享受工作。
The BMJ是醫生福祉的捍衛者。適逢10月4日和5日召開的第十屆醫師健康計劃——受傷的醫者年會,我們組編了過去幾年The BMJ發表的相關文章的電子版合集(www.bmj.com/wellbeing),包括最近發表的幾篇關于員工參與的重要性15、如何應對霸凌同事16,以及改善夜班睡眠17的文章。我們還在考慮如何改革醫療系統18,將從業者把醫療工作看成“生產線”上的工作這種思維轉變為“與患者合作產出服務”的態度19。
根本性改變
我們認為需要對文化、系統和實踐進行根本性改變,以幫助維護和改善所有醫療衛生專業人員以及患者的福祉。我們召集了一個專家顧問小組,以明確了解這些問題,并歡迎廣大讀者將你們最關心的告訴我們,以便我們調整活動優先事項。
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和對醫療的預期提高,醫療衛生系統的壓力將不可避免地增加。為向患者提供最安全和最優質的照護,保持臨床醫生的身心健康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