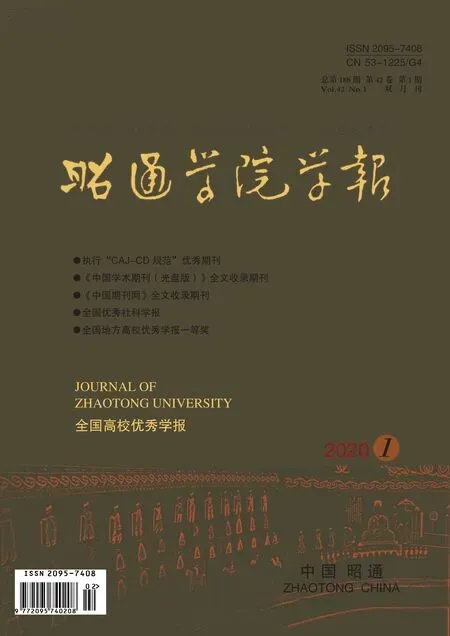方志興修與國家認同
——明代烏蒙山地區地方志修撰考略
胡 超
(西南民族大學 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一、明代烏蒙山地區行政區劃建置及其區域特征
烏蒙山脈坐落于貴州高原西北部和滇東高原北部,呈東北-西南走向,橫跨今貴州畢節、六盤水、黔西南,云南昭通、曲靖、昆明北部一帶,長時間以來都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域。元代以前中央王朝對這些地區多實行“統而不治”的“羈縻”政策,元朝平定云南后先后在此設立“烏撒烏蒙宣慰使司”(轄烏蒙路、烏撒路、東川路、芒部路)、“曲靖宣慰使司”(轄曲靖路、普安路、普定路)等土司機構,以流官為正,土官副之。明洪武十四年明太祖命征南將軍傅友德率藍玉等人領十四萬大軍平定云南,分胡海洋一支偏師由永寧進兵以進攻攻烏撒等部,白石江大戰擊敗元軍主力后,傅友德又自率大軍“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1]8003,與胡海洋等人合軍一處擊敗了烏撒等部彝族土司。洪武十五年平定烏撒等部后,以元東川路、芒部路、烏撒路、烏蒙路、普安路、曲靖路、仁德府分置東川軍民府、芒部軍民府、烏撒軍民府、烏蒙軍民府、普安軍民府、曲靖軍民府、尋甸軍民府,均屬云南。十六年因諸部叛亂,將芒部、烏蒙、烏撒改屬四川,十七年將東川改屬四川;二十一年普安軍民府被削,洪武三十三年(建文二年)設普安安撫司,永樂十三年革去,改設普安州,隸貴州布政司;成化十三年革去尋甸軍民府,改設尋甸府。其中尋甸軍民府改流后由流官管理;普安州、曲靖軍民府由流官主事,其治下均有土通判、土知州等土官名目;東川、烏蒙、烏撒、芒部四軍民府由土官主事,流官為佐貳;貴州宣慰司則不設流官。整個明代雖然在烏蒙山區進行了一些改土設流的工作,但大部分地區仍然是處于土官的管理之下。
而且烏蒙山區的土司“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于羅羅,厥后子姓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肇、水西”[2]2889-2890。其關系錯綜復雜,時而互相仇殺,時而聯合叛亂。由于該地區分屬三省,作為中間協調者的國家力量—川滇黔三省鎮巡官—往往也各執一端,難以協調,多次產生重新調整行政區劃隸屬的大討論。
總而言之,明代的烏蒙山區雖被劃歸三省,但這些地區的社會、政治結構存在著廣泛而深刻的聯系,因其少數民族土司地區的特殊性使得其區域特征明顯,劃分省域而治并未割裂烏蒙山區的整體聯系。
二、明代烏蒙山地區方志考略
方志修撰作為邊疆文化逐漸向內地靠近的一大參照因素,其修撰的次數可以看到其與“改土歸流”之間的關系。通過對《中國地方志綜錄》《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明代方志考》等志書目錄及《貴州圖經新志》、嘉靖《貴州通志》、萬歷《貴州通志》、嘉靖《四川總志》《正德云南志》等古方志中序跋和引用情況的梳理①,可以看到烏蒙山地區明代至少修撰了以下十四部方志,其中部分志書有存目而無作者及年代,但其修撰的時間段亦可就引用情況和存目情況看出。
(一)明代烏蒙山地區現存志書情況
1.六盤水地區
永樂《普安州志》十卷,修纂者不詳,永樂十六年(1418年)修,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有膠卷版[3]809。
嘉靖《普安州志》十卷,高廷榆修,寧波天一閣藏有嘉靖刻本,1961年上海古籍書店以天一閣本為底本影印了該志,2006年出版的《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輯》以該本收入。《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及《明代方志考》載其成書于嘉靖二十八年,卷首有蔣宗魯序一篇,并附永樂舊志序。蔣宗魯所作的《嘉靖普安州志·序》:“嘉靖昭揚赤奮若之歲,普安志成。”[4]3按此說則該志成于嘉靖癸丑年,即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若按志敘中稱“舊志成于永樂十六年,距今一百三十年矣”[4]10上,則剛好是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但志敘中雖然提到了該書綱目體例,但并未明言何時成書。且其科貢年表記至嘉靖乙丑年,即嘉靖四十四年(1564年)[4]37上,則天一閣本成書更在其后。
2.曲靖地區
《尋甸府志》二卷,王尚用修,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成書。卷首有王尚用自序。寧波天一閣存有嘉靖二十九年刻本[3]827
(二)未見存世的烏蒙山地區明代志書
據上列志書來看,烏蒙山地區現存明代的志書資料遠遠算不上豐富。但現存志書的狀況遠遠不能代表明代這一地區志書修撰的真實情況,通過對明代歷次修撰的貴州、四川、云南三省的通志、《大明一統志》《民國貴州通志·藝文志》以及明清兩代川黔邊界各地志書的序跋記載和引用的梳理,可以看到除了現存的3種志書外,還有一些明代修撰但久經歲月而亡佚的志書存在。除《明代方志考》已有考證出六盤水地區的景泰《普安州志》、萬歷《普安衛續志》;曲靖地區的《陸涼州志》《馬龍縣志》外,[5]415,423至少還有以下三個地區的七部方志。
1.東川區
《東川軍民府府志》,《大明一統志·卷七十二》“東川軍民府”條載東川風俗“貿易為業”,下注:“府志:‘夷人有一種,其一曰僰人’”[6]3237。《嘉靖四川總志·卷十七》風俗條完全照抄《大明一統志》,其后的《萬歷四川總志》論及東川、烏蒙、烏撒、芒部四軍民府幾乎完全照抄《嘉靖總志》,此處不論。至清初東川改流時該府志已亡佚,乾隆《東川府志》序說道:“滇蜀黔隸土人之地皆無志,不獨東川也。”[7]1清初時修志之人已不知有此府志存在。按東川在明洪武十五年設府,十七年改軍民府,當修于明洪武之后。考之于《文淵閣書目·卷四》“新志”條,確有《東川軍民府志》[8]230,成書年代當在正統《文淵閣書目》成書之前。
2.畢節地區
《烏撒軍民府志》,《明一統志·卷七十二》“烏撒軍民府”條載烏撒形勝“前臨可渡,后倚烏門”,下注出處:“郡志”[6]3242,風俗“刀耕火種,不事蠶桑,病不醫藥,惟禱鬼神”,下注出處:“郡志”[6]3242。當地在元代已有修撰志書,元李京著有《大德烏撒志略》四卷,《民國貴州通志·藝文六》記《大德烏撒志略》:“《方輿紀要》引‘元志’云:‘烏撒山崖險厄,襟帶二湖,羊腸小徑十倍蜀道’,即京書之文也”[9]554上。按該句在《大明一統志》中有引用,并注明出處均為‘元志’。與同書所注的“郡志”顯然不是同一部書。就烏撒、烏蒙等地設府的時間來看,郡志應修于明代《大明一統志》成書之前。考之于《文淵閣書目·卷四》“新志”條,有《烏撒軍民府志》[9]230。則該書成書更在正統《文淵閣書目》成書之前。
《烏撒衛志》《明一統志·卷七十二》“烏撒軍民府”條載烏撒風俗“荷氈披毳”,下注出處:“烏撒衛志”[7]3242。《弘治貴州圖經新志》“烏撒衛”一條載烏撒衛形勝“山高地險”,下注:“烏撒衛志:‘界于諸夷之中,山高地險,實西南要厄之處’”[10]173。由此來說該書應當在弘治前就已經成書。按《嘉靖貴州通志》對《烏撒衛志》的引用,此時《烏撒衛志》應當還流傳于世。《萬歷貴州通志》中已不見引用。《文淵閣書目》中亦不見收錄此書。
萬歷《畢節衛志》一卷,民國《貴州通志·藝文六》:“《萬歷畢節縣志》一卷,明高少室、韓襟江撰。”下文說道:“羅英《畢節縣志序》云‘畢志,明萬歷中高少室、韓襟江先生所撰’”[9]555上。按萬歷時畢節有衛無縣,故而不可能存在“縣志”。以民國《貴州通志》所引的史料源頭來看,高、韓二人編畢節志的說法最早是出自清代羅英的《畢節縣志序》,考之,該序只說“畢志”,未言“畢節縣志”。又查《道光大定府志·舊志敘錄》,則明言“萬歷畢節衛志一卷”[11]162上。則記為萬歷《畢節縣志》是民國《貴州通志》之誤。《畢節縣志序》中提到的“畢志”,應當是萬歷《畢節衛志》。
《貴州宣慰司志》②。《明一統志·卷八十八》載貴州宣慰司風俗:“病不識醫藥,披氈衫以為禮。”下注:“俱貴州宣慰司志”[6]3934。《明代官修四種貴州省志考評》和《貴州方志考略》均認為《貴州宣慰司志》修于元代③,考之于《文淵閣書目·卷四》“新志”條,有《貴州宣慰司志》[9]230。既稱“新志”,又與《烏蒙軍民府志》等志書同列,當修于明代正統以前。
3.昭通地區
《芒部軍民府志》《嘉靖四川總志·卷十七》載鎮雄府風俗“性勁而愚,俗樸而野,男業耕稼,婦絕粉黛,子日貿易。”,下注:“府志”[12]274上。《大明一統志》中所引的同一句話下面注解為“以上俱郡志”[6]3239,可以發現“府志”“郡志”實為同一部書。考之《文淵閣書目》“新志”條,有《芒部軍民府志》。按明代府有稱郡之慣例,而明以前此處未設府,成書當在正統《文淵閣書目》成書以前。
《烏蒙軍民府志》《明一統志·卷七十二》“烏蒙軍民府”條載烏蒙府形勝:“龍洞環于左,涼山聳于右”,下注:“新志”[6]3240,《嘉靖四川總志·卷十七》“烏蒙軍民府”條引用本句,下注:“本府志”[12]272上。參照各總志和通志中分別用到的“元志”“府志”“郡志”“新志”四種注解。“元志”應是指李京的《大德烏撒志略》,此書《文淵閣書目》和《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均未見收錄,《大定府志·舊志敘錄》及《民國貴州通志·藝文志》有存目。《嘉靖四川總志》中稱的“本府志”在《大明一統志》中被稱為“新志”,明代以前該地無府亦無郡,參考《芒部軍民府志》的“府志”、“郡志”為一書的例子,《烏蒙軍民府志》所引用的“府志”“郡志”“新志”應是同一本志書。考之于《文淵閣書目·卷四》“新志”條有《烏蒙軍民府志》,則烏蒙確在正統以前就有府志。
三、方志興修與國家認同
隨著中央王朝對西南邊疆政治掌控的不斷加深,相應的文化建設也逐步跟進,現代研究者已經注意到明代在這些地區設立學校、開科取士、土官承襲與入學掛鉤等內容并作了深入研究,這些內容反映出封建中央王朝以傳播儒學的方式來加強邊疆地區的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而志書作為記載一方物產、風俗、政教、山川的重要載體,具有傳承歷史記憶、保存珍貴文化,促進內地邊疆一體化等重要的作用。金燕在研究“改土歸流”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時將國家認同定義為“個人或群體在特定情境下,認為自己屬于國家,是國家的一分子,既享受著依靠國家所獲得的利益,又承擔著國家規定的義務。”[13]63誠然,個人或群體對國家所授予的權力和規定的義務的承認顯示出地方對國家的認同,但普安州和尋甸府兩地志書的序中可以使人注意到國家和地方之間認同的另一個層面——國家對地方的認同。
《周禮·地官·誦訓》說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鄭玄注:“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14]441上這說明了自古以來,方志作為一地掌故之書,具有向統治者傳達地方情形以方便治理的作用。貴州作為邊疆之地,“在寰宇西南之極”,明人以為貴州“在古為荒服,入圣代始建官立學……百七十年來骎骎乎齊美華風”,故而增修方志,“以啟百代之瞻仰”[15]193-194。而云南則“古淪異域,山經地志皆鮮及之”,志書修撰之后,使得觀志者得以知曉云南“昔為不毛之地,而今建郡作邑張官置吏也,昔為旃毳干戈,而今衣冠弦誦也”。[16]
《普安州志·序》亦云“普安軍民指揮使司所轄地本西南荒服之表,蠻夷部落,元世始拔土豪吏置官署,頑風暴俗仍習舊污,大略羈縻而已。幸入圣朝,城守屯戍,懷德畏威,而來三十余載,墾田編戶,趨事赴功,漸擬于華郡。”[4]5-6其開創之意,甚為明晰。在明人的視野中,西南地區歷來是國家控制之外的邊疆之地,而在明代將其納入版圖,并且開科取士,教化邊民,新修或增修方志將這一百代未成之功業傳之后世,以便后世考察明朝在開疆域、設制度方面的歷史功績,并宣揚有明一朝在西南地區的文治武功,彰顯出明朝在西南治理歷史上的開創性作用。故而泛覽西南邊疆地區的明代志書,都有意突出與前代的對比而強調其“骎骎向化”“漸擬華風”,以展現出要荒之服逐漸化為內地,由“野蠻”而化為“文明”,凸顯出國家力量到來之后當地面貌煥然一新的結果。而尋甸府則“昔為土部而改設流官,涵濡圣朝文化有年矣,禮樂頗垺中土亦久矣,可缺是典而使文獻無征于郡耶?”[17]1可見在修志的同時就意味著華夏的中心承認了羈縻之地成為治下之邦,因而要將它的歷史掌故記載并納入華夏整體的文化脈絡之中,摒棄了土官制度而直接處于朝廷管理之下的邊疆“涵濡文化”、“禮樂垺于中土”,這樣的地區值得興修一部方志來記載中央王朝“變夷為夏”的歷史功績,“改土設流”正是尋甸府方志興修的一大前提。方志是華夏的文化邊緣逐漸向邊疆、山地逐漸擴展的一種表現形式,國家控制逐漸加深是烏蒙山區地方志修撰的一大重要原因,亦是在日益加深的儒家文化影響下的結果。

圖1 烏蒙山區明代方志修撰次數示意圖
由上圖可看到烏蒙山區明代方志至少有十四部,有九部修于正統以前,僅有五部修于正統后(《陸涼州志》④《嘉靖尋甸府志》《嘉靖普安州志》《萬歷普安州續志》《萬歷畢節衛志》),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正統后持續修志的都是長期處于流官管理或初設流官不久的地區。東川、烏蒙、烏撒、芒部四軍民府府志及貴州宣慰司志均修于正統之前,這一時期平定云貴的軍事余威仍在,且朝廷在這一地區派駐了很多的流官佐貳,修志具有穩固的政治基礎。這幾個土司地區的方志極大可能是在明初修一統志時各地修志的大浪潮下修撰的。但也可以看到,這些地區的方志在正統以后就未見新修。從正統時開始,這幾府的流官相繼被裁撤。[19]122這恰好和方志修撰的時間段不謀而合。可見,代表國家控制力度的流官管理是方志興修的一大重要條件,方志的興修體現出中央王朝對新納入直接管理體系的地區的文化承認。
四、結語
明代的烏蒙山區土司林立,地理環境和政治環境錯綜復雜,但從緩慢進行的改土歸流動作和方志興修事業仍然可以看出明代中央王朝在邊疆推行國家管理體制的努力。邊疆方志作為地方文化的載體,不僅其內容可以反映出中央王朝對邊疆認知的逐漸擴展,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方志興修本身也反映出了古代華夏中心對邊疆國家文化認同的塑造。方志的修撰狀況與國家管理力度和對邊疆地區的認同是息息相關的:“改土歸流”帶來的是將邊陲納入國家直接管理體系的需要,而方志興修帶來的是邊疆—內地的雙向認同。我們無法想象當貴州水西地區沒有被納入中央王朝直接管理時是否能夠有足夠的人力和組織力修纂一部令大部分志書都“未能望其項背”的道光《大定府志》,當然也無法想象沒有道光《大定府志》和道光《遵義府志》的大定府和遵義府能夠為梁啟超津津樂道并為后世讀者所采擇摘取。⑤方志在無形中加深了邊疆和內地的文化心理聯系,促進了地方和國家之間的文化認同。當華夏的邊緣不斷對外擴展并吸納更多的族群進入華夏體系時,方志的興修正是這一過程的體現。
注釋:
①《中國地方志綜錄》中載有《嘉靖普安州志》、《嘉靖尋甸府志》;《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除此二部外還載有《永樂普安州志》;《明代方志考》對此三部均有著錄,并將已佚之景泰《普安州志》、萬歷《普安衛續志》、《陸涼州志》、《馬龍縣志》、萬歷《畢節縣志》(即萬歷《畢節衛志》)收入。見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 增訂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5.林平,張紀亮.明代方志考[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②明代貴州宣慰司治貴陽城,但其地大部分在今畢節地區,故列入.
③見張新民.明代官修四種貴州省志考評[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02):45-52.史繼忠.貴州方志考略[J].貴州民族研究,1979(01):95-101.
④《陸涼州志》修撰者為張星耀,按《乾隆陸涼州志·卷三》“監司”條載有張星耀,同卷載明“監司”始設于萬歷十九年,故而《陸涼州志》應當修撰于萬歷以后.
⑤林則徐曾贊道光《大定府志》“編纂之勤,采輯之博,選擇之當,綜核之精,以近代各志較之,惟嚴樂園之志漢中,馮魚山之志孟縣,李申耆之志鳳臺,或堪與此頡頏,其他則未能望其項背也。”梁啟超則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將《大定府志》、《遵義府志》均列為清代名志。見肖忠生.林則徐與《大定府志》[J].福建史志,2005,(第6期).梁啟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