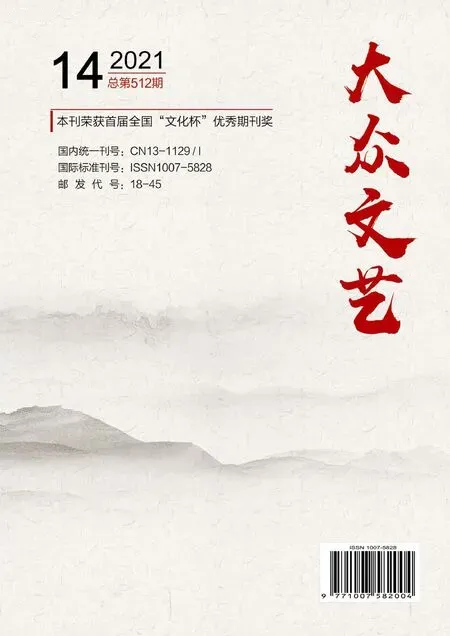《失業者》中的貧困敘事
張亞男 吾文泉
(南通大學,江蘇南通 226019)
瑪格麗特·哈克內斯(Margaret Harkness)于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出生在倫敦一個普通牧師家庭。作為接受過良好人文主義教育的女性,哈克內斯對政治經濟特別感興趣。因而,她選用十八世紀初最有名的經濟學家的名字--約翰·洛(John Law)作為筆名。然而這位女作家并沒有局限于社會經濟問題的理論研究,在八十年代初,她開始深入倫敦的貧民窟,直接了解人民的生活。期間,她在自由派雜志上發表關于郵政部門女工和鐵路工人勞動狀況的文章。隨后,哈克內斯出版第一部現實主義中篇小說《城市姑娘》(A City Girl,1887),之后兩年分別出版了《失業者》(Out of Work,1888)和《最黑暗的倫敦》(In Darkest London,1889),這也被稱為真實反映倫敦貧困的“三部曲”。
《失業者》以木匠工人喬瑟夫·科尼的失業與碼頭工人生活為主體,集中描寫了黑暗倫敦下的失業人群以及求工狀況,并結合哈克內斯深入貧民窟的親身經歷,反映底層人民眼中的貧困東區。雖然受左拉的自然主義文學影響,《失業者》卻仍然實現了“紀實現實主義”寫法。另外,相較于《城市姑娘》,哈克內斯充分考慮并接受恩格斯“無產階級生活的積極一面”的建議,在《失業者》中表現出工人主動爭取權利的進步性,但最終還是以消極群眾的“不能自助”結束。國內外學者對此小說的研究差異較大,且國外多集中于小說的藝術手法研究,特別是恩格斯給予哈克內斯在現實主義手法方面的評價與建議。反觀國內,研究極為匱乏。盡管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中,哈克內斯并不是很有名氣,“但是她的作品卻是19世紀90年代社會主義小說中傳播最廣的。她的作品中彌散著充滿激情的正義感和堅定的社會改革信心。”(常耀信,638),而《失業者》作為貧困研究的代表作,更具研究價值。
一、“黃金時代”的灰色人群
歷經工業革命洗禮,至維多利亞時代末期,雖面臨德美兩國的商品沖擊,英國仍然保持著世界霸主的地位,并在海外市場,出口貿易,全球金融等方面也始終占據統治地位。而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地不斷推進,被機器生產取代手工勞動的工人們與失去土地等生產資料的農業人口大量涌進城市,帶來人口數量與規模發生了根本性的結構變化,同時加劇城市生活壓力。但是,在生產力原本顯著提高并積累大量財富的“黃金時代”下卻暗藏著深陷失業沼澤的灰色人群。珍妮特·羅巴克在描述英國貧困時的狀況時說“大量生活在惡劣環境中的居民被稱為窮人,工人或者底層,其生活環境暗淡,骯臟并充滿痛苦,他們掙扎在可怕的生存邊緣上。那些窮困的農業工人作為工業化的附屬物,很少有自己的財產。”(羅巴克,2)失業現象愈發嚴重,成為英國社會難以掩蓋的“瘡疤”。小說中,喬瑟夫·科尼(Joseph Coney)因為在家鄉找不到工作便懷揣希望來到倫敦,卻也被告知“你可以到的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倫敦了。在這里有上成千上萬的木匠都失業了。”(Harkness,61)倫敦的失業形勢是嚴峻的,“僅僅在倫敦,成千上萬的人失業,整個英國呢,有一百萬人在找尋工作。”(Harkness,66) 根據查爾斯·布斯(Charles Booth)在其著作《倫敦人民的生活和勞動》(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中得出的結論“不是25%,而是超過30%的倫敦人口生活在他所謂的貧困線之下”。在經歷了多次求工失敗,遭受到瘡痍倫敦生活的折磨后,喬瑟夫·科尼在給家鄉人的信中這樣說道“請告訴家鄉人,不要再到倫敦來了,這里沒有工作,除了饑餓什么都沒有。”(Harkness,104)而失業問題所帶來的連鎖反應的直接后果就是饑餓與死亡。
失業,饑餓與死亡纏繞下的黑暗倫敦是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嚴重財富不均的結果。中上層階級家庭占全社會的25.6%,但其所占的國民收入卻達到了60.9%,體力勞動者家庭占全社會74.4%,但他們所占有的國民收入只有39.1%。(Perkin,420)小說中,喬瑟夫·科尼曾有這樣的感慨:“工作的人要挨餓,可不工作的人卻可以吃飽飯。”(Harkness,40)“他意識到那些先生和女士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饑餓,也不會感到失業的痛苦和被拋棄的苦悶。”(Harkness,89)
二、貧困者的“巴士底獄”
英國貧困問題由來已。1834年前,英國政府主張“院外救濟”,即增加貧困支出,對濟貧院外的貧民提供一定的生活資料與救助。但是這樣的濟貧措施非但沒有明顯的效果,反而增加了濟貧稅收負擔,且貧困人口數量持續上升。于是,1834年英國通過《新濟貧法》,正式廢除了“院外救濟”,所有接受救濟的貧民必須到濟貧院工作。這一措施的理論基礎則來自功利主義的奠基人邊沁。邊沁認為貧民應當依法接受救濟,這是他們天然的權利。但是,他認為擺脫貧困的關鍵在于根本性獨立勞動,因此,“在濟貧院內,工人必須最大限度地工作,計件工作是一個原則,所有的窮人工作必須完成救濟他們的價值。”(波因特,134)之所以提倡這種“院內救濟”,英國政府認為“懶惰”是貧困的根本原因,因而主張要對貧民進行嚴苛的管理,并“強迫勞動”以實現相應救濟的價值,這樣才是所謂的“公平”,從而徹底解決貧困。但是,濟貧院并沒有如預期那樣真正解決英國的貧困現象。
首先,貧民的“懶惰”并不是貧困的根本來源。小說中,像喬瑟夫·科尼這樣有技藝的人成百上千,但是即使他們擠破腦袋,費盡全力也仍然找不到工作。“饑餓的人很多,但工作卻沒有。”(Harkness,105)資本家們延長工人工作時間,剝削其剩余價值,減少工人需求量,縮減人工成本進而達到利潤最大化,因此對招工需求量的減少也是失業嚴重的原因之一。其次,濟貧院的生活環境與管理制度十分嚴苛甚至極端,加重貧困現象。喬瑟夫·科尼因失業走投無路來到濟貧院,這里“除了墊子以外什么都沒有,冷風貫穿整個房間,沒有門,只有一個欄桿包圍的鐵窗,寒風刺骨,從皮膚滲透進血液。”(Harkness,p182);另外,濟貧院的食物量少單一,“食物就放在床邊的地板上,一小碗粥,一點點面包。”(Harkness,p185);更糟糕的是,在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下,接受救濟的人們必須完成各種繁重又危險的工作,包括砸石頭,用手碾碎玉米,扯麻絮,碾碎骨頭以用于施肥或制造業。
三、道德教化的“階級性缺失”
在失業與貧困危機籠罩下,嗜酒,暴力,犯罪,死亡,冷酷,缺乏秩序感和目光短淺,都是對貧民的典型描繪,且成了整個東區的主旋律。“清晨六點半是倫敦令人沉悶的時刻,街道骯臟,商店閉門,衣衫襤褸的孩子們趴在門前的臺階上,什么人都沒有,警察們叫喊著討論這里的自殺,那里的謀殺”(Harkness,127);饑餓使人喪失理智與情感,“小旅館的老板娘曾經有一個孩子,但她以十八便士的價格賣掉了”(Harkness,153);死亡成為最好的解脫方式,小說中索菲亞臨死這樣說:“死亡意味著平靜;死亡意味著一切都已結束,如果我死了,這種恐怖的痛苦就會結束,我也會忘記科尼,我已經沒有活下去的理由”(Harkness,266);失業總是與嗜酒相伴,喬瑟夫·科尼求工失敗期間多次在酒吧以酒精麻痹自己,漸漸地無法克制自己,將僅有的存款拿去喝酒,并再次失去碼頭得來不易的工作。社會問題愈演愈烈,貧困現象也走向極端。
《新濟貧法》認為,貧困的根源在于貧民的“懶惰”,因此要嚴苛管理,強迫勞動,讓貧民擺脫懶散習慣。查爾斯·布斯也認為,貧困的成因之一就是“不良的生活習性”。社會學家托馬斯·查爾莫斯也認為,“個人的經濟狀況是由其道德狀況反映,要改善一個人的經濟處境,就必須改善其道德素養。”但是,社會問題并不是由于貧民的產生而出現。失業者處于混亂無序的社會環境中無可避免地染上不良的生活習性并使人墮落,于是進一步造成新生貧困,因而形成“貧困--墮落--貧困”的惡性循環。
四、結語
在《失業者》中,瑪格麗特·哈克內斯以倫敦東區的嚴峻失業形勢為縮影,展現產業工人和都市貧民等灰色人群在無序社會環境下的艱難生存,并折射出維多利亞末期英國長期的極端貧困的經濟根源來自資本主義制度所導致的社會財富嚴重分配不均,造成“窮人越窮,富人越富”的局面。由此可見,英國的失業與貧困是多種原因作用的結果,但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以此衍生出的諸多因素加劇貧困程度。《失業者》中失業與貧困關系的視角有利于認識和把握英國社會的貧困問題,為我國的貧困書寫與研究提供一絲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