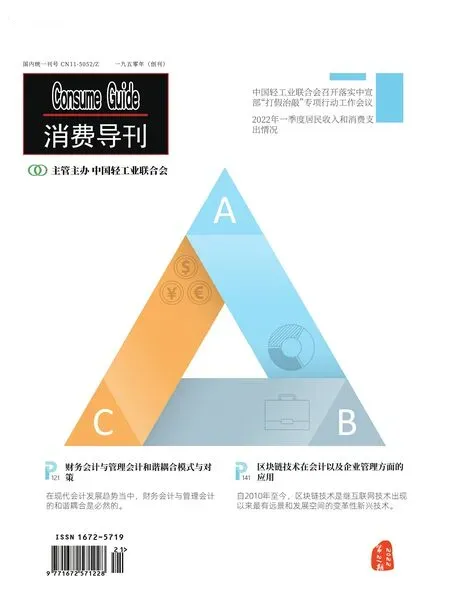“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和借鑒意義
朱思雅 首都經(jīng)濟(jì)貿(mào)易大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院
一、引言
2006年世界銀行發(fā)布了《東亞經(jīng)濟(jì)發(fā)展報(bào)告》,在該報(bào)告中,“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被初次提出。它的基本含義是低收入國(guó)家想要成功步入高收入國(guó)家行列的希望十分渺茫。當(dāng)一個(gè)國(guó)家的人均收入達(dá)到中等水平時(shí),未能及時(shí)的進(jìn)行經(jīng)濟(jì)改革將導(dǎo)致其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動(dòng)力不足,并最終導(dǎo)致衰退。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智利,這幾個(gè)國(guó)家在1970年前后都已經(jīng)進(jìn)入中等收入國(guó)家行列,但是直到2007年,他們?cè)谌司?000-5000的GDP發(fā)展階段仍處于掙扎狀態(tài)。截至2011年,拉丁美洲“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平均拘留期為37年。這種現(xiàn)象稱為“拉丁美洲現(xiàn)象”。《東亞及太平洋報(bào)告:危機(jī)10年后的狀況》表明,許多經(jīng)濟(jì)體通常可以達(dá)到中等收入發(fā)展階段,但是只有少數(shù)幾個(gè)國(guó)家可以跨越這個(gè)階段,因?yàn)閷?shí)現(xiàn)這一飛躍所需的政策和體制變革涉及技術(shù),政治,社會(huì)等多方面。未來(lái),東亞國(guó)家應(yīng)采取措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經(jīng)濟(jì)學(xué)分析
有學(xué)者認(rèn)為,世界銀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現(xiàn)象,現(xiàn)實(shí)中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陷阱”有可能會(huì)出現(xiàn)在各個(gè)階段,包括低中高三個(gè)收入階段。通過(guò)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模型,我們可以對(duì)“中等收入陷阱”進(jìn)行理論解釋。
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中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理論認(rèn)為,系統(tǒng)是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決定因素,影響和限制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變遷[1]。這里的“系統(tǒng)”包括經(jīng)濟(jì)制度,產(chǎn)權(quán),法律,社會(huì)習(xí)俗和意識(shí)形態(tài)等類別。諾斯認(rèn)為,投入因素不增加,僅體制創(chuàng)新就可以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制度變革與技術(shù)進(jìn)步有關(guān),既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又是社會(huì)進(jìn)步的源泉。發(fā)展中國(guó)家跳出貧困陷阱應(yīng)該靠制度建設(shè),通過(guò)制度建設(shè)來(lái)提高組織的創(chuàng)新能力和效率。典型的例證就是我國(guó)在上世紀(jì) 80 年代實(shí)行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后經(jīng)濟(jì)的高速增長(zhǎng)。因此,我們可以說(shuō),“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質(zhì)是 “轉(zhuǎn)型陷阱”。國(guó)家在轉(zhuǎn)型前積聚了許多矛盾,暫時(shí)沒(méi)有顯現(xiàn)出來(lái)。在進(jìn)入這個(gè)時(shí)期后,矛盾爆發(fā),原有的政治經(jīng)濟(jì)體制、法律體制的缺陷暴露無(wú)遺,無(wú)法有效應(yīng)對(duì)新時(shí)期社會(huì)各方面的風(fēng)險(xiǎn),對(duì)人們的生活產(chǎn)生負(fù)面影響。改革初期的一些既得利益集團(tuán)往往會(huì)阻礙變革,憑借自己的力量對(duì)政治、經(jīng)濟(jì)體制施加影響,用權(quán)力的方式賺取資源,造成以維穩(wěn)為代表的一系列“弊政”開(kāi)始形成,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速度停滯不前,推遲了國(guó)家進(jìn)入高收入國(guó)家的行列。此外,在資源邊界既定的前提下,任何經(jīng)濟(jì)體都會(huì)受到邊際收益遞減規(guī)律的約束。許多發(fā)展中國(guó)家在進(jìn)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往往會(huì)放緩甚至停滯。這是具有理論依據(jù)的,而不僅僅是對(duì)現(xiàn)象的簡(jiǎn)單總結(jié)。[2]
三、發(fā)展中國(guó)家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一)錯(cuò)失發(fā)展模式轉(zhuǎn)換時(shí)機(jī)
選擇了錯(cuò)誤的經(jīng)濟(jì)制度是發(fā)展中國(guó)家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部分國(guó)家沒(méi)能及時(shí)調(diào)整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模式,從而失去了模式轉(zhuǎn)換升級(jí)的機(jī)會(huì)。比如,一些勞動(dòng)密集型國(guó)家依靠產(chǎn)品出口拉動(dòng)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進(jìn)入中等收入階段后,這些國(guó)家繼續(xù)以原有模式向前發(fā)展。產(chǎn)品總成本增加,整體產(chǎn)品結(jié)構(gòu)變化,市場(chǎng)需求有利于勞動(dòng)價(jià)格更低的國(guó)家等原因造成了財(cái)政赤字以及經(jīng)濟(jì)發(fā)展遲緩的局面。以馬來(lái)西亞為例,初級(jí)工業(yè)品和傳統(tǒng)資源的出口對(duì)外貿(mào)和居民收入水平已經(jīng)很難做出提升。還有的國(guó)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jià)為破壞的環(huán)境買單,而昂貴的環(huán)境治理成本阻礙了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和收入增長(zhǎng)。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尼西亞,曾經(jīng)大幅度破壞本國(guó)森林資源尋求大量出口,但如今自然資源枯竭,解決新的替代性出口產(chǎn)品迫在眉睫。當(dāng)然,也有通過(guò)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成功跨過(guò)“中等收入陷阱”的國(guó)家。波蘭、匈牙利、捷克等國(guó)通過(guò)向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轉(zhuǎn)變、較快地融入歐洲統(tǒng)一市場(chǎng)并實(shí)現(xiàn)了經(jīng)濟(jì)復(fù)蘇和增長(zhǎng),目前已經(jīng)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入高收入國(guó)家的行列。而俄羅斯經(jīng)過(guò)艱難轉(zhuǎn)軌,2007 年人均 GDP 接近15000 美元,也進(jìn)入了高收入國(guó)家行列。
(二)難以克服技術(shù)創(chuàng)新瓶頸
在當(dāng)今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增長(zhǎng)十分依賴現(xiàn)代技術(shù)。由于我們國(guó)家在技術(shù)創(chuàng)新方面一直以來(lái)依靠西方國(guó)家的支持,萬(wàn)一外國(guó)切斷了對(duì)我們的技術(shù)援助,我們的部分產(chǎn)業(yè)將無(wú)法繼續(xù)下去。例如,我國(guó)的芯片產(chǎn)業(yè)研究很長(zhǎng)時(shí)間內(nèi)沒(méi)有突破,依賴對(duì)外技術(shù),一直難以取得突破。同時(shí),因?yàn)榭蒲许?xiàng)目的投資風(fēng)險(xiǎn)比較高,企業(yè)不愿意投入大量資金來(lái)搞科研,這就導(dǎo)致沒(méi)有很多人愿意花錢去支持科技的投入,政府也只能盡可能地幫助一些,滿足投資要求的門檻仍然很高。由于技術(shù)創(chuàng)新項(xiàng)目與市場(chǎng)之間的脫節(jié),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體系并不完善,技術(shù)創(chuàng)新公司成為保護(hù)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瓶頸。隨著規(guī)模回報(bào)率的提高,人均國(guó)民收入只有超過(guò)“門檻”時(shí)才能發(fā)展。發(fā)展中國(guó)家貧窮而倒掛的原因是它們還沒(méi)有越過(guò)這個(gè)“門檻”,仍然處在貧困陷阱中。這種貧困陷阱的原因被稱為“技術(shù)陷阱”。
之前,許多企業(yè)在改革開(kāi)放中崛起,以較低的成本大量出口,促進(jìn)了對(duì)外貿(mào)易和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但進(jìn)入21世紀(jì)后,我國(guó)經(jīng)濟(jì)步入中等收入行列,這一優(yōu)勢(shì)已經(jīng)不能適應(yīng)新的發(fā)展需要,各個(gè)階段的產(chǎn)品都無(wú)法與同等階段的國(guó)家相競(jìng)爭(zhēng)。在這種激烈的競(jìng)爭(zhēng)中,國(guó)家漸漸失去了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助推力,經(jīng)濟(jì)發(fā)展放緩甚至停滯。因此,我國(guó)從低成本優(yōu)勢(shì)轉(zhuǎn)向科技創(chuàng)新優(yōu)勢(shì)勢(shì)在必行。在當(dāng)前的國(guó)際技術(shù)變革形勢(shì)下,加大技術(shù)投入力度,是應(yīng)對(duì)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的必然選擇。[3]
(三)對(duì)發(fā)展公平性重視不夠
社會(huì)財(cái)富分配不公已經(jīng)成為了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國(guó)家無(wú)法忽視的問(wèn)題。個(gè)別國(guó)家在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中沒(méi)有及時(shí)的對(duì)兩極分化趨勢(shì)進(jìn)行遏制,收入分配制度沒(méi)有得到及時(shí)的改革。不同社會(huì)階層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例如,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國(guó)家正處于城市化階段,城市化率從50%上升到70%,收入分配也越來(lái)越不合理,不同個(gè)體之間的差距十分巨大。1970-1979年位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國(guó)家以0.44-0.66的基尼系數(shù)成功地成為了中等收入國(guó)家。再加上收入邊際的消費(fèi)呈遞減趨勢(shì),有效的社會(huì)消費(fèi)因?yàn)榭傂枨蟛蛔銓?dǎo)致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較為緩慢。同時(shí)收入分別配置間的差距還使得微觀經(jīng)濟(jì)層面的勞動(dòng)力存在流動(dòng)異常與離職頻繁等現(xiàn)象,這使得企業(yè)勞動(dòng)力的穩(wěn)定性以及創(chuàng)新性都大幅度下降。這些負(fù)面影響最終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產(chǎn)生負(fù)面影響,使這些國(guó)家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像一輛“方輪”馬車,坎坷不平。
四、給中國(guó)的啟示
1.我們需要及時(shí)地進(jìn)行深入的改革和系統(tǒng)的制度建設(shè),提高組織的有效性。我們需要界定和保護(hù)產(chǎn)權(quán),讓其在競(jìng)爭(zhēng)環(huán)境進(jìn)行分散決策并結(jié)合自身情況制定信息反饋機(jī)制,使得信息可以得到即使有效的反饋。
2.中國(guó)需要真正意識(shí)到內(nèi)需增長(zhǎng)和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變化。出口商品結(jié)構(gòu)由勞動(dòng)密集型轉(zhuǎn)變?yōu)榧夹g(shù)密集型,通過(guò)人民幣評(píng)估和出口產(chǎn)品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優(yōu)化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實(shí)現(xiàn)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同時(shí),增加內(nèi)需,通過(guò)消費(fèi)帶動(dòng)經(jīng)濟(jì),并進(jìn)入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率穩(wěn)定的高收入國(guó)家。中國(guó)要以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創(chuàng)新為突破口,為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樹(shù)立新的動(dòng)力。我們需要保護(hù)國(guó)內(nèi)市場(chǎng)的擴(kuò)大和改善,減少外部經(jīng)濟(jì)波動(dòng)的影響。[4]
3.鼓勵(lì)技術(shù)進(jìn)步和自主創(chuàng)新,提高科研投入。堅(jiān)持人才強(qiáng)國(guó)的戰(zhàn)略,從教育抓起,培育出新一代具有創(chuàng)新力和思考力的青年。[5]政府需要增加對(duì)企業(yè)研發(fā)的投資,完善科技創(chuàng)新的機(jī)制,完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制度,使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盡快向以技術(shù)創(chuàng)新為導(dǎo)向的軌道轉(zhuǎn)變。
4.在社會(huì)收入分配方面加大調(diào)節(jié)力度,以推動(dòng)公平分配為切入點(diǎn)切實(shí)解決我國(guó)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系列問(wèn)題,為經(jīng)濟(jì)的不斷增長(zhǎng)大俠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以人為本,一切為了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