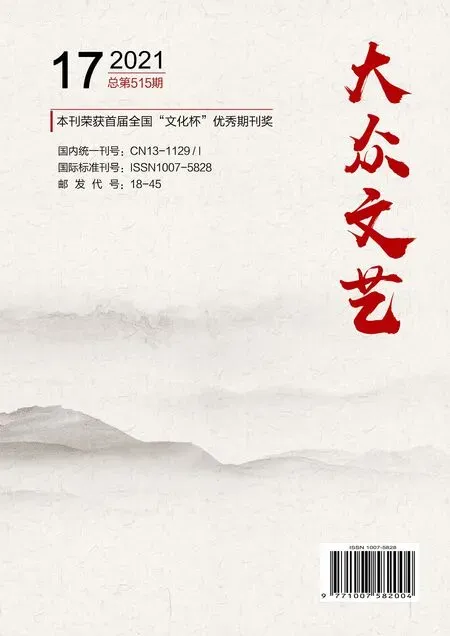被扼殺的女性主義萌芽
——解讀《胎記》喬琪安娜之死的深層意蘊
鄒曉雨子
(江西農業大學,江西南昌 330045)
《胎記》作為霍桑較為成熟的短篇小說之一,描寫的不僅僅一個妄圖使用科學來戰勝自然規律的科學家,祛除妻子臉頰胎記失敗,而終致妻子死亡的事件。從其深層解讀,實則體現出男權社會物化女性、壓制女性的事實。一直以來研究者們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分析《胎記》均把喬琪安娜之死,視為用生命的代價爭取到了身體和靈魂的自由,或是對男權社會主導權的抗拒和傾覆,從而達到女性自我意識的醒悟和解放。然而本文從喬琪安娜的死亡中,卻看出女性主義萌芽被消解的狀況。因此本文嘗試從男權社會下女性主義初露端倪以及處于萌芽期的女性意識逐步被扼殺兩方面進行文本分析。
一、女性主義萌芽的端倪
1.時代背景下女性主義的狀況
1846年霍桑創作短篇小說《胎記》,此文錄入于其作品集《古屋青苔》中。其創作背景正值十九世紀中期,美國的女權運動開始興起,西方女性自我意識開始不斷增強。歐洲范圍內的女權運動崛起并且不斷興盛,與處在十九世紀中期女性自我意識不斷省悟,意圖解決大多數積弊已久的社會問題,并寄希通過諸如此類的運動,改變受壓迫的現狀息息相關。[1]可以說霍桑的作品創作中或多或少受其影響,體現出女性意識的端倪。加之霍桑的個人生活經歷:幼年喪父,由母親獨自將其撫養成人,在他的人生經歷中目睹了很多處于社會邊緣地位的女性,以及父權社會抑壓女性、物化女性等等社會現狀。在他生活最艱難的時依賴于妻子的辛苦勞作來糊口度日,妻子所展現的睿智和社交生存能力使他開始重新認識女性。后由于霍桑工作等原因和其外交家的生涯中,相繼接觸一些卓越女性和部分女權主義者,開始深入地了解女權運動。[2]對于當時的女性主義思想,霍桑開始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并在文章中有所展現,譬如《紅字》的赫斯特形象等等。
2.內在單薄——女性的自我認知不足與同性苛責
《胎記》一文中,女性意識展現在喬琪安娜對于丈夫的權威有過的抗爭,譬如在丈夫對喬琪安娜的胎記表現地在意和震驚時,喬琪安娜叫道:“它使你震驚,我的丈夫!”感到非常委屈,起初她一時的憤怒而漲紅了臉,但隨后就哭了起來。“那么你為什么把我從我母親身邊娶了過來呢?你總不能愛上使你震驚的人吧!”[3]最初,喬琪安娜試圖勸服埃爾梅對胎記釋懷,在她口中這是“嬌媚動人”的特征。不難看出喬琪安娜不能理解丈夫的觀念和想要改變這種想法的反抗。然而這種女性力量過于渺小,在抗爭后期則被完全壓制。同一時期,在自我認知不足的情況下,女性還承受著同性苛責。在原文中,有些愛審視他人的女性斷言這只血手使喬琪安娜的美貌消散地無影無蹤,使其面容可怖。[3]來自同性間的嫉妒和惡意,更使得女性意識的生存狀況顯得頗為艱難。恰恰正是因為處于萌芽時期的觀念,喬琪安娜并不能很好的定位自己,對自己的評價往往來源于外界的贊揚和批評,反而使得自身的意識走向沒落,搖擺在他人目光中。
3.外界壓迫——男性主導社會話語權
歷史上,父權為主導的文化中, 女性自我意識被壓制,表達權被剝奪,更喪失拒絕的權力,從來都不曾作為獨立思想主體而存在。[3]在《胎記》中雖然體現了女性主義萌芽,然而這種發展過程并不是順利的。小說中在男女地位的描寫上,女性仍是從屬于男性的。在小說開頭的描寫就顯得耐人尋味:“說服了一個美麗女子做他的妻子”、結婚不久,丈夫臉上露出的是愈發苦悶又懊惱的神情,他一直“注視著”妻子,并終于開口了問詢喬琪安娜是否有祛除胎記的念頭。[3]在男主人公埃爾梅眼里,妻子只是一個可以說服的工具人,其最大價值就在于她的美麗的外貌可以最大程度地取悅自我,然而妻子臉上的胎記妨礙了她的美麗的完整性,于是埃爾梅便渴望祛除此物,使喬琪安娜變為“世上理想中完美無瑕的標本”,[4]并且開始入手科學實驗。不難看出,對于女性的外貌評判標準完全是由男性來主導的,并且喬治亞娜說話必須遵循丈夫的意圖,外界的壓迫使得女性意識只能處于一個萌芽狀態而無法恣意發展生長。
二、被扼殺的女性主義萌芽
1.無奈妥協——強顏歡笑,掩埋內心恐懼
起初,喬琪安娜的年輕美貌深深吸引了埃爾梅,婚前埃爾梅罔顧與妻子之間的溝壑,對安娜臉上的胎記置若罔聞,執意娶妻;婚后,卻發現自己日益加深對妻子的胎記不安且嫌惡之情。喬琪安娜的勸說和反抗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效果,反而安娜在這個過程進行無奈妥協,屈服于男性話語權。縱觀全文,喬琪安娜與丈夫的交流內容僅是妻子的簡單重復,或是表達對丈夫的恭敬仰慕,女性失去訴說自我想法機會,被剝奪話語權,這場婚姻中,埃爾梅一個人的聲音足矣取代了兩個人的聲音。話語權的喪失標志著喬琪安娜開始向男權社會妥協,不僅如此,喬琪安娜的回應方式也處于桎梏中。妻子與丈夫談話,即便是不贊成埃爾梅的看法,也都次次面帶微笑,“她勉強做出一個無力的微笑”“一面微弱地笑著”“她安詳地微笑著說”[3]等等。這樣的行為,都展現出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和控制,女性意識在這一階段開始逐步分崩離析。
2.自我催眠——以男性眼光內省、物化自我
除喪失話語權外,喬琪安娜還需忍受丈夫的“凝視”。據米歇爾·福柯的理論:“看”這個行為是擁有權柄的表現。“看”的權利被賦予觀看者,通過這個行為動作樹立自己的中心地位;被觀者淪為觀察的對象,同時感受到觀看者目光所帶來的權勢壓力,迫于前者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需求從而自省自察、自我物化。[5]當埃爾梅產生了胎記需要祛除這個想法之后,每時每刻他的目光都會不自覺地看向妻子的胎記,無論是“曙光初照睜眼時”,或是“夜晚兩人坐在壁爐邊”,[3]丈夫作為 “觀看者”,始終將自我的意志凌駕在妻子這個“被觀者”的從屬身份上,[6]妻子終是無法忍受這樣的目光,只能進行自我催眠,自我審視,規訓思想,將男性的目光內化,使其與男性的審視目光更為貼切,最終實現自我物化。處于父權社會,女性即使是洞察了男權實質意圖,仍然不得已自覺屈從于男權社會主流意識形態,這是迫于女性性別角色的社會性要求,只得自我催眠物化。[4]這一階段,喬琪安娜幾乎喪失了所謂的自由意志,她放棄了反抗的權利,放棄了作為妻子的權力,放棄了作為一個平等的人所擁有的權力。
3.放棄生命——淪為男權社會下無辜的犧牲品
女性意識開始一步步走向深淵,從喪失話語權開始,逐步的自我催眠,完全迷失在男權社會的泥淖之中,物化自我的程度不斷上升,使得喬琪安娜完全沒有能力阻止最后的“殺戮”,反而成為傷害自我的幫兇。為了使自己更符合丈夫心中的完美女性形象。為此,喬琪安娜直言可以放棄自己的生命:“埃爾梅,我將大口地喝完你給我的無論什么藥水;但是同樣的,我也將喝下一劑毒藥,只要是你親手遞給我的。”即便是在喬琪安娜的臨終遺言中, 她還在為埃爾梅申辯: 正是由于丈夫的目標崇高、行為高尚,感情純潔,因此辭絕了塵世所給予他最好的禮物,并告訴丈夫不要因此懊悔。[7]這段描寫,不僅在為自己的幫兇行為找借口,還體現出喬琪安娜在靈魂層面已經放棄了自我,放棄了做一個獨立的個體, 而淪落為丈夫的附屬品,一個為了討好丈夫心甘情愿成為失敗的科學試驗品。在肉體層面,喬琪安娜放棄生命,使自己與世長辭,這更不是對父權話語進行的顛覆和反抗,而是男權社會下無辜的犧牲品。喬琪安娜是殺害自我的幫兇,也是扼殺自我女性意識的萌芽無情的劊子手。
三、結語
在《胎記》中,女性意識本就處于萌芽階段,不僅受到外在異性的壓迫和遏制,甚至于同性內部間也遭受極多苛責不解。喬琪安娜沒有受到任何身體上的暴力傷害,然而來自話語的壓迫,眼神的凝視,以及不斷的操控等等,更令人窒息。喬琪安娜的辭世,證明男權社會對女性的無形壓迫,以及女性意識自身的羸弱。冀希女性真正進行獨立意識的覺醒,拒絕自我物化和他人物化,重獲話語權和身體支配權,改善女性生存狀況,堅持人格上的“獨立性”與“主體性”,從而使悲劇不再上演,使女性意識不再處于萌芽狀態,恣意生長,平等而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