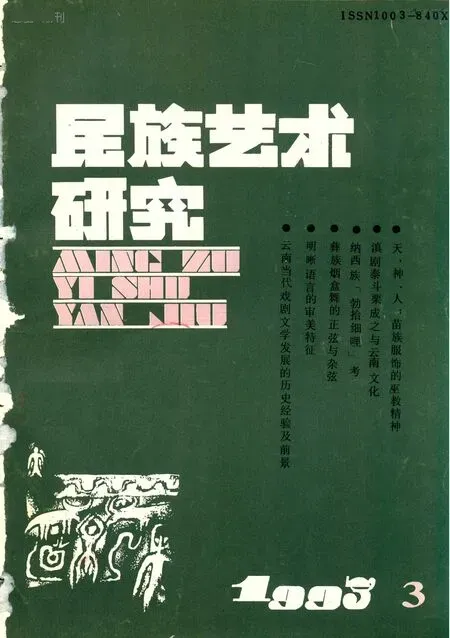古滇青銅器中舞蹈造型的空間形態研究
王馨曼
司馬遷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中這樣記載:“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說明在漢朝,“滇”的強大已載入史冊。20世紀50年代中期,考古發掘了滇文化墓群中較有代表的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貢天子廟、昆明羊甫頭等墓葬群,共發掘出一千多座戰國至東漢初期的墓葬,出土了古滇國文物15000余件,此外尚有100余件流失海外藏于倫敦大英博物館。①蔣志龍:《晉寧石寨山——第五次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古滇國青銅器相較于中原青銅器,有著更為濃郁的民族部落特征,其中,其舞蹈造型的發掘再次呈現出云南民族舞蹈文化的雛形。
舞蹈在古代被認為是游戲和祭祀等的重要體現。美國舞蹈理論家約翰·馬丁認為早期舞蹈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由簡單的游戲、宴享和性愛舞蹈所構成;第二類由或許可以稱為緊張狀態的祭祀所構成;第三類則由放松狀態的祭祀所構成。②[美]約翰·馬丁:《舞蹈概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頁。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古滇國時期的舞蹈同樣與這三者的起源分不開。造型的空間形式建構是一種設計思維,設計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可以幫助考古學及舞蹈學學者更好地理解考古對象。古滇青銅器中的舞蹈造型如果是一個符號的話,從這個符號中可以獲得不同角度的認知。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空間是抽象的與時間相對的一種物質客觀存在形式,抽象形式來自具象素材的集合,若無具體人物、器物、道具、場景及精心選擇等的造型研究,所謂的總體空間觀便沒有來由。而采用這種空間觀又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認識既有的舞蹈形式,這種形式正如戲劇有賴于視覺、聽覺和空間等種種元素一樣,其考辨和分析也也更符合古代造物的傳統常識。
一、古滇青銅器中舞蹈造型研究的范疇界定
對古滇青銅器的舞蹈分類標準,較有代表的研究主要有:1.以舞蹈和音樂圖像分類的標準進行分類。郭凈和金重兩位學者從“先秦兩漢時期云南的民族舞蹈”角度對滇文化青銅器中的舞蹈圖像進行分類,并借用中國古代漢族的廟堂舞蹈“文舞” “武舞”之名,作為舞蹈圖像的分類標準。①郭凈、金重:《先秦兩漢時期云南的民族舞蹈》,《云南民族舞蹈論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頁。《音樂圖像學與云南民族音樂圖像研究》 (王玲,2009)將音樂圖像學的分類方法用來劃分古滇國青銅器舞蹈。 《古滇國青銅器舞蹈圖像研究》(彭小希,2010)對舞蹈圖像進行系統的收集,結合古滇國的政治、經濟與宗教各方面展開論述。2.以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民間舞蹈與宗教舞蹈相結合的標準來分類。《云南民族舞蹈史》 (石裕祖,2006)將古滇青銅器的舞蹈分為“民族樂舞”和“宗教祭祀樂舞”兩類。《云南藝術史》(李昆聲,2006)將古滇青銅的舞蹈分為“廟堂樂舞蹈”和“民族自創舞蹈”兩類。《古滇藝術新探索》 (顧峰,1992)分別對滇文化的 “銅制樂器”與圖像中的 “狩獵舞” “祭祀舞” “巫舞”以及“樂舞”進行了分析,并提出 “這批樂舞是古滇族在奴隸制時代的生活反映和祭祀寫實”的看法。《滇人青銅器巫舞圖像析論》(張瑛華,1989)從宗教的視角將石寨山出土的“八人樂舞銅扣飾” “四人樂舞銅飾物”“四人銅舞傭”和銅鼓上的“龍舟競渡”羽人船紋分別劃為娛神樂舞、儺覡樂舞、祭祖樂舞、祈神樂舞四類。3.藝術考古學背景下以舞蹈器物形態的標準來分類。《南方古代民族樂舞名謂選釋》 (楊德鋆,1990)用文物記錄的方法對“銅鼓舞”“舞盤”“舞干”進行了分類。《滇國與滇文化》(張增琪,1997)將古滇舞蹈按 “徒手舞”與“器具舞”兩個類型來劃分。《云南青銅樂器及其滇人的樂舞意趣》 (詹七一、吳曉梅,2008)《滇國及其境內外的民族》 (尤中,1999)則從樂器的角度對古滇青銅器舞蹈進行精細劃分。
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以舞蹈和音樂圖像的標準來分類的大多是對圖像的內容和功能進行研究闡述的。以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民間舞蹈與宗教舞蹈相結合的標準來分類的大多是偏向于民族民間舞蹈學和音樂學的研究。以藝術考古學背景下舞蹈器物形態的標準來分類的更接近舞蹈造型形態的研究。因此,本選題的分類標準參照舞蹈器物形態的標準結合造型空間原則來分類,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器物的形態研究屬于設計學,而設計學的研究更為接近功能和審美的本體。其二,由于該選題屬于交叉性學科,涉及舞蹈圖像學、美術考古學、設計學、符號學及民族學等學科,從已有研究學者的學術背景來看,以出身于舞蹈學及民族學的學者較多,設計學及美術學的研究學者較少,而設計學及美術學出身的研究又大多停留在紋飾特征的表象研究上。因此,微觀、系統及不同角度的舞蹈設計分析,尤其是不同舞蹈類型的“空間范式”需要確立。同時,設計美學的本體意義及其價值告訴我們:“由理性對感性實行的審美判斷在人類設計的軌跡中始終表現出雙向互動的關系,設計作品本體的存在現象不僅反映出表象和深層次結構之間的關系,而且還反映出它們共同的審美特征。”②刑慶華:《設計美學》,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頁。古滇青銅器的舞蹈設計作為造物的附屬產品,最初是一種功能元素,雖然也兼具一定的藝術性,但這種藝術性與其本體功能相比,它的藝術性是為造物而服務的。而不同舞蹈類型的“空間范式”研究可以為我們理解古滇青銅器打開新的視野。從古代器物的分類來看,古滇青銅器作為古代的重要器物,依據明代萬歷三十五年工圻《三才圖會》第12卷 《器用部》將 “器”劃分為“食器類 (食器、設食器、酒器、水器、洗具)、祭器類 (明器、符節)、樂器類 (金、石、茲、竹、匏、土、革、木)、舞器類(舞器、射侯、舟類)、車輿類(軍事用車、運輸用車、玩具用車、農業用車)、漁器類 (網器、竹器)、兵器類(冷兵器、重兵器)、蠶織器類 (紡器、織器、養蠶器)、農器類(盛儲器、研磨器、灌溉器、生產器、插秧器、收割器)、什器類(文房用具、家具、閨閣之物、照明器具、食品器具、刑具)等”③鄒其昌、范雄華:《論〈三才圖〉設計理論體系的當代建構》,《創意與設計》2018年第6期,第10—11頁。的分類,結合古滇青銅器的舞蹈造型特征,將這一研究對象的類別分為銅鼓類、道具類、樂器類及徒手類共四個類型。結合舞蹈器物造型的標準分類,將古滇青銅器中舞蹈造型分為距離型造型、情節型造型、連貫型造型和偶像型造型四種空間造型。以“空間”視角進行上述舞蹈造型的分析,意在把研究的視線從孤立的舞蹈來源和考證圖像引出,探索解讀古滇青銅器作品新的可能性。
二、“道具”舞:情節型造型
“道”是造物的哲學思想、倫理道德之一。 《周易·系辭》載“備物致用”、王艮“百姓日用即道”以及老子“大器免成”等思想,就是古代造器的形式與智慧的體現。“圣人制事必有法度”更是中華器具研究話語體系中獨特的東方思維。在古代的 “道具”研究對象中,依據功能可以分為:宗教道具、喜慶道具、交通道具、農耕道具、狩獵道具、軍事道具等。古滇青銅器中舞蹈造物的“道具”主要有日用道具、宗教道具、軍事道具、交通道具以及農耕道具這幾種。
“道具”舞中,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日用道具舞,《四人對舞》(表1-1)就是較典型的日用道具舞。從它的造型形式來看,四個舞者均為正側面構圖,舞者的視知覺由手引入手中的道具;從舞者的動態來分析,下排舞者各執一短棍,相對而立,腿部為跪坐式,腳掌撐地,兩人中間放置一方形物。右邊舞者右手曲肘高舉棍,左邊舞者左手執棍向下擊打方形物。上排兩位舞者,其中左邊一人為跪坐式,手中高舉一長桿,桿頂部有一圓(梯)形物,其面部表情似乎十分關注桿上的物體。在這一舞蹈中,木棍、長桿等均為日用常見道具,在內容的表現中,有喜慶的意味在里面。在軍事道具舞蹈造型中,較有代表的是《七人執矛舞》(表1-2)《單人執劍舞》(表1-3)。在《七人執矛舞》中,七個舞者呈水平構圖,每個舞者的構圖為正側面構圖,排列整齊,七位舞者皆手執長矛扛于左肩,體態挺拔,舞者舞姿同一,動作規范,舞蹈隊形排列極具儀式感。在《單人執刀舞》中,舞者側臉正身,左臂上舉正對著畫外觀眾,手的造型比例被夸大,五指張開,右手手舉一長劍,左腿在下、右腿在上,該舞蹈突出與戰爭相關的內容。交通道具在古滇青銅器中表現較多為舟類,較有代表的是《船上執戈舞》 (表1-4)、 《羽人船上執矛舞》(表1-5)、《競渡舞》(表1-6)。在《船上執戈舞》中,船上的三位舞者為正側面構圖,“船首一舞者髻飾雙角,穿對襟上衣;船中兩位舞者身披獸皮綴尾衣,獸尾上翹,后衣領中插一牦牛尾高聳過頭。第一位舞者背對船首直身端坐,一手執鑼,一手持棍,呈現擊棍、擊鑼舞姿。另兩位舞者一前一后,一左一右背對執鑼舞者,以跪蹲之式身體向前傾俯,而頭部卻作扭頭回望狀朝向擊鑼者。離擊鑼者較近的舞人靠向船體左側,左手執戈,頭向右后轉;后一位舞者靠向船體右方,右手執戈,頭向左后轉。兩人同時執戈高舉作向前揮砍狀。”①彭小希:《古滇國青銅器舞蹈圖像研究》,昆明:云南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10年。其前左后右的交叉站位方式充滿了舞蹈的形式感。在《羽人船上執矛舞》中,舞者的造型在構圖中的比例較小,頭上戴的羽冠占了較大的比例,均為側身,姿態較為規范,四個舞者似乎為裸體。在《競渡舞》中,“船首有一牛角形物,船上共坐十五人,有的頭飾一根長羽、耳戴大環。除船首一人外,其余十四人分為七組,每組兩人并肩而坐,皆背部直立,上身前傾,嘴微張,手中各執一槳,置于船體兩側。船體下方有游魚及水鳥。舞者頭部的長羽向后彎曲飄動的形狀和眾人身體整齊前傾的姿態呈現出強烈的動勢,在指揮者揮漿舞動的帶動下,所有舞者口喊號子,在統一節奏中前進。整齊的動作、默契的配合產生出協調的美感,也產生了力的美感。”②彭小希:《古滇國青銅器舞蹈圖像研究》,昆明:云南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10年。由于古滇國位于滇池周邊,水上競渡游戲之風盛行,也因此,許多古滇青銅器鑄造中刻有競渡舞姿。
從以上“道具”舞造型的圖像來看,無論是日用道具、軍事道具還是交通道具,都具有較強的敘事性,敘事的過程中遵循“情節型”原則,即作品內容表現出舞者之間相互關系的一系列事件。這些“道具”舞呈現出的基本特點包括:1.多以側面構圖;2.通過姿態、動作和相互關系顯示正在發生的事件,相互呼應并處于運動之中。3.這種圖像空間的邏輯因此是自足和內向的,內容的表現依賴于空間內部的圖像元素,圖像不與觀者視線直接互動。在“道具”舞的各種敘事元素中,其視覺空間是圖像空間的敘事表達,圖像空間是視覺空間的原型意象。

表1 “道具”舞蹈圖像

序號 “道具”舞圖像 圖像名稱 出土地 時期 資料出處1-6images/BZ_137_429_484_1256_793.png《競渡舞》 晉寧石寨山《云南晉寧出土銅鼓研究》(7)
三、“樂器”舞:連貫型造型
明代萬歷三十五年工圻 《三才圖會》第12卷 《器用部》將樂器分為金、石、茲、竹、匏、土、革、木等種類。古滇樂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由竹子制作而成的蘆笙,因此,蘆笙舞是古滇 “樂器”舞中最主要的舞蹈。除此之外,銅鼓、錞于、編鑼、羊角鈕鐘、銅鈴等樂器也是古滇樂器舞蹈中常用的的樂器,但特征沒有蘆笙樂器典型。 《三人跪坐樂舞》 (表2-2)、《五人跪坐樂舞》 (表2-3)等舞蹈造型中,都有吹蘆笙的形象和畫面。《二人跪坐樂舞》(表2-1)、《三人跪坐樂舞》、《五人跪坐樂舞》的造型特征很相似,所不同的只是樂舞人數的變化。從人數較多的《五人跪坐樂舞》來看,“女樂舞者穿長袖對襟衣裙,耳戴大環,皆以蹲坐或跪蹲姿勢演奏手中樂器。兩位葫蘆笙演奏者相擁而坐,另三位舞者皆以正面跪坐式進行演奏。五位舞者手中皆持有樂器。右邊兩人中,一人抱持曲管葫蘆笙,另一人用嘴吹奏。余下三人中,一人懷中抱一圓狀器物,左手放于器面;一人擊打側抱的銅鼓,銅鼓側放在一面平置向上的銅鼓上;另一人手持一件管形樂器。”①彭小希:《古滇國青銅器舞蹈圖像研究》,昆明:云南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10年。從這個合奏蘆笙舞曲的畫面可以看出滇人在跳蘆笙舞的過程中,蘆笙用的是曲管胡蘆笙,形如葫蘆,從考究的文獻記載來看,這種葫蘆笙上有五孔或七孔,和云峰在 《象形文字里的記憶遺產——納西族東巴音樂的歷史承襲及分期》(《民族藝術研究》2019年第3期)一文中認為葫蘆笙 “一般插有5支帶簧片的笙,約16—66cm,蘆笙為木制笙斗,一般插有6支笙管,長約33—333cm不等”。在吹奏的方法上,除了單人抱吹之外,還有雙人合奏的形式,即由一人按音孔,另外一人吹奏的形式。從以上的跪坐樂舞來看,吹奏方式和圖像是一致的。蘆笙舞又稱葫蘆笙舞,一般不在固定場合也能跳。無論是婚禮、祭祀、喜慶、愛情、日常生活中等。從考古文獻跳蘆笙舞的記載來看,跳舞時,頭戴著羽毛做的雞冠帽,身穿的長長的裙子拖在尾后,即史書上所寫的“衣著尾”等這些特征來看,所跳的舞蹈即是蘆笙舞。從以上演奏的畫面來看,在奏樂的過程中,一人吹蘆笙作為向導,眾男女起舞是蘆笙舞的主要形式。《云南志略》在記載蘆笙舞時寫道:“男女動數百,各執其手,團旋歌舞為樂”,《海滇虞衡志》說:“揮扇環歌,拊掌踏足,以鉦鼓蘆笙為樂”。在 《四人銅鈴舞》(表2-4)中的舞蹈屬于銅鈴舞。從其舞蹈特征來看,正面四舞者動作相同——皆右臂曲肘平抬至肩,手握一筒狀銅鈴;左臂曲肘,手為握拳形,舉至左胸前。舞者頭、肩部向右傾靠,胯部左移,雙膝彎曲向左,重心靠向左腳,右腳腳尖點地。舞者手中的銅鈴或垂直或傾斜。
從上述 “樂器”舞造型的空間形態來看,他們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1.從上述古滇 “樂器”圖像中除了看出其是動作幅度較大的動態舞蹈外,大部分的舞蹈場景呈水平構圖,其構圖方式和學校集體畢業照較為相似,且每位舞者以正臉正身正對著畫外的觀者;2.其樂舞場景的造型符合“連貫”空間原則。這個原則涉及的是某種視覺對象的內在連貫性,這種連貫性體現在古滇樂舞圖像中是水平人物簡化的聯系性。“一個結構單位的形狀愈是連貫的,它就愈易于從它所處的背景中獨立出來。”①[德]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騰守堯、朱疆源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頁。例如 《二人跪坐樂舞》 《三人跪坐樂舞》《五人跪坐樂舞》就比情節型造型的舞者更容易被辨認出來。因此,古滇樂器舞是連貫型空間中舞蹈的典型體現。

表2 “樂器”舞蹈圖像
四、“徒手”舞:偶像型造型
“徒手”舞姿多次出現在古滇青銅器上,彭小希在 《古滇國青銅器舞蹈圖像研究》(2010)一文中,將古滇國的徒手舞姿分為立掌舞姿、翹掌舞姿、攤掌舞姿等舞姿。以此可以看出古滇青銅器“徒手”舞姿的豐富性、多樣性以及其注重手姿的技巧性。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學者對古滇青銅器中徒手舞的研究主要偏向于舞姿描述本身,從美術學及設計學視野對其進行造型的空間形態的分析探索較少,且“空間”在美術史及設計史研究中沒有像“圖像”和“形式”那樣上升到方法論的層面。基于此,對徒手舞姿的分析以在前期研究成果型的背景下結合形式對其進行空間觀分析。
在立掌舞姿中,從已有的研究文獻來看,主要由立掌跪姿、立掌蹲姿和立掌坐姿三種組成。在立掌跪姿中,較有代表的作品是《單人蛙舞》 (表3-1) 《八人雙層樂舞》(表3-2);在立掌蹲姿中,較有代表的作品是《雙人疊蹲蛙舞》(表3-3);在立掌坐姿中,較有代表的是江川李家山出土的《坐式蛙舞》(表3-4)。三種立掌舞姿中,舞姿形式最為典型的是立掌跪姿。《八人雙層樂舞》是較為完整的立掌舞,作品分為上下兩層,每層各四位舞者,由8個舞者組成,從圖像上的形式來看,舞者似乎是停留在歌舞表演的一瞬間。上層舞者邊歌邊舞,左邊三個舞者舞姿統一,兩手臂平舉上伸,立掌,掌心向正前方,拇指與耳朵平行;上層最右邊舞者的舞姿與前三個舞者有一些差別,造型似領唱者,手部的造型表現為右手曲肘至胸大肌,掌心向內,左手放與左腹外斜肌。下面四層的四個舞者神態各有不同,似乎是正在認真演奏:從左到右,左一雙手持葫蘆笙于嘴前;左二雙手捧一短管樂器于嘴前;左三左手抱鼓,右手放于鼓面;左四雙手執葫蘆笙于嘴前,雙臂平舉。上層的手形均為大拇指外展,后四指并攏;下四層的手形與歌舞表演的瞬間相呼應。從其空間觀來看,八位舞者都正對著作品外的觀眾,這個空間不是封閉和內向的:八個舞者不僅存在于畫面內部,同時也與畫外觀眾互動。美術史論家巫鴻在《中國繪畫中的“女性空間”》把這種空間觀定義為“偶像型空間觀”。同樣的造物空間觀也體現在《單人蛙舞》《雙人疊蹲蛙舞》和《坐式蛙舞》的圖像特征中,如圖所示。
翹掌舞姿,是古滇青銅鼓形銅貯貝器中常鑄的舞蹈紋樣。例如 《十五人徒手環舞》(表3-5)《二十三人羽人執羽舞》(晉寧石寨山出土,西漢早期,云南省博物館藏,圖片提供:邢毅) (圖1),還有較多李家山、晉寧石寨山等地出土的單個舞蹈紋樣。《十五人徒手環舞》中,舞者環圓而舞的場景中跳的是翹掌舞,每位舞者掌心向外的動作巧妙地和其他舞者的掌心形成相互對應之勢。其舞姿個體雖然有差別,但整體風格上呈現出統一性特征,舞者的手平舉于身體的兩側,與肩部平行,立腕翹掌、掌心向外,另外還有五個舞者掌心同朝前方。舞者下身分腿而立,左腳在前、右腳在后。如果把十五個舞者的姿態分解為兩個手臂與腳位姿態、以及一個轉身姿態,再按照動作的連續性將其連接起來進行動姿組合,可以看到舞者身體重心的相互交替關系。翹掌舞姿是圓舞中出現較多的集體舞蹈隊列形式,類似的除以上作品外,還有《二十三人羽人執弓舞》 《十八人圈舞》(江川李家山出土,戰國末期,云南省博物館藏,圖片提供:邢毅)(圖2)等作品。有些作品雖然細節有一定差異,但舞姿類型具有較大的相似性,在舞蹈形式中,舞者呈現出集中于圓心的內向型空間,從而有一種向心力,特別是身體接觸的舞者之間通過其連續性傳達出相互之間的凝聚力;同時,也從了一個側面反映了被敬畏、被崇拜、被施予、被祝福等的偶像崇拜心理。蘇珊·朗格在《情感與形式》中也論證了受眾對圓舞的偶像崇拜心理:“圓舞作為舞蹈形式與自發的跳躍無關,它履行一種神圣的職能,也許是舞蹈最神圣的職能——將神圣的‘王國’與世俗存在區分開來,這樣,它就創造了跳舞的舞臺,這舞臺自然而然地以祭壇或一些類似的東西(如圖騰、祭司、火堆、用作祭品的其他部落酋長的人頭)作為中心。在這具有魔力的舞圈中,所有的精力都釋放出來了”。①[美]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18頁。
攤掌舞姿能夠較好地體現古滇青銅器舞蹈中“以手為容”的審美特點,如果在之前的立掌和翹掌舞姿中對于手部有夸張和突出的表現的話,在攤掌舞中,對于舞者手部不同姿態的表現較之前更為細膩。這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晉寧石寨山出土的《九人銅舞傭》(表3-6),我們從圖中可以看到這組舞姿中手的變化較之前其他舞姿更為豐富。云南民族舞蹈研究的學者聶乾先在《云南民族舞蹈文集》一書中認為:“將三舞傭的舞姿以一拍一動連接起來,恰似現今彝族葫蘆笙舞中的‘甩腳笙’”①聶乾先:《云南民族舞蹈文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版,第301頁。。與此同時,與立掌舞姿和翹掌舞姿相同的是,其空間是開放的和外向的,即舞者不僅存在于畫面內部,同時也與畫外觀眾互動。

表3 “徒手”舞蹈圖像
五、“銅鼓”舞:距離型造型
古人造物重要的是創造一個器物構成的世界,以使得這個器物在真實世界之中有存在的意義。因此,雖然古代的器物有實用和審美的功能,但其從來都不僅僅是為了“實用”和“美觀”的。更高的一個層次是人們試圖記錄一種生活方式。因此,《左傳·成公二年》中記載有“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的器物觀。 “器以藏禮”的器物觀正是古代祭祀與隨葬兩大信仰觀念的遺存。銅鼓作為古滇人造物的重要載體,同樣具有“器以藏禮”的器物觀。從銅鼓的外形來看(圖1、圖2),古滇銅鼓的器物造型符合古人“天圓地方”的世界觀。同時也與《考工記》中的“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①聞人軍譯注:《考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頁。宇宙觀相符合。
古滇青銅器中的舞蹈造型大多呈現到銅鼓這一載體上,“銅鼓”舞中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四人踏銅鼓舞(出自李家山M69:162)、十五人徒手環舞(出自石寨山M12:2)等作品。銅鼓舞大多以鼓的圓形作為邊界和中心,將舞者的造型按圓形等距離地排序后進行描繪。在《四人踏銅鼓舞》 (表4-1)中,鼓面上站立著的四個舞者,背朝內,面朝外,環鼓邊而立的他們充分體現了等距離等規則,這可以從他們的高度、與圓心的直徑距離、舞者的比例大小、形態等方面看到。“四位舞者分別位于四方形的四個對角,面對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由于該銅鼓為祭祀用銅鼓,不是打擊樂器,因此四位舞者站立的位置以及他們的舞蹈具有明顯的祭祀寓意,中外古代諸多民族的舞蹈史上都有跳四方祭祀神靈的形式。”②彭小希:《古滇國青銅器舞蹈圖像研究》,昆明:云南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10年。同時,每一個舞者的舞姿、服飾及裝飾等又有區別。從舞姿來看,“圖中左邊兩舞者姿態基本相同:左臂上抬彎曲至左胸前,最左邊一人手執一短棍斜靠于左肩;右臂曲肘前抬,平舉于肩,手呈握拳狀或執物。物體因殘破無法辨識。雙膝微曲,平行位站立。”③彭小希:《古滇國青銅器舞蹈圖像研究》,昆明:云南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10年。另外兩個舞者則呈平行位站立,大臂平抬至肩,小臂上舉,立掌,掌心向前,雙膝微曲。從服飾及裝飾來看,左邊兩舞者頭戴錐形高帽,肩披獸皮長披風,獸尾拽地,內穿短袖對襟及膝長衫,帶束腰圓形扣飾,腰左側佩劍。另外兩舞者耳墜大環,頸部戴有多重項鏈,內穿襟及膝長衫,帶束腰圓形扣飾,腰左側佩劍。這種空間觀在《十五人徒手環舞》中,體現得更為明顯。由此可見,古滇青銅器的工匠造物觀與古代器物的實用和審美觀是一致的。

表4 “銅鼓”舞蹈圖像
這種視覺空間呈現出的基本特點包括:1.對稱構圖;2.人物環鼓的圓形而立;3.圖像空間的構成和與觀者的關系方面,圖像不僅可以存在于鼓面內部,同時也與鼓外觀眾互動。 “這種‘開放性’的圖畫空間實際上以假設存在的畫外膜拜者為前提,以神像與膜拜者的交流為目的。”①[美]巫鴻:《中國繪畫中的“女性空間”》,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頁。同時,這種以正方形去再現正方形、以圓形去再現圓形、以對稱去再現對稱的空間觀建構的造型,大大強化了舞者形態的知覺效果,換句話說,其對舞蹈的實際樣子進行了忠實的模仿。
結 語
統而論之,在古滇青銅器中舞蹈造型的空間表現中,“銅鼓”和“徒手”舞是集宗教、政治和意識形態運動為一體的“距離型”“偶像型”構圖。這種構圖與 “道具”舞中“情節性”造型有著根本的區別。在空間的構成和觀者的關系方面,“情節型”構圖中的形象多為側面或半側面形象,相互呼應并處于運動之中。這種圖像空間的邏輯因此是自足和內向的。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距離型”“偶像型”構圖中的舞者造型總是正面直視著畫外的觀者,而觀者的目光也被畫面的對稱構圖和兩側圖像的“趨中”傾向引導到舞者身上。同時,在銅鼓舞中的“距離”型的造型特征與“徒手”舞中的翹掌舞姿特征有一定的相似性和交叉性,這也反映了古代舞蹈集宗教、政治和意識形態運動為一體的視覺觀,巫鴻在 《中國繪畫中的 “女性空間”》一書中曾這樣解釋為什么偶像型圖像成為世界上各種宗教藝術中表現神祇的通用方式:“這種‘開放性’的圖像空間實際上以假設存在的畫外膜拜者為前提,以神像與膜拜者的交流為目的”。而在“樂器”舞中的連貫型空間中,連貫的人物的靜態表現,每個舞者執樂器或物品,或站或蹲或坐,從未顯示出劇烈動作,他們所表現的偶像性和情節性沒有“銅鼓” “道具”及“徒手”舞那么強烈,同理,其政治和教喻功能也較后三者隱晦,而以滿足視覺感官觀賞需求作為圖像的目的性較后三者更具有顯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