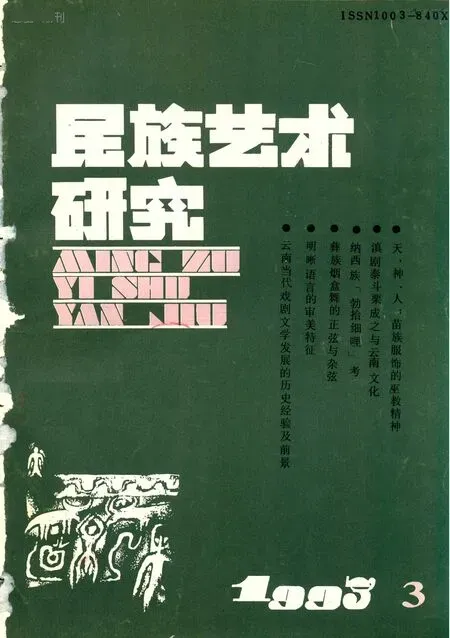瑜伽焰口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研究
胡曉東
儀式表演作為音樂(音聲)的重要承載,其整體性研究已受到更多學者的關注。英國人類學家詹姆斯·G·弗雷澤 (J.G.Frazer)認為,儀式是民間信仰的實體與核心結構,人們通過儀式營造氣氛,并在儀式表演中創造各種音樂環境以獲得心靈的慰藉。①[英]弗雷澤(J.G.Frazer):《金枝》,徐育新、張澤石、汪培基譯,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頁。而所有這些,都歸因于儀式所具有的表演功能。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茲(Clifford Geertz)認為,儀式就是一種 “文化表演”,是對信仰的展示、實現和形象化。②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New York:Basic Books.1973,p.113.美國人類學家理查德·鮑曼(RichardBauman)把儀式“表演”看成一種“特定的、藝術的交流模式”,“是一種語境性(contexts)行為”,并傳達著與語境相關的意義。③[美]理查德·鮑曼:《作為表演的口頭藝術》,楊利慧、安德明譯,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198、31頁。此理念為儀式信仰的闡釋路徑提供了可能,也為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研究提供了理論依托,因為執儀者及參與者的各類儀式化行為必然是基于特定的儀式信仰(觀念)、文化背景、社會制度和文化身份,并在特定的情態動機(儀式目的)主宰下的身體反應。
格爾茲進而指出,儀式表演是依靠一組獨立的象征符號,引發一組情態(moods)和動機(motivations) (一種文化精神),確定一種宇宙秩序的定義(一種宇宙觀),這種表演造成了儀式信仰樣式的 “對象性”模型(models for)和“歸屬性”模型(models of)在互相間轉換。①轉引自楊民康:《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一種從藝術切入文化情境的表述方式》,《民族藝術》2016年第6期,第17頁。這一轉換在哲學意義上相當于實踐和理論相互轉化過渡的過程:“對象性”模型常常體現出活態的、具體的文化個案的儀式表層現象,一般稱為“符號表征”;“歸屬性”模型則是有關此過程的靜態的、抽象的或隱性的,通常表現為思想、概念和法規的理性歸納或定義,又被稱為 “象征符號”。前者是后者所依賴的行為基礎,后者通過對前者過程的總結,可上升為某種對前者具指導意義的行動準則(或游戲規則)。②楊民康:《論音樂民族志理論范式的塔層結構及其應用特征》,《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第127頁。
儀式音樂作為儀式表演中最具活力和藝術的因素,因其特有的靈媒③即在宗教儀式中用以溝通人神之間的媒介,如儀式音樂、法器等。詳參巴利·諾頓、Kim Nguyen Tran、鐘雋迪《神靈之歌:現代越南的音樂和靈媒》,載《大音》2014第1期,第275—277頁。特性成為溝通人神二界的重要介質。因此,從表演民族志(Performing ethnography)的角度審視儀式音樂,可建構起一整套圍繞儀式表演與音樂符號為核心的象征符號與符號表征系統,并與儀式群體與個體之精神、觀念緊密相關。學者楊民康對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做出如下界定:
以儀式化音樂表演為對象和路徑,借以觀察和揭示人們在其音樂表演活動中如何經由和利用儀式表演行為,將觀念性音樂文化模式轉化為音聲表象的過程和結局,并輔以必要的闡釋性分析和文化反思。④楊民康:《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一種從藝術切入文化情境的表述方式》,《民族藝術》2016年第6期,第18頁。
可見,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研究高度重視在文化語境中展開對儀式音樂符號的闡釋和文化反思,旨在探究并揭示深藏于文化持有者內心深處的信仰與觀念。從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視角審視重慶羅漢寺瑜伽焰口儀式⑤胡曉東:《巴渝地區瑜伽焰口儀軌音樂的類型與結構》,《中國音樂》2017年第1期,第38—39頁。,猶如一場內容宏富、形式綜合的儀式戲劇(音樂劇)表演,表演者們(包括金剛上師、隨眾法師及信眾)基于共同的儀式信仰,集文學、音樂唱誦、舞蹈、美術等表演手段于一體,以程式化、直觀與象征性的方式昭示其深層的佛教義理與觀念,在維系鄉土社會秩序、傳承中華傳統文化以及和合人倫關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社會功能。通過觀察并分析該儀式表演中所呈現的具有典型意義的象征符號(“歸屬性”模型)和符號表征(“對象性”模型),筆者認為,羅漢寺瑜伽焰口儀式音樂表演是在佛教“三密合一”、閾限等觀念下的儀式戲劇表演,由此建構起一整套完整的儀式音樂符號表達系統。
一、儀式戲劇
意大利學者加斯特(Theodor Gaster)認為,神話是對原始神的行為 “敘事 (narrate)”,而儀式又是此敘事的 “扮演 (enact)”。換言之,儀式的表演實是扮演神話理想,因此神話中隱喻著儀式戲劇意識。⑥Gaster,Theodor.Myth and Story.Numen2.1954.Thespis:Ritual,Myth and Drama in the Ancient NearEast.Reviededition.New York:Harper&Row.1961,p.207.而作為戲劇所扮演的瑜伽焰口儀式音樂語境,包含了虛擬性、藝術性、功能性以及兩極漸變的音樂體系等幾個重要特征。
(一)虛擬性
無論儀式表演手法是求真還是虛擬,其本質是虛擬性的。⑦薛藝兵:《神圣的娛樂——中國民間祭祀儀式及其音樂的人類學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頁。瑜伽焰口儀式音樂語境是在虛擬場景中的虛擬表演,因此整個儀式情境都是虛擬的理想王國:其一,儀式音樂場景虛構。在儀式音樂表演進行當中,金剛上師有大量的虛構場景的動作,如唱誦《金剛地真言》時,上師手拈花米于曼呾上右旋散灑,如空注雨,戒指于曼呾上作一外圍,成大鐵圍山,再于曼呾作一內圍,成鐵圍山,這些儀式音樂場景都是通過虛擬的方式得以構建。
其二,儀式音樂中的結構與功能具有虛指性。瑜伽焰口儀式中的社會結構是反結構(anti-structure),與正常社會結構——位置結構(Structure of Status)狀態有較大差異。①關于瑜伽焰口儀式中的位置結構(Structure of Status)與反結構(anti-structure),將在文后“閾限期”一節詳述,此處僅涉其結構與社會功能之虛擬性。在儀式音樂唱腔結構里,眾生平等,即使是惡貫滿盈的惡鬼,也可以通過法師的超度,洗脫罪惡,脫離苦趣,修得無上正等正覺。換言之,這種理想化的反結構模式與社會功能,是人們在現實的社會結構模式中苦尋未果后,在焰口儀式中虛擬建構的,而這種建構正是儀式結構與社會功能的本質。
其三,儀式音樂表演中的情節具有虛擬性。瑜伽焰口儀式音樂唱腔中有大量的敘事性情節,如整場儀式結構的四大部分“開壇”“請圣”“施食度鬼” “圓滿奉送”就包含著嚴謹的敘事性,而每一個部分的每一個儀程,又都蘊含著虛擬的敘事情節。仿佛一個完整的故事在上演,環環相扣,具有很強的敘事性。
其四,儀式音樂表演中的意境具有虛幻性。儀式意境或被稱為儀式氛圍,是指儀式場景內特有的儀式氣氛以及攝人心魄的神秘氣氛。它存在于特定時空環境中,以綜合的形式展現出來,又被稱作“儀式情境”。②薛藝兵:《對儀式現象的人類學解釋》(上),《廣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第30頁。主導儀式意境的因素有很多,最重要的輔助手段有儀式音樂和舞蹈(儀式手印),它們皆具虛幻性。如儀式開始及中間部分的鳴法螺,嗚咽的法螺聲平添了法場的神秘意境;上師請齋主拈香時唱莊嚴徐緩的《香贊》,營造出莊重肅穆的儀式氣氛;金剛上師、上文③上文、下文是儀式中上師的主要助手,分坐于上師的左右兩邊,接應上師的各類唱腔與演奏。、下文誦《結界真言》 《遣魔咒》等真言或咒語時,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只傳其聲,不譯密意”的特征,加之誦唱咒語或真言時音調深沉緩慢,更加重了其神秘莫測之感;瑜伽焰口“身密”之手印,蘊含著佛法之無窮奧妙,具有通神伏魔之法力,亦是營造儀式現場神圣氣氛的利器;另有各法器牌子的名稱,如【七星板】【三星板】【蓮九板】等,蘊含著神秘的儀式氣息,這些都是為了營造出這種虛擬的儀式現場氣氛而設計的儀式手段而已。
(二)藝術性
藝術性當屬瑜伽焰口儀式的宗教外功能,雖不是其核心功能,但卻是宗教內功能得以優化實施的有力保障。瑜伽焰口儀式音樂表演的藝術性主要體現在音樂性、舞蹈性、美術性、文學性四個方面。
音樂性是瑜伽焰口儀式音樂表演藝術性最顯著的特征。整場儀式就像是一部規模宏大的儀式音樂劇,包括各種體裁、結構、風格的唱腔和法器牌子,共同營造出美輪美奐的音樂世界。莊嚴沉緩、婉轉柔美的 《香贊》,綿延悠長、慈悲圣潔的佛號,神秘莫測、變化多端的咒語或真言,鏗鏘有力、疾風驟雨般的偈文吟誦,音色豐富、結構玄妙的法器牌子,加之唱腔曲牌在組合上的結構美,法師演唱的潤腔之美、語音之美,演唱形式上的烘托對比之美,所有的音樂元素皆構成一部章法有度、音樂豐美的藝術巨制。
舞蹈性是瑜伽焰口儀式音樂表演又一重要特征,主要表現為焰口手印之豐美。手印是瑜伽修行三密之身密,是重要的方便法門。據統計,羅漢寺瑜伽焰口儀式表演共出34套手印,是焰口儀式視覺審美的重要內容,與儀式音樂表演交相輝映、相得益彰。美術性則主要體現在儀式音樂表演現場的陳設布置上,主要以視覺審美為主。如大雄寶殿的布景裝飾,三寶法壇、藥師法壇、寒林法壇三個法壇的造型布置,法桌上供品的陳設,佛像與牌位的擺放,法器的造型,牌位上的書法字體等,皆具有視覺審美意義,與儀式音樂表演一道構成整場儀式表演的重要內容。文學性主要指梵唄唱詞的格調與內涵美,本身已具有強烈的儀式表演特性。瑜伽焰口儀式音樂唱腔包括贊、偈、咒、文四大文體,每一種文體都有其特定的詞格。修辭美也是焰口唱詞的重要特征,常見的修辭手法有比喻、夸張、比興、借代、擬人、對仗、排比、互文、設問、反問、祈使等。此外,意境美也是唱詞著意打造的重要審美特征,需借助詞格、修辭、語調、樂調等綜合手段來塑造。這些唱詞原本所具有的文學藝術之美是瑜伽焰口儀式音樂表演綜合美感的重要因素。 譜例1《香贊》局部
(三)功能性
作為儀式音樂表演,與純粹的舞臺戲劇有很大差異。前者重點強調功能性和有效性,后者則多強調娛樂和審美性。在數千年華化與歷史演變中,佛教與漢地儒、道等文化之間進行了深刻的濡化與涵化,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支柱。佛教儀式及其用樂因其特有的傳承時空和宗教功能,客觀上承襲了華夏傳統音樂文化的基因,在構建中華民族共同心理特質、促進民族融合與國家認同的歷史演進中發揮了重要的社會治理功能。佛教儀式音樂以其攝心縛人的教化功能,在維系我國鄉土社會秩序、傳承中華傳統文化以及和合人倫關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佛教儀式音樂表演的功能往往展示出較強的層次和針對性,由于個體或群體的需求不同,同一場儀式所達成的功效亦不一樣。根據這一點,可將羅漢寺瑜伽焰口儀式音樂表演的功能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核心的宗教內功能。如以僧人為代表的純宗教(也有一定經濟方面的因素)功能,重在弘法利生并增加自己的修行;以齋信為代表的群體,他們的主要意圖是祭祀祖先,度亡薦靈。二是外圍的宗教外功能。如僅是欣賞瑜伽焰口儀式音樂表演形式之美的旁觀者,他們參加或參觀焰口儀式表演,重點是為享受其視覺與聽覺上的愉悅感;又如研究瑜伽焰口儀式音樂表演的學者,或以文化產業為噱頭炒作的商人等,他們基本游移于瑜伽焰口儀式文化內涵與功能的外圍,對他們而言,同一場儀式表演的功能性大相徑庭。一般地,宗教內功能是儀式戲劇表演的重要功能和本質特征,也是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土壤。宗教外功能則是其附屬功能與非本質特征。宗教內功能可以主宰宗教外功能,反之未然。①此二功能或可稱為宗教功能與非宗教功能,但采用“宗教內”與“宗教外”意圖更多地指向與宗教儀式相關的人群。
這種層次性在儀式表演結構及其用樂原則上亦表現出鮮明的針對性,為保證宗教內功能的實施和延續,瑜伽焰口儀式音樂必須保持結構相對固定,軌范嚴謹,并盡量完善其宗教外功能,以促進宗教內功能更好地行使其本質功能。如在演唱一些共性較明顯的唱腔(如《香贊》《觀世音菩薩圣號》《大悲咒》 《尊勝咒》等)時,法師們會盡量保持其原有結構和風格,有意襯托其莊嚴和神圣性。而在一些個性較強的唱腔(如各種真言及對偈部分)或法器伴奏 (如 【蓮九板】【七星板】 【倉倉板】等)上,自由空間較大,無嚴格恪守的固定法則。
(四)兩極漸變的音聲體系
音樂表演是整場儀式戲劇表演的重要組成部分,曲目豐富、形式多樣,是推動儀程發展、營造儀式氛圍并實施社會教化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正因為儀式音樂表演在實際運用中的表現方式多樣,學者們對這一概念及范疇的界定尚存爭議。比如,應該將哪些音響視作儀式音樂?儀式音樂具有怎樣的特征?等等。薛藝兵認為,儀式環境中的各種聲音都有可能是儀式音樂,區別的標準是看其是否與特定的儀式環境、情緒、目的相吻合,并對參與者產生生理和心理效應。②薛藝兵:《儀式音樂的概念界定》,《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第33頁。筆者按照旋律化程度 (音樂性)對羅漢寺瑜伽焰口儀式唱腔進行分類,可清晰地看到其由旋律化至非旋律化逐級變化的特征,即歌唱腔的旋律化程度最高,直誦腔反之,誦唱腔則居前二者中間,成為旋律化程度由強至弱的過度環節。若按此標準將這一結果推而廣之,整場儀式構建了一個兩極漸變的龐大音聲體系:第一層次分為人聲與器聲兩大類,人聲基本涵括在歌唱腔、誦唱腔、直誦腔③歌唱腔是指一般聽賞意義上的旋律婉轉優美、音響和諧悅耳、樂音起伏流暢等常態審美范疇下的歌唱性腔型,即通常所謂梵唄,不包括其他少數特例;誦唱腔即亦唱亦誦之腔;直誦腔則是腔型簡單,近似朗誦的腔型。詳參胡曉東《佛樂分類新論》(《音樂研究》2014年第2期)第84頁。三類中;器聲則分為法器牌子和自由器聲兩類。④自由器聲是指由法器或非法器等物件,在無人為固定的嚴密邏輯思維控制下的相對自由發聲,如上師壓佛尺聲,振鈴聲、鳴法螺聲等。按照音樂性程度由高到低將上述五類儀式音樂排列如下:
從歌唱腔至自由器聲,音樂性逐級遞減。整場儀式音樂表演都涵蓋于這一音樂性兩極漸變的音聲體系中。在實際儀式應用中,這種兩極漸變性音聲呈現出功能化的傾向。一般而言,用于贊神譽佛的唱腔常為旋律化程度較高的歌唱腔,如《香贊》《楊枝凈水贊》等;用于薦亡度鬼的唱腔常為旋律化程度次之的誦唱腔和直誦腔,如《奉食咒》 《遣魔咒》等;純粹的法器牌子在儀式中往往被賦予特殊的法力,通常用于超度亡靈、救拔餓鬼、驅魔凈壇等儀程中,具有重要的宗教功能,如【蓮九板】 【七星板】等;自由器聲是各儀程銜接部分常用的手段,具有承上啟下、渲染儀式氣氛的作用,演奏規范相對寬松,但貫穿了某種核心思維,如儀式音樂表演中金剛上師曾幾次振鈴,時間少則長達五六分鐘,其間常以某一種節奏片段貫穿始終,體現了執儀者特定的宗教觀念。如圖2所示,在兩極漸變的音樂體系中,其實隱含著佛教儀式音樂表演中深層的功用主義思想,即施用于神佛與人鬼的儀式音樂大致分別居于音樂性強弱的兩端。
二、三密合一
從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視角來審視瑜伽焰口儀式,“三密合一”是其中最重要的宗教觀念(“歸屬性”模型),這一模式與儀式表演中的身體行為和音樂唱誦等符號表征(“對象性”模型)互為表里,成為儀式音樂表演及音聲景觀 (Sound scape)的主宰和基礎。瑜伽焰口儀式除向餓鬼施食、度亡薦靈之外,更重要的任務是向其說法,使其皈依授戒,具足正見,最終實現普度六道眾生之目的。瑜伽本是密教修行的重要法門,“yoga”一般譯作“相應”,常含五義,即與境相應,與行相應,與理相應,與果相應,與機相應。密教認為,身結印、口誦咒、意觀理,三者相應,謂“三密合一”。四川成都文殊院 《瑜伽焰口·焰口序》亦云:“瑜伽,竺國語,此翻相應,密部之總名也。約而言之,手結密印,口誦真言,意專觀想。身與口協,口與意符,意與身會,三業相應,故曰瑜伽。”在整場瑜伽焰口儀式中,金剛上師圍繞身、口、意三密合一展開所有的表演。身密主要指手結瑜伽焰口手印;口密是指口誦真言或咒語,即佛教梵唄唱腔;意密則主要是以心觀想佛緣種子溝通神鬼等。儀式表演中,要求此三密貫通合一,專神持久,方能于得三摩地①三摩地又被稱為三昧地、三摩提、三么地、三昧、三摩底、三摩帝等,常譯作“定”,即心無旁騖,駐心于一境不散不亂之意。《顯揚圣教論》第二卷第六頁道:三摩地者,謂已轉依者,心住一境性。后獲取各種神通。佛教還宣揚修行瑜伽三密合一最終能證得三乘之果,即阿羅漢果、緣覺果和佛三種果位。②《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27冊,第203頁。
事實上,在瑜伽焰口儀式音樂表演中,此三密合一的修行愿力是考驗金剛上師修行高低的試金石,法師們認為,若能定力專一、心住一處,即可通達六道,獲得三乘之果,增福添壽。反之,心神散亂、三密不合,非但不能得正果,反而會觸怒神鬼,惹禍上身。明祩宏《竹窗隨筆》釋云:
手結印,口誦咒,心作觀,三業相應之謂瑜伽,其事非易易也,今印咒未必精,而況觀力乎?則不相應矣!不相應,則不惟不能利生,而亦或反至害己。③[明]祩宏:《竹窗隨筆·竹窗三筆·施食者》,撰于萬歷四十三年(1615),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刊行。
因此,在對瑜伽焰口儀式唱腔音樂(口密真言)進行研究的同時,必然要緊密結合其身密(手印及其他身體行為)與意密(觀想)二符號表征系統進行綜合整體觀照。以下列舉儀式音樂表演儀程中部分唱誦真言(口密)、手結密印 (身密)、及意專觀想(意密)的內容及要求,以資說明。④表中的手印及種字圖,皆取自四川成都文殊院流通處印行的《瑜伽焰口》。
關于上述儀式音樂表演中唱誦的真言或咒語屬典型的音樂符號,筆者已有專文對其音樂形態進行分析⑤詳參筆者關于羅漢寺瑜伽焰口儀式唱腔音樂形態分析的論文,如《佛樂分類新論——以重慶羅漢寺瑜伽焰口唱腔為例》(《音樂研究》2014年第2期)及《我國民族音樂調式型號體系研究舉隅——以重慶羅漢寺為例》(《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等。,此不贅述。本文僅探討在“三密合一”這一歸屬性模型統領下,音樂符號表征與其他行為、觀想等符號表征之間的關系,以此探析羅漢寺瑜伽焰口儀式表演中的文化模式及其符號學表達。透過上述符號表征 (“對象性”模型)與象征符號(“歸屬性”模型)之間的關系,揭示出這些特定的儀式活動皆是在固有宗教觀念指導下的神話表演,反過來又為其整體宗教觀念體系的確立提供強有力的事實支撐,雙方互為因果、相互轉化。在瑜伽焰口儀式的絕大多數儀程中都包括上述“身結印、口誦咒、意觀理”三密合一的表演。此三者中,前二者重其表,是外殼,后一者重其內,是核心,正所謂 “身與口協,口與意符,意與身會,三業相應”是也。因此,瑜伽行者尤重意密內理的修持,并以此作為評判法師修為高低的重要標準。

表1 “三密合一”及其符號表征對應關系
三、閾限期
英國人類學者特納 (Victor Turner)指出:“儀式表演是一門開放的、永不終結的、處于閾限階段(1iminal phase)的藝術,是一個社會過程的研究范式。”①Turner Victor.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NewYork:PAJPublications.1986.p.8.特納以閾限期泛指儀式過程中結構關系轉換的過渡階段,是一種在兩個穩定“狀態”之間的轉換。當處于這一有限的時空階段時,人們的社會關系呈“反結構”狀態,即儀式參與者們的身份、地位和社會等級均顯示出與正常的社會結構關系 (位置結構)截然相反的結構 (反結構)②特納將人類社會關系分作兩類狀態:一是正常狀態,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呈現出相對穩定的結構模式,又可稱為“位置結構(Structure of Status)”。“位置(Status)”是指人們在社會上所擁有的職業、法權地位、職務等社會常態,個人的生理或心理生活狀態,儀式前與儀式后皆屬此類社會關系狀態。另一類是與日常社會生活不同的儀式生活狀態,呈現出“反結構(anti-structure)”的特點,而儀式過程中的閾限期(1iminal phase)則是對儀式前和儀式后兩個正常穩定狀態的反轉過程。,特納將其稱為“反結構共同體 (anti-structural communities)”。③TurnerVictor.The Ritual Process: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Chiago:Aldine Pub.Co.1969.pp.103—106.在特納看來,人類是結構與反結構共同造就的實體,人類在反結構中成長,在結構中生存。④特納:《戲劇、場景及隱喻:人類社會的象征性行為》,劉珩、石毅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329—330頁。這種“反結構共同體”正是大多數儀式的結構特征,它折射出人們對現實生活的不滿與追求,并在信仰世界力尋求慰藉的心理過程,它們并非彼此對立,而是彼此互鑒、水乳交融,共同構成人們生活的整體,潛在地促進人們的身份認同、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在瑜伽焰口儀式音樂表演中,眾生平等,六道皆有佛性,金剛上師(儀式核心人物)化作毗盧如來佛普度十方六道眾生,這正是人們對正常社會中的位置結構反思后,將理想王國寄托于佛教儀式的具體體現。例如在瑜伽焰口儀式唱腔中常用的《三昧耶戒偈》就表達了在理想佛國,諸佛菩薩與眾生平等,皆可獲得真正平等覺知一切真理的無上智慧的觀念:
汝等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
可見,儀式信仰的本質就在于儀式閾限期內的反結構社會關系,人們可在其中獲得在正常社會生活狀態下不可能體會到的理想的大同世界,從而得到心靈的慰藉。這一結構模式對于維護和諧社會秩序,調和人倫關系具有良好的化導功能,儀式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在儀式音樂表演中,“閾限期”往往與“迷幻(trance)”現象聯系在一起,即隨著儀式表演的深入,人們在某種儀式觀念的主導下,伴隨著一定的誘因(主要是音樂和舞蹈表演)由“自我”進入“他我”狀態的過程。法國學者吉爾伯特· 羅杰 (Gilbert Rouget)將其喚作“迷幻”,是指一種人類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在某種特定的儀式場合出現的短暫性意識變化過程或狀態,這期間音樂、舞蹈或某種法器等共同參與表演促使迷幻發生。美國學者貝克(Judith Becker)隨后將其改為“trancing”,更注重其“入境→保持→出境”動態轉換過程。⑤蕭梅:《通過羅杰的觀看:〈音樂與迷幻——論音樂與附體的關系〉》,《中國音樂學》2009年第3期,第46頁。在羅漢寺瑜伽焰口儀式表演中,以金剛上師在法臺上戴上五佛冠(毗盧帽)為節點,迷幻即已發生,閾限期開始,此時金剛上師化身為毗盧如來佛,儀式音樂表演即進入第一人稱代言的話語敘事方式,上師可行使如來佛的一切法令和法術,呈現出與位置結構截然相反的“反結構”狀態。此時音樂唱腔表演與此配合,眾師齊唱誦《盧舍那佛圣號》,音樂成為上師進入迷幻狀態的催化劑。 “閾限前期”與“閾限后期”則分別指金剛上師戴冠前及除冠后的儀式結構部分,為第三人稱敘事方式。當上師誦唱《尊勝咒》之后除冠并脫去袈裟,即刻便還原本身 (自我)。此時,眾師配合唱誦《尊勝幢菩薩圣號》,助其回歸真身。可見,五佛冠這一符號表征成了閾限前后期儀式音樂表演轉換的制動器。其角色轉換,可用下圖示意之:
作為儀式音樂之承載,閾限期及其“反結構共同體”對儀式用樂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從閾限期與結構狀態來看,整場瑜伽焰口儀式表演過程為:
閾限前期(正常狀態:位置結構)?閾限期(儀式狀態:反結構)?閾限后期(正常狀態:位置結構)
上述這種身份與儀式身份的雙重“位差”現象潛在地影響著儀式的程序與結構,固然也影響著儀式音樂的原則與風格。例如處于閾限前期與后期的儀式(即儀程的前后端)結構及內容較為松散自由,用樂方式與音樂形態亦相對自由多變,而處于閾限期的儀式(即儀程的中間主體部分)結構及內容較為嚴格穩定,其用樂原則與音樂形態則要嚴謹穩定得多。其原因在于閾限期外的金剛上師僅是法師本人,執儀者與信眾二維關系處于正常的位置結構狀態,儀程結構與用樂方式的自由空間要大些,而閾限期內的金剛上師成為如來的化身,執儀者與信眾之間的關系處于非正常的反結構狀態,出于崇佛譽神、莊嚴佛法之旨,其儀程結構、用樂原則及內容應力求嚴謹穩固。②關于羅漢寺瑜伽焰口儀式結構與儀式用樂之關系,筆者已在《巴渝地區瑜伽焰口儀式音樂的類型與結構》(《中國音樂》2017年第1期)與《佛樂傳播與國家在場——以瑜伽焰口儀式音樂為例》(《民族藝術》2017年第1期)兩文中有專述。圖4可展示羅漢寺瑜伽焰口儀式中執儀者與信眾二維結構與儀式結構、儀式用樂之關系(見圖4)。
在田野考察中,筆者曾就儀式閾限期內的音樂表演問題對多位金剛上師進行訪談,部分上師不愿深談,表示“不記得自己做了什么”。另部分上師則表示這一規范是從師父、師父的師父那里傳下來的,因為從“登座啟會”儀程戴冠開始,就暗示著金剛上師已經化身為毗盧如來佛,佛菩薩的一舉一動(音樂唱誦表演)是不能隨便改動的。可見,作為符號表征系統的瑜伽焰口儀式音樂表演(“對象性”模型)的變化與差異,本質上受制于儀式閾限期這一宗教觀念(“歸屬性”模型),閾限期內的音樂表演與閾限期前后相比,執儀者的敘事方式(儀式音樂表演)悄然發生改變,在自我(第一人稱代言)和他我(第三人稱敘事)之間相互穿梭,以此達成儀式音樂表演的社會功能。執儀者與參與者皆對儀式閾限這一結構模式有著高度的心理認同,在長期的文化浸潤中形成了強有力的文化身份認同感,進而對和合社會人倫、維系鄉土社會秩序發揮了積極作用。
結 語
儀式音樂表演因其“攝心縛人”的社會教化功能,在維系鄉土社會秩序、傳承中華傳統文化以及和合人倫關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佛教儀式音樂通過構建中華民族共同心理特質,在促進民族交往、交流與交融以及文化認同、國家認同的歷史演進中發揮了重要的社會治理功能。因此,儀式音樂表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以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視角審視佛教儀式音樂,對儀式音樂表演沖突中的一系列“行為”與“場景”進行細致觀察,借用符號學與闡釋學等學科理念,對其儀式音樂表演過程中呈現出的一系列象征符號與符號表征進行解讀,可深入探究儀式文化持有者內在的文化精神與觀念構型,由此揭示出儀式行為及其產品——儀式音樂與儀式表演行為——儀式文本與文化主體觀念之間的深層關聯,進而達到對儀式音樂表演語境與社會功能的整體認知,豐富其文化闡釋的內涵,推進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研究全面深入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