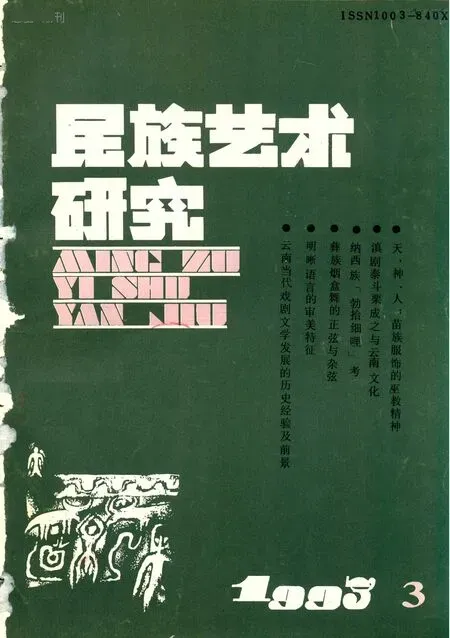文化符號在舞蹈創作中的運用
——以“茶馬古道”題材大型舞作為例
唐白晶
“符號”的范圍很廣泛,能夠作為某一事物標志的,都可稱為“符號”。索緒爾認為符號是“能指”與“所指”的復合體;皮爾斯認為符號是相對于某人在某個方面能代替(代表、表現)他物的某種東西;羅蘭·巴特將索緒爾的“符號二元論”運用到文化研究中,將“意指系統”分為“元語言”和“含蓄意指”兩種類型,讓符號與文化之間形成了不可分離的緊密聯系;卡西爾的“文化符號論”提出“藝術可以被定義為一種符號語言”,每一個藝術形象,都可以說是一個有特定含義的符號或符號體系;蘇聯“莫斯科—塔爾圖”學派以洛特曼等人為代表提出“符號形成文本,文本形成文化,文化形成符號圈”①康澄:《文化符號學的空間闡釋——尤里·洛特曼的符號圈理論研究》,《外國文學評論》2006年第2期。,他們從大處著眼于文化研究,以“符號場”的理論解釋“任何文化現象都應該從符號開始,從解碼開始。”②[俄]尤里·洛特曼:《俄羅斯文化的歷史和類型學》,轉引自康澄:《文化及其生存與發展的空間——洛特曼文化符號學理論研究》,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符號所表現的不是事物,而是文化內涵,事物只能通過交際空間賦予它的文化底蘊才能被認識。”③王銘玉:《語言符號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頁。中國符號學家趙毅衡認為“符號是攜帶意義的感知。”④趙毅衡:《形式之謎》,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93頁。因此,在認知系統中,符號指代一定意義的意象,可以是圖形、圖像、文字、聲音、建筑、造型,也可以是一種思想意識、文化理念,甚至是時事人物。文化符號是文化內涵的重要載體和形式,也是一種文化的典型表征。在文化的繼承與傳播中,文化符號是文化精神的表征,同時也是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的標志。歷史上世界對中國的認識,主要是通過茶葉、瓷器、絲綢、京劇、武術等文化符號實現的。
舞蹈作品作為一種藝術文本,是產生文化意義的符號活動,同時也是我們闡釋文化記憶的媒介,文化符號在藝術文本中的運用至關重要。在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北有絲綢之路,南有茶馬古道”。“一路”“一道”,兩相輝映;“一絲” “一茶”,千年畫卷——共同描繪了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在舞蹈創作中,有關“絲路”題材的作品不勝枚舉,“敦煌舞”“飛天”“莫高窟”等文化符號在《絲路花雨》 《大夢敦煌》等經典作品中都有很好的呈現;而以“茶馬古道”為題材的作品卻屈指可數,特別是大型舞臺創作(以下簡稱“大型舞作”)方面,僅有舞蹈詩《茶馬古道——高原女人·大山漢》《茶馬古道——古道留痕》,舞劇《茶馬古道間的鈴聲》《茶馬古道》,旅游歌舞《茶馬古道》和 《印象·麗江》的部分篇章等,而且部分舞蹈作品因為對于茶馬古道的文化符號挖掘不深、認識不夠,從而在舞蹈創作中對茶馬古道所表征的文化意義和價值觀念體現不足。本文通過對“茶馬古道”文化符號的梳理,探析文化符號在“茶馬古道”題材大型舞作中的運用以及文化符號的運用對于大型舞作的意義,以期找出文化符號在舞蹈創作中的運用規律,從而提升大型舞作的人文價值。
一、茶馬古道的文化符號
“茶馬古道”一詞最早出自1992年由云南大學出版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被后世譽為“茶馬古道六君子”的木霽虹、陳保亞、李旭、徐涌濤、王曉松、李林在這次“史無前例”的田野調查中,提出了“茶馬古道”這一學術概念:“茶馬古道是連接橫斷山脈與喜馬拉雅山脈兩大民族文化帶的走廊;它主要呈東西走向,并與西南絲綢之路形成十字交叉并有相當部分的重合,同時與費孝通先生反復強調的藏彝走廊形成部分交匯和重合;它主要興起于漢藏之間源遠流長的茶馬互市,以傳統的背夫、馬幫和牦牛馱隊作為運輸交通載體;它萌發于唐代,在宋元明時期以茶馬互市逐漸發展成型,在清代到達商貿互動的鼎盛時期,進入民國雖逐漸顯示衰敗之象,但到抗日戰爭時期它一度成為中國唯一的對外陸上通道,體現了罕見的繁盛和輝煌。”①李旭:《茶馬古道——橫斷山脈、喜馬拉雅文化帶民族走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自序。在中華文明這個大符號圈中,茶馬古道有其獨特的文化意蘊,茶馬古道文化符號可以簡要概括為以 “茶”“馬”“道”“市”“人”為主,包含與生產生活相關方面的大型文化符號集,其間的符號與符號之間是相互交織、共生互融的關系。本文以皮爾斯的符號分類理論②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頁。,將茶馬古道的文化符號按照“像似符號”(icon)、“指示符號”(index)、“規約符號”(convention)進行歸納梳理,如下圖:

類型文化符號像似符號 指示符號 規約符號茶與茶相關的圖像;茶形(餅茶、磚茶等);茶具;祭茶祖儀式;茶香等采茶調、采茶舞;與茶相關的詩詞;制茶工序 (曬茶、打酥油茶、壓茶等);茶行牌匾(“隆昌號”)等飲茶禮儀、習俗;茶的“個性”(如:老班章的霸氣、易武的陰柔、冰島的清甜、困鹿山的雅致等);茶道等馬 與馬相關的圖像;聲音、味道;模擬馬的姿態、動作等馬蹄印;馬鞭;馬燈;馬鞍;銅鈴;馬幫旗等騾幫、牦牛幫統稱馬幫;馬幫男性化;馬幫的文化禁忌等

類型文化符號像似符號 指示符號 規約符號道與路相關的圖像、文字;青石板;雪山、懸崖、密林、深山、江邊等“之字形” “蛇形” “橫排”“豎排” “斜排”等隊形、舞美;地圖路線;路標、方向牌等道阻且長的意識;文化遺產走廊等市古鎮、驛站的圖像、文字;屋舍、集市、寺院等場景;車水馬龍、叫賣等聲音地圖上的名字(奔子欄、麗江、勐海、石屏等);不同國家的舞蹈展示(泰國舞、印度舞、斯里蘭卡舞等)貿易交往;安逸、繁榮、富饒的象征;民族多元風情的表達等人趕馬人、馬幫、背夫、商戶、僧侶、采茶女、土匪、民族首領、留守女人等形象與人相關的物品如:打杵棍、行囊、服飾、道具等馬幫為男人,留守家鄉的是女人的認知;男人思鄉,女人盼歸等
首先,“像似符號”指符號與對象給人的感官帶來“像似性”的感覺,主要分為形象式像似,這是視覺感官,例如與茶形象相關的圖像呈現、模擬馬的動作等;圖表式像似,是一種構造類似,例如表現茶馬古道山路崎嶇的舞蹈隊形流動、循環、疊加等;比喻式像似,這是比形象式像似更抽象的一種,脫離了符號的初級像似,是一種思維像似和“擬態”像似,例如祭茶祖儀式就是一種比喻式像似符號,以一種關系比喻地模仿人神交往。
其次,“指示符號”指符號與對象因為鄰接、因果、部分與整體等關系而能互相提示,從而讓接收者感知符號。指示性符號一般由像似性符號推出,或者由解釋者的經驗和語境來理解。例如采茶調的旋律、茶行的牌匾等都能指示茶這一文化符號;路牌、馬幫旗、鈴聲等指示茶馬古道的馬幫;不同民族風情的舞蹈指示不同的區域等。
最后,規約符號指的是社會約定符號與意義的關系。規約符號,被認為是最為復雜的符號,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語言符號。在語言符號之上建立的文化符號以及在語言符號之下的自然符號,都可以被視為規約符號,因為規約符號的建立基礎,就是習慣,即一個連續發展、跨越了自然和語言文化的概念。大多數符號都具有社會規約性,規約性是社會性的,需要界定于同一個文化語境中。規約符號必然具有指示性,它是約定俗成的,可以說是一種象征(symbol),但都離不開解釋者的存在。例如,茶馬古道文化中馬幫全是男性,采茶的人多為女性;在茶馬古道上跑長途的馬幫,其實稱為“騾幫”更名副其實,川藏線還有“牦牛幫”,但社會規約還是統一為“馬”。
當然,現實中這三類符號存在交叉重疊的功能,皮爾斯也指出任何符號多多少少都有指示性,指示符號可以與像似符號結合,特別是在舞蹈中,舞蹈動作語言符號的指示性應當擺在首位,因為有指示性就一定有像似性,而有像似性卻不一定有指示性。例如舞蹈中演員手持簸箕曬茶,身體姿態重復這一曬茶、簸茶的動律,這一舞蹈語言符號就具有像似—指示的意義。相當多的符號混雜了各種成分,無法截然說某個符號屬于哪一種,只是各種成分多少而已。我們更多的是需要明白:“像似性使符號表意生動直觀;指示性使對象集合井然有序;規約性讓符號表意準確有效。”皮爾斯說:“盡可能均勻混合的符號(blended as equally as possible),是最完美的符號。”①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頁。
二、大型舞作中“茶馬古道”文化符號的運用
文本是文化符號學的核心概念,大型舞作被視為一種文本,在文化符號到符號圈的發展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橋梁作用。文化符號學的代表人物洛特曼認為,“文本可以傳遞、保存及產生信息。”②康澄:《文化符號學的空間闡釋——尤里·洛特曼的符號圈理論研究》,《外國文學評論》2006年第2期。文本是“文化的縮小模式”,是“一種產生意義的復雜的和互動的活動——符號活動。”③郭鴻:《文化符號學評介——文化符號學的符號學分析》,《山東外語教學》2006年第3期。因此,在梳理“茶馬古道”題材的大型舞作中,文化符號在這一藝術文本中的運用值得關注。
(一)表意感知—經驗理解—抽象理解
皮爾斯認為符號的理解有三個階段:“第一性”即顯現性;“第二性”能夠表達意義;“第三性”能夠對事物形成判斷。這是一個從表意感知到經驗理解再到抽象理解的逐漸深化的過程。筆者認為,在藝術文本中,能夠表現這“三性”過程的文化符號應該是運用很好的范例。
舞劇《茶馬古道》④舞劇《茶馬古道》是國家藝術基金2019年度的資助項目,2020年1月10日由四川省歌舞劇院在四川大劇院首演。總導演馬東風、編劇吳瑜婷、作曲顧磊等。(馬東風/2020)選取了茶馬古道川藏段“背夫”這一文化符號為全劇的核心,“背夫”手握一根細小的打杵杖、背著龐大沉重的茶包,他們短小精悍、堅韌不屈的身體與背上的茶包形成對比,這一人物形象作為一種像似符號給觀眾帶來一種深刻的視覺印象。背夫們在 “洗腳舞”“鋪蓋舞”等舞段中所表現出來的詼諧幽默、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與在崎嶇艱難的古道上行走的舞蹈動態形成對比,此時背夫這一文化符號傳遞出了茶馬古道四川段獨有的人文氣息。在國難當頭時,背夫們用無數沉重的腳印,走出了一條史上最艱難的茶馬古道,挺起了中華民族不屈的脊梁,他們統一重復著單腳抬起與杵杖同時跺地、甩動手臂、彎腰喘氣嘆息的舞蹈形態,一聲聲振聾發聵的響聲直擊人心,高潮迭起,背夫這一文化符號更是隱喻了中華民族勇敢樂觀、堅韌不屈的精神品質。
舞蹈詩《茶馬古道——古道留痕》⑤舞蹈詩《茶馬古道——古道留痕》總編導:唐鏞,由云南尚柔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昆明市民族歌舞劇院共同演繹。2017年在昆明新亞洲體育城以“裸演”(無燈光、舞美、服飾等)的形式面向社會公演。(唐鏞/2017)選取茶馬古道的男人與女人不同的精神狀態作為文化符號來結構舞蹈詩的文本。在序《馬幫》中以20位裸露上身、背著草帽的男子群舞開場,他們唱著“趕馬調”,動作整齊劃一、節奏強烈地行進著,舞蹈采用彝族踩蕎和“大褲腳”的動律,突出了大山漢子堅韌豪爽、樂觀勇敢的精神面貌;第一章《山村》以20位女子聯袂踏歌的打歌形式蜿蜒出場,行進的路線像極了茶馬古道崎嶇的山路,直至集中于點狀形成了盼歸女子的群像,一位身懷六甲的婦女在中間呈現出個像與群像的對比,伴隨著納西族歌曲《美麗的白云》低吟出高原女人的隱忍、堅強。這樣的藝術處理方法在大型實景演出《印象·麗江》⑥大型實景演出《印象·麗江》(雪山篇)總導演:張藝謀、王潮歌、樊躍,于2006年7月在云南麗江玉龍雪山的甘海子藍月谷劇場正式公演。中也有呈現,開篇《古道馬幫》中幾十個男演員身披白色羊毛褂,手持馬鞍,呈橫排的隊列統一行進,環形立體舞臺的“之字形”道路,看得見一排排馬幫漢子“趕著馬”走在紅土高原崎嶇的山路上,時而穿插騎著真馬的演員奔馳而過,虛實的對比顯示出馬鞍這一道具運用的巧妙創意。如果說,馬鞍舞體現了馬幫漢子瀟灑勇猛的陽剛之美,那么隨后的納西族婦女身背竹籮、塌腰抬腳屈膝的舞蹈動律則體現了高原女人勤勞樸實的堅韌品質。比演員身體大出兩倍之多的竹背籮與塌腰屈膝的人物體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一視覺效果與之前提到的舞劇《茶馬古道》背夫的形象異曲同工,茶馬古道上的納西女人披星戴月、一步一個腳印地走過人生的每一步,她們任勞任怨,背負了所有的艱辛,支撐起整個家園。
舞劇《茶馬古道間的鈴聲》①舞劇《茶馬古道間的鈴聲》總導演和編劇:李進,中央民族大學舞蹈學院2010級編導班的畢業作品,于2013年12月首次公演,經過修改后2014年12月進行了第二次公演。(李進/2013)在序《鈴命天授》用一段很有民族特色的東巴舞來展現,1位東巴大祭師和6位東巴各持不一樣的法器:牦牛尾、長刀、法杖、經書、板鈴等,以圓圈的運動軌跡祈福禱告,其步伐在牦牛舞、祈福舞的基礎上作了夸張放大,使得保留民間舞蹈形態的同時又有舞臺化的表演。兩位男主角圍繞著“銅鈴”這一文化符號進行舞蹈,所有的矛盾沖突也因為“銅鈴”而展開,“銅鈴”不僅寓意著茶馬古道馬幫文化的統領地位,還寓意著文化的代際相傳,這一民族文化符號的運用,對于整部舞劇的氛圍營造、文化基調的定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劇中對于馬的擬人化表演令人印象深刻。男子群舞以跳步、后踢腿、跪地、轉圈等動作展現了云南境內茶馬古道的騾馬特色,云南歷來就有這樣的老話:“人比人,氣死人,馬比騾子馱不成。”騾子擅長穿行于橫斷山脈崎嶇不平的山路,因而在設計 “馬”的動作時,編導突破了動作語言的慣性,沒有沿用蒙古族的馬步動作,而是選擇了氐羌民族舞蹈注重下肢跳步的風格,完成了“馬”這一文化符號從表意感知到經驗理解再到抽象理解的過程。
(二)在文化符號運用上的單一和不足
“文化是人們有意識的行為創造的,但一種文化現象上升和抽象化為一種文化特有的表征符號,卻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變革中,經過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不斷選擇、淘汰最終定型的。”②邴正:《面向21世紀的中國文化形象與文化符號——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理論思考》,《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3期。這就需要藝術家具有挖掘文化符號的敏銳眼力和文化積淀。
《茶馬古道——高原女人·大山漢》③舞蹈詩《茶馬古道——高原女人·大山漢》總編導:唐鏞,由云南藝術學院文華學院演出,2013年參加云南省第十二屆新劇目展演榮獲新劇目特別獎和編導、表演、音樂創作一等獎,參加第九屆“荷花獎”舞劇舞蹈詩比賽獲得作品和表演銀獎。(唐鏞/2013)在表現馬幫漢子與馬的形象時,選擇的是單一的動作元素,演員四肢著地“一順邊”前進意為 “馬”的文化符號,其他演員在旁邊跟著彪悍前行意為 “趕馬人”的文化符號,這種動作符號機械化地重復,缺乏“抽象理解”的解釋。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舞蹈評論家歐建平提出:“動作的主題確立之后,變奏與發展當然是必要的,否則會讓觀眾產生審美疲勞,覺得某個舞段過于冗長!比如在第一章的《女人》中,大群女子各抱一個襁褓的那個舞段,就需要提煉并發展云南婦女抱孩子、奶孩子、愛孩子的特有方式與動作習慣,而不是從頭到尾,只有走路的動作和彎腰的身段!再如《彩虹舞》,也有類似的不足,而單一的素材組合,只能釋放單一的情緒,難以表現深刻的戲劇內涵!”④歐建平:《詩情畫意 樂舞渾融——第九屆中國舞蹈“荷花獎”舞劇舞蹈詩評獎決賽點評》,《舞蹈》2014年第1期。除此之外,在表現趕馬人思鄉時的文化符號僅用夢境的形式呈現一段雙人舞,表現留守女人盼歸時的文化符號僅用身體前傾站立、遙望遠方的動作元素,顯然過于簡單直白了。
大型駐場民族風情秀《茶馬古道》⑤大型駐場民族風情秀《茶馬古道》總導演劉翠,由普洱市人民政府、云南湄公河集團與中國東方歌舞團聯合創作出品,于2018年1月15日在普洱大劇院首演。(劉翠/2018)在展現茶馬古道少數民族風情的同時,也發揮了中國東方歌舞團的優勢,將緬甸舞、印度舞、斯里蘭卡舞、埃及舞等融入劇情發展中,體現了茶馬古道文化輻射南亞、東南亞的特點。雖然不同民族舞蹈展現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例如布朗族的祭茶舞、拉祜族的蘆笙舞、傣族的沐浴舞、佤族的木鼓舞等,但是這種組舞風情秀的方式,只將舞蹈符號停留在“表意感知—經驗理解”的層面,欠缺更深層的文化內涵表達。
舞蹈詩《茶馬古道——高原女人·大山漢》編導將多元的民族舞蹈符號進行“再生產”,重組、解構出新的動作元素進行新的藝術表達;旅游歌舞《茶馬古道》將各民族舞蹈如風情畫卷般一一呈現于舞臺……這些處理方式都沒有達到文化符號“抽象理解”的高級層面。筆者認為,對于文化符號的抽象理解一定要落實到“人”上,確切地說應該是人的“精神”上,“文化符號一經形成,首先標志著文化核心價值觀的形成。文化符號是文化精神的表征。一種文化現象被人們普遍接受為標志性的特征,說明它所代表的事物、人物、事件及其體現出來的精神,被人們普遍認同,從而產生群體的一致性。”①邴正:《面向21世紀的中國文化形象與文化符號——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理論思考》,《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3期,第13頁。在大型舞作中,我們通過把文化的創造性、先進性、特殊性,轉化為符號的形式,最終得以將精神文化用符號來表達,從而保存、理解、傳播和發展。
(三)文化符號脫離特定文化語境的誤用
文化符號的意義取決于具體的語境。同一個文化符號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所折射的意義會出現不同,而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誤用文化符號,則會顯得“不合時宜”。不同的文化群體對符號有不同的理解,符號的任意性與受眾的文化背景、社會地位和其他因素有關。這就要求我們對于文化符號的運用要準確,要符合特定的文化語境。
舞劇《茶馬古道間的鈴聲》表現的是茶馬古道滇西段的故事,以納西族文化為背景。第二幕《鈴響定情》中為了表現納西族女子勞作的場景,以及突出“茶”這一文化符號,編導將女主的人物設定為采茶女,也呈現了納西族女子采茶、曬茶的群舞舞段。然而茶馬古道的茶自古產自普洱和西雙版納地區,麗江的納西族是不采茶、不制茶的,如何在符合文化語境中突出茶文化,使得茶這一重要的文化符號在劇中具有可舞性,還需要編導再深入進行研究;第三幕《鈴慟爭鳴》中,“茶女”懷孕跟著馬幫一起生活,這種劇情設計犯了馬幫文化的禁忌。“因為過去的馬幫是不許攜帶女性同行的,更沒有女性參與馬幫運輸活動,他們認為有女性同行就不吉利,這種忌諱跟畏懼自然不同,主要是擔心在艱難旅途中發生男女關系,從而引發男性之間的不和與爭斗。”②李旭:《茶馬古道——橫斷山脈、喜馬拉雅文化帶民族走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頁。這部劇的矛盾沖突恰恰因為犯了這樣不該有的禁忌才導致了劇情結局的悲劇,然而由于文化符號在不同文化語境下的誤用,使得劇情接下來的發展都脫離“真實性”,所以如何使“茶女”的出現合情合理,需要交代鋪墊的劇情,為了突出戲劇人物的可舞性,需要通過三人舞的情感糾葛,才能使劇情沖突的導火索“點燃”。
簡言之,符號意義的產生取決于具體的文化語境。不同的語境具有不同的敘事、象征結構,這將對文化符號的意義建構產生重要的影響。為了減少符號意義的偏離程度,有必要根據期望生成的意義在目標語境中的邏輯、象征結構做適當的調整。一旦文化符號“不合時宜”地誤用到其他文化語境中,就會削弱文本的“真實性”,同時在文本的信息傳播、儲存中也會造成 “以訛傳訛”的誤讀。
三、文化符號的運用對于大型舞作的意義
“符號在人類文化交流中起著很重要的中介作用,任何符號活動的目的就是要傳遞一定的內容和意義。”③張杰、康澄:《結構文藝符號學》,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頁。“藝術文本是復雜構筑的意義,它所有的元素都是意義的元素。”④[俄]洛特曼:《藝術文本的結構》,王坤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頁。所以說,文本產生意義,意義是作為符號活動的文本的產物。研究文本的意義,必須解讀文化符號,文化符號的運用對于大型舞作的意義主要表現在:
(一)“文本真實”的體現
藝術創作始終是與探索 “真實性”緊密相連的。廣義的 “真實”,是傳達的基礎。對于文本的接收者,沒有理由接受明知為假的符號文本。“文本內真實性,必須符合融貫原則,即文本各成分邏輯上一致,意義上相互支持…… (對于)藝術虛構文本,則需要依靠接受者的情緒浸入,與社會的道德感情體系融貫。文本內真實性,是人類社會符號表意的基本原則。”①趙毅衡:《文本內真實性:一個符號表意原則》,《江海學刊》2015年第6期,第28頁。在大型舞作中,文化符號的巧妙運用,能夠幫助 “文本真實”的體現,讓觀眾在 “真實性”中接受信息、感同身受。
唐鏞創作的兩部舞蹈詩《茶馬古道》系列,都運用了不同人物關系——父子、夫妻、姐弟、祖孫的對白串聯于篇章結構之間,所不同的是,最初創作的《茶馬古道——高原女人·大山漢》用的是普通話對白,而修改版的姊妹篇《茶馬古道——古道留痕》用的是少數民族語言對白配合多媒體的漢字解釋,后者所達到的場景真實性明顯優于前者,這是因為少數民族語言這一文化符號在茶馬古道的文化語境中拉近了“文本真實”。劇中父女之間關于“茶馬古道彩虹路”的對白更是成為全劇的點睛之筆,串起原本碎片化的舞段,強化了舞蹈詩的戲劇性,并在結尾的獨白—— “我看到了阿爸的道,是光透過我的淚,映出七彩顏色的阿爸的道”——闡釋出茶馬古道的路是家、道、歲月共同交織而成的“彩虹之路”,詩意化地升華了主題,向現場觀眾呈現了時間、空間、情緒所營造的“文本真實”的力量。
(二)“文化記憶”的體現
洛特曼等人提出的“文化是社群的非遺傳性記憶”與揚·阿斯曼主張的“把文化視為記憶”有相通之處,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依賴象征載體的符號性存在,即“通過象征編碼的文化記憶”,這個載體其實就是洛特曼所說的 “文本”。作為 “文化記憶”外在符號載體的“象征”就是“文化記憶”中的文化符號,被象征所承載或指涉的記憶形象就是文化符號的對象。記憶的核心問題是重現、表征,是語言和實在對象之間的邏輯聯系和審美聯系。因此,文化符號在大型舞作中的正確運用,可以將藝術文本當作媒介,進而闡釋“文化記憶”,并將其帶入一個開放的 “記憶空間”中,該空間的中心是“真實的過去”——我們的經驗和經歷,即不可撼動、確實存在的歷史。
舞劇《茶馬古道》展現了一段藏區僧人熬大鍋茶的舞蹈,8名紅袍僧人手握長棍,圍繞著一口大鍋搗茶,在限定的圓形結構中舞蹈,動作編排很有層次感,那飛揚的紅色僧袍與身后神圣的寺院交相輝映,營造出莊嚴、神圣的畫面感。據了解,這段舞蹈的創作靈感就取自康定一座寺廟的熬茶鍋,編導在采風期間了解到這樣的傳聞:“當年寺廟的規模有多大,就看它熬茶的鍋有多大。”于是,表達這一段記憶如同敘述一段故事,由于記憶的現實情境和需求不同,主創會對其進行適應性的調整和修改,從而使之更傾向于成為“可被理解和接受的真實”。觀眾通過這部舞劇進而了解到這段文化記憶,誰又能想象當年的藏區,寺院會是茶葉的最大買主呢?!根據文獻記載:“藏區的喇嘛寺一打酥油茶就是大鍋大鍋的,一天從早喝到晚,茶的消耗量特別大。有些喇嘛寺動輒幾千人,一天不知要喝掉多少茶。據說茶葉所具有的醒腦安神功能,有助于僧侶們念經修行……茶馬古道貿易的一個很突出的特色——遍布茶馬古道沿途各地區的藏傳佛教寺廟成為藏區最大的貿易公司。”②李旭:《茶馬古道——橫斷山脈、喜馬拉雅文化帶民族走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頁。當文化符號在大型舞作中運用得如此“真實”,這段文化記憶自然可以通過這一藝術文本而保存下來。
(三)“人文精神”的體現
卡西爾認為,“與其說人是理性的動物,還不如說是符號的動物。正是符號,人的創造力才得到最大的發揮,藝術、語言、宗教、哲學、歷史、藝術等等文化形式才得以產生;正是符號,才使人與動物同處于一個物理世界,而又能擁有建設一個他自己的世界,建設一個‘理想的世界’的力量。”③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頁。從某種意義上說,人之所以是萬物之靈,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獨特的精神文化。英國著名美學家科林伍德指出:“沒有藝術的歷史,只有人的歷史。”通過文化符號在大型舞作中的運用,我們追求的終極目的始終是人文精神的彰顯,反映的是在特定時代背景下人們的價值觀、人性觀。
在以“茶馬古道”為題材的大型舞作中,通過對茶馬古道“馬”“人”“道”等文化符號的運用,大部分作品都體現出了馬幫文化中冒險進取、團結合作的精神。馬幫在茶馬古道上不僅要面對人與大自然的矛盾,克服高山峽谷、草地雪嶺種種艱難險阻,而且還要面對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例如生意上的冒險、土匪強盜的威脅。在抗戰期間,許多趕馬人積極投鞭從軍,“馬鈴兒響叮當,馬鍋頭氣昂昂。今年生意沒啥子做,背起槍來打國仗。”①李旭:《論大西南馬幫精神》,《云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第44頁。馬幫的利益與國家民族的興衰息息相關,茶馬古道上的不少馬幫一直走出國門,把生意做到了南亞、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他們是最能直接感受到“國強則民強”這一道理的。面對時局的不穩,馬幫和商幫們往往體現出一種向心力,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昌盛,因此,馬幫文化還具有一種強烈的愛國精神。目前除了舞劇《茶馬古道》將這一精神有所體現外,其他藝術創作對于這一精神品質的彰顯還有待于挖掘。除此之外,以“茶馬古道”為題材的大型舞作還通過對多元的民族文化符號的運用,例如打歌“聯袂踏歌”的圈舞形式體現民族團結的向心力;漢族采茶、制茶、運茶與藏族打酥油茶、煮大鍋茶、喝茶舞等文化符號體現“漢藏一家親”等民族和諧的精神。還有一些作品分別通過“馬鍋頭” “背夫” “玉石”等文化符號的“傳承”,象征著茶馬古道歷史文化的傳承精神,這種傳承的精神源于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永不停歇的歷史,源于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包容和諧。
結 語
綜上所述,我們應該建立一個符號圈或文化空間的概念,不能孤立地看待文化或文本,從廣義上講,所有的文化都是文本形態的,“符號圈中的一切文本與文化都同時既是部分,又是整體;既是主體,又是客體。”②康澄:《文化符號學的空間闡釋——尤里·洛特曼的符號圈理論研究》,《外國文學評論》2006年第2期。大型舞作只是文本的一部分,文化符號在大型舞作中的運用,既要深入挖掘文化符號,也要考慮特定的文化語境,盡可能“均勻混合”(blended as equally as possible)使用能夠表現“表意感知—經驗理解—抽象理解”過程的文化符號,追求的終極目的始終是人文精神的彰顯,反映的是在特定時代背景下人們的價值觀、人性觀。
相較于 “絲路”題材大型舞作的興盛,離不開敦煌學的研究成果、中國古典舞敦煌舞派的建立以及絲綢之路歷史、文化、藝術等全面保護和研究,更離不開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由于 “茶馬古道”學術發現的時間較晚,目前藝術學界對于茶馬古道的研究是缺位的,其研究成果呈碎片化的狀態,所以更需要我們深入挖掘文化符號,進一步解讀文化符號的意義。茶馬古道不僅僅是一個交通線,抑或是一個商貿活動的場所,它更重要的是其文化的意義——濃縮了中國西部邊疆民族的歷史文化,蘊含了馬幫文化的傳奇歷史和精神特質,“包括了漢民族和中國傳統文化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傳播、積淀及相互作用的歷程和內涵,充分表現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在西部邊疆的交匯融合與源流承繼”③李旭:《西南古道的民間性及其經濟、文化雙重價值》,《中華文化論壇》2008年S2期,第143頁。,體現了中華民族一體多元的文化格局,也體現了國際間區域性合作的意義和價值。許倬云先生曾經指出,“過去人們總以為世界古文明都是從幾條大河的流域開始發展的,這不一定完全正確……中國文明的一個特色是建筑由城墻圍繞的聚落點,點與點之間主要以道路來聯系。道路將若干‘小區’結合為一個整體,及至成為更大的政治單位——國家……中國的文化,與其說是由河流 (尤指黃河)衍生,竟不如說是道路的文化了。”①許倬云:《中國文化發展的點和線》,載《觀世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160頁。茶馬古道文化蘊含了眾多文化符號,不是一個維度、一個視角所能囊括的,需要多學科的研究和介入,特別在強調文化建設的當下,藝術界 (尤其是舞蹈界)需要結合多學科的文化視角對其投入更多的重視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