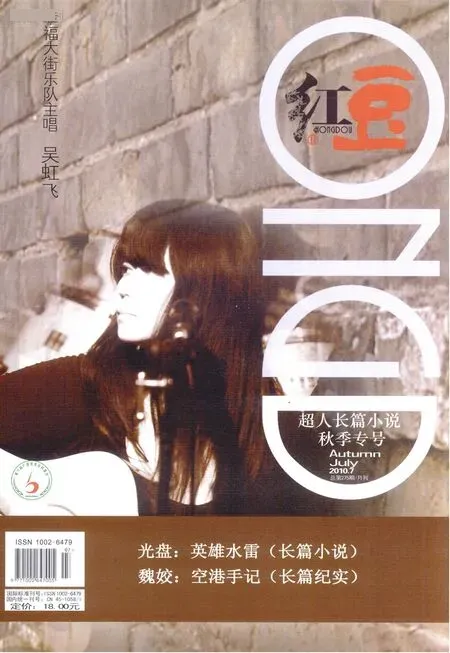人物卷子之十四
胡竹峰,1984年生于岳西,安徽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出版有《空杯集》《墨團花冊:胡竹峰散文自選集》《衣飯書》《豆綠與美人霽》《舊味》《不知味集》《閑飲茶》《民國的腔調》《雪天的書》《竹簡精神》《茶書》等散文隨筆集。曾獲孫犁散文獎雙年獎、安徽文學獎、紫金·人民文學之星散文獎、滇池文學獎、林語堂散文獎、《草原》文學獎、《紅豆》年度作品獎,《中國文章》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提名。部分作品被翻譯成日語、英語、俄語、意大利語對外交流。
秦嘉與徐淑
車還空返,甚失所望,兼敘遠別恨恨之情,顧有悵然……
東漢詩人秦嘉與徐淑的來往信件見于《藝文類聚》,讀其《重報妻書》,兒女情長映照莊嚴。筆墨之間,情意綿軟,如梅堯臣論詩所說的“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秦嘉以從容舒緩之筆,敘談日常生活之事,抒寫夫妻離別之念,格外有情。情在日常中,帶有男歡女愛的相悅色澤。顧有悵然,仿佛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中“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的味道,抑揚頓挫、剛柔相濟。
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稀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致寶釵一雙,價值千金;龍虎組履一;好香四種,各一斤;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去穢,麝香可以辟惡氣,素琴可以娛耳。
銅鏡幽幽,既明且好。設想在陽光明媚的早晨,徐淑在屏風下對鏡顧影,思念遠在中原洛陽的郎君,拉開抽屜,有好香四種、寶釵一雙。窗外,天空蔚藍,飄滿白色的蒲公英,鏡中人一時心生惆悵。
曾經把玩過一面銅鏡,那是塊古老的銅鏡,背面長滿銅綠。鏡中影影綽綽的面容映在冰涼的鏡面上,連同鏡前人的一顰一笑,沉到時間深處。鏡面蒼黃,鏡面滄桑,想起這塊鏡子曾經重疊過多少人影,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層層像紙一樣,疊壓在古鏡的底部。
既惠音令,兼賜諸物,厚顧殷勤,出于非望。
不是秦嘉,亦非詩人,也覺得徐淑的回信婉轉有致,婉轉有致中親切可人。
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于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
在中原生活久了,憶雨、念雨,懷想江南的水汽。夜里讀到這樣的短箋,心際波光粼粼。樓外有風,拂吹窗簾,如在鄉野,忍不住扭頭去看。
覽鏡執釵,情想仿佛,操琴詠詩,思心成結。敕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嘆。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據敦煌文獻寫本,秦嘉隨書贈予徐淑的,除了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外,還有詩歌十首,并說:“詩人感物以興思,豈能睹此而無用心乎?”見到秦嘉所贈諸物及詩作,徐淑“覽鏡執釵,情想仿佛,操琴詠詩,思心成結”。
染世已深,不再思心成結。年齡漸長,鄉愁是說不出口了。年齡漸長,春愁是說不出口了。年齡漸長,思心成結一類的話也說不出口了。
秦嘉早逝,后,妻兄逼徐淑改嫁。徐淑作《為誓書與兄弟》明志,云:“烈士有不移之志,貞女無回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后已。”未幾,哀郁而終。今所存者,皆秦徐夫婦往來敘情之作。夫妻事既可傷,文亦凄怨。凝眸、深情、懷想,青衿飄袂、時間如刀,快兩千年了。
姜夔
姜夔以詞名,實則他的詩亦好,譬如《送范仲訥往合肥三首》其二。
我家曾住赤闌橋,鄰里相過不寂寥。
君若到時秋已半,西風門巷柳蕭蕭。
姜夔的詩詞,溫潤如玉,傷懷入骨,“西風門巷柳蕭蕭”一句,讀得人心意闌珊又起彷徨之情。姜夔才華橫絕,可惜身上那種孤硬的氣質,使其一生落魄、前途徘徊。
夏承燾先生尋繹鉤沉,姜夔早年客居合肥,與一對擅彈琵琶的姊妹相遇。正月元宵燈會的夜里,王孫公子、五陵年少提著燈籠遍地游賞。那年姜夔在熱鬧的人群中,聽到了琵琶女姊妹的彈奏,與其中一位結下不解之緣,卻因生計難能自足,只得游食四方,無法廝守終生。姜夔用情之專之深,使得其詞極為感人,誠如夏承燾先生所言,在唐宋情詞中最為突出。
姜夔下筆克制,風格近似李煜和納蘭性德。
姜夔,字白石,其詩詞亦如石,孤花瘦石,骨骼清奇。姜夔詞中有真情,然被凄清孤冷的筆墨包裹了,所以王國維說他隔,認為白石詞雖然格調高絕,卻終如霧里看花、水中望月,隔了一層。姜夔這種欲笑還顰、欲歌先斂的風格,王國維不喜,張炎卻欣賞。張炎說:“白石詞如野云狐飛,去留無跡。”又說,“白石詞……不唯清空,又且騷雅,讀之令人神觀飛越。”
張炎乃世家子弟,推重姜詞,自作詞卻略顯空疏,學得姜夔字句典雅,學不到意境清空,更學不到幽林遠澗的悠遠氣息。
王國維以境界作評判詞牌的標準,抱著自己的審美不松手。隔實則也是中國藝術的高境之一。姜夔的隔透著文人的清氣,既不是蘇、辛的大言豪邁,又不同婉約派的一味愁苦,更沒有脂粉、富貴氣,不濃艷、不平淡,淡里深情,有適中的好。
有年冬天祭灶后一日,大雪夜里,李慈銘燃燭讀姜夔詞,次日呵筆記之:“清脆如坐古梅花下煮冰雪飲之,亦一快也。”李慈銘又說,“遍讀姜夔絕句,恍如殘雪在地、寒江不流、山木明瑟、夕暉淡然。寒鳥浴冰缺處,琮琮作珠玉聲也。白石以詞名,而詩實高出數倍,律體則非所長耳。”老夫子見識彌堅。
李清照論詞,于前人多所指摘,設或易安見到姜夔,又當如何?落拓江湖,一生潦倒,姜夔灑脫的山人氣是卓越布衣風味。周作人不喜歡山人氣,然梅花訪友,一洗塵俗,也是身而為人、生而為文的最后清貴。
我在杭州的時候,住地離馬塍路很近,據說姜夔死后葬其處。如今高樓林立,連塊黃土也找不到了。
湯顯祖
元朝五世十一帝,九十八年,詩詞文章無甚起色,雜劇大放光芒。東京瓦肆勾欄各種技藝的演出本子,因為關漢卿、王實甫、白樸、馬致遠、鄭光祖的改編或創作,氣象一新。
其后明朝,談到劇作,湯顯祖最為我所喜。湯顯祖的好,好在滿園春色關得住,一枝紅杏不出墻。湯顯祖出身書香門第,早有才名,三十四歲中進士,做過官,政績斐然。隔了幾百年,我對此幾乎一無所知。所喜歡的,還是人家的文章、學問,更喜歡那一本《牡丹亭》。
《牡丹亭》全名《牡丹亭還魂記》,改編自話本小說《杜麗娘慕色還魂記》,故又名《還魂記》,這些名字皆不如“牡丹亭”三字春意纏綿。看《杜麗娘慕色還魂記》如睹畫美人,看《牡丹亭》如睹真美人。畫美人亦好,但無真美人之羅襪生塵,更無真美人之活色生香。《牡丹亭》的好,好在活色生香。沈德符《顧曲雜言》說:“《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牡丹亭》是湯顯祖得意之作,曾言“吾一生四夢,得意處唯在《牡丹》 ”。四夢者,《紫釵記》《牡丹亭》《邯鄲記》《南柯記》也。
湯顯祖耽于夢、夜氣方回、雞鳴枕上、癡人說夢,慕繁華、愛熱鬧,系懷閨閣、無事記夢,寫出了一幕熱鬧的大夢。湯顯祖百年之后,曹雪芹也愛夢,那場《紅樓夢》更宏大,更波瀾壯闊。《金瓶梅》亦是夢,煙花春夢、浮生若夢。 “得意處唯在《牡丹》”,實則得意處唯在《牡丹亭》洋洋一卷好文字。
湯顯祖落墨有種正大的好,不偏不倚,是大風之聲、是大雅之言,好得浩浩蕩蕩、好得橫無際涯、好得氣象萬千。明清一代,小品盛行,格調上來了,局面往往狹窄。湯顯祖下筆有楚聲,即屈原的風氣。不獨屈原的風氣,縱橫捭闔不失史家氣派,行跡又有文人爽朗灑脫狀,自高處平易近人。
男歡女愛、吹拉彈唱、飲食日常、人情世故,在湯顯祖筆下如日似月。《牡丹亭》造句尤為和風麗日,無怨憤、無哀傷,讀來清嘉婉媚,不似牡丹,更近碧荷芳草。《牡丹亭》是日影,風動日影、水流日影。《牡丹亭》有喜悅有深情有心動,描盡男女相悅之悅、男女相親之親,高情的相遇,繾綣千古。
我讀《牡丹亭》,覺得不枉然。世間男女有高情厚誼,如夢如幻,帶著夏夜的清露,讀來喜不自勝。湯顯祖是古往今來第一大情種,《牡丹亭》題詞有明人所無的魏晉風度:“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湯顯祖晚年潛心佛學,自稱“偏州浪士,盛世遺民”,說“天下事耳之而已,順之而已 ”,以“繭翁”自號。有人作繭自縛,可惜可嘆。有人終其一生作不出繭,無所可縛,亦可惜可嘆也。
戴震
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粗粗翻過,翻得出學問也翻得出心血,學問是心血之精華。
段玉裁對戴震一見傾慕,謄抄他的著作,以弟子謙稱,決意拜其為師。戴震堅辭不就,六年后,方許以師徒相稱。
戴震年長段玉裁十二歲,中舉時間卻晚兩年。段玉裁恪盡弟子之誼,亦師亦友如同顏回與孔子。八年后,戴震在京逝世,段玉裁悲痛萬分,厚赗戴震遺族,親撰祭文。此后,有人提及戴震名諱,段玉裁定然垂手拱立,每至朔望,必定莊重地誦讀戴震手札一通。八十歲時深懷感念:“輯先生手跡十五匯為一冊,時時覽觀。嗚呼!哲人其萎,失聲之哭,于茲三十有八年矣。”
孟子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戴震絕無此患,學問大佳卻不好為師。桐城姚鼐寫拜師帖,戴震回信說:“至欲以仆為師,則別有說,非徒自顧不足為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也。古之所謂友,因分師之半。仆與足下無妨交相師,而參互以求十分之見,茍有過則相規,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固大善。”字字可見人情,字字通曉物理。
周作人辨古今思想與文章之好壞,以人情物理為第一要義。不懂人情物理,“結果是學問之害甚于劍戟,戴東原所謂以理殺人,真是昏天黑地無處申訴矣。”“學問淵博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見識通達尤為難得,有了學問而又了解物理人情,這才能有獨自的見解……此又與上文所云義理相關,根本還是思想問題”。
據說戴震十歲才會說話,稍后入塾,過目成誦,日讀數千言不肯休。師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戴震問:“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 “此朱文公(朱熹)所說。”即問: “朱文公何時人?”曰:“宋朝人。 ”“孔子、曾子何時人?”曰:“周朝人。 ”“周朝、宋朝相去幾何時矣?”曰:“幾兩千年矣。 ”“然則朱文公何以知然?”師無以應,曰:“此非常兒也。 ”
戴震十七歲時立下志向,要以探索古今治亂之源,闡明治國平天下的基本原理為平生治學的目的,也就是聞道。
戴震的道在其《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曾自況: “仆生平論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戴震是穿古服的現代人文學者,據說紀曉嵐拿到這本書,讀了幾頁又驚又氣,把書扔到地上。段玉裁也說讀不懂這部書。
戴震朝向元典,直承六經孔孟,識見不同常人。紀曉嵐以《閱微草堂筆記》之眼看戴震,或者懂得會多些。戴震的學問大,我讀了,不能說一無所知,更不敢說知,一言概之,或可曰:疾虛妄。
責任編輯? ?丘曉蘭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