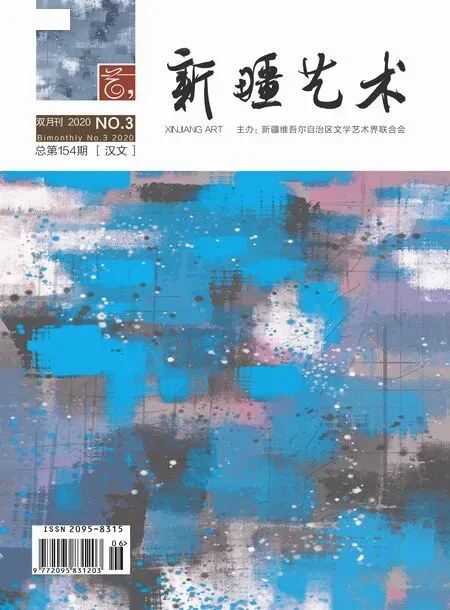文藝民俗學視野下王蒙的《在伊犁》解讀
□ 董佳文

《王蒙文集在伊犁新大陸人》
當代著名作家王蒙,著有長篇小說《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等近百部小說,其中,王蒙以新疆生活為題材的一系列作品展現了新疆不同于內地省市的地域特色和人文風情。1963 年王蒙離開北京來到新疆伊犁,曾在伊寧縣下屬巴彥岱公社二大隊生活、工作了六年有余,同新疆的各族同胞們一起勞動、生活,并且熟練掌握了維吾爾語言,能夠流利地運用維吾爾語和當地居民正常交流,對當地人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也日漸熟稔。這段不同尋常的人生經歷,不僅成為他創作生涯中終生難忘的記憶,在這里的所見所聞,所積累的豐富的民間知識經驗也為他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創作素材。伊犁巴彥岱在王蒙心中一直作為第二故鄉而存在,也因此,《在伊犁》系列小說中,王蒙便以自述的口吻對這里的一草一木和生活民情侃侃而談,使得作品中呈現出一幅自然生動的民俗風景畫。本文在文藝民俗學視野的觀照下,從生活文化民俗、地緣風貌民俗以及民俗浸染下的文藝寫作三方面對王蒙作品中的民俗呈現做一梳理。
一般而言,文藝民俗學是“研究民俗文化對一般文藝發展的影響和相互的關系,兼容民間文藝學研究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基本內涵”①的一門學科,側重于研究文藝創作中民俗的功能和表現,探討民俗對作家創作的影響,主要側重研究書面文學作品中的民俗事象②。王蒙的《在伊犁》收錄了八篇篇幅長短不一的小說,伴隨著小說中彼此聯系的人物逐一登場,一幅鮮活生動的伊犁生活畫面徐徐展開,伊犁維吾爾群眾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馕茶餐食、每一戶人家的庭院風格、熱情隆重的待客之道、生產勞動的駕馭工具以及美麗迷人的伊犁河景致等等都成為王蒙寫作審美觀照的客體,小說中活潑風趣的文字、粗獷中帶有柔情的筆墨描摹無不體現出作者對這片土地所寄予的深厚感情。
一、多姿多彩的生活民俗
民俗學家陳勤建指出民俗從生活中形成,反饋回去成為生活的某一樣式,更多的本身就不脫離生活,以一類程式化的“生活相”呈現在人類社會中。①《在伊犁》中通過一位從北京來的知識分子“老王”的主觀視角完成對伊犁故事的敘述,將新疆民俗文化中獨特的飲食文化、待人之俗、家居風格等民間生活中的點滴細節娓娓道來,讓讀者充分感受到浸潤在新疆民間生活之中的民俗之美。
具體而言,其文本描述的細節表現在如下三方面:
首先,《在伊犁》中描寫了很多新疆少數民族的特色民間飲食,馕作為新疆最具特色的食物,也是維吾爾群眾飲食結構中最重要的食物,“馕”這一新疆民間特有的主食,已超出純粹飲食意義的范疇,成為新疆民間具有飲食民俗符號的食品,有著深刻的文化內涵。《在伊犁》系列小說中,“馕”頻頻出現在人物的餐飲場合,真實呈現出伊犁老百姓的民間生存狀態。如在《虛掩的土屋小院》一文中塑造的阿依穆罕大娘便極其喜歡喝茶,飲茶時也一定要有馕搭配,原文寫道:“一天中午,我們一起在枝葉茂盛、陽光搖曳的蘋果樹下喝奶茶,把干馕泡在奶茶里,這就是一頓飯”,③馕和奶茶或清茶總是“混搭”出現在伊犁老百姓的餐桌上,現實生活中也是如此,不管去任何一家伊犁當地群眾家里做客,都能嘗到酥軟可口的馕。

王蒙
小說在敘述愛彌拉姑娘和新婚丈夫回家探望時,寫道:“喝奶茶的時候,他挑揀一個打得最好的馕掰碎,帶著他手上的汗,放到愛彌拉姑娘的碗里”,③這段描寫中,馕這一重要食物由丈夫親手遞給妻子,讓小說中本來有著著男尊女卑思想的街坊鄰居大為訝異,男主人公對妻子呵護有加、細膩周到的特點也躍然紙上。
再如,小說中寫“老王”的妻子看到鄰居打完馕后,“包著一個形象和色澤都非常完美的小馕,悄沒聲息地走上我們的廊沿,輕輕地敲門,把這最好的新馕獻給了我們”,③這也讓“老王”聯想到穆敏老爹曾告訴他“維吾爾人認為馕——糧食是世界上最高貴的東西”,這段描述意在突出人物對打馕技術的認可以及對“送新馕”這一樸素的“送禮”行為所蘊含街坊情誼的感動之情。
眾所周知,地理區位和自然環境對飲食習俗的影響深遠,不同的地域和氣候將生產出與之相應的飲食和民俗,新疆地處我國西北干旱地區,降雨量較少,四季分明,氣候炎熱干燥,脆弱的生態環境中,馕成為新疆民間百姓中的主食,它一度支撐著絲綢之路上駱駝客走過漫長征程,成為新疆極具代表性的地域飲食文化的構成性要素。在王蒙的小說中,一個馕、一碗茶對伊犁人來說已是滿足,它能填飽勞動過后的空肚子,招待來訪的客人,驅趕路途中的寂寞。伊犁普通老百姓對馕有著誠摯的敬意和深厚的感情,它作為一種主食,絕不能被隨意丟棄或浪費。每逢重大節日或儀式,馕也會成為一份重禮或一個必不可缺的環節,反映出伊犁民間百姓樸素而美好的愿望。今天的伊犁民間,維吾爾普通群眾間至今還保留著新郎新娘同吃鹽水馕的風俗,新郎新娘將馕蘸著鹽水吃進去,以表示海誓山盟,同甘共苦,白頭偕老。這些不停跳躍的飲食民俗事象,不僅承載著物質的功利性,也充盈著民俗氣質,構成小說中一個個豐富飽滿的文化審美意象。馕在伊犁民間特別是在維吾爾百姓心目中早已不只是裹腹的食物,更是一種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清苦的飲食中只要有馕相伴,即便面對再艱難困窘的日子也能忍受。
小說中,除了日常飲食中的馕,作者也多次提到新疆其他的特色美食,如作者提到一次夏收動員大會上的牛雜碎湯:這天的中午,肯定是牛雜碎湯,湯中最好吃的叫做“面肺子”。先和好面,洗出一桶淀粉水,流出面筋,再把淀粉水灌入牛肺,把牛肺撐得比牛在世時深吸氣的時候還要大五倍——真是大得嚇人,封上扣,與牛肝、牛肚、牛腰、牛腸……煮在一起,熟了以后,既有牛雜的葷腥味,又有一種類似北方人夏季吃的蕎麥面扒糕的光滑筋道的觸感。③伊犁牧場上牛羊成群,即使在物質匱乏的年代,重大節日、儀式中上的餐食中也少不了牛羊肉,同時新疆人講究牛羊肉的“原汁原味”,油葷鮮香的肉湯便是一道極具民俗滋味的美食。這一段描寫細致詼諧,文字中仿佛也飄出一股牛雜湯“無所不用其極”的葷腥風味,閑敘家常的敘述風格也讓讀者切身感受到新疆民俗飲食的文化魅力。而在“老王”心中,夏收動員大會上的動員只是例行公事,農忙食堂的牛雜湯才是大會聚集的重點所在,其間,面肺子的特殊做法與獨有味道既讓他重溫家鄉記憶,又讓他對西部遠方有了更多的回味。
其次,新疆民間老百姓間極注重禮節和待客之道,每逢家中有客人拜訪時,不管家境清貧或富裕,一定要擺出豐盛的食物和茶水來招待客人。在《虛掩的土屋小院》里,作者寫道,客人從你的一株果樹上吃了一百個蘋果,那么這一株樹明年會多結二百個——也許是一千個更大更甜更芳香的蘋果。客人喝了你家的一碗牛奶,明天你的奶牛說不定會多出五碗奶,③可見新疆伊犁民間注重禮儀民俗,各族群眾熱情好客,每當客人來家里做客時,都會受到熱情款待。
在《淡灰色的眼珠》中,老王無法推辭馬爾克“到家里坐一坐”的盛情邀請,受到這一家人極為熱情的款待,吃得“超飽和”,“甜食、肉餅、奶茶、抓飯、酒菜、面片湯”統統下肚,王蒙將這次招待稱之為“成龍配套、一絲不茍而又嚴格地符合禮儀的”。③如此誠摯溫暖的飯菜酒食,在伊犁任何一家百姓家里,大概都會如此。同時,小說還寫道,在裝修房屋時,大多數伊犁老百姓特別是維吾爾老鄉都要修建一間專門招待客人的房間,這間客房也遠比休息的臥室和吃飯的房間要裝扮得更為用心,如馬爾克招待“我”時:馬爾克把我讓進了里屋,習慣上,這應該算是他們的客房。客房比外屋大多了,墻龕里放置著一盞赤銅老式煤油燈,發出柔和的光,地上鋪滿深色花氈子。穆敏老爹一家改善居住生活條件時,用拆掉小庫房的材料為正房再接出一間來,形成里外屋的效果,這樣就有了專用于待客的里屋。
另外,小說在描述伊犁民間家居與普通老百姓服飾風格方面,也處處體現出伊犁民間普通群眾對美的感知和審美追求。花枝蔓延、色彩鮮艷的服裝紋飾在姑娘們的衣裙上隨處可見,打開每一扇大門都能看見藤枝彎繞、花香襲人的庭院……④

伊犁河冬韻
翻開《在伊犁》,總能看到作者濃墨重彩去細描“老王”親自造訪的每一位伊犁民間少數民族同胞的庭院特點來。如馬爾克家的院子不僅栽種著紅白相間的玫瑰花,還特意為牲畜和毛驢車設計出一條“專道”,客房的陳設也別有講究。“這間客房墻壁是粉刷成天藍色的,在煤油燈光的照耀下顯得十分安寧。正面墻上竟貼著五張完全相同的佩戴著紅衛兵袖章的毛主席像,五張像排列成放射形的半圓,這種獨出心裁的掛“寶像”的方法確實使我目瞪口呆。至少在晚上,這五張花環式的照片與天藍色的墻壁,與古老的煤油燈及同樣古老的赤銅洗手用曲肚水壺,與雕花木床及雕花木箱,與壁毯及精美的窗簾在一起,并無任何不諧調之處”,③此番寫實又夾雜評論的描述,讓我們也仿佛置身其中,觸摸到了立體的雕花,感受到他們追求生活之美的熱烈。
再如老王夫婦在愛彌拉姑娘的陪同下,去她哥哥穆薩阿洪家中做客時,映入眼簾的是庭院內的紫丁香,“他們住的兩間房子門前,有一株紫丁香,我們去的時候紫丁香開花已經盛極而衰,給人以沒入遲暮之感。穆薩阿洪的房子雖然不大,房間內的裝修設計卻令人印象深刻:老式的天花板和地板分別漆著藍漆和紅漆,窗臺低矮的窗戶臨街,窗外還有一層俄式雕花木窗扇,室內全部鋪有印花羊毛氈,墻上掛著一塊鮮艷奪目的庫車地毯和一塊繡有三潭印月西湖風光的絲織壁掛。室內各種物品充分利用空間,像搭積木一樣地堆砌在一起,巧妙、雕琢、雅氣。”③這段簡單生動的描寫也足以見得伊犁民間百姓特別是維吾爾群眾在美化房屋上的巧妙智慧與用心程度。
陳勤建認為,民俗化傾向是文藝民俗作品創作的一大藝術特色,就是作品對時代社會生活本質某些方面的揭示,它是通過對民俗逼真的刻畫中實現的。⑤王蒙用真實質樸的文字記錄了富有文化內涵、美好象征意義的民間主食“馕”和呼朋喚友、爽直好客的伊犁民間禮儀民俗以及伊犁民間老百姓家庭院落布置中所體現的對美的崇尚,這些點滴細節的描述不僅是新疆民間民風民俗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屬于作家王蒙的伊犁民間記憶;它們既是新疆伊犁民間獨特的風物特產,也凝聚著作者對這片土地的眷戀與寄托,讓我們從中窺見作者深沉的家鄉情思,真切感受到新疆伊犁民間民俗文化的藝術魅力。
二渾然天成的風景民俗
自然景觀(山川風物、四時美景)是文學書寫富有民族化、地域化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文學作品具有濃郁的地域色彩和民族風格,超越時代局限的一個重要因素。⑥如沈從文筆下的淳樸邊城、孫犁描繪的荷花淀、汪曾祺書寫的詩意翠湖等,在作家創作中,這些自然山水都不自覺地與本土民俗聯動起來,牽動著讀者的心,使人心馳神往。生活在北京的作者來到遼闊奇特的西部荒野,極目之景與內地大不相同,因此,王蒙筆下的伊犁在地理地貌、風土人情等方面也呈現出獨特的風采,低矮的土屋、密密麻麻的葡萄藤、芬芳四溢的蘋果花、雪山、草原等風情景物構成了一幅幅充滿神奇色彩、獨具西域情調的自然民俗畫。同時,作者也將自己對新疆這片熱土的深情融化于字里行間,用心和生命去體驗新疆的自然與文化。
《在伊犁》記述了老王在毛拉·孜公社生活勞動的點點滴滴,也對這里的一草一木寄寓了無限美好的柔情。那寧靜奔騰的伊犁河在作家筆下牽動著作者的心,《逍遙游》中作者著重談到了自己對伊犁河最初記憶、伊犁河一年四季之景,河岸兩邊遍布著幽幽馬蘭,伊犁河春日的蓬勃、夏季的翻騰、秋冬的金光雪韻,它有奇妙變幻的美麗,也有洪水沖擊后的危險和堅強,“這一切給了我這樣強大的沖擊,粗獷而又溫柔,幸福而又悲哀,如醉如癡,思歌思吟。而化雷化閃,問天問地,也難唱出這祖國的歌、大地母親的歌、邊疆的歌、帶有原始的野性而又與我們的人民無比親密的伊犁河之歌于萬一。”初見伊犁河,王蒙心中就涌起難以忘懷的感慨,這條塞外江南的河,以其充沛濕潤滋養著伊犁人民,讓每一個身處異鄉的伊犁人民心生想念,也讓離開伊犁的老王始終牽掛,它與伊犁的所有人和事,都成為自然與民間生活交相輝映的風景。

王蒙和夫人在新疆
沿襲著民俗飲食傳統,伊犁老百姓用飲食文化模式傳達出對自然最真摯的情感,并且這種情感伴隨著他們的成長日漸根深蒂固。⑦在伊犁,維吾爾老鄉樂于享受自然空間下閑適的飲食環境,很多伊犁民間維吾爾老人家中的院子里都搭建了適合吃飯、飲茶、聊天的棚子,在藍天星夜下,花香縈繞中感受閑暇之意。小說敘述到“老王”在與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大娘二人生活的時光里,室外簡易的涼棚成為日常生活中一道特別的風景線,它與繽紛花果、物候天色融為一體,體現出伊犁的四時景象,迎接每一位到訪的客人,陪伴阿依穆罕大娘度過美好的飲茶時刻,在自然風景的映照下讓日常生活習俗慢慢發酵。作者不惜筆力地描述著這道給予他們生活情趣的獨特景致:別看茶棚簡陋,自從有了它,我們便盡可能地在室外喝茶、吃飯、談心、夜話。從三月初雪還沒有化盡,到十月底清晨已經見了冰碴,我們都在室外活動,夏天,更是直到深夜也舍不得進屋。小小的院落、小小的果園,小小的關也關不緊的屋門,仍然是充滿了生活的溫馨和生動。連小小的麻雀也喜歡停留在茶棚的枝杈上,或是干脆降落到離盤腿喝茶的我們不遠的地面上,吱吱喳喳,一跳一跳地走路。而成雙的燕子,經常款款地在茶棚上下飛翔,呢喃絮語。夏日,當把路邊明渠的水引入小園內的毛渠去澆老媽媽栽種的少許辣椒、西紅柿和茄子的時候,潺潺的水聲更給我們這閑適的茶棚增添了新鮮的生趣。③在借“老王”回憶這個簡單的茶棚時,王蒙的文字敘述中充滿了依戀:清新自然的花果之味、燕雀的婉轉清脆和細細的流水等細節都被描寫得極為生動,也正是伊犁民間老百姓對自然適性生活的追求深深感染著王蒙,才使他借老王的回憶描述感染著每一位讀《在伊犁》小說的讀者。
事實上,自由和諧、美麗怡情的飲食風景在新疆依然隨處可見,人來人往的巴扎、煙火繚繞的烤肉、醇香濃郁的馕等都是一道令人流連忘返的民俗風情,它與室外光景自然拼接,讓人們享受自由愜意的生活瞬間。
再如小說中多次寫到伊犁的雪,雪在北方的冬天極為常見,而王蒙筆下的伊犁之雪卻不同于人們真實生活經驗中的刺骨凜冽,它在作家的主觀視點中被禮贊地加以表述,“這兒的雪熱烈而又清涼,放肆卻又溫柔,潔白卻不孤立,輕盈而又厚重”,③從這幾句充滿喜愛、甚至尊崇之情的描寫中,讀者也無不被這俏皮的伊犁之雪所吸引,作者繼續寫道“它能陪伴你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整整一冬,一無所有而又無所不在,錘煉你,振奮你,懲戒你,卻又給你以意想不到的安撫”③。在王蒙所刻畫的新疆伊犁風光中,雪有著治愈功能,不管和雪發生了什么,故事最后都會有一個完美的結局。《在伊犁》中,如此“可愛生動”的雪不僅僅可以用來欣賞,還與伊犁居民的生活習俗——掃雪發生著聯系。“及時掃雪是所有的伊犁居民的習慣,更準確一點說,是一種愛好,一種享受。有沒有成套的足夠的掃雪運雪工具,這是判斷一戶人家是否地道的‘老伊犁’的一個標志。”③伊犁氣候相對濕潤,鮮有不降雪的冬季,人們已經習慣了每年和雪“打交道”的時光,并將掃雪看作是鍛煉身體、聯絡鄰里感情的途徑,自然是樂在其中。當地的老人們也時常盼望著下雪,認為大雪不僅能帶來豐收,還能消除災病,包含了對新年新生活的美好期盼。
自然環境是民俗文化產生的基礎,民俗文化是對自然環境的另類呈現。⑧《在伊犁》從民俗的角度呈現出伊犁特有的風土景象,真正打動作者的不光是那壯闊神奇的天然景觀,還有那深埋于雄奇自然下的質樸民俗事象,作者用生命和心靈去體悟,感受這里的每一寸草木風景和庭院生活。
三民俗浸染的自然流露
人類的生活,是文藝取之不盡的源泉,文藝離不開生活,同樣也離不開民俗,蘊量豐富的民俗生活狀態,同樣是文藝的源泉,為文藝反映和表現生活提供了廣闊天地。⑤王蒙自29 歲來到新疆,45 歲離開這里,十六年的新疆生活經歷深深印刻在他的內心,《在伊犁》中,王蒙對新疆伊犁民間民俗事象和民俗文化的縱情描寫,與這段刻骨銘心的經驗分不開,與伊犁各族群眾豐富質樸的民間文化緊密相連。
新疆地域遼闊,多民族生活在一起,有著絢麗多姿的文化資源和人文風貌,具有獨特的地域風情。伊犁的民間生活對作家王蒙來說,是鮮活的充滿民間的生命力與民俗事象,一切新鮮的、陌生的民間事象乃至質樸的民間方言,都成為他到伊犁之后迫切想要了解與記錄的。同時,王蒙親身參與到伊犁各族群眾的生產生活現場中,不可避免地會接觸到生活中具體的民俗事象,這為他的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和經驗。伊犁民間民居建筑中有水有花果的庭院式民居、別具匠心的屋舍安排;飲食搭配上以面食為主食,牛羊肉、奶茶和馕搭配的飲食結構;穿戴服飾上簡單大方的紋飾、活潑鮮明的色彩表現,無不體現出伊犁民間的審美情趣;各種節日儀式中暗含美好意蘊的習俗以及人際交往中熱情開朗的待客之道……所有這些無不打動作家王蒙的心,進入到他的創作中。小說的故事發生在由一幅幅新疆伊犁民間民俗特色畫面構成的環境中,豐富著作家王蒙的創作經驗,同時也豐富了小說中“老王”這一人物的性格塑造,展示了人物的生存環境,真實反映出小說背景中的農村生活。
《在伊犁》后記中,王蒙提到有一段時間讀者評論他的作品越來越像作家寫的東西了,那時他是深感惶惑和不安的,那意味著他的作品越來越像“寫”出來的,而不是情之所至,自然流露。⑨的確,通讀《在伊犁》后,不難發現,小說中“老王”回憶的富有生活哲理的穆敏老爹、向往美好愛情的愛彌拉、熱情耿直的馬爾克等令人印象深刻的基層群眾形象,以及他與阿依穆大娘在葡萄藤下一同吃馕喝茶的悠閑場景、與伊犁各族同胞在田地間勞作、嬉笑的生動畫面,是作者王蒙對自己生活的真實記錄,真摯、熱誠,令人感動不已。正是因為作者根植于在伊犁生活的真實經驗,在小說中以主人公“老王”的口吻加以敘述,將自己對“第二故鄉”的情感充分投射于文字中,通過場景描寫自然展示出大量存在于伊犁民間基層生活中不易為人覺察的民俗事象,讓小說的民俗特色和審美價值在“潤物細無聲”的體驗書寫中不斷發酵,使得這部小說整體呈現出一種“非虛構”的紀實之感來。
綜上可知,《在伊犁》的系列小說創作中,作家王蒙通過將自己的生命體驗和情感記憶融入其在新疆的伊犁經驗,以細膩精準的筆觸呈現出伊犁民間各族群眾豐富濃郁的民俗風情,展現出新疆伊犁優美的景物風光,溫情書寫出主人公“老王”的新疆故事,給予讀者真實感人的美學效果。同時,在與新疆各族人民的朝夕相處中,在深切感受新疆獨具魅力的風土人情的過程中,作者也獲得了一份嶄新的精神感悟,并持久影響到他后來的文學創作之中。用王蒙的話來說,便是“這塊我生活過、用汗水澆灌過六七年的土地上,在我孤獨的時候給我以溫暖,迷茫的時候給我以依靠,苦惱的時候給我以希望,急躁的時候給我以慰安,并且給我以新的經驗、新的樂趣、新的知識、新的更加樸素與更加健康的態度與觀念的土地上。”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