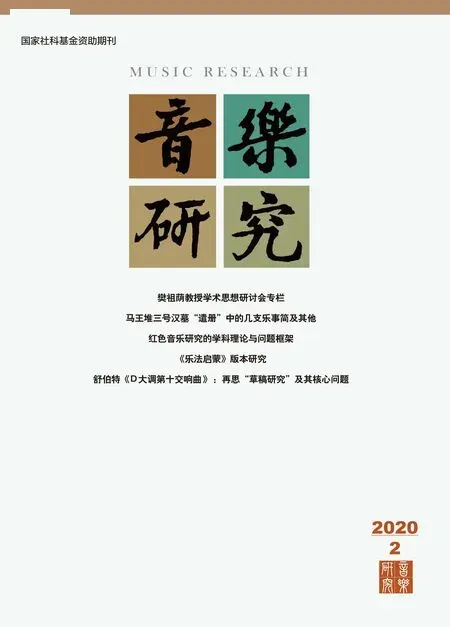積微致著 尋端見緒
——樊祖蔭教授多聲音樂研究成果學習筆記
文◎張伯瑜
首先,祝賀樊祖蔭教授學術思想研討會的順利召開!對樊老師的學術成就表示衷心的敬佩,也感謝樊老師多年來的幫助與教誨!筆者在近二十年來的各種學術活動中,與樊老師有很多的相處,從樊老師那里學到了很多有價值的東西,特別是對音樂內在結構的分析和洞察力,受益匪淺。與此同時,樊老師同樣能夠把音樂形態延伸到音樂的歷史和文化層面,其廣度與深度都令筆者非常敬佩。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音樂和西方藝術音樂之間,在音樂形態上的巨大差異之處就在于多聲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和聲性。在以往的認識中,很多人認為中國傳統音樂是線性思維,所指內涵是:中國傳統音樂中沒有(或少有)多聲性及和聲性的音樂表達。對此,中國學者認為這種特征體現出中國傳統音樂和西方藝術音樂之間的本質差異,與此同時,也或多或少地對此做了一種美學闡釋,即把無多聲性、無和聲性的音樂從線性美感上進行解釋。但是,在實際的音樂實踐中,中國現代音樂的創作卻鮮明地把多聲與和聲引入。中國傳統音樂中果真沒有多聲性嗎?在一個具有56個民族的大家庭中,音樂豐富多彩,難道就找不出多聲性的音樂嗎?為找到答案,樊祖蔭老師開始了他的中國傳統多聲性音樂研究旅程。
一、樊祖蔭多聲音樂研究成果歸納
樊老師有關中國多聲音樂的研究視角非常廣泛,成果豐碩,體現了中國傳統多聲部音樂研究上最為重要的理論創見。本人閱讀了樊老師發表的部分文章和書籍,對這些成果與創見有了初步的了解,但也發現對其進行一個全面的總結將是一個很困難的工作。所以,本文并非是對樊老師在中國多聲部音樂研究上的全面總結,只是學習之后的粗淺認識。基于本人的理解,把樊老師在相關方面的研究成果歸納成以下十個方面。
(一)概述性研究
所謂“概述性研究”,即針對中國傳統多聲性音樂進行整體的考察與論述,其論述焦點主要集中在多聲性音樂的起源、發展、流布和記譜方式等問題,也包含多聲部的分類,以及對多聲音樂形態的概述。《中國多聲部民歌概述》①載《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2003 年第1 期,第45—49 頁。一文,追溯了中國多聲民歌的起源、主要的流傳族群、表現內容、歌唱形式、織體形式、和聲類型等內容。文章認為,早期的人聲“大混唱”已經具有了多聲的因子。樊老師反對中國的民間合唱是由西方基督教傳入的認識,在《多聲部民歌的產生與發展》②載《當代音樂》2016 年2 月號(下),第1—4 頁。一文中,他進一步說明了中國多聲部民歌起源于“大混唱”之觀點,強調了審美趣味在形成多聲部民歌上的作用,并用“布依族群眾對有些不成熟的歌手在演唱中把二聲部無意間唱成單聲部齊唱時,則會譏笑為‘公母相混’”的說法加以證明。
《中國多聲部民歌概述》列舉了流傳有多聲民歌的29 個民族,比在《我國多聲部民歌的分布與流傳》③載《音樂研究》1990 年第1 期,第13—18 頁。一文所列舉的23 個民族多了6 個,可見其在研究過程中視野在逐漸擴大,研究在逐漸深入。在《我國多聲部民歌的分布與流傳》一文中,把中國少數民族多聲部民歌的形成原因歸結為生產勞動方式的影響、生活風俗的影響、語言的影響、自然條件的影響、歌手素質的影響和審美意識的影響等諸多原因。從早期的“大混唱”,在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之后逐漸形成了不同形式的多聲部,這其中顯示出一種歷史的發展脈絡。既然多聲部音樂在其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受到各種不同因素的影響,就必然會在音樂形態上有所差異,從而形成不同的類型。因此,《中國多聲部民歌概述》又擴展出了相關多聲音樂的許多其他問題,諸如多聲部民歌按照功能類型可分為勞動生產類、生活風俗類、祭典儀式類、傳說故事類和社會斗爭類;多聲部民歌的歌唱形式分為由二人或三四人組合而成的重唱,和由多人組合而成的合唱;把多聲部民歌的織體形式分為支聲型、主調型和復調型三類;把多聲民歌的和聲特點歸納為以五聲式自然音程和以四、五度以內的密集式音程為主的構成方式,其中以大二度和純四、純五度及小三度音程的運用最多。而且,如果多音和音出現在三聲部以上的旋律進行上,音與音之間的縱向結合便可產生和聲音響。和聲結構方式主要有以下兩類:一類是由大二度與純四、純五度音程組成的和音結構,其中既可以是大二度或四、五度音程本身的疊置,也可以由大二度與四、五度音程相結合而構成;另一類是由do、mi、sol 或la、do、mi 三個音組成的三度和音結構。此外,《多聲部民歌的采錄記譜與分類方法》(《中國音樂》1992 年第1 期)一文,對多聲部民歌的錄音、記譜和分類問題進行了論述。
(二)多聲部民歌研究之研究
此類文章是對研究多聲民歌的文獻進行分析與綜述,其中包含兩篇文章。一是發表于《中國音樂》1991 年第1 期的《多聲部民歌研究四十年》。該文通過對40 年間有關多聲部民歌研究的綜述,把我國現存的多聲部民歌按照題材內容進行了分類,其中有依存于某些勞動生產方式的多聲部勞動歌曲,以及存活在民族傳統風俗活動中的以表現愛情、婚戀為主要內容的多聲部風俗歌曲。
另外一篇是發表于《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版)》2009 年第3 期的《近三十年來的中國多聲部民歌研究及展望》,該文總結了1978 年后30 年間涌現出的對多聲部民歌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拓寬其研究層面的設想和要求。其中包括:加強與國外多聲部民歌的比較研究,因為多聲音樂是世界各國共生現象;加強民間多聲部音樂的整體研究,即把多聲音樂的研究延伸到戲曲音樂、說唱音樂和民間器樂;加強與創作、教學相結合的應用研究。
(三)不同族群的多聲部音樂個案研究
對中國不同族群所擁有的多聲音樂品種的研究,是樊老師數十年音樂研究的重點,所獲得的成果也最多,④主要有(以發表年代為序):《浙江畬族民歌的音樂特點》,《中國音樂》1984 年第2 期;《廣西仫佬族民歌的風格特點》,《人民音樂》1985 年第5 期;《豐富多彩的毛難族民歌》,《廣州音樂學院學報》1985 年第Z1 期;《畬族“雙條落”的基本規律及其偶然因素》,《中國音樂》1985 年第1 期;《簡論多聲部的號子音樂》,《中國音樂學》1986 年第2 期;《布依族、壯族多聲部民歌之比較研究》,《音樂研究》1987 年第2 期;《論漢族的多聲部民歌》,《音樂藝術》1988 年第1 期;《云南多聲部民歌研究》,《中國音樂》1988 年第2 期;《羌族多聲部民歌的種類及其音樂特征》,《中國音樂學》1992 年第1 期;《論壯侗語族諸民族的多聲部民歌》,《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4 年第1 期;《壯侗語族與藏緬語族諸民族中的多聲部民歌之比較》,《中國音樂》1994 年第1 期;《壯侗語諸族民間音樂原始形態的初步構擬》,《音樂研究》1996 年第1 期;《刀朗木卡姆多聲形態研究》,《音樂研究》2001 年第1 期;《阿美與布農的多聲部民歌之比較研究》,《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2 年第1 期;《侗族大歌在中國多聲部民歌中的獨特地位》,《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03 年第2 期;《“潮爾道”——蒙古族長調藝術和潮爾藝術中的珍品》,《音樂研究》2009 年第5 期;《紹劇中的多聲部音樂》(與車文海合著),《中國音樂》2014 年第2 期;《漢族的多聲部民歌及其生存現狀》,《當代音樂》2015 年第3 期等。對揭示中國所擁有的多聲音樂品種及其構成規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刀朗木卡姆多聲形態研究》一文,把刀郎木卡姆的多聲織體分成了和應型織體、支聲型織體、主調型織體和復調型織體。《漢族的多聲部民歌及其生存現狀》主要就漢族勞動號子中的多聲音樂進行分析,其中包含行船號子與林區號子。樊老師認為,這類音樂在和聲音程中除了大、小三度和純四度之外,大量運用大二度音程,并在句尾拖腔上形成大二度的平行進行,最后以大二度斜向進入主音同度結束,構成“廣西式終止”的典型終止進行方式,而這一和聲特點,與廣西的壯族、瑤族、毛南族和仫佬族的多聲部民歌是一致的。文章特別分析了橫縣的多聲部山歌的歌唱組合形式,其中有一男一女或兩男兩女的混聲重唱,民間把兩個聲部分別稱之為“公”“母”聲;以及二聲部同起同收,以大致相同的節奏唱同一歌詞,構成支聲織體。
表1 列舉的是在數篇文章中統計出的對不同地區和民族的多聲性織體的類型劃分,從中可以看出樊老師在分析多聲民歌中的思維方式和對多聲民歌的認識。

表1
無論文章中把某種織體稱為“型”或“式”,其內涵都是指“多聲結構形態”,但是,有的多聲形態之中又包含多個分支類型,這樣就形成了織體結構形態的兩個層次。把以上的所有多聲性織體類型進行整合,可分為接應型、支聲型、主調型、復調型和綜合型五大類型,以及接應式、支聲式、幫腔式、和音式、襯托式、持續音式、模仿式、對比式和綜合式等九種方式。分析五大類型和九種方式,我們可以將其關系歸納如下(見圖1)。

圖1
這五大類型和九種方式體現出樊老師所分析和總結出的中國多聲部音樂在聲部織體關系上的基本認識,也是直至今日,在中國多聲部音樂研究上最重要的成果。樊老師在所發表的文章中對這些織體類型均有明確的界定。
(四)多聲部民歌的形態特點
這部分成果對中國多聲部民歌的節拍節奏、調關系、曲體結構,以及織體形式進行了研究。如樊老師連續在《中央音樂學院學報》發表的系列文章:《多聲部民歌的節奏節拍形式研究》(1990 年第1 期)、《多聲部民歌的調發展手法研究(1990 年第3 期)、《論變唱——中國多聲部民歌創作方法研究》(1992 年第2 期)。《多聲部民歌的調發展手法研究》就中國多聲部民歌的調式“滲透與重疊”和調式的“轉換與重疊”進行了專門的分析。《多聲部民歌的節奏節拍形式研究》就多聲部民歌的節拍類型和節拍與節奏的復合方式進行梳理。在節拍類型上包含自由性的節拍和均勻性的節拍;在節拍與節奏的復合方面包含不同節拍類型復合、模仿式節奏的復合,以及不同速度的復合。《論變唱——中國多聲部民歌創作方法研究》論證了中國多聲部民歌不同聲部之間的旋律演進關系。“變唱”即演唱時對旋律的裝飾變化,其中包括:(1)不同聲部的同時變唱,即兩個或多個聲部采用相同節奏或不同節奏進行旋律加花、互補與派生;(2)不同聲部的先后變唱,即兩個或多個聲部之間在整首歌曲中采用先后變唱,或在歌曲的某個部分中先后變唱;(3)綜合性變唱,即在三個聲部以上的變唱中,某兩個聲部采用同時變唱,而另外聲部則采用先后變唱。
此外樊老師還撰寫了《橫向變唱與多聲部民歌中的變奏曲體》一文,論證了由于變唱所引發的不同聲部間的曲體變化,其中包含平列式變奏體、回旋式變奏體、起承轉合式變奏體和遞增式變奏體。樊老師認為:“在音樂的陳述和發展過程中,將前面已出現過的主題或其片段,經過改變音樂構成和表現因素(如音高、節奏、和聲、織體及調性等)中的一個或幾個方面之后加以再次呈現,以使基本樂思得到深化和發展。橫向變唱即是一般音樂術語中的變奏,變奏作為基本的音樂發展手法之一,不僅廣泛地運用于結構段落的內部,而且還常常運用于全曲的結構段落之間,從而使其具有曲式構成上的功能和意義。”⑤載《音樂研究》1992 年第1 期,第54 頁。
樊老師《中國多聲部民歌的織體形式研究》一文,就中國多聲部民歌的織體類型、支聲性織體形成的原因、各聲部演唱時的“分”“合”關系、聲部進行特點、支聲體類型的形象意義、主調型織體(即某旋律為主要旋律)的類型、復調型織體的類型等,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歸納。在支聲性織體形成的原因上,樊老師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同一曲調在流傳過程中產生的不同變體在眾人合唱時‘疊合’而成的。這種形成方式主要出現于勞動號子的和唱聲部中”⑥載《藝術探索》1991 年第1 期,第3 頁。。
(五)中西多聲音樂比較研究
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我國民間多聲與西方近現代音樂》《和而不同與不同而和——中國傳統多聲部音樂的思維特征與中西多聲結構差異原因之探究》《從中西多聲部音樂的比較談起》《論支聲音樂》《從“多聲部民歌”一詞的英譯談起》。⑦分別載于《中國音樂學》1987 年第2 期、《中國音 樂》2016 年第1 期、《黃鐘》1991 年第1 期、《中國音樂》1983 年第1 期和《人民音樂》1992 年第11 期。
《我國民間多聲與西方近現代音樂》一文從四個方面比較了西方音樂與中國多聲音樂之間的差異,即調式交替與調式重疊之間的差異、雙調或多調重疊的差異、以四五度或二度為特征的和聲結合,以及多聲結構形態方面的差異。盡管中國民間多聲音樂中的多聲織體結構形態十分多樣,但其中主要有支聲型、主調型(包括和聲式固定音型襯托、持續音襯托)和復調型(包括模仿式、對比式)三類。在當代專業音樂創作中,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作品明顯借鑒了傳統音樂的因素,傳統多聲音樂對以西方音樂為原則的專業音樂創作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是專業音樂家在創作中無意識的返璞歸真,也可能是有意識地運用本民族的民間音樂材料的結果。
《和而不同與不同而和——中國傳統多聲部音樂的思維特征與中西多聲結構差異原因之探究》是樊老師的一篇力作。該文就中國傳統多聲音樂的思維特征和中西和諧觀念進行了專題研究,總結出普遍存在的織體類型與和音形態。從和音的縱向組合方式上看,中國多聲部音樂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由純四度、純五度、大二度及小三度和聲音程組成的五聲性和音結構,另一種是泛音性和音結構。樊老師認為:“中國傳統多聲部音樂的發展情況與歐洲迥然不同,它堅守著橫向的線性思維定式,著眼于旋律及其變體的疊合進行,在縱向關系上則處于自由而隨機的自然結合的狀態。這種思維方式直接影響到多聲音樂的結構、技法以及觀眾的審美選擇。”中西音樂之間的異同在于“和而不同”與“不同而和”。
《從中西多聲部音樂的比較談起》一文,就中國傳統音樂中的多聲思維與多聲技法為什么一直停留在民間自發階段,未能發展成為一個完整體系的問題進行分析。樊老師一方面認同沈知白先生《和聲在中國已往不能發展的原因》(《音樂藝術》1982 年第2 期)一文的說法,即從不同的宗教與音樂的關系和中國長期的封建制度阻礙多聲音樂發展來闡析。與此同時,樊老師也認為,對此還可進一步從科學技術發展與音樂的關系,以及中西方不同的審美選擇、傳統思維方式及其藝術表達方式等方面進行深入的探討。
《論支聲音樂》一文進一步論述了作曲家在專業音樂創作中運用支聲的創作方法,即在縱向或橫向上與其他織體相融合,構成混合織體,包括裝飾性分支聲部與主調的伴奏音型相結合,支聲與對比復調相結合,或支聲與模仿復調相結合。
《從“多聲部民歌”一詞的英譯談起》一文,就“支聲音樂”相對應的英文詞匯heterophony 談起,闡述了多聲部音樂的基本內涵。而在《我國民間多聲與西方近現代音樂》中認為,支聲音樂是世界各地古老的民間音樂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織體形式。
(六)多聲部民歌的和聲研究
既然是多聲部音樂,聲部與聲部之間一定會有縱向的和聲關系。樊先生發表在《中國音樂》1988 年第4 期的《多聲部民歌的和聲特點》一文,研究了中國多聲部音樂的和聲材料,以及和聲的運動邏輯。中國各民族多聲部民歌在和聲材料上包含和聲音程(即三度疊置的)和多音和音(非三度疊置的)兩大類;和聲運動邏輯是通過組成各聲部的旋律—調式邏輯關系表現出來的,其中,主音同度的和音是穩定的,其他和音是不穩定的。
樊先生撰寫的《五聲性調式和聲研究》(《中國音樂學》2017 年第1 期)一文,進一步闡述了中國多聲音樂的和聲特點與五聲性和聲的和弦結構,從和聲與旋律的關系來看,和弦結構主要包括三度結構、四五度結構、二度結構、縱合性結構,以及混合結構。
(七)演唱方式方法研究
在樊老師有關中國多聲部音樂的研究中,其重點研究對象是各地和各民族的民歌。在樊老師看來,中國多聲部音樂的形成與不同組合的演唱方式有關。《多聲部民歌的演唱形式與演唱方法》⑧載《當代音樂》2016 年3 月,第1—4 頁。一文,把演唱方式總結為合唱類和重唱類兩種。合唱類中有男聲、女聲、童聲、混聲,以及以合唱方式形成的男女對唱;在重唱類中有男聲、女聲、童聲、混聲,以及以重唱形式構成的男女對唱。其中,一領眾和與突出高聲部是各類演唱組合中最具特色的兩個特點。文章還總結了各種嗓音的運用。
(八)民間多聲部合唱研究
如前所述,樊老師把多聲部民歌的演唱類型分成“合唱類”和“重唱類”;而在研究多聲部民歌的形態特點時則把焦點放在了織體形式、調關系、和音/和聲關系,以及曲體結構和節拍節奏等。
在樊老師的研究成果中,有三篇文章專門就合唱類的民間音樂形式進行了形態分析。《廣西民間合唱的多聲結構形態》 (《音樂藝術》1984 年第2 期)則把廣西的民間合唱類型劃分為:分聲部式支聲合唱、和聲式合唱、持續音合唱(其中又包含襯腔式持續音、加裝飾的持續音和固定音型的持續音)、對比式合唱,以及模仿式合唱。《廣西民間合唱中的調發展》(《中國音樂》1982 年第2 期)把該地區的民間合唱的調式特點描述為:同宮系統的縱向滲透與橫向交替、不同宮系統的同主音交替、瑤族民歌中的二度關系轉調。《廣西民間合唱的和聲音程特點》(《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2 年第4 期)一文把該地區的合唱音程關系劃分為:窄音程、不同調式的音程運用、大二度和聲音程的運用幾部分。文章特別論述了大二度音響產生的緊張度和不穩定性的解決問題。樊老師認為,這種大二度的應用所造成的緊張感和不穩定性同樣需要解決,其解決方式與西方和聲學中的方法不同,在廣西,這種不協和的解決是采用主音同度的方法,這種終止方式是當地唯一的解決去向。
(九)多聲樂器研究
2012 年,樊老師的“中國傳統多聲部音樂形態研究”獲得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項目重點課題立項。作為階段性成果之一,樊老師和王碩共同署名發表了《中國民族樂器中的多聲樂器》(《音樂藝術》2015 年第1 期)一文。該文是對多聲樂器的構造和多聲原理的探究。文章論道:在中國的民族樂器中,以多管、多弦為構造特征的樂器具備演奏多聲音樂的可能性;不同構造的樂器在多聲構成方式上既有自身的特點,又在客觀條件上具有共性。
(十)中國傳統音樂多聲思維研究
2017 年,樊老師發表了一篇名為《關于線性思維與音樂術語——中國傳統音樂研究中的兩個問題》(《黃鐘》2017 年第1 期)的文章,專門討論了中國傳統音樂多聲思維的問題。文章認為,中國傳統音樂的思維方式,以橫向線性思維為其特征,但是,這并不是說中國音樂只是單聲部的旋律,在同一旋律的變體中有各種疊合方式,形成了進行中的多聲性。所以,中國傳統音樂是線性思維,但并非單聲線性思維。在研究和聲與傳統多聲部音樂時,運用最為頻繁的音樂術語有和聲、和音、音程、和弦、對位、織體、支聲、復調、模仿復調、對比復調、主調、固定音型和持續音等等。由于這些術語幾乎都是從歐洲引進的,在中國傳統音樂文獻中找不到相對應的詞語,怎樣運用這些概念和術語是一個難題。
在談及以上各類成果之后,我們必須提及樊老師在多聲音樂研究上的一部重要論著《中國多聲部民歌概論》⑨人民音樂出版社1994 年版。。這部巨著綜合了以上各類成果,就多聲部民歌相關問題而展開討論。在上、中、下三編中,樊老師就多聲部民歌的產生、發展、消亡、題材、與其他民間音樂的關系等問題展開討論;就23個民族的多聲部民歌展開個案研究;對多聲部民歌的音樂形式要素、演唱形式和方法、聲部的構成、節拍節奏特點、調式調性特征以及織體形式、和聲特點、曲式結構等進行分析。可以說,這部巨著是體現樊老師多聲部民歌研究的重要文獻,也是中國傳統音樂,特別是中國少數民族音樂教學與研究中的重要文獻。
二、對樊祖蔭教授多聲音樂研究的幾點認識
通過以上的敘述,我們大致可以了解樊祖蔭老師在中國多聲音樂研究上所取得的令人驕傲的成績(當然,此文的總結一定是不全面的)。筆者通過學習這些文獻,對樊老師的研究有幾點感受。
(一)中國多聲音樂的民間性
西方有復調音樂,中國有復音音樂,這兩者都是多聲性的,但性質不同。西方的復調屬于專業音樂創作領域,而中國的復音音樂屬于民間音樂領域。然而,西方復調音樂也有其發展的歷程。以西方音樂思維來探討音樂的織體,可以把不同的音樂類型分成單旋律音樂(monophony)、復音音樂(polyphony)和主調音樂(accompanied music)。復調音樂在16 世紀以前稱為“復音音樂”(polyphony),16 世紀以后稱為“復調 音 樂”(counterpoint)。counterpoint 一 詞來源于拉丁語nota contra nota,其本質含義是“音對音”。之后,逐漸發展為一音對多音,多音對多音,逐漸形成了旋律對旋律的不同類型。可見,西方的復音音樂(polyphony)和復調音樂(counterpoint)主要是兩個或多個聲部之間的關系,并形成了多種規則類型,諸如卡農、賦格等,成了一種可以通過書本學習而獲得的作曲手法,并用于創作實踐中。
但是,在世界上,還存在另外一種多聲性的音樂,英文稱為heterophony,其含義是幾個聲部一起演奏同一旋律,有些聲部有意無意地偏離旋律音符而形成了多聲部現象。這種現象是非規律性的,具有隨機性特點,是在演奏實踐過程中形成的,并運用于演奏實踐之中,所以,不能通過書本學習而獲得。樊老師堅信,中國各民族音樂中一定存在多聲音樂現象,這需要學者進行深入細致的田野調查。⑩參見樊祖蔭《壯侗語諸族民間音樂原始形態的初步構擬》,《藝術探索》1997 年第4 期,第163 頁。在《從“多聲部民歌”一詞的英譯談起》?載《人民音樂》1992 第11 期,第13 頁。一文中,樊老師論及英文詞匯heterophony 的概念和多聲部音樂的內涵,認為中國多聲部民歌是有意識的歌唱行為,從“雙聲”“雙音”“哈雙”等名稱即可以看出這種有意識的歌唱行為方式。在《浙江畬族民歌的音樂特點》一文中,樊老師則更進一步地論述了中國多聲音樂產生的原因:“(一)開始唱時,其中一人未能準備好,晚進來一、二拍;或中途忘詞,想起來再補,于是形成‘模仿’。(二)齊唱開始為同度,時間一長,有人底氣不足而降低調門,于是形成‘平行進行’。不過降低的度數常是固定的:四度(如同對唱時產生的低四度‘調交替’一樣),這樣,就臨時構成四度平行進行,甚至四度卡農模仿。”?載《中國音樂》1984 年第2 期,第78 頁。可以看出,由這兩個原因所形成的多聲現象與西方的heterophony 一詞所指的支聲完全一致。只是這類多聲部民歌基本上起源于古代的“大混唱”,而且后來也沒有走向“規范化”,沒有形成有規律的結構原則與方式。根據樊老師的觀點,這種民間的多聲現象終將伴隨勞動方式、風俗習慣和審美趣味的改變而逐漸消失。
(二)詳細的歸納總結與未來的發展潛能
“多聲音樂”說到底是音樂形態問題,沒有對音樂形態的分析,在音符中找到多聲音樂的存在及其存在方式,不可能論證中國多聲音樂是否存在,也不能說明中國多聲部音樂具有哪些與西方多聲部音樂一樣或不一樣的特點。閱讀樊老師的成果,每篇文章中均有對樂譜深入細致的分析,在復雜多樣的、近乎無規律的音樂現象之中去努力尋找規律,由表層的統計,到深層的結構類型劃分,這是一個艱巨的工作,特別是面對大量來自不同地區和民族的音樂樣本時,沒有扎實的音樂分析功底是不可能做到的。可以肯定,樊老師早先所打下的作曲技術理論基礎在此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其中有四個重要觀點對筆者認識中國多聲音樂產生了重要影響。
其一,多聲部民歌織體形式的五大類型和九種方式。這是基于大量的音樂文本分析,歸納和總結出的具有規律性的認識。西方的比較音樂學和民族音樂學,雖然有從音樂到文化視角的變化,但音樂本體分析從來沒有從研究中消失。樊老師在多聲部音樂研究上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是中國傳統音樂中是否存在多聲部音樂現象,如果存在,它們是怎樣構成的?回答這個問題,離開音樂本體的分析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什么是“中國傳統音樂研究”?什么是“民族音樂學研究”?什么是“把音樂作為文化來研究”?什么是“在文化中研究音樂”?這些問題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者感興趣的問題是什么,以及為了尋求答案所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從這一點來看,在中國傳統音樂研究(或民族音樂學研究)中,音樂本體分析不僅在過去是有效的方法,而且必將伴隨未來的研究過程。
其二,在樊老師的研究中,和聲問題是與多聲問題平行的中心問題。由于聲部之間會形成音與音的縱向關系,因此,在研究橫向旋律線條的結構關系時,縱向的和聲關系也是樊老師研究成果的中心內容之一。在分析歸納時,樊老師采用了“和聲音程”和“多音和音”兩個概念,以此來區分多聲部音與音之間的音程類別,并得出了中國傳統多聲民歌的和聲特點是以四、五度加二度或三度構成的密集式音程為主的結論。
其三,既然聲部之間有音程及三音和音(和弦)的關系,那么,這些音程或和音就一定會有協和與不協和之分,而不協和的音程或和音所造成的緊張感則需要解決。這不僅僅是音樂規律的需要,也是人神經感官的需要。西方音樂在此方面有一套完整的理論與方法,中國多聲民歌是怎樣來處理這一問題的呢?樊老師認為,中國多聲民歌中所采用的不協和音程與和音的解決辦法是走向“主音同度”。
其四,通過樊老師歸納出的中國多聲部民歌所采用的九種支聲方式(即接應式、支聲式、幫腔式、和音式、襯托式、持續音式、模仿式、對比式和綜合式),我們可以看出,前七種都是以一個聲部為主,其他聲部支撐的方式;在對比式和綜合式中,不同聲部之間可能有并列性質。所以,樊老師認為,在中國傳統多聲部民歌中,高聲部占據多聲部的主導地位。
如果把上述四點作為規律性的總結,并運用到未來的專業化創作之中,在創作實踐中加以豐富和完善,是否能夠形成中國獨特的“復調”(而非“復音”)呢?由此就可避免伴隨勞動方式、風俗習慣和審美趣味的改變而使這些豐富多彩的多聲音樂逐漸消失呢?這可能需要中國作曲家們的思考與努力,也使樊老師的研究成果能夠為中國專業音樂的發展發揮應有的作用。
(三)“多聲”概念與內涵的拓展
由于中國傳統音樂種類繁多,隨著研究的深入,樊老師逐漸把研究視角從少數民族民歌擴展到漢族民歌,以及戲曲、說唱、器樂等不同的音樂品種和類型之中,探討多聲部音樂現象。在這種廣闊的視野中,逐漸拓展“多聲性”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在突出橫向旋律關系的同時,逐漸把“多聲”擴展到了音關系、節奏關系、音色關系、主奏與伴奏等聲部之間的關系,等等。
比如,在《中國民族樂器中的多聲樂器》一文中,通過樂器構造、演奏方法,以及主弦與空弦之間等不同視角,探討了中國各類民族樂器的多聲現象。另外,中國獨具特色的鑼鼓樂樂種采用不同的打擊樂器,其中包括不同形制的鼓,型號不一的大鑼、小鑼、大鐃、大鈸、鐺子和小镲,等等。這些樂器在合奏中擊打不同的節奏,構成了復合節奏關系;在音色上更是各不相同,構成了復合音色的關系。樊老師在《和而不同與不同而和——中國傳統多聲部音樂的思維特征與中西多聲結構差異原因之探究》一文中說道:“鑼鼓樂合奏,即是不同的音高、音色與節奏的縱橫向結合體,其中的節奏與其他種類的音樂相同,起著骨架與組織的作用,各樂器之間不同的節奏形式構成各種節奏對位。其織體的形式,以往多列入復調型的節奏對位,也有主張為主調性的,實際上,它是包含有各種織體成分的、具有鑼鼓樂自身特色的綜合型織體。”?參見注⑦。
(四)審美選擇依然是中國多聲音樂產生的基礎
樊老師在認同音樂文化屬性的同時,堅守把多聲音樂作為一種“藝術”現象,確立審美對多聲現象產生的決定性作用。在《浙江畬族民歌的音樂特點》一文中所論述的由于演唱失誤造成的分聲部現象,雖然“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是歌者有意識地去構成的,因此,還算不得通常意義上的‘多聲部’。不過,從中似乎也可窺見民間多聲音樂的發端:這種偶然產生的現象,如果符合審美要求而多次重復,一經成為有意識的活動,就可能逐漸形成多聲思維”?參見注④。。布依族群眾把雙聲部唱成單聲部稱為“公母相混”。可見,審美意識在中國民間多聲部形成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從“大混唱”,到由于演唱錯誤而產生聲部誤差,到有意識地強調這種誤差,多聲部的意識逐漸形成,在生產勞動方式、生活風俗、語言和自然條件等因素的影響下,中國各種各樣的多聲音樂逐漸成形,它成了中國傳統音樂中的重要類型,也塑造了中國傳統音樂多元一體的獨有特征。
在《和而不同與不同而和——中國傳統多聲部音樂的思維特征與中西多聲結構差異原因之探究》一文中,樊老師強調了中國傳統音樂的“多線”思維,認為:“這種思維方式直接影響到多聲音樂的結構、技法,以及觀眾的審美選擇”?參見注⑦。。“和而不同”體現了中國哲學對和諧的理解,“和”是兩個不同的事物能夠相向而行,既符合規律,又各不相同;“不同而和”體現了西方哲學對和諧的理解,是兩個不同事物在對立中達到和諧。中國的審美規律是“和諧統一”,而西方審美是“對立統一”。所以,在“原生性”和“自發性”的中國傳統多聲部音樂之中,依然包含著深層審美規律的驅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