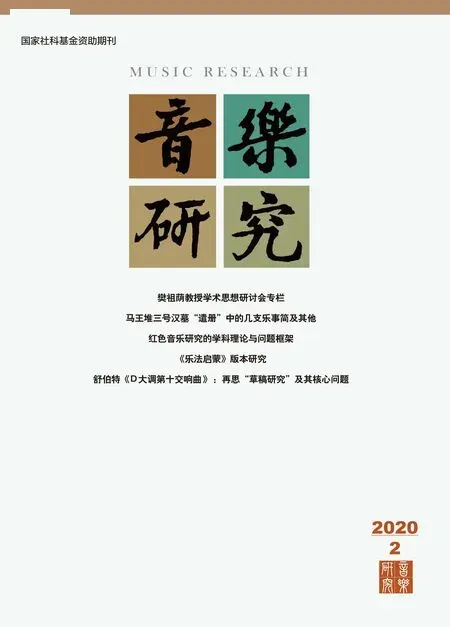中國傳統(tǒng)音樂多聲思維之存在
文◎項(xiàng) 陽
所謂多聲音樂,是聲樂和器樂在展示中非簡單唱奏同一旋律,而是在一定時間內(nèi)有多條旋律線展開,呈層次性和豐富性的同時顯現(xiàn)豐滿與張力;或稱雖突出主要旋律線條,卻在相同時間內(nèi)顯現(xiàn)不同聲部組合,音樂思維呈聲部豐富性而不是單一性存在。西方多聲部音樂,既有主調(diào)和聲式,亦有復(fù)調(diào)對位式,在多聲思維認(rèn)知提升的前提下,逐漸創(chuàng)造出作曲技術(shù)理論,生發(fā)出音樂重要類型并在多種音樂體裁中運(yùn)用。
學(xué)界認(rèn)定,西方自5 世紀(jì)羅馬教皇格里高利圣詠時期即有多聲部音樂產(chǎn)生,但多聲部音樂真正的發(fā)展,卻是在近千年之后的文藝復(fù)興和工業(yè)革命浪潮中,由此形成一系列音樂體裁和形式,凸顯多聲思維引領(lǐng)并成為西方專業(yè)音樂的重要標(biāo)志。以城市為中心的文藝復(fù)興始于14 世紀(jì),其后工業(yè)革命促使科技和經(jīng)濟(jì)大規(guī)模發(fā)展,也促進(jìn)了創(chuàng)造理念和藝術(shù)形態(tài)的變化,多聲音樂思維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逐漸轉(zhuǎn)化為專業(yè)發(fā)展勢態(tài)。問題在于,西方多聲音樂思維在文藝復(fù)興之前雖有存在卻未彰顯,倘若中國音樂發(fā)展亦成多聲思維彰顯樣態(tài),也同樣可以溯源探流。換言之,中國傳統(tǒng)音樂文化是否自身沒有多聲思維,受西方音樂影響方建立起多聲觀念,值得深入探討。探求中國多聲音樂思維的諸種因素是一個重要課題,對中國傳統(tǒng)音樂文化更是值得人們下功夫和氣力去認(rèn)真把握,以明確中國人創(chuàng)造音樂文化的深層內(nèi)涵。
一、中國多聲音樂的諸種因素
學(xué)界認(rèn)為中國傳統(tǒng)音樂文化中缺乏多聲部音樂思維,若有,不過是近兩百年的事情,這當(dāng)然是以西方專業(yè)音樂為參照系,或稱受到西方音樂影響方有所建立和發(fā)展。中國多聲音樂思維是否真的產(chǎn)生得這么晚,依筆者看來似乎并不如此。中國多聲音樂存在的因素真是不少,關(guān)鍵在于怎樣去認(rèn)知。我們既應(yīng)以西方專業(yè)音樂技術(shù)理論作為參考對中國傳統(tǒng)音樂以行觀照,亦應(yīng)回到歷史語境中依多聲音樂基本形態(tài)去考量,如此才會明確中國傳統(tǒng)音樂文化自身的特色。
(一)禮樂中雅樂和非雅樂類型的多聲存在
筆者曾通過《國語·周語》“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對中國早期多聲思維進(jìn)行過相關(guān)的探討和辨析,①項(xiàng)陽《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中國早期多聲思維淺識》,《人民音樂》2015 年第12 期。這是兩周時期、或稱三千年前經(jīng)典樂隊(duì)組合樣態(tài)。金石具有重器、禮器、祭器和樂器的多重功能,在這一時期,社會上層人士擁有樂懸的數(shù)量不盡相同,所謂“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其所用樂器隨著時代的發(fā)展逐漸在數(shù)量上進(jìn)行內(nèi)部擴(kuò)充,在依制擁有的情狀下拓展了編列數(shù)量,金石在樂隊(duì)中可能更多是作為骨干音的演奏,而將主旋律交與絲竹類樂器。既然依制擁有,這種樂隊(duì)組合非僅限于廟堂,還會用于朝堂和廳堂,是為禮俗兼用。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wèi)之音,則不知倦”,與鄭衛(wèi)之音可能由同一種樂隊(duì)承載,周代是這樣定位。漢唐間則將這種以金石樂懸領(lǐng)銜(樂器均為中原自產(chǎn))的樂隊(duì)組合置于禮樂最高端,視其為“華夏正聲”,為雅樂所獨(dú)用,將其小眾化。但這種形態(tài)卻是一以貫之地存在,唐宋以降因國家科舉制度實(shí)施,在全國普設(shè)文廟,作為“文廟祭禮樂”之必須,國家太常統(tǒng)一創(chuàng)制,連同這種樂隊(duì)組合頒至全國府衙一級,州縣依府式而制,使得雅樂繼續(xù)在宮廷為用的同時,其一支脈來到地方各級官府,這就將同屬“金石動,絲竹行”的演奏形態(tài)延展到了全國。
這樣的多聲樣態(tài)原本漢唐間在宮廷中一直延續(xù),繼而唐宋以降來到全國縣治,雅樂一脈成為從宮廷到各級地方官府的廣泛性存在(絕非宮廷不再,雅樂便不再)。這種多聲形態(tài)不似西方專業(yè)多聲音樂那樣彰顯,無疑屬于多聲思維,一直延續(xù)至1911 年。當(dāng)下仍有活態(tài)存在,這就是作為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作的“瀏陽文廟祭禮樂”。
金石樂懸早期因未有樂譜和舞譜,難以把握本體形態(tài)。樂譜發(fā)明后,直至明代對雅樂形態(tài)的記錄始為單旋律,無節(jié)奏與時值,明末《太常續(xù)考》所見國家大祀雅樂所用樂譜依舊如此。清代出現(xiàn)新變化,在乾隆六年由和碩莊親王允祿奉旨編纂的《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成書于乾隆十一年)中,用工尺譜記寫的樂譜中已見節(jié)奏與時值符號。正因?yàn)榇耍“四辏?743)面向全國頒布的版本仍是沒有節(jié)奏與時值的單旋律譜,這給當(dāng)下可見節(jié)奏與時值符號的創(chuàng)制留下空間。瀏陽邱之稑《丁祭禮樂備考》(道光二十年,1840)據(jù)乾隆十二年(1747)宮中太常在闕里教授相同版本實(shí)際演奏記錄的樂譜顯示不僅具多聲樣態(tài)(見封二上,圖1、2、3②邱之稑《丁祭禮樂備考》卷中“樂章律音譜”“管樂笙字譜”“琴譜”,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圖書館藏本。),且記錄不同聲部,“諸如‘聲韻譜’(顯示每一個字規(guī)范的開口、合口、重唇、半舌、喉、牙、正齒、齒頭、舌上、輕唇等多種發(fā)聲樣態(tài))、‘舞譜’(展現(xiàn)祭孔舞蹈中的立容、舞容、首容、身容、手容、步容、足容、禮容等多種姿態(tài))、‘琴譜’(琴的演奏分譜)、‘瑟譜’(瑟的演奏分譜)、‘管樂聲字譜’(用工尺譜記寫,已經(jīng)有節(jié)奏和時值符號,應(yīng)為管樂器演奏實(shí) 用譜③在《丁祭禮樂備考》卷下中記有特鐘、編鐘、特磬、編磬、琴、瑟、鳳簫、洞簫、篪、笛、笙、塤、楹鼓、應(yīng)鼓、搏拊鼓、鼗鼓、柷和敔等樂器18 種,有麾幡、旌節(jié)、籥和翟舞器4 種(籥在此為舞蹈專用)。在樂器中,吹奏樂器6 種,弦樂器2 種,擊奏樂器10 種,這管樂聲字譜應(yīng)該是為管樂演奏所用。),這是對祭孔樂舞較為全面的展示。”④項(xiàng)陽《一把解讀雅樂的鑰匙:關(guān)于邱之稑的〈丁祭禮樂備考〉》,《中國音樂學(xué)》2010 年第3 期,第19—20 頁。換言之,這樣的形態(tài)延續(xù)了數(shù)千載,只是早期沒有如此詳盡的記錄而已。
乾隆版未記錄節(jié)奏和時值的《文廟祭禮樂》頒發(fā)全國,多種地方志書記載可為佐證。《丁祭禮樂備考》由邱之稑在道光年間編纂成書,將主旋律譜原樣記錄,后有多種譜式,展現(xiàn)分譜意義,其標(biāo)記的節(jié)奏與時值符號,與《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乾隆《律呂正義后編》一致,乾隆年間可能是這種符號的創(chuàng)制年代。在20 世紀(jì)50 年代,楊蔭瀏先生率領(lǐng)團(tuán)隊(duì)將瀏陽孔廟中實(shí)際演奏的《文廟祭禮樂》以五線譜方式記出(見下譜⑤楊蔭瀏《孔廟丁祭音樂的初步研究》,《音樂研究》1958 年第1 期,第61—62 頁。),為邱譜的部分組合(聲韻譜和舞譜未列),呈現(xiàn)“總譜”樣態(tài),以多聲部存在。雖然僅將編鐘、編磬和部分打擊樂器與演唱旋律記出,而未記錄琴譜和瑟譜,但演唱者旋律與樂隊(duì)形成整體,且節(jié)奏與時值有如“絲竹行”,與樂隊(duì)形成多聲樣態(tài)。編鐘與編磬有旋律線,但節(jié)奏不同。


我們說邱之稑《丁祭禮樂備考》是解讀雅樂的鑰匙,涉及諸種因素,最為要者是雅樂形態(tài)以華夏正聲為主導(dǎo),數(shù)千年間其主要演奏形態(tài)和用樂方式相對固化,相關(guān)文獻(xiàn)表述清楚。由于唐宋之前缺乏樂譜,即便其后有樂譜之時也僅記錄主旋律,難以全面把握。作為“有心人”的邱之稑,了解到宮中太常寺樂師要到闕里教授國家頒發(fā)的“文廟丁祭禮樂”,征得縣令批準(zhǔn)前往參加習(xí)學(xué),然后嚴(yán)格記錄唱奏分譜,方使我們得見清代演奏頒布全國之雅樂的實(shí)際狀況。瀏陽方面在尚有傳承的基礎(chǔ)上對其恢復(fù),成為當(dāng)下我們認(rèn)知有著數(shù)千年傳統(tǒng)國家雅樂的重要窗口。
中國傳統(tǒng)音樂多聲思維非僅限于雅樂形態(tài),甚至不僅限于禮樂形態(tài),兩周時期如此,宋代教坊所用之大晟樂同樣如此。
今太常獨(dú)與教坊樂音殊絕何哉?……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yuǎn),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zhì)器與聲樸,后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后世易之為方響;絲竹,琴簫也,后世變之為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為甌;革,麻料也,擊而為鼓;木,柷、敔也,貫之為板。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而不達(dá)者,指廟樂镈鐘、镈磬,宮、軒為正聲,而概謂胡部、鹵部為淫聲,殊不知大輅起于椎輪,龍艘生于落葉,其變則然也……⑥(元)馬端臨《文獻(xiàn)通考》卷146“樂考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依制,以金石樂懸領(lǐng)銜的華夏正聲樂隊(duì)組合不應(yīng)用于教坊,但宋代太常屬下大晟府創(chuàng)制大晟雅樂的同時亦創(chuàng)制大晟燕樂,并撥用于教坊,如此以鐘磬之于方響,琴簫之于箏笛,塤以甌代,柷敔為板等為替代。這說明雖然其樂器品種有差,但同屬禮樂范疇,由同一機(jī)構(gòu)創(chuàng)制,只不過從樂隊(duì)組合上有所區(qū)隔而已。“政和三年詔,以大晟樂播之教坊,頒行天下。尚書省言,大晟燕樂已撥歸教坊,所有習(xí)學(xué)之人元隸大晟府教習(xí),今當(dāng)并令就教坊習(xí)學(xué),從之。”⑦同注⑥。教坊承載大晟燕樂之樂隊(duì)組合對應(yīng)雅樂有變化,其創(chuàng)作思路依舊。所謂“大輅起于椎輪,龍艘生于落葉”,同樣是音樂本體思維下的產(chǎn)物,這就將多聲思維和形態(tài)再次拓展到多類型禮樂為用,同時也說明此時的教坊實(shí)際承載非雅樂之禮樂職能。
(二)俗樂組合的多聲部意義
在樂隊(duì)組合中,有些樂器隨時代而發(fā)展,逐漸豐富演奏技法,有脫胎換骨之感。諸如漢魏南北朝直至隋唐時期,除中原產(chǎn)的秦漢子外,從西域傳來的琵琶皆屬“充上銳下”⑧“今清樂奏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頸而小,疑是弦鼗之遺制。其他皆充上銳下,曲項(xiàng),形制稍大,疑此是漢制。”載《舊唐書》卷29“志第九”,中華書局1975 年版,第1276 頁。,即不管是曲項(xiàng)還是直項(xiàng),四弦還是五弦,演奏者將梨形音箱在上、帶軸軫一端向斜下方抱持。即便晚些時候銳端向斜上方,也是左手托住頸項(xiàng)的同時去按弦,難以快速移動把位演奏旋律,這是這一時期琵琶有相無品、隨著向斜上方抱持其品逐漸增多的道理。畢竟左手托舉頸項(xiàng)難以多把位按弦;至于右手,用捍撥彈奏,此間技巧不像后世改指彈時更為靈便和豐富,形成一定局限,難以成為樂隊(duì)主奏。雖有唐太宗時琵琶演奏家裴神符廢撥改指彈說,但從唐代乃至遼、宋、金、元琵琶演奏的相關(guān)圖像來看,似乎社會尚未認(rèn)同這種彈奏方式,更多還是以撥彈為主導(dǎo)。當(dāng)琵琶尚未真正豎抱解放左手拓展把位時,其在樂隊(duì)中以演奏骨干音為主的方式似沒有創(chuàng)制右手技法的急切訴求。真正兩手都得以解放還是在明清時代。即便在改變之時,這種橫抱撥彈樣態(tài)在當(dāng)下尚以“活化石”樣態(tài)存于陜北和福建南音中,為我們把握琵琶千年橫抱撥彈的存在提供了考察的依憑。以南音為例,四大名譜《四時景》《梅花操》《八駿馬》《百鳥歸巢》等,主奏旋律的是二弦和尺八,琵琶演奏骨干音,在為演唱伴奏之時亦如此。由是考量,中國傳統(tǒng)樂隊(duì)組合中多種形態(tài)都應(yīng)是這種樣態(tài)。所以說,中國傳統(tǒng)樂隊(duì)組合在俗樂中亦有多聲樣態(tài),未受西方配器手法影響,表明中國傳統(tǒng)演奏形態(tài)確有多聲思維存在。至于多聲思維是否被有意識地提升,使之成為音樂創(chuàng)造的主動性存在又是另外一回事。
從不同時期樂器性能把握,由于樂器自身之局限(或稱特色)會受到速度等方面影響,樂器職能各自不同,有演奏加花變奏旋律和骨干音之別。這種現(xiàn)象在傳統(tǒng)樂隊(duì)中較為廣泛存在,諸如同一樂隊(duì)組合中同為旋律樂器的云鑼與管子、嗩吶,云鑼不可能奏出潤腔旋律,只以骨干音顯現(xiàn),而管子、嗩吶和笛等,其實(shí)際演奏要比樂譜豐富,通過音的添加和潤腔技巧形成風(fēng)格。南音樂隊(duì)組合中琵琶與二弦、尺八也是同樣道理,傳統(tǒng)絲竹管弦樂曲演奏多聲思維的存在值得深入考察與思辨。
(三)獨(dú)立樂器的多聲部意義
中國樂器中,最能體現(xiàn)多聲意義的笙,至遲在兩周已有之,其以合音方式演奏,自然而然形成兩個甚至多個聲部,彰顯音響的豐滿與厚實(shí)。笙是中國本土創(chuàng)造之樂器,由簧及笙。榮獲2018 年全國十大考古發(fā)現(xiàn)的陜西神木石峁遺址出土了23 件骨質(zhì)口簧(見封二上,圖4),其演奏原理是以口作為共鳴腔,控制氣息致使聲響擴(kuò)大的同時,撥奏骨簧可顯現(xiàn)音高及音色的變化,亦有較為豐富的技巧存在。簧在發(fā)展過程中結(jié)合于匏,竹苗刻簧(后從自體簧發(fā)展為異體之銅簧)以氣息振動,以匏為共鳴腔終變?yōu)轶稀N覀児们也徽摵笫琅d隆笙對西方相關(guān)樂器之影響,僅就簧與笙之間創(chuàng)造性演化應(yīng)在距今四千至三千年間完成,所謂“鼓簧”焉知不是既有撥奏又有吹奏之意?周代中國吹奏樂器形成兩大類:有簧與無簧,均為自產(chǎn)。
笙作為定律樂器在發(fā)展中漸成四、五、八度主導(dǎo)和音演奏樣態(tài),笙的演奏基本不以單音形式出現(xiàn),以平行的兩行甚至多行旋律進(jìn)行,自然是多聲,當(dāng)下民間樂社和班社傳承未受專業(yè)院校之影響。以河北安新縣圈頭音樂會笙的演奏為例:譜面上每一個字同時有2 至4 個音發(fā)響,若以合字為調(diào)首建構(gòu)音階,則合與六、尺同響,四、五、工同響……如此形成的和音以五度關(guān)系為主導(dǎo),兼有八度、四度發(fā)聲。
笙處于樂隊(duì)中聲部位置,樂人們講其存在讓樂隊(duì)“黏糊”,將諸種樂器演奏融為一體,所謂“和聲”“和音”理念,形成五度、八度、四度和諧觀念。有意思的是,作為音階第七音級,凡的和音是勾字,構(gòu)成協(xié)和五度,樂人們講音樂會就是這樣代代傳承,是中國人自己的傳統(tǒng),笙這種樂器顯為多聲部而生。
中國傳統(tǒng)打擊樂,雖然重在節(jié)奏亦顯現(xiàn)一定音高關(guān)系,音色變化豐富,可謂多種樂器之交響。鑼鼓譜顯為多聲部存在,記譜和實(shí)際演奏均如此,所有這些均應(yīng)一并納入多聲思維范疇考量。
二、道法自然與有意識提升
毋庸置疑,中國傳統(tǒng)音樂具實(shí)踐意義的多聲思維觀念長期存在,自周代國家制定禮樂制度后一以貫之三千載,無論從禮樂之雅樂、非雅樂乃至俗樂均如此,最具典型意義者即為雅樂的延續(xù)。然而卻未有意識在提升和強(qiáng)化多聲理念基礎(chǔ)上發(fā)展,只在“低層次”上延續(xù)。所以有多聲理念存在,有賴于中國禮樂文明國家早期存在的先進(jìn)性,未進(jìn)一步提升可認(rèn)定為主動選擇。反觀歐洲專業(yè)音樂,自教會影響世俗,從專業(yè)音樂創(chuàng)作層面有意識提升,形成專屬類型,且影響諸多音樂體裁與形式,成為音樂創(chuàng)作理念而存在,引領(lǐng)音樂創(chuàng)作技術(shù)理論發(fā)展之潮流。中國音樂多聲思維之形成在早期階段應(yīng)具先進(jìn)性,既有樂器自身因素,亦有樂隊(duì)整體考量,是在國家意義上以制度和相關(guān)機(jī)構(gòu)規(guī)范其發(fā)展演化,畢竟起于三千年之前。由此引發(fā)的反思即是,中國何以未曾有意識強(qiáng)化與發(fā)展多聲思維理念,雖有豐富性卻在多聲意義上顯現(xiàn)張力不足,在相關(guān)技法上未進(jìn)一步開創(chuàng),止于變奏、疏密相間的“縱向疊合”(樊祖蔭先生語)。
中國的確有多聲音樂思維,但有意識提升不足,這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基本狀況,只有發(fā)掘出其內(nèi)涵方能在借鑒意義上進(jìn)一步發(fā)展,諸如和聲的疊置與西方專業(yè)音樂之不同亦應(yīng)考量在內(nèi),這是否亦為制約多聲豐富性發(fā)展和提升的重要因素?應(yīng)對中國傳統(tǒng)音樂文化中的多聲思維觀念進(jìn)行深入探討,在強(qiáng)化本土意識的基礎(chǔ)上挖掘深層內(nèi)涵,在溯源探流的前提下有意識提升,在彰顯自我的同時有效借鑒外來,如此對中國傳統(tǒng)音樂文化發(fā)展有促進(jìn)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