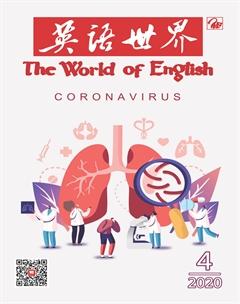他們的確講另一種語言
勞拉·J.斯奈德 丁占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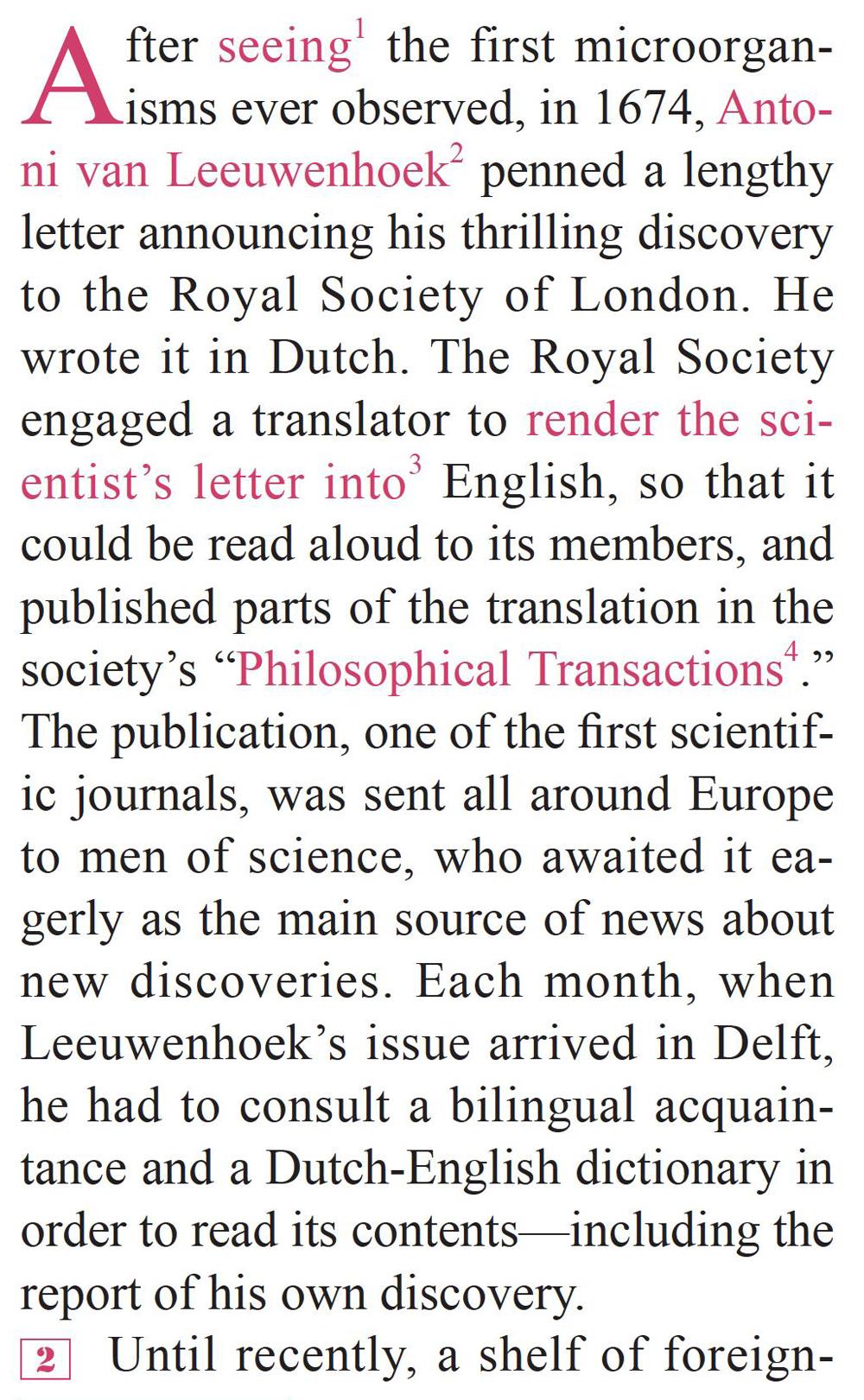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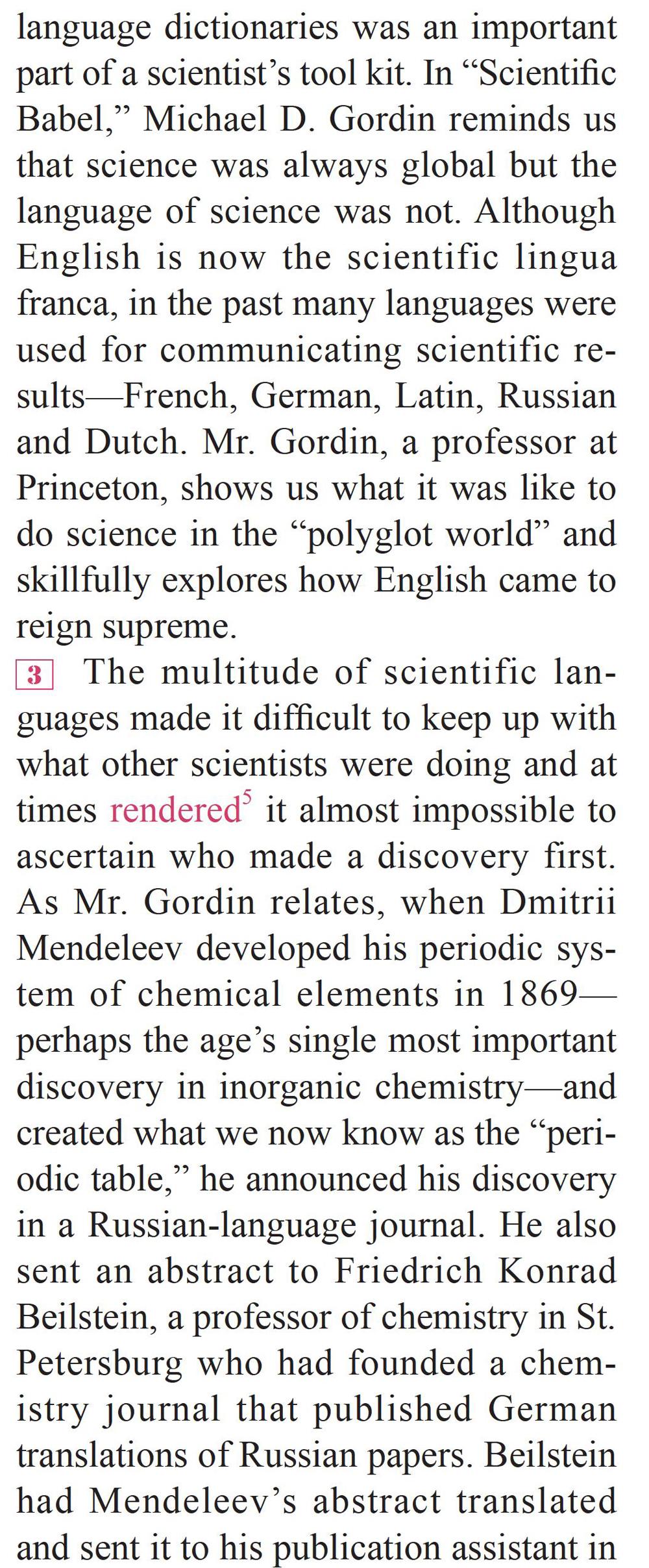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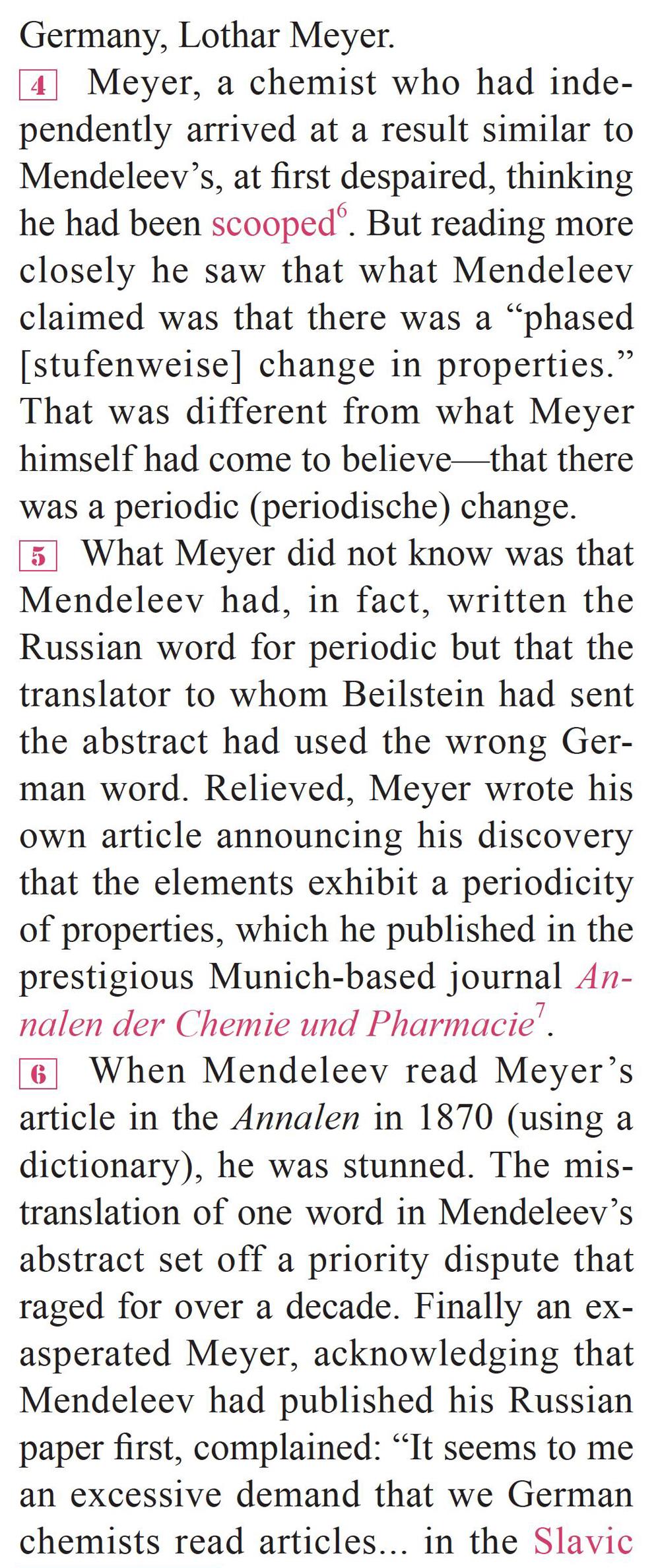
1674年,安東尼·范·列文虎克第一次看到所觀察的微生物后,給倫敦皇家學會寫了一封長信,宣布這一激動人心的發(fā)現(xiàn)。信是用荷蘭語寫的,所以皇家學會聘請一位翻譯將這位科學家的信譯成英文,以便向會員宣讀來信內容,并將部分譯文刊發(fā)在學會的《自然科學會報》上。作為世界上最早的一大科學期刊,該出版物當時要寄給歐洲各地的科學家,大家都熱切期盼,把它視為新發(fā)現(xiàn)的主要消息來源。每月寄給自己的那期到達代爾夫特后,列文虎克都不得不去求教一位懂荷英雙語的熟人,并借助荷英詞典來了解期刊內容,包括有關自己的發(fā)現(xiàn)的研究報告。
2直到最近,滿滿一書架的外語詞典還都是科學家百寶箱的重要組成部分。邁克爾·D.戈爾丁在其著作《科學的巴別塔》中提醒我們,科學向來是全球性的,但科學的語言并非如此。雖然現(xiàn)在英語是科學界的通用語言,但在過去,法語、德語、拉丁語、俄語和荷蘭語等許多語言都曾用來交流科研成果。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戈爾丁先生向我們講述了在“多語世界”里做科研是一番怎樣的情形,并以精妙的筆觸探討了英語的統(tǒng)治地位是如何形成的。
3科學語言多種并存,讓人很難跟進其他科學家的工作進展,有時幾乎無法確認誰是某一發(fā)現(xiàn)的第一人。戈爾丁先生講到,1869年德米特里·門捷列夫提出了化學元素周期系——這也許是那個時代無機化學中最重要的發(fā)現(xiàn),他還創(chuàng)立了如今所知的“周期表”,此后在一本俄語期刊上宣布了自己的發(fā)現(xiàn)。他也把論文摘要發(fā)給了圣彼得堡的化學教授弗里德里希·康拉德·拜爾施泰因,因為后者創(chuàng)辦的化學期刊就是出版俄語論文的德文譯本的。拜爾施泰因請人將門捷列夫的摘要譯為德語,并將譯文寄給了他在德國的出版助理洛塔爾·邁爾。
4當時,化學家邁爾已經(jīng)通過獨立研究得出了與門捷列夫相似的結果,所以一開始他深感絕望,以為自己的成果被別人搶先發(fā)表了。但仔細閱讀后,他發(fā)現(xiàn)門捷列夫主張的是“性質的相(stufenweise)變”,這與邁爾自己得出的“周期性(periodische)變化”結果是不一樣的。
5邁爾不知道的是,門捷列夫事實上用的就是俄語的“周期性”一詞,但拜爾施泰因請的那位摘要譯者使用了錯誤的德文單詞。不明真相的邁爾松了一口氣,撰文宣布了自己的發(fā)現(xiàn),即元素性質呈周期性變化,并將此文發(fā)表在慕尼黑一家頗富聲望的雜志《化學和藥學年鑒》上。
6 1870年,門捷列夫(借助詞典)讀到邁爾發(fā)表在該《年鑒》上的文章時,大為震驚。就這樣,門捷列夫摘要中一個單詞的誤譯引發(fā)了一場長達十余年的孰先孰后之爭。最終,惱怒的邁爾承認門捷列夫發(fā)表的俄語論文在先。他抱怨道:“我們德國化學家得讀……用斯拉夫語寫的文章,這個要求看起來過分了。”
7進入20世紀,科學語言形成“三雄并立”的局面——法語、英語和德語成為主要的官方科學語言,但許多科學家仍夢想著用同一種語言進行科學交流。由于這三種主要科學語言中任何一種語言的使用者都不愿選擇其他兩種,一些科學家和語言學家因而支持采用一種中立的“輔助l!生”科學語言。法國邏輯學家、語言學家路易·庫蒂拉在其1905年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科學家的兩難境地,戈爾丁先生援引他的話說:“學者要了解自己感興趣的特定科研工作,就必須通曉多種語言;但要成為多語通曉者,就必須放棄其他所有研究工作,而這樣一來,他們的專業(yè)知識也便幾近枯竭了。”
8 1907年,一個由語言學和科學界權威組成的國際委員會召開會議,審議設立一種世界通用的科學語言的問題。世界語這一由波蘭醫(yī)生、發(fā)明家盧德維克·柴門霍夫于1887年創(chuàng)造的語言,似乎是個誘人選項,也得到了許多委員的認同。但是一天上午,委員們到達審議會場后發(fā)現(xiàn),打印材料上所描述的卻是另一種被稱作“伊多語”的新造語言。直到若干年后,做手腳者才被曝光。戈爾丁先生饒有興致地講述了這個故事。原來,該委員會主席、德國化學家威廉·奧斯特瓦爾德迷上了伊多語,認為它具有表達化學關系的潛力。他成了伊多語的狂熱支持者,甚至將自己1909年所獲諾貝爾獎金的大部分捐出用于推廣該語言。但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奧斯特瓦爾德改口稱,他認為科學的唯一語言應該是德語,這令其同行既震驚又憤怒。
9結果卻不如奧斯特瓦爾德所愿。戰(zhàn)爭結束后,科學界為講德語的科學家設置了重重障礙,以制裁德國的政治侵略。國際理論化學與應用化學聯(lián)合會把德語移出了官方語言之列,其他國際科學組織也紛紛效仿。
10但是到了1930年代,德國科學家在量子物理學這一新領域居于領先地位,德語作為科學交流的手段再次被接納。然而,希特勒的掌權迫使許多德國一流科學家移居國外,從而以新的語言去學習知識、傳授知識、發(fā)表著述。戈爾丁先生講述了物理學家莉澤·邁特納等科學家在語言上遇到的困難,后者覺得自己在瑞典“客居于斯德哥爾摩瑞典皇家科學院的生活十分窘迫”。她整夜整夜地學習瑞典語、閱讀瑞典語小說,她哀嘆道,離開了自己的母語國家,“一個人絕不會享有平等的權利,且內心總是孤獨無依”。
11二戰(zhàn)結束時,作為對德國政治抵制的一種手段,美國和其他國家已停止教授學生德語。很快,英語擊敗了其他語言而成為科學語言。今天,英語幾乎總是用作國際科學會議唯一的交流語言。在自然科學頂級期刊中,超過98%的論文用英文發(fā)表。無論科學家的母語是法語、德語、俄語、日語還是烏爾都語,他們都應精通英語。
12英語崛起為全球性科學語言的故事讀來頗具趣味,它說明科學與政治之問相互依存。正如戈爾丁先生向我們表明的那樣,這一結果沒有必然性。英語是通過一系列偶然的歷史事件,特別是在“納粹暴行引發(fā)了多國對德國毫不含糊的政治反擊”之后才取得的統(tǒng)治地位。誰都不能斷定英語能否永保全球性科學語言的地位,也不能斷定另一個“科學的巴別塔”是否會出現(xiàn),若是出現(xiàn)了,也不知會讓科學變得更好還是更糟。
(譯者為“《英語世界》杯”翻譯大賽獲獎者;單位:中華女子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