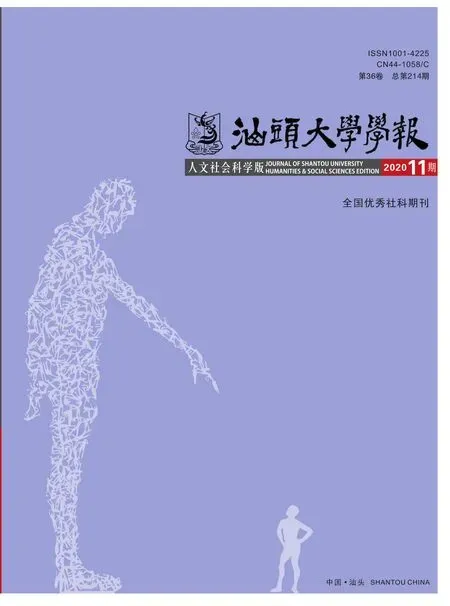社交媒體使用與抑郁關系的元分析
吳曉旋,毛良斌
(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廣東 汕頭 515063)
一、問題提出
隨著社交媒體用戶增多,一些研究者開始關注社交媒體使用強度與抑郁的關系,即使用社交媒體是否導致抑郁水平的升高或降低,以及這種影響關系發生的條件和機制。然而,既有研究結果未達成一致,甚至相互矛盾。部分研究發現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可以顯著地提升抑郁水平[1],有學者甚至提出“臉譜抑郁”(Facebook Depression),用來形容在Facebook 上花費太多時間而引發抑郁癥的現象。[2]但其他研究卻發現社交媒體使用強度不能顯著提升抑郁水平[3],甚至會降低抑郁水平[4]。
社交媒體使用強度是否會顯著提升個體的抑郁水平?哪些調節變量會影響社交媒體使用強度與抑郁水平的關系?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問題,本文使用元分析方法,對既有研究的效果量進行綜合計算,以期得到更全面、準確的結論。
二、研究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基本概念
1.社交媒體使用強度。社交媒體使用強度(Social Media Intensity)是用來衡量個體在使用社交媒體時的投入水平、與社交媒體的感情聯系強度以及其融入個體日常生活程度的指標。[5]個體在使用社交媒體時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投入水平和粘性,呈現不同水平的使用強度。[6]
Ellison 等人編制的Facebook 使用強度量表在學界和業界被廣泛認可與使用,具有良好的信度。[7]在該量表中,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包括三個維度:Facebook 朋友數量、每天花在Facebook 上的時間、Facebook 融入日常生活的程度。[5]除了Ellision等人提出的三個維度,一些研究也把“社交媒體使用頻率”作為一個重要維度納入測量。[8]
基于以往研究,本研究將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具體化為以下四個測量維度:社交媒體使用時間、社交媒體使用頻率、社交媒體上朋友數量、社交媒體卷入程度(即融入日常生活的程度、依賴程度、情感投入程度)。
2.抑郁。抑郁(Depression)是以心境和情緒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征的心理和情緒問題,影響范圍廣泛,影響程度嚴重。[6]抑郁癥患者常出現疲勞、失眠和食欲不振等癥狀,嚴重時還可能產生自殺信念或發生自殺行為。[9]學界和心理治療領域依據表現特征、診斷標準以及嚴重程度,將其分為三種類型,即抑郁情緒(Depressive Mood)、抑郁綜合癥(Depressive Syndromes)和嚴重抑郁(Major Depression)或抑郁障礙(Depressive disorder)[10]。
(二)理論背景
如何理解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抑郁的影響,三個理論提供可能的解釋。
1.自我概念分化假說。自我概念分化假說(Self-Concept Fragmentation Hypothesis)認為個體使用社交媒體探索和嘗試自我的不同方面,可能面臨自我不同方面無法統合的風險,導致自我概念模糊、個人屬性內部不一致和低穩定性,即自我概念清晰度較低。[11]研究發現,個體在社交媒體上進行自我探索和表達對自我清晰性有顯著消極影響。基于自我概念分化假說,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可能以降低自我概念清晰度為中介,提高個體的抑郁水平。[12]
2.社會比較理論。社會比較理論(Social Comparison Theory)認為,人有對自己的思想、動機、行為、個性、能力等進行評價的意愿和需要。當缺乏客觀、直接的自我評價手段時,個體會通過與他人的觀念和能力進行比較來評價自我。[13]按對象不同,社會比較可分為平行社會比較(與自己同等水平的人比較)、上行社會比較(與優者比較)、下行社會比較(與劣者比較);按場合不同,社會比較可分為線上社會比較和線下社會比較。
社交媒體為線上社會比較提供可能。個體一方面可以在社交媒體上創造和分享內容呈現自我,進行印象管理。另一方面,通過鏈接進入他人主頁、與他人互動,可以形成對他人的印象。有研究發現,社交媒體上行社會比較會顯著提高個體抑郁水平。[14]
3.社會資本理論。社會資本理論(Social Capital Theory)將社會資本分為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粘結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橋接型社會資本主要來自弱關系,如同學、同事,它能為個體提供豐富有用的信息;粘結型社會資本主要來自強關系,如家人、親戚、好朋友,個體從中獲得情感和實質性支持。[15]
基于該理論,使用社交媒體有助于降低個體的抑郁水平。一方面,社交媒體加強了個體與朋友的連接感,增加其獲得情感支持的可能性,有利于降低抑郁水平[16];另一方面,社交媒體為個體接觸外界信息、專業知識和積累在線橋接型社會資本創造條件,有助于個體開拓眼界,提高社交技能,促進情緒健康發展,緩解抑郁情緒。[17]
(三)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抑郁影響的主效應
綜上所述,針對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抑郁水平的影響效應和作用機制,現有理論解釋存在差異。自我概念分化假說認為,個體使用社交媒體探索和嘗試自我不同方面,可能降低其自我概念清晰度,提升抑郁水平;線上社會比較理論認為,個體進行社交媒體上行比較時,如果把自我劣勢歸因為能力低下而非其他因素,容易產生負面自我評價,增加抑郁風險;社會資本理論認為,個體使用社交媒體可以獲得更多橋接型或粘結型社會資本,緩解抑郁情緒。
基于上述梳理,可以發現既有研究和理論對社交媒體使用強度與個體抑郁水平的關系持不同觀點。研究將通過使用主效應分析解決以下問題,確認兩者關系。
RQ1:社交媒體使用強度會顯著提升個體的抑郁水平嗎?
RQ2:社交媒體使用對個體抑郁水平的影響效果有多大?
(四)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抑郁影響的調節變量
除了對社交媒體使用強度與抑郁關系進行主效應檢驗外,本研究還將對影響兩者關系的調節效應進行分析,以期解釋現有研究結果之間的差異。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檢驗以下四個變量是否為調節變量。
1.被試類型。對青少年(介于10-18 歲)和大學生(介于18-22 歲)來說,社交媒體有重要意義。
社交媒體對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影響早已引起學界關注。[18]一方面,青少年最有可能在該時期首次產生重度抑郁癥狀。[19]在尚未形成穩定的個人和社會身份意識時,他們使用社交媒體無法逃避潛在負面影響。Kraut(1998)和Young(1998)最早發現頻繁使用社交媒體會增加青少年患抑郁癥的風險。隨著社交媒體被廣泛使用,青少年的抑郁癥發病率一直在上升。[20]另一方面,部分研究卻表明,渴望從社會關系中獲得歸屬感的青少年可以通過使用社交媒體加強與新舊朋友聯系,獲得社會支持,降低抑郁水平。[2]
社交媒體對大學生的抑郁水平也有重要影響。研究表明,抑郁癥狀的增加與大學生高強度、問題性地使用社交媒體有關。[21]社交媒體通過外部因素,如社會隔離、減少學術成就、減少運動、影響睡眠,或通過內部因素如減少自我規范,顯著提升大學生的抑郁水平。[22]
本研究有三種被試類型,青少年、大學生和成年人。在此基礎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被試類型不同,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個體抑郁水平的影響效應存在顯著差異。
2.測量工具。在納入元分析的文獻中,抑郁水平的測量工具包括以下幾種: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II,BDI-II),旨在評估受訪者的情感、認知和軀體狀況;[23]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要求受試者思考過去一周的感受,并使用4 點量表表示感受出現的頻率;[24]九項病人健康問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items,PHQ-9),將9 個項目的結果相加,可得出被測者的抑郁程度;[25]抑郁焦慮壓力量表(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21,DASS-21),可分別測試抑郁、焦慮、壓力水平;[25]醫院焦慮與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有14 個項目,4 個備選答復,越高的分數表示癥狀的水平更高;[25]成人患者報告結果測量信息系統(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Measurement Information System,PROMIS),用于評估病人的心理、身體和社會健康狀況;[25]其他量表(OTHERS),大多數研究將上述量表作為測量工具,也有學者使用其他量表來測量抑郁水平,如抑郁癥狀自評問卷(Questionnaire Of Self-evaluated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QD2)[26],Zung 氏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27]。
本研究中,通過對文獻進行編碼統計,將抑郁癥狀的測量工具分為以下幾類:(1)BDI-II;(2)CES-D;(3)PHQ-9;(4)DASS-21;(5)HASD;(6)PROMIS;(7)OTHERS。由于一些測量工具只在個別研究文獻中使用,本研究把它們合并為一類。在此基礎上,提出以下假設。
H2:抑郁癥狀測量工具不同,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個體抑郁水平的影響效應存在顯著差異。
3.文化背景。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劃分在跨文化傳播中被廣泛關注和運用。一般認為,歐洲和北美社會是典型的個人主義文化,亞洲、非洲和南美社會是典型的集體主義文化。[28]個人主義文化下,強調個人自治、自我實現和個人獨特性;集體主義文化下,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29],個體的行為常常受到他人思想、言論、行動的影響。[30]
社交媒體使用強度與抑郁的關系可能受到文化背景差異的影響。在集體主義文化下,個體更注重使用社交媒體與他人建立關系,從而獲得更多社會和情感支持,減少抑郁情緒。個人主義文化下,個體更注重在社交媒體上表達自我觀點,塑造個人形象,盡管能提升主觀幸福感,但容易忽視他人意見和形成良好關系的重要性,獲得較少社會支持和較弱歸屬感,更容易產生抑郁情緒。在此基礎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3:文化背景不同,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個體抑郁水平的影響效應存在顯著差異。
4.社交媒體平臺。不同社交媒體對社交媒體使用強度與抑郁水平關系可能產生重要影響。有研究表明,社交媒體的滲透力和影響力越強,用戶使用的時間越長[27],因此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可能以平臺的滲透力和影響力為中介,對抑郁水平產生影響。此外,有研究發現社交媒體的特性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素。與其他媒體相比,Facebook、Instagram、微信更頻繁地推送其他用戶的信息,更鼓勵用戶進行積極自我呈現,這容易導致個體在社交媒體社會比較中產生“自己過得不如別人好”的情緒多元無知,從而增加抑郁情緒。[31]
本研究中,通過對文獻進行編碼統計,將社交媒體分為以下幾類:(1)QQ;(2)微信;(3)Facebook;(4)Instagram;(5)國內其他社交媒體;(6)國外其他社交媒體。由于其他社交媒體,如Titter、Snapchat、微博只出現在個別文獻中,因此按照國別分為國內其他社交媒體(包括微博、QQ 空間)和國外其他社交媒體(包括Twitter、Snapchat 等)。在此基礎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4:社交媒體不同,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個體抑郁水平的影響效應存在顯著差異。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檢索和獲取
本研究遵循PRIMA(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報告規范的要求[32],篩選文獻時經過了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步:檢索文獻。使用主題檢索,對中英文電子數據庫中的相關文獻(2008-2020)進行檢索。外文數據庫主要檢索PsycINFO,Ebsco,Scopus,Web of Science,中文數據庫主要檢索CNKI 中的期刊論文數據庫、碩博論文數據和重要會議論文數據庫。運用布爾運算進行檢索:外文數據庫檢索為:(“Social NetworkingSite*”OR“SNS”OR“Social-Media*”OR“Facebook*”OR“Twitter*”OR“Instagram*”OR“Snapchat*”OR“Youtube*”OR“Wechat*”OR“QQ*”OR“Microblog*”)AND(“Depression”OR“DepressiveSymptoms”OR“DepressiveSyndromes”)AND(“Intensity”OR“Frequency”OR“Friends number”OR“Involvement”)。中文數據庫檢索為(“在線”OR“網絡”OR“社交媒體”OR“社會化媒體”OR“社交網絡”OR“社交網站”OR“微博”OR“微信”OR“QQ”)AND(“抑郁”OR“壓抑”)AND(“使用強度”OR“好友數量”OR“依賴程度”OR“卷入程度”OR“情感投入”)。共獲得1245 篇文獻,其中英文1 108 篇,中文108 篇,文獻回溯獲得29 篇英文文獻。
第二步:篩選文獻。在已發現文獻基礎上,通過標題和摘要等信息,篩選出符合要求的文獻。篩選標準:(1)文獻必須實際測量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及抑郁水平;(2)文獻分析了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和抑郁水平的關系;(3)重復發表的只選其一;(4)學位或會議論文在期刊上發表的,取期刊論文。獲得168 篇文獻,其中英文137 篇,中文31篇。
第三步:對文獻進行資格審查。審查文獻全文內容以判斷其是否符合元分析要求。審查標準包括:(1)文獻報告了社交媒體使用強度與抑郁關系的具體數據(如相關系數、回歸系數、平均數、標準差、樣本量或F、t 和χ2值);(2)報告量表信度系數。獲得73 篇文獻,其中英文55 篇,中文18 篇。
第四步:研究納入。在文獻編碼和使用過程中,發現3 篇明顯存在質量問題。經過檢索、篩選、資格審查、研究納入四個步驟,最后獲得符合元分析要求的文獻70 篇,其中英文55 篇,中文15篇,獨立樣本量57 313 人。
(二)文獻編碼
對納入元分析的文獻進行編碼,包括論文信息(作者與發表年份)、被試類型、被試數量、測量工具、文化背景、社交媒體名稱、自變量和因變量測量信度效果量α 值、計算效果量的相關數據;編碼時遵守以下準則:(1)一個獨立樣本產生一個效應值,如果同一篇論文有多個獨立樣本,則貢獻多個效應值;(2)除了綜合社交媒體使用強度,一些研究還區分了使用強度具體維度,包括社交媒體好友數量、社交媒體使用頻率、社交媒體使用時間、社交媒體卷入程度(即融入日常生活的程度、依賴程度、情感投入程度)。若某研究對使用強度類型做了區分,則分別對使用強度的分維度對抑郁影響的效果量進行編碼,再取其均值作為總的效果量;如果研究直接給出使用強度對抑郁水平影響效果量,則將其作為綜合使用強度的效果量。以上兩種情形均記錄不同社交媒體影響下的效果量;(3)部分研究測量不同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個體抑郁水平影響結果。若某研究對不同社交媒體進行區分或交代,則分別對不同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個體抑郁影響的效果量進行編碼,再取均值作為綜合使用強度對個體抑郁影響的效果量。
兩位編碼員在接受培訓后分別進行編碼,隨后由論文作者核對編碼結果,并對不一致的情況進行分析、討論、修改,最后每個編碼類目的一致性為93%。表1 為納入元分析的70 篇文獻的基本信息特征。

表1 納入元分析文獻的基本信息特征

注:1.本表僅列出第一作者姓氏;2.測量工具中,CES-D 表示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抑郁量表,BDI-II 表示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PHQ-9 表示9 項病人健康問卷,DASS-21 表示抑郁焦慮壓力量表,HADS 表示醫院焦慮與抑郁量表,PROMIS 表示成人患者報告結果測量信息系統,OTHER 表示其他測量量表;國內其他社交媒體指除了微信、QQ 之外在中國的社交媒體;3.國外其他社交媒體指除了Facebook、Instagram 之外在國外的社交媒體。
(三)數據統計分析
以相關系數r 值為統一效果值,并將數據錄入CMA 軟件(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中運行,對結果進行分析。如果一些研究沒有報告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和抑郁關系的相關系數,而是報告了均值、t 值、p 值,將直接在CMA 軟件中將其轉化為r 值;如果僅報告了回歸系數β,則利用Peterson 等人提供的公式r=β+0.05λ(β≥0,λ=1;β<0,λ=0),先將回歸系數轉換為相關系數,再錄入CMA 進行分析。根據上述流程,在4 篇文獻分別貢獻2 個效果量的情況下,本研究共獲得74 個效果量。在利用CMA 軟件對效果量進行綜合計算時,先將每個EScr轉換成Fisher Z 值,再將Fisher Z 值的加權平均數轉換為r 值,獲得總效果量。
四、結果分析
(一)異質性檢驗
元分析前需要對多個研究的結果進行異質性檢驗,以便根據異質性結果選擇適當的效應模型。當各研究效果量有明顯異質性,即研究結果的差異過大,超出抽樣誤差所能解釋的范圍,合并效果量時優先選擇隨機效應模型,反之選擇固定效應模型。[33]本研究中,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及其分維度與抑郁水平關系的異質性檢驗結果見表2。
從表2 中可發現,社交媒體使用強度與抑郁關系的異質性檢驗結果為Qw=1148.773(p<0.001),表明研究間存在明顯的異質性,各個研究效應量間的差異來源除了由抽樣誤差引起之外,還存在其他來源,可進一步探討異質性的來源。I2=93.65>75,說明效果量間有93.65%的變異是真實存在的;τ2=0.02,表明真實效應值的方差為2%,即有2%可用于計算權重。綜上,在對社交媒體使用強度與抑郁關系進行主效應分析時,隨機效應模型為最佳選擇。

表2 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及其各維度對抑郁影響和對應的效果量異質性檢驗結果
(二)主效應檢驗結果
通過主效應分析可首先解決以下問題:社交媒體使用強度是否會提升人的抑郁水平,對抑郁水平的影響效果量有多大?通過表2 可知:社交媒體綜合使用強度和社交媒體使用時間對抑郁水平有顯著正向影響,但效果量微弱(效果量依次為r=0.087,p<0.001;r=0.105,p<0.001);社交媒體卷入程度對抑郁水平有顯著正向影響,且效果量中等(r=0.244,p<0.02);社交媒體使用頻率和好友數量對抑郁水平沒有顯著影響(效果量依次為r=0.068,p>0.05;r=-0.076,p>0.05)。
(三)調節效應檢測結果
本研究考察了被試類型、抑郁水平測量工具、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社交媒體對社交媒體使用強度與抑郁關系的調節作用,結果見表3。表3 結果表明以下幾點。

表3 研究特征對社交媒體使用強度與抑郁關系的影響
(1)不同被試類型間,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抑郁水平的影響效果量沒有顯著差異(Qb(2)=2.492,p>0.05),表明被試類型對綜合效果量不存在調節效應,假設1 不成立。
(2)不同測量工具間,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抑郁水平的影響效果量存在顯著差異(Qb(6)=55.953,p<0.001),表明測量工具對綜合效果量存在調節效應,假設2 成立。使用HADS 測量工具時,有中等程度的顯著正向影響效果量(r=0.237,p<0.001);使用BDI-II、CES-D、PROMIS 以及其他測量工具時,有微弱水平的顯著正向影響效果量(效果量依次為r=0.071,p<0.01;r=0.068,p<0.01;r=0.048,p<0.001;r=0.124,p<0.001);使用DASS-21 和PHQ-9 時,沒有顯著影響(效果量依次為r=0.091,p>0.05;r=0.0141,p>0.05)。
(3)不同文化背景間,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抑郁水平的影響效果量不存在顯著差異(Qb(1)=0.412,p>0.05),表明文化背景對綜合效果量不存在調節效應,假設3 不成立。
(4)不同社交媒體間,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抑郁水平的影響效果量存在顯著差異(Qb(5)=31.016,p<0.001),表明社交媒體平臺對綜合效果量存在調節效應,假設4 成立。在微信上,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抑郁水平存在中等程度的顯著正向影響(r=0.468,p<0.001);在Facebook、Instagaram 上,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抑郁水平存在微弱的顯著正向影響(效果量依次為r=0.099,p<0.001;r=0.089,p<0.001);在QQ、國外其他社交媒體平臺和國內其他社交媒體平臺上,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抑郁水平不存在顯著影響(效果量依次為r=0.132,p>0.05;r=0.101,p>0.05;r=-0.008,p>0.1)。
(四)發表偏倚檢驗
元分析納入的文獻通常不是這個研究的所有文獻,因為小樣本和結果不顯著的文獻不易發表,被納入元分析中的可能性小,容易造成納入缺失,從而導致元分析結果或結論偏離真實值,即出現發表偏倚。任何一項元分析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發表偏倚的影響,因此對其進行檢驗尤為重要。[33]本研究采用以下方法檢驗發表偏倚。
一是漏斗圖(funnel plot)。漏斗圖以合成效果量為中心,若各研究效果量呈對稱分布,說明發表偏見對元分析結果影響小[32]。如圖1 所示,各研究效果量以合成效果量為中心線,基本呈對稱分布,表明發表偏倚對研究結果影響小。

圖1 發表偏見分析漏斗圖結果
二是Kendall 的τ 系數。τ 系數用于評估標準化效果量與方差之間的相關性。若兩者相關不顯著,表明發表偏見對結果影響小。[34]本研究τ 系數為0.056,p=0.487,發表偏倚對結果影響小。
三是失安全系數(Fail-safe N)。當元分析結果顯著時,計算需要納入多少丟失的、未發表的研究才能讓合成效果值不顯著,即為失安全系數。一般認為,未發表研究數量保守估計為5k+10,其中k 為檢索得到的研究數量。失安全系數越大于保守估計數,發表偏倚越小。本研究中失安全系數為5 725,大于保守估計數量360(5*70+10=360),說明發表偏倚較小。
通過以上三種方法檢驗,說明本研究結果具有較好穩定性,受發表偏見影響小,結論較為可靠。
五、討論
(一)社交媒體使用強度與抑郁的關系
總的來說,社交媒體使用強度會顯著且微弱地提升人的抑郁水平,這與自我概念分化假說和社會比較理論一致,即使用社交媒體容易導致個體的自我概念清晰度較低,或者在上行社會比較中產生負面自我評價,提升抑郁水平。
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及其各維度與抑郁關系的分析中發現:社交媒體的使用時間和卷入程度對抑郁水平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社交媒體使用頻率、好友數量與抑郁水平沒有顯著相關,一些研究甚至發現好友數量與抑郁水平呈負相關關系。這支持了社會資本理論提出的假設,即個體在社交媒體上結識的好友能夠提供社會資本和情感支持,緩解抑郁情緒。這種此消彼長的情況有助于解釋為何社交媒體使用強度整體上對個體抑郁水平影響效果量較弱。
(二)社交媒體使用強度與抑郁關系的調節效應
測量工具和社交媒體平臺是社交媒體使用強度與抑郁關系的調節變量,但在被試類型和文化背景上,沒有發現調節效應。
首先,抑郁水平測量工具對兩者關系存在調節效應。元分析結果發現,使用HADS、BDI-II、CES-D、PROMIS 以及其他測量工具時,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抑郁有中等或微弱水平的顯著正向影響;但在使用DASS-21 和PHQ-9 時,沒有顯著影響。該結果表明,DASS-21 和PHQ-9 的測量結果與其他量表測量結果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可能的原因是,DASS-21 包括3 個分量表,分別測試抑郁、焦慮、壓力水平。這3 個分量表并不獨立區分,而是相互混合交叉。量表內的陳述時而測量壓力、焦慮水平,時而測量抑郁水平,如此循環往復,直到21 個陳述全部完成,這可能影響測量結果。只測量抑郁水平可能是一種比較可靠且穩定的測量方式。此外,相比起其他量表,PHQ-9僅有9 個陳述,數量較少,且均是根據自己的感覺進行選擇和評分,可能存在漏診和誤診。
其次,社交媒體平臺對兩者關系存在調節效應。元分析結果發現,在Facebook、Instagram、微信上,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抑郁水平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在QQ 和國外其他社交媒體平臺上,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抑郁水平存在顯著正向影響(邊緣性顯著水平);在國內其他社交媒體平臺上,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抑郁水平不存在顯著影響。該結果表明,國內其他社交媒體和其他媒體的效果量存在較大差異。據《中國社交媒體影響報告》顯示,中國人每天使用時間最長的社交媒體依次為微信、QQ、微博。人們每天停留在微信和QQ 上的時間超過總聯網時間的61%。①中國社交媒體影響報告.http://www.199it.com/archives/801830.html.中國人使用除微信、QQ 之外的其他社交媒體較少,使用強度較弱,可能導致在國內其他社交媒體上,使用強度與抑郁水平之間關系不顯著。此外,在研究國內其他社交媒體使用強度與抑郁關系的論文中,研究者常引入友誼、上行社會比較、反芻思維、嫉妒、性別等中介因素,導致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和抑郁之間呈現負相關或相關性不顯著,這可能是導致在國內社交媒體上觀察到的影響效應與其他媒體不同的重要原因。
再者,被試類型對兩者關系沒有調節效應。元分析結果發現,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成人、大學生和青少年三類人的抑郁水平均具有顯著提升效果;在青少年上觀察到的影響效應略高于大學生和成人,可能是和青少年這個群體的特殊性有關。對于青少年來說,其正處于建立自我認同的階段,尚未形成穩定的個人和社會身份意識。社交媒體一方面可以為他們提供構建不同角色與多元身份的機會。但另一方面,在社會比較的壓力下,比起大學生和成年人,這種探索和嘗試更可能導致自我概念模糊。[10]由于自我概念清晰性是影響抑郁水平的決定性因素。[35]因此,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進行多元身份嘗試和建構時,其自我概念清晰性更容易降低,抑郁水平更容易提高,這可能是導致在青少年群體上觀察到的影響效應大于大學生和成年人的重要原因。
最后,文化背景對兩者關系不存在調節效應。元分析結果發現,無論是個人主義文化還是集體主義文化,社交媒體使用強度對抑郁水平都存在顯著提升影響(效果量依次為r=0.093,p<0.05;r=0.067,p<0.05),這可能和兩種文化背景的缺點有關。一方面,個人主義促進自我價值的追求,但以社會孤立為代價。[36]當個體過分關注如何利用社交媒體表達觀點、塑造形象時,容易忽視他人的意見和建立良好社交關系的重要性,因而獲得較少社會支持,容易引發抑郁情緒。另一方面,集體主義雖然能為個體提供社會支持和歸屬感,但卻以抑制負面情緒的表達為代價。[37]為了與他人(尤其是強關系)建立良好的線上關系,個體在使用社交媒體時總是避免直接公開地表達個人負面情感,這種情緒的壓抑容易導致抑郁水平的提高。[38]不過,社交媒體的匿名性讓個體在弱關系社交中也能釋放宣泄情緒,緩解壓抑情感所帶來的抑郁情緒。[39]這種此消彼長的情況也許能解釋為何在集體主義背景下觀察到的效果量略低于個人主義背景下。
(三)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存在若干不足,有待未來的研究進一步完善:(1)元分析對文獻查全率要求較高,但是受到語言、工具等限制,本研究的文獻不包括中英文以外其它語言所撰寫的研究成果,中英文文獻中也極有可能遺漏了一些未出版或尚在投稿中的研究,以及不公開的學位論文;(2)研究僅考察了被試類型、抑郁水平測量工具、文化背景、社交媒體平臺的調節作用,但并不完善,如性別、社交媒體使用強度的測量工具、研究設計類型等,都可能是調節變量,后續研究可作進一步研究;(3)本研究中不少獨立樣本的效應值通過平均化處理方式獲得,可能影響信息準確。要想提高信息的準確性,后續實證研究有必要同時報告變量間總體及維度的相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