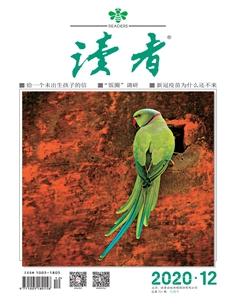柏林愛樂的孤獨夜晚
李斐然

沒有觀眾的柏林愛樂演出現場
音樂還在
柏林的每個夜晚,音樂都在。它有時候出現在教堂,有時候出現在街頭,但最好的音樂從晚上8點開始,它出現在柏林愛樂音樂廳。這是每天晚上音樂會的開場時間,也是一天當中最熱鬧的時段。整個大廳回蕩著提示廣播,工作人員急匆匆地幫遲來的觀眾找座位,走在樓梯上都會有人提醒:“快點,音樂會就要開始了!”
一切從2020年3月12日開始變得不太一樣。這是柏林愛樂暫停公開演出的第一天,那天晚上的主角是英國指揮家西蒙·拉特,他是柏林愛樂前任首席指揮,與樂團有16年的合作經驗。他也是最受歡迎的世界級指揮大師之一,舉辦由他指揮的音樂會的晚上,音樂廳外面總是堵車。
但那一天,音樂廳外面的路上空蕩蕩的。上午排練到一半,樂團經理來通知,今晚沒有觀眾來了。怎么辦?
在柏林愛樂138年的歷史上,有過不止一次這樣的特別夜晚。這個世界頂級交響樂團用音樂陪伴人們度過了一天又一天,它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冷戰時期柏林墻的修建與倒下、經濟危機。不管發生什么,柏林愛樂的音樂會是不會停辦的。納粹統治期間,樂團的首席指揮是富特文格勒,老音樂廳在一場空襲中被炸毀,指揮家就帶著樂團去柏林歌劇院演出;不久后,歌劇院也被炸為廢墟,他們就繼續換地方演出。有時候音樂會會被空襲警報打斷,觀眾甚至習慣了按序疏散,等到警報結束再回到大廳,聽樂團把剩下的曲子演奏完。戰爭結束后,柏林愛樂在廢墟中舉辦了戰后的第一場音樂會。
“二戰”結束之后,一個記者在德國街頭采訪,他拉著來往的人問:“每天經歷轟炸和死亡,你是如何熬過戰爭,熬到明天的?”其中有一個人想了想,回答他:“因為明天還有富特文格勒的音樂會。”
柏林愛樂必須演出,音樂必須在,這一點無須討論。觀眾來不了,他們就想辦法把音樂送過去。于是,在取消公眾聚集現場音樂會的通知發出后,他們很快發了另一條通知:“柏林愛樂大廳將關閉至4月19日。但是,西蒙·拉特爵士及柏林愛樂的音樂家們決定,在沒有觀眾的情況下,也要繼續完成本場音樂會原定曲目盧奇亞諾·貝利奧《交響曲》和貝拉·巴托克《樂隊協奏曲》的演奏,并免費向全世界直播。”
面對空無一人的觀眾席,晚上8點,音樂會開始,西蒙·拉特站上了指揮臺,他和樂團成員們互相看了看,笑了起來。在這個夜晚,西蒙·拉特和柏林愛樂想要向世界傳遞一個信號——音樂還在。
音樂的答案
今晚的音樂主角是兩個活在困境里的人,和他們對命運的回答。他們所講述的是音樂的一個經典命題——在殘酷的命運里,在熬不下去的時候,人為什么活下來?
第一部作品是意大利作曲家貝利奧的《交響曲》,這是一部創作于20世紀60年代的作品——那是一個充滿變化的時代,也潛藏著變數,“當你順著音樂走到終點,會發現,自己回到了最初出發的地方,但已經在不知不覺間,變成了另一個人”。
另一部作品是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創作于1943年的《樂隊協奏曲》,它是一個孤獨的病人對命運的解讀。“二戰”中,巴托克公開反對法西斯:“我看到你們如何對待猶太作曲家,從今天開始,我要求你們也這樣對待我,雖然我并不是猶太人。”為此他不得不離開家鄉,移居紐約,但是他幾乎不會說英語,也和紐約的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在紐約,他不算一個客人,但那里不是他的家,他也沒有能夠回去的地方。每天被困在自己的房間里,疾病、孤獨和異鄉感一起襲向他,他總是發燒,幾乎無法作曲,沮喪地判定自己的職業生涯走到了盡頭。他被生活困住了。
1943年春天,巴托克的一位小提琴家朋友寫信給當時波士頓交響樂團的指揮謝爾蓋·庫賽維茨基,請求他的幫助——巴托克需要藥,但他更需要音樂,“音樂也是一種治療”。
庫賽維茨基為這位作曲家到美國軍隊求情,希望能給他使用青霉素。那時候青霉素在美國只有軍隊有權支配,是僅次于核計劃的頂級項目。一個月后,指揮家來到巴托克的病床前,給他帶去了青霉素,還有一份交響樂約稿,他希望巴托克創作《樂隊協奏曲》。這給了巴托克極大的希望,音樂成為他的動力,雖然身體依然虛弱,但他在精神上得到了極大舒緩。這一年的夏天,他用了55天時間,一氣呵成地寫完了全部5個樂章。巴托克是全世界第一個使用青霉素的平民,他因此熬過了那個垂死的1943年,有機會看了自己代表作的首演,聽到現場觀眾的喝彩,也獲得了額外的時間,為妻子的生日偷偷寫了一首曲子,藏在曲譜的后面。顯然,這是一次有效的治療,治愈他的有時候是青霉素,有時候是《樂隊協奏曲》。
這位被困在命運難題里的作曲家,把他所有的情感都寫在《樂隊協奏曲》中,這成為他最知名的代表作——它包含著令人窒息的黑暗,時而又跳躍著幽默,在最后的章節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樂觀和明亮。

西蒙·拉特
對西蒙·拉特來說,演奏巴托克的作品像是一場從黑暗駛向光明的旅行,但他常常覺得樂譜最后十幾個小節實在是太明亮了,在經歷了之前的種種黑暗、挫折、迷茫、困頓后,迎接我們的出口是什么?光明的終點之后,那是什么?
在柏林最孤獨的夜晚,這個答案逐漸清晰起來。這個晚上,在場所有的音樂家似乎感同身受地理解了這份隔絕中的孤獨、未知中的希望,他們在交響樂中又一次實現了靈魂的共鳴。西蒙·拉特說,在音樂最后的十幾個小節,他看到巴托克在音樂中復活,就坐在他們面前,講述他自己的故事。事實上,青霉素并沒有拯救巴托克,他在兩年后的秋天去世了。最后一次住院治療前,他懇求醫生再多給他一天時間,讓他把另一部鋼琴協奏曲寫完。可惜他的時間只夠勉強寫完草稿,在最后一個音符后面,他歪歪扭扭地寫下了“The End(曲終)”。不久后,他的生命也走到了終點。然而,正是藏在樂譜里的這些音符,開啟了屬于巴托克的新音樂時代。終點之后,是另一個起點。
音樂結束之后
最后一個音符不可避免地到來了。音樂的世界有一條真理:任何音樂會都有結束的那一刻。走出音樂廳,帶走的可能是傷感、感動、希望、失落,或是無法平息的激動。即便是在柏林愛樂的數字音樂廳,曲終也是不可避免的告別:“音樂會結束了,謝謝你的觀看。保重!你的柏林愛樂。”
然而,還有另一條音樂真理:等到明天醒來,無論世界將變成什么樣子,柏林愛樂一定還會演出。它可能以不一樣的方式出現,演奏不一樣的曲目,但它一定會出現,在歷史的任何一個夜晚,音樂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