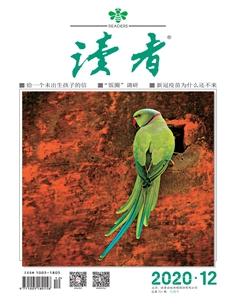成功,在高曠荒原上突然闖入的詞
阿來
5月,內地已是春暖花開,而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上勁吹的暴風中卻夾雜著紛飛的雪片。我同幾個年輕的記者在青藏鐵路沿線采訪,正在昆侖山和唐古拉山之間那片高曠的荒原上。年輕的司機因為缺氧倒下了,我臨時兼任了我們這輛車的司機,載著我們年輕的攝影師,不斷地追逐行駛的火車,讓他拍一些火車在雪山下、曠野中奔馳的美麗鏡頭。我們不斷狂奔,超過火車,跑到前面某個預計可以拍到精彩畫面的地方,靜靜地等待火車從深遠明凈的高原天邊蜿蜒駛來。我坐在駕駛座上,感到發動中的汽車引擎在輕輕震顫,車窗外快門聲和同行記者們興奮的叫聲響成一片。等到火車在視線盡頭順著山勢轉出一個優美的弧線,消失在藍天下面,大家又跳上車,我一轟油門,開始下一輪追逐。這一天,手機間或在沖鋒衣口袋中輕輕顫動,我都沒有理會。直到傍晚,太陽西沉,我們的追逐之旅也到了最后一站——長江西源沱沱河上那數公里長的鐵路橋上。所有人手中的“長槍短炮”都準備好了。橋上的天空中,淡淡的云彩正幻化成緋紅的霞光,橋下那漫長曲折的河流閃爍著金屬般的光芒,仿佛那不是水流,而是一種超現實的意念,映射著非物質的光輝。
大家都坐在高高的河岸上等待這一天的最后一組鏡頭。我也從車上下來,備好相機,坐在河岸邊稀疏的草地上。天地間一片安詳,好像火車這樣的事物在這個世界上從來不存在一樣。我掏出手機,查看未接電話和未讀短信。省青聯秘書處的一條短信就在其間,意思是說,他們正在編輯一本書,把曾經當選過“十杰青年”的人以這樣一種形式聚集在一起,需要每個入選者談談感想,來“感悟成功”。
我必須說,在這樣一個海拔高度上,在這樣一個四顧皆空茫之處,“成功”這樣一個詞從手機屏幕上跳進腦海,真的容易引起一種虛無之感。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自己身處中國西部這樣荒僻而遙遠的地方,就覺得曾經的那些事情一下子離自己非常遙遠了。是的,領獎臺上搖曳變幻的聚光燈,那些掌聲,那些短暫的激情迸發,在這一刻都顯得非常非常遙遠了。于我而言,不知此時的空曠與彼時的喧嘩哪一個對自己的生命來講更為真實。這段時間,每天掏出衛星定位儀,都看到所處的海拔在節節升高。從格爾木出發踏上青藏線的前一天下午,我特意去看了昆侖山下的玉珠峰車站,那里的標高是4100多米。現在,我們節節上升,已經在4700米的高度了。明天,我們還將上到海拔5200米以上的高度。那么,當年的獎杯、鮮花和掌聲,也就是一個人一生中,曾經經過的一個海拔高度吧。省青聯發來的短信里說,那是一種成功,要我今天來感悟這成功。但這時,我的耳邊響起一位歐洲古代哲人的詩句:
名聲看起來是多么美好,但這動聽迷人的聲音,不過是一曲回聲。
這樣的詩句有一點悲觀,有一點虛無。但我想,當我們談論成功的時候,這樣一種態度可能比一味地沉湎更有意義。這樣的看法與態度,可能會使我們在面對所謂成功的時候,更加冷靜與理智。對一個理性的人來說,成功是時代賜予的機遇,機遇總是暫時性的,所以,所謂成功,不過是重新出發時的一個起點,一個在同一行業領域中稍稍早于或略略高于別人的起點。成功不是登山,登上了珠穆朗瑪峰,這個世界便不再有更高的山峰。更何況,也不會有一個登頂者,一直待在最高處。他必須下來,這是自然規律,是天道對人的一種制約。這種制約讓人自省,讓人感到自身力量的同時,也感到自身的局限。自然和歷史的規律不會讓一個幸運的登頂者在世界的絕頂處永遠沉醉于成功的眩暈!
幾天后,我到了云南。我們正沿著一條叫紅河的大河一路向南前進。這是另一片高原,但海拔降低了,也就是1000多米。同行的人換了一批,其中一些人也有輕微的高原反應,因為氧氣減少了。我也有反應,氧氣對我來說太多了,教人在車上總昏昏欲睡。就在這個時候,省青聯再次打來電話,催問稿子的事情,而寫這樣的稿子,就必然要去回味當年的鮮花與掌聲,而此處相對青藏高原已顯得太高的含氧量卻讓我提不起精神。我想,這正好是命運之神賜予的特別隱喻。這個隱喻的本義,正是法國哲人蒙田一篇文章的題目:命運的安排往往與理性不謀而合。
成功者可能走向新的成功,成功者也可能在輝煌一刻后,走入永遠的平凡。這里,就有了兩種危險。一種,成功者頭上套著光環,開始遠離自己的事業,在我們社會這個過于看重成功者的機制中,謀取更多的功名;一種,把短暫的成功當成永遠的幻覺,猶如一個在過多的氧氣中昏昏欲睡的人。其實,不同海拔氧氣的含量早由自然規律做了規定,因為缺氧而眩暈,因為氧氣過多而昏睡,都是人自身的不適應。自然界就用這樣的方式提醒人類,并根據人類的適應程度優勝劣汰。而在人生的道路上,社會的機制也是一個永恒的法則,它制造成功,也制造失敗。在用成功制造成功的同時,也用成功制造出更多的失敗。所以,我想,感悟成功,就是感悟成功之后命運的各種可能走向。

今天,社會對成功者的所謂關注,過于注重成功本身,而不太關注走向成功的途徑,這其實才是全社會應該給予更多關注的一個問題,因為成功的方法與途徑包含了更多的道德與倫理因素。
又想起另一個旅途中的小故事。那一年4月,因為一本新書譯本的出版,我在瑞士待了一段時間。在蘇黎世,我想去積雪尚未消融的阿爾卑斯山看看。我小說的德文譯者阿麗絲堅持要我帶一些巧克力進山,理由有兩個,一個當然是巧克力的高熱量,另一個是,“我們瑞士的巧克力是歐洲最好的,你一定要品嘗品嘗”。一個東西既然是一個地區的標志性產品,此地便免不了四處開著面向外國游客的專門商店。但阿麗絲只是一個勁地往前走,我們是在經過了十多家巧克力店以后,才進了一家百貨公司,乘電梯連上數層才來到幾架巧克力前。還是路邊店里的那些牌子,價格也未見得便宜。但很顯然的是,她感到非常滿意。在樓下喝咖啡的時候,我問她為什么要跑這么遠來買同樣的東西。她臉上現出一本正經的表情,說:“因為這是一家有道德的商店。”不是因為這家的巧克力更好,而是因為這是一家有道德的商店,所以,當地人對這家店表示支持,盡量來這里消費。
我沒有問有道德的表現是哪些,但我知道,他們選擇消費的地方包含了道德的考量。這個問題,比后來置身阿爾卑斯山那些純凈的雪峰中間引發了我更多的感觸與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