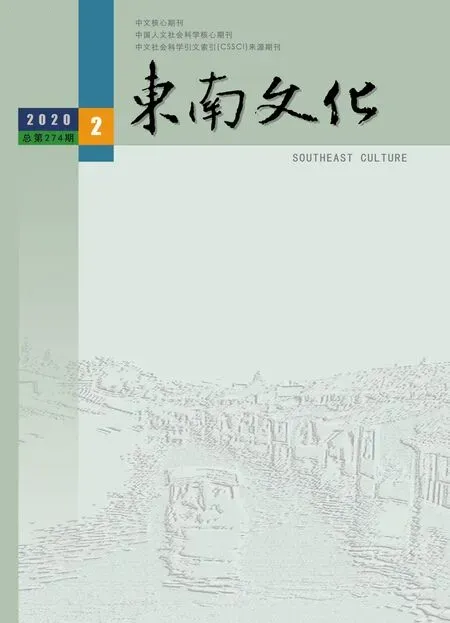博物館化的拓展:原因、進程與后果
嚴建強 毛若寒
(浙江大學考古與文博系 浙江杭州 310028)
內容提要:人類對一些物品產生特殊情感,源于在其中發現了價值與意義,即“博物館性”。確定了博物館性,通過博物館化的行為將其與現實時空分離,“物”轉化為“博物館物”,這就是人類的收藏。隨著人類的認知深化及收藏活動的社會化,人類在越來越多的物中發現越來越多的“博物館性”,博物館物的數量與類型出現持續擴張,這一過程就是“博物館化的拓展”。持續的拓展導致種類繁多的博物館的誕生。隨著物作為意義載體的價值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及機構性收藏成為主流,博物館物被視為一種優質的教育資源并被賦予更高的傳播使命,由此深刻改變了博物館的功能及其與社會的關系,也相應地帶來博物館組織結構,展覽建設的原則、程序與方法等一系列變化。
艾琳·胡珀-格林希爾(Eileen Hooper-Green?hill)在描述博物館的急劇變化及人們面對這些變化所表現的態度時寫道:“在過去幾年里,博物館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和重組。變化是極端和迅速的。對許多熱愛博物館的人來說,這種變化似乎是前所未有的、出乎意料的和不可接受的。它拋棄了以前關于博物館性質的假設。”[1]她認為,令許多業界人士感到震驚的原因是他們對博物館的身份始終抱有一種固定的、一成不變的看法,為此,她指出,“如果認為博物館只有一種形式的現實、只有一種固定的模式,那就大錯特錯了”[2]。
格林希爾指出的部分從業者面對變化所表現出的態度頗具代表性。不過,也應該看到,在博物館發展的歷史中,變化并非近年才出現,而是由來已久和持續的,且變化也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突然、不確定和難以預料,其具有自身的內在邏輯。若對這一變動的歷史做更仔細的梳理,從更深入的層面進行審視,我們可以發現導致博物館持續、深刻和多方位變化的原因,與一種我們稱為“博物館化拓展”的現象有關。正是這一持續不斷的拓展給博物館發展帶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問題,從而導致博物館的社會使命與功能及其內部組織結構、工作程序與方法等一系列變革。博物館文化的發展正是在這種持續的突破和再平衡的交替運動中進行的。鑒于此,探明博物館化拓展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后果,就成為我們了解和適應這些變化并采取積極和明智行動的可靠依據。
一、博物館化與博物館性
“博物館化”是捷克博物館學家斯貝尼克·斯坦斯基(Zbyněk Stránsky)在嘗試構建科學博物館學體系時所提出的概念。作為一名教授博物館學的大學教師,他明顯感受到來自理論思辨橫向比較的壓力。按照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知識理論,作為科學學科的研究對象必須具有穩定與永恒的特質。如果將博物館學的研究對象局限于17世紀之后成長起來的博物館機構,那顯然不符合亞里士多德的定義,也不能被稱為科學學科。博物館化正是他為此所尋找的具有穩定與恒久性的研究對象[3]。在他看來,博物館化是人類對物的一種獨特的認知與態度,其本質是將物從現實時空中抽離出來,使“物”轉變為“博物館物”。這是一種人類普遍存在的行為,在人類形成后即出現,并且不會因機構的消失而終止。為此,斯坦斯基認為博物館學是一門明確且獨立的學科(scien?tific discipline)。其認識在于人類對其現實采取的一種特殊手段,這種特殊手段在客觀層面透過歷史上不同的博物館表現出來,它同時也是記憶的系統表現與局部反映[4]。
博物館化何以發生?其心理學依據如何?由于收藏的對象是物,所以,我們首先要了解“物”及人類對物的態度。
人類生存方式的最大特點是借助“物”而達成目的。為此,人們在行事之前首先要制造物作為工具與用器。格林希爾的同事蘇珊·皮爾斯(Su?san Pearce)在談及物時做了語義學分析,從三個角度進行考察:第一,物件可以被當作物質器物(material artefact),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視角;第二,物件可以被當作符號(signs)和象征(sym?bols),創造分類和傳輸可讀信息;第三,物件可以根據含義(meaning)來研究[5]。從物所承載信息的角度來看則有兩種不同的類型。一類器物基于實用功能的目的而制作,人們在制作時并沒有傳播學的思考,物是純粹的實用器。然而,在物的使用過程中會發生一些有意義的故事,物就像海綿一樣吸納不斷增加的相關信息:成為某一事件曾經發生的證物,抑或成為某種已逝情感的寄托。在這種場合下,它們在不經意間成為意義的載體。另有一類物,人們在制造時已帶有某種傳播學的訴求,比如一些物品上有符號或圖像,其意義正是物品制造者想要傳達的信息;又如某些意義的表達是通過材料、形狀、色彩,或刻畫于其上的紋飾。如果說前一種物所傳遞的是無意信息,那么后一種物所傳遞的則是有意信息。無論哪種類型,它們都具有超越物質功能的精神內涵,這就是它們作為研究對象的依據。
物的這種特征使它在提供實用功能之外可對人的情感發生作用,從而改變人們對它的態度。當人們與物產生情感關聯后,物的功能就被改變,被賦予精神或文化的價值。我們可以將這種對物的喜愛并渴望擁有和珍藏的情感稱為“博物館情感”(museum emotion)。換言之,導致博物館情感的原因是人們在物中發現了對自己而言的特殊“價值”和“意義”。斯坦斯基將這種意義與價值稱為“博物館性”(museality)。正是這種情感和價值判斷導致了人類的獨特行為:將物從它所處的時間與空間中分離出來并妥善保護。這一將物與其現實時空分離的過程就是“博物館化”(musealization)。通過博物館化,“物”(object)轉化為“博物館物”(museum object)。
博物館性是理解收藏文化與博物館文化的關鍵概念。正如弗德利希·瓦達荷西(Friedrich Waidacher)在《博物館學——德語系世界的觀點》中所指出的,博物館學的研究對象不是博物館或博物館的收藏,而是博物館性[6]。在人類收藏史上,收藏品的內涵與外延經歷了持續的拓展與擴張,其關鍵原因就是博物館性的開放性和泛化。也就是說,從歷史上看,人類對物是否具有博物館性的判斷變得越來越敏感和寬容。這種敏感性與寬容性導致收藏動機的不斷強化。之前被認為普通的物品,由于敏感性的增加,人們便發現其中蘊含的意義和價值,收藏的動機也隨之產生。由此,越來越多的物轉化為博物館物,人類的收藏無論從數量還是類型,都出現極大的增長。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人類文明演進中的精神性成長。就如我們從孩提時代走向成熟,對事物的認知越來越由表面向內部深化。隨著這種精神性成長,人類的認知能力不斷增強,收藏意識更趨成熟,更善于從物中發現豐富的精神內涵,從而使博物館情感變得熾熱。另一個原因則是收藏的社會化。早期的收藏多為個人或家族行為,收藏目標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收藏與保護能力也頗為有限。宗教團體的收藏雖具有社會屬性,但很少超出宗教的范疇。近代社會形成后,伴隨著收藏主體擴展到學術團體、學校、企業、基金會及政府,收藏成為一種組織化和制度化的行為。不僅收藏視野極大擴張,保存能力也大大增強。這類收藏行為帶有明確的保存社會記憶的目的,并負有向公眾傳播的使命。因此,對博物館性的判斷,不是從個人的情感而主要從社會的需求出發。從某種意義而言,個人的博物館情感(museum emotion)逐漸被社會的博物館意識(museum consciousness)取代。
二、博物館化的拓展
隨著收藏品進入交換領域,藏品變成一種特殊商品,既能滿足收藏者的精神需求,也具有保值與增值的經濟價值。人們通常將這些來自古代的收藏品稱為“古董”。古董在漢語中多指古人所遺之精華。“古”是指已經成為過去的東西;“董”則有經典之意。古董進入流通領域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首先,必須是可移動的,否則無法在市場中交易;其次,“物件”必須具有三維空間的物質屬性,而非抽象和無形的。
人類收藏史的演進以此為原點,伴隨著近代社會的興起而逐步展開。這一進程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但其中最具實質性的仍體現在博物館化的拓展上,這一拓展經歷了從經典到日常、從可移動向不可移動、從物質到非物質及從過往到現生的突破。每一次突破都帶來了新的增量和類型。
第一是從經典到日常的博物館化拓展。早期的精品型收藏主要關注美麗珍貴的事物,相應地產生了精品定位的藝術類博物館。這類物品通常是各時代人類文明的代表性杰作,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因而受到經久不息的追捧[7]。在這類博物館中,人們主要出于審美和欣賞的目的觀看實物展品。在展品體系上,其屬于單一實物展品要素體系,展覽的質量判斷主要依據物件觀賞環境的營造,包括清晰性、珍貴性、舒適性等,其建設的運作相對簡單。
隨著區域社會的形成,之前具有從屬性的人際關系開始被一種以地緣為基礎的社區關系取代,人群與特定地域形成了親密和穩固的關系。人們開始建立地方歷史學會、撰寫志書,希望通過整理文獻和收集文物來探明本地的歷史進程和文化特征[8]。這類收藏更關注物品作為記憶載體的身份和價值,它們不一定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但能夠有效證明本地曾發生的事件和現象。它們包括日常的生產與生活用品、各種貿易和職業生活中的契約和文件,以及各種反映信仰的物品。這些物品都與這片土地聯系密切,早期收藏中“英雄不問來路”的泛地域特征不復存在,物品的“在地性”成為收藏的必要前提。更重要的是,這類博物館負有明確的傳播使命,有責任向觀眾講述這片土地與人們的故事,為他們梳理歷史的脈絡并增強社區的文化認同。與此目標相關的博物館有多種不盡相同的類型,包括地方博物館、方志博物館、考古博物館,以及以本地有關人物與事件為主題的紀念館等。此外,為自然科學研究而進行的收藏,為發展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而征集的各類物品等,都體現出去精英化的色彩。對收藏對象的博物館性判斷,也越來越強調其作為日常生活/現象記憶載體的價值,同時也強化了從審美與欣賞向學習與理解轉變的傾向。
第二是從可移動遺產到不可移動遺產的博物館化拓展,這與工業革命及近代社會的形成有關。隨著建筑材料從石木等自然材料向鋼筋混凝土與玻璃的人工材料轉變,人類的居住條件變得更便利與舒適,由此引發了大規模的舊城改造。最突出的案例是法國波拿巴三世(NapoléonⅢ)對巴黎城的改造。在這種大拆大建的浪潮中,許多人們熟稔的景物迅速消失,居民變成熟悉城市里的陌生人。這種現象引起了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警惕,在他的呼吁下,法國政府于1840年頒布了世界第一部歷史建筑保護法案,開啟了將不可移動文化遺產納入保護的先河。此后,越來越多的不可移動遺產進入保護清單,我們可稱之為“不可移動文化遺產的博物館化”,其過程通過相應的法律文件來實現。在日益明確不可移動遺產重要性的背景下,人們也開始意識到孤立存在的建筑和構筑在失去語境后實現其價值的困難,遂逐漸擴大保護范圍,出現了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的拓展。這種不可移動遺產的博物館化不僅表現在人文歷史方面,在自然方面也有大量的遺跡和保護區被要求盡可能以保持原狀的方式進行保護。
在這一種拓展浪潮中,被卷入博物館化的物品帶來了新的博物館類型,除了故居、事件現場紀念館、考古遺址博物館、自然遺跡博物館之外,另有兩種影響頗大的博物館:露天博物館與生態博物館。前者是一種將各地孤立落單的歷史建筑易地重組,再用展演的方式再現歷史生活,屬于非原生態、非原生活的博物館類型;后者則是完整地保持原有的建筑及格局,讓原居民按照傳統的方式生產與生活,既保留了建筑的原生態,也保留了居民原先的生存方式,屬于原生態、原生活的類型。
第三是從物質遺產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博物館化拓展。這個突破始于20世紀50年代。1950年日本《文化財保護法》率先提出“無形文化財”的概念,包括普通的無形文化財(戲劇、音樂、工藝技術)和無形民俗文化財(衣食住行、生產、生活、信仰、節日、風俗習慣和民俗藝能等)。這一做法得到了韓國和中國的積極響應,韓國的“人間國寶”(living human treasure)和中國的“傳承人制度”相繼問世。在美洲和歐洲,對無形文化遺產的保護也進行得如火如荼。這一突破意味著博物館化突破了物質的藩籬進入新階段,但同時也帶來新問題。可移動遺產和不可移動遺產都具有三維空間的物質屬性,博物館化將物與其現實時空的分離可通過收藏和立法的行為來體現,但對于無形文化遺產來說無疑是一個難點。既然是無形的,就不可能通過簡單的分離動作來實現。無形文化遺產本質上是以人的文化行為為載體的過程性現象,當人的行為停止了,這一可觀察的現象也就消失了。所以,對于這種現象的感知,既不可以超越空間,也不可以超越時間,必須滿足“在地的”和“即時的”條件。如果不是身處現場,那就必須通過記錄與播放設施。基于這一特點,對無形文化遺產的博物館化,就需要通過現場展演或裝置對原發過程進行記錄與播放。對于這類以過程性現象為特點的遺產收藏,通常要借助于錄—播裝置,所收藏的實際上是一種“現象—裝置”的結合體。
第四是從過往向現生的博物館化拓展。在人文歷史博物館領域,長久以來人們都奉行物“以古為貴”“以稀為貴”的理念。不過在今天,各種反映行業現狀和當代社會生活、文化生活的物品等也開始受到人們的關注。至于自然博物館領域,其在興起時就表現出對現生世界的關注,所收藏的去生命化的動植物標本反映的都是現實生活中的事物。到現在,自然博物館的博物館化拓展出現了新現象,表現為不再局限于標本孤體,而將標本視為一個系統,比如在征集鳥類標本時,人們也收集它們的巢,并錄下其鳴聲;又如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活體展品等。
在過往向現生的拓展中,另有一種現象值得關注,那就是現實生活中業已出現的“社會生活博物館化”的趨勢。這種博物館化的過程并不是前文所述的一個具體行為,而主要表現為一種觀念。比如,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建立了參觀廊道,當一位對現代金融生活不甚了解的人在廊道觀察正在交易的人們時,這些交易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博物館物”,他們的行為變成為人們理解當代金融活動的展品和教科書。這種博物館化并不伴隨著相應的行為和動作,僅通過觀念實施,我們可將此理解成博物館化的一種隱喻方式。
通過上述四個環節的突破,博物館物在全球范圍出現了幾何級數的增長,類型也極為復雜和多樣化。從內容上看,我們將這些物品分成“自然”與“人文”兩大部類。這兩大部類又都包含“過往”和“現生”兩大部分。從存在形式看,它們有“可移動的”“不可移動的”和“無形的”三種類型。將這三個要素進行組合,就形成博物館物的清單(表一)。
以上是幾個世紀以來博物館化拓展的成果。我們今天在博物館領域所遇到的各種變化在很大程度上都與這一拓展有關。
三、博物館化拓展的后果
現在,讓我們回到格林希爾所談到的現象。博物館持續的(有時是急劇和迅速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與博物館化的拓展有關。這一拓展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博物館物的增長導致了博物館類型的豐富化,新興博物館履行傳播使命又為博物館的組織機構提出了新要求,同時,大量以學習與理解為宗旨的博物館的出現又為展覽建設帶來新挑戰。
(一)引發博物館家族的急劇擴張,呈現出類型多樣的博物館世界
博物館化拓展帶來的最明顯后果是博物館家族的急劇擴張:上述每一類博物館物都形成了相應的博物館,并形成以下博物館類型清單(表二)。
需要指出的是,此處所列舉的博物館類型是依據藏品的學科屬性而分類,是一種被理論概括的純粹形式。在現實中,博物館除了依藏品學科屬性外,還有按管轄機構的級別、按藏品所有及經營的主體,以及按主要服務對象等分類。另一些博物館呈現出多學科混雜的綜合樣式。例如,地方博物館通常就包含各種藏品類型的綜合內涵,既有人文的、也有自然的,既有過往的、也有現生的,既有物質文化的、也有非物質文化的;而在另一些情形下,一家專題博物館可能只涉及某一學科領域內很小的、很專門的一部分。這種復雜的組合和細分使得現實世界的博物館五花八門、多樣紛呈。

表二// 在博物館化拓展中衍生的博物館家族
(二)導致博物館定義處于持續和長久的爭論中
在早期博物館類型相對單一的情形下,博物館定義容易包含各種類別。博物館類型劇增后,要確定一個能被廣泛認可的定義變得困難。從管理角度而言,定義在實際操作中具有準入決定權,符合定義即可成為成員。隨著博物館化的拓展,新成員不斷出現,但其中一些成員與原先成員區別很大,不僅原先的成員感到詫異,理論界也頗感棘手。
不可移動遺產進入博物館物的范疇,尤其是大型的文化空間如考古遺址、自然遺跡、生態博物館等,與傳統的室內博物館大相徑庭,博物館如何將它們納入定義中?“機構”是否依舊是一個適宜的詞匯?無形文化遺產的概念出現并進入博物館后,由于它們并不具有三度空間的物質屬性,原先的博物館定義中所強調的“物”的屬性是否還能堅守?動物園和水族館的進入使原先展品的去生命化特點不復存在,更重要的是,隨著現生和活體標本進入后,“遺產”這一概念是否依舊適用?科學中心也帶來了新的困惑。在本杰明·吉爾曼(Benjamin Gilman)看來,藝術博物館是一座神廟,而科學博物館卻是一所學校,兩者實際上是相互矛盾的,這兩個領域是不可調和的[9]。的確,從實物藏品的角度看,兩者正好各執一端,藝術博物館展品幾乎是清一色的實物展品,而典型的科學中心幾乎全是為展覽專門設計制作的裝置。在這種情形下,博物館定義能否為兩者都發放準入證?
從功能上看,隨著博物館化拓展和新型博物館的加入,博物館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發生了變化。早期的博物館很少會自覺承擔科學研究與社會教育的責任。但在自然科學興起的背景下,許多博物館尤其是自然類博物館、人類學博物館等都承擔了大量的科研任務,有些甚至成為某一學科領域的研究中心,于是,在博物館定義中就增加了這方面的任務。隨著地方博物館、行業博物館和科學博物館的興起,博物館開始承擔更多的社會教育職能。面對這樣的現實,2007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改變了定義中研究與教育的位置,將教育作為博物館的首要功能。
可見,博物館化的每一次拓展、每一次新的博物館物和新的博物館類型的誕生都會為博物館理論界帶來新的挑戰。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持續修改中的博物館定義正是理論界對博物館化拓展的現實所作出的響應。
(三)導致建筑形態及營造程序的變化
博物館化拓展的影響不僅限于理論或觀念層面,而是滲透到實際運作的各方面及作為運行基礎的場館建設上。新博物館類型的增長從多個方面影響了博物館建筑的形態及營建程序。早期藏品和展品基本屬于精致小巧的可移動物品,對展覽空間沒有特殊的要求。隨著新類型博物館物的進入,情況發生重大變化:從實物展品看,一些大型的工業產品、生物標本、民俗與民族學物品的進入,對展覽空間提出了新要求;從非實物展品看,作為不可移動遺產和非物質遺產的代理者,包括大型復制品、情景再現的大型媒體技術、大型操作互動和體驗裝置等也有各自的技術參數;從深化拓展教育的目的看,輔助性闡釋與敘述的電影院、小劇場及各種拓展教育項目都使得建筑的功能性結構變得非常復雜。這種復雜的、非標準化的結構無法采用統一的標準化設計方法,而必須先行調查資源特征與規模,初步設定表達方式和審美風格,然后才能確定建筑的規模、形制、組合關系和特殊空間。在這類博物館建設的過程中,總規劃(master plan)就成為保障質量的必要環節。只有在充分明確了上述要求的前提下,才能寫出可行的、有效的建筑設計任務書。
(四)導致展覽建設的一系列變化
展覽的變化包括目標、功能、題材、理念與方法,是博物館所經歷的一系列變化中最突出和引人注目的,這是因為這一切都與收藏動機有關,而收藏動機又取決于博物館性的判斷。博物館化的拓展正是博物館性判斷不斷寬容和泛化的結果,在博物館展覽建設的以下諸方面體現出來。
1.展覽要素的復雜化
博物館類型的增長導致展覽要素復雜化。在傳統的以藝術精品為主體的展覽中,展覽要素是單一的,是可移動文化遺產一統天下,為“單一的實物展品要素體系”。但隨著不可移動遺產、非物質遺產進入人類收藏的視野,它們也成為博物館講述土地與行業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過由于它們不能親身前往,所以通常采用造型與媒體的方式進行再現。另一方面,有時為了對展品進行更深入的闡釋,也會采用造型物、媒體和裝置等進行輔助。隨著造型、媒體和裝置的進入,上述單一的實物展品要素體系也被改變了,出現了“多元混合的展品要素體系”。也就是說,以往的展覽都是用實物構成的,而現在的一些區域博物館、行業博物館等主題類博物館為了更好地闡釋和敘事,其展品中既有“實物”、也包括造型與媒體等“非實物”。博物館與展覽類型的多樣化不僅導致展覽要素的復雜化,也強化了前文提到的展品的非標準化特色,這給展覽的制作帶來了大量新問題。
2.策展內涵的復雜化
在傳統的美術館,策展人扮演著重要角色,工作重點是提煉主題、組織展品。由于藝術作品主要滿足于人們的審美與欣賞,且作品本身就具備較強的傳播力和自明性,策展人對展品的闡釋責任并不具有強制性的要求;加上單一的實物要素展覽機構比較簡單,標準化程度相對較高,建設的過程比較接近標準化工程,策展與設計的難度相對較小。但隨著以學習與理解為宗旨的博物館的興起,許多展品不再是精美的藝術品,而是記憶的載體。這類展品的價值與意義蘊藏在物的深處而較難被理解,所以,對它們進行闡釋就成為策展中不可或缺的工作。另外,以闡釋與敘事為特征的主題性展覽,其展品要素變得復雜多元,非標準化增強也使策展工作變得復雜,例如如何確定主題、選擇展品,如何將展品組織成一個有效實現傳播目的的有機系統,如何讓觀眾通過觀察與閱讀理解展品的內涵。博物館要妥善解決這些問題,在策展環節需由策展人、釋展人和設計師構成的團隊運作。
3.質量保障的復雜化
在這個復雜的、以非標準化為特征的營建過程中,如何有效保障展覽品質也變得格外復雜。在以欣賞為主的展覽中,由于人們的審美本身具有較強的主觀性,難以對觀展獲益進行度量,只能滿足于觀眾的一般性印象。但對以科學普及為使命的博物館,揭示事物真相、傳遞科學知識是其職責所在,如在歷史博物館、自然科學博物館、非物質文化博物館中,許多過程、原理和技術已在研究中得出結論,那么展覽的傳播效益及觀眾參觀受益程度就成為驗證博物館質量的核心維度。要做到這一點,不僅要有優質的策展,而且要在博物館建設過程中將其落到實處。為此,博物館界建立了包括前置評量、形成中評量和總結評量三大環節的質量保障系統[10]。
在博物館建設程序上,為保證策展人的意圖能貫徹落實,標準化工程的分階段實施方法顯然不再適用。一方面,經過不同階段的易手,策展思路會在不斷的變化中發生偏離;另一方面,各階段易手會由于缺乏單一的責任主體而出現互相推諉的現象。尤其是在當代中國大陸博物館營建中缺少形成中評估環節的背景下,制作團隊即便發現二維設計圖中的問題也不愿作出積極修改,使設計缺陷進入產品中,從而影響展覽質量。為防止這種現象,許多國家采用了總承包制,在始點進行招投標確定團隊,由該團隊作為唯一的責任主體,保證策展思路得以貫徹落實。
四、結語
為對導致博物館持續變化的原因作較全面的分析,我們將注意的焦點放在“博物館化拓展”這個關鍵節點上。這是因為博物館化拓展既是文明演進、社會發展與觀念變遷的產物,又是刺激與推動博物館各個環節進行變革的直接動力。在前一個環節,隨著文明演進的精神性成長和社會變遷中收藏主體的擴張,人們得以從更廣大的范圍和更深入的層面理解物所蘊含的精神內涵和記憶價值,從而極大地推動博物館化的拓展。在后一個環節,大批新成員給博物館帶來新的使命與功能,使博物館物收藏活動自覺地打上傳播與教育的印記。正是出于對傳播與教育使命的有效履約,博物館在眾多方面展開了變革,包括組織機構、場館硬件、展覽建設程序、理念與方法以及展覽評估和拓展教育等。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完全不必把博物館變化視作來自外部的不確定因素而惶然,相反,應將它們視為博物館響應時代變遷召喚、履行社會責任的自覺行動。了解這種變化的內在邏輯,不僅有助于我們發現觀念和行動上的滯后之處,作出積極改變,而且有助于我們對未來可能出現的變化有更準確的判斷和更深入的理解,從而使我們的建設行為更加清醒和自覺。
[1]Eilean Hooper-Greenhill.Museums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1.
[2]同[1]。
[3]關于“博物館化”的詳細評論,可參閱〔法〕安德烈·德瓦雷、方斯瓦·梅黑斯指導,張婉真譯:《博物館學關鍵概念》,Armand Colin,2010.
[4]Z.Stránsky.La musēologiescience ou seulement travail pratique du musēe.MuWop/Do Tram,1:22,24.轉引自張婉真:《從博物館學學科發展歷程談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學博士課程開設意義》,《博物館學季刊》2004年第3期。
[5]S.Pearce.Archaeological Curatorship.London and New York: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0:156.
[6]〔奧地利〕弗德利希·瓦達荷西著,曾于珍等編譯,張譽騰審校:《博物館學——德語系世界的觀點》,臺灣五觀藝術管理公司2005年。
[7]直至今日,以此定位的博物館依然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博物館。
[8]由于古代中國很早就處于統一的王朝統治下,并采用郡縣制的方式進行社會治理,所以撰寫志書的歷史要悠久得多,但以區域為單位的機構性收藏卻不曾建立起來。
[9]B.Gilman.Museums Ideals of Purpose and Method.Edited by H.Genoways,M.Andrei.Museum Origins:Reasdings in Early Museum History and Philosophy.New York,Rout?ledge,2008:107-115.
[10]目前中國大陸尚未有效開展上述三大評量,尤其是形成中評量既沒有進入建設流程,也沒有相應的資金保障,造成大量設計缺陷進入終結產品中。參見〔美〕凱瑟琳·麥克林著、徐純譯:《如何為民眾規劃博物館的展覽》,臺灣海洋生物館2001年;徐純:《博物館實踐與博物館理論的關系——以博物館展覽為視角》,《東南文化》2011年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