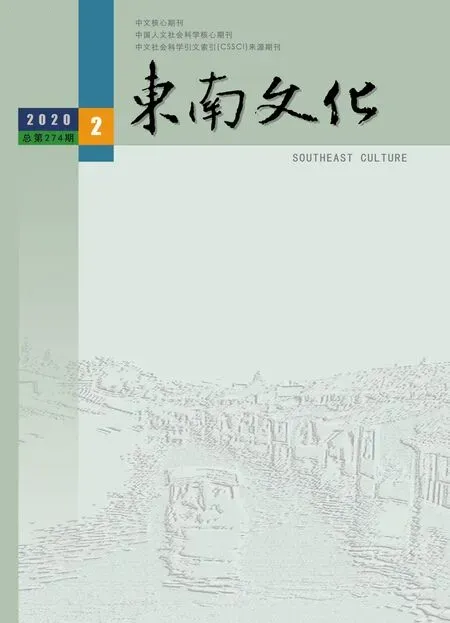南京棲霞山舍利塔營造年代與形制來源考
徐永利
(蘇州科技大學 江蘇蘇州 215011)
內容提要:通過分析棲霞山舍利塔營造者的官職升遷與權責,該塔的營建年代范圍可以較精確地限定在公元961-964年之間。基于年代限定,該舍利塔形制的教派成分得到了梳理,并與南唐皇室、建造者以及棲霞寺的教派信仰變化做相關對照,最終將舍利塔形制主要來源集中到華嚴宗、禪宗等教派上。其他因素中,隋代舍利塔以及五代江南佛塔形制對南唐舍利塔的影響得到了著重分析,由此該舍利塔各部形制來源都得到了初步判定,其形制多元拼貼的特征得以揭示。
南京棲霞山原稱攝山,劉宋泰始年間(465—471年),居士明僧紹(號棲霞)在此結廬而居。后受法度禪師影響,舍宅為寺,并請法度禪師主持,稱“棲霞精舍”。時值蕭齊永明七年(489年),為棲霞寺的濫觴。之后寺名代有更迭,唐代武德年間(618—626年)稱功德寺;上元年間(674—676年)為隱君棲霞寺;會昌五年(845年)寺廢;大中五年(851年)重建,稱棲霞寺;南唐時(937—975年)重修,改稱妙因寺[1]。
隋仁壽元年(601年),隋文帝楊堅頒詔于各地建舍利塔,蔣州(南京)棲霞寺列于諸州名單。該塔毀于唐會昌年間(841—846年),南唐重修妙因寺時,重建為石塔(圖一)[2],主持者為林仁肇與高越[3]。石舍利塔為密檐五層,塔身立于須彌座上,通體雕刻精美,密檐之下為仿木椽頭,與北朝至唐代流行的空筒密檐塔具有顯著差異,反開遼金時期流行的實心密檐塔之先河[4]。此類佛塔形制在江南罕見,在同類佛塔中又時期占先,其形制由來耐人尋味。
一、舍利塔營造年代推測
關于棲霞山舍利塔的營造年代,多籠統定于南唐[5],時間跨度有39年之長。邵磊將之縮短到南唐保大三年(945年)至乾德三年(965年)的20年之間[6]。此外,薛政超認為此塔建于元宗李璟在位期間[7]。該塔采用八邊形平面,與10世紀中葉杭州保俶塔及之后的眾多江南石塔相類,但其密檐形制,又似乎有著唐代密檐塔的余緒。細化該塔建造的時間段,對辨析其形制來源應有所助益。
該塔建造主持者為林仁肇與高越。據陸游《南唐書》,林仁肇先為閩國武將,公元945年閩國滅后歸順南唐。元宗李璟時為潤州節度使,之后“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8],北宋開寶六年(973年)被南唐后主毒殺[9]。林仁肇任潤州(即隋代蔣州)節度使之前地位尚低,參與舍利塔建造的可能性并不大。南唐僅兩都江寧、江都稱“府”,其余行政區稱州。南唐自認承唐祚,新舊唐書《百官志》《職官志》的制度可作為推定“潤州節度使”權責的參考,節度使“掌總軍旅,顓誅殺”[10],看似職責與建塔無關,但因乃當地軍政長官,實際權限廣大。另外,潤州節度使管轄范圍應包含江寧府的攝山(棲霞山),唐代《法苑珠林》曾有“唐潤州攝山棲霞寺”的記載[11],所以綜合來看林仁肇是有條件在潤州節度使任上參與舍利塔營造的。離開潤州之后任職的鄂州(武昌)、南都(洪州,今南昌)俱遠離棲霞山,林參與建造棲霞山舍利塔應無可能。新舊唐書均未載節度使品秩,但《舊唐書·職官志》稱其“外任之重,無比焉”[12],因持“旌節”,一般認為應高于刺史,至少為二品官,要高于南都“留守”一職。參考《新唐書·百官志》“三都留守”的設置,“留守”為“府尹”從三品兼任[13],實為貶職,并非林仁肇得到重用之時,所以離開潤州之后的身份也并不合適。

圖一// 南京棲霞山舍利塔
高越在南唐烈祖李昪稱帝后,“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14],岳父盧文進死后,不得志;元宗李璟在位時長期擔任中書舍人,多起草交兵詔書,參照《新唐書·百官志》為正五品上[15];“后主立,始遷御史中丞勤正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16]。按《新唐書·百官志》,御史(臺)中丞、戶部侍郎均為正四品下。從官職來看,烈祖時期其所任“祠部”,按《新唐書·百官志》記載屬禮部,“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17],正適合負責建塔。但烈祖李昪在位為937—943年,這段時間林仁肇尚未由閩歸順;元宗李璟時的“中書舍人”主職是起草詔書文案,這兩段時期高越均無主持建塔可能。所以建塔時間很有可能是后主重新提拔高越“遷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這段時間。按《新唐書·百官志》戶部侍郎“掌天下土地、人民、錢谷之政、貢賦之差”,戶部下的金部“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兩京市、互市、和市、宮市交易之事,百官、軍鎮、蕃客之賜,及給宮人、王妃、官奴婢衣服”[18],與皇室消費支出直接相關,也必然涉及為皇室修塔建寺的財政、宮市交易,當然高越曾任祠部的經歷也當是選其主持的理由之一。另外,高越與潤州節度使林仁肇搭檔,亦應在御史中丞、戶部侍郎這一官階最高之時。
后主即位在961年,高越去世時間雖然不詳,但“謚曰穆,貧不能葬,后主為給葬”[19]。按前文,高越葬于妙因寺附近,應該是后主選定的墓址,后主應很熟悉高越、林仁肇與舍利塔的關系。林仁肇改遷南都(洪州)留守在北宋乾德三年(965年)[20],之前又曾遷鄂州(武昌),假設任上至少一年,則為964年。所以本文推測,舍利塔建于南唐后主李煜在位、高越任戶部侍郎、林仁肇任潤州節度使之時,即961—964年之間[21]。
二、舍利塔形制的教派來源
既然可以大致厘定石舍利塔的營造時間,那么后主李煜及其以前時期南唐的佛教信仰狀況必然會對舍利塔的重建形成直接影響。本文嘗試從舍利塔形制與佛教教派可能的淵源關系入手加以初步探討。
(一)南唐及妙因寺的教派信仰
南朝蕭梁之時,江南佛教成實宗最盛,但自遼東僧朗南下后,南京棲霞寺成為其所傳“三論宗”祖庭。南唐重修為妙因寺之后,其所修教派也有所變化。
五代之時,幾大佛教教派已然形成,雖興盛程度不一,但仍舊通過所奉經書的傳播產生不同影響。同時,隨著佛教世俗化的發展,教派之間雖有競爭,但不同時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融合。中唐以后,禪宗壯大,南唐佛教諸派之中,影響最大的仍屬禪宗。李昪在建國之初,即迎禪師文益于金陵報恩院及清涼寺,弘揚禪法[22]。但五代時期的禪宗,并不排斥其他教義,例如文益曾作《三界唯心》頌、《華嚴六相義》頌[23],其禪理之中融入了唯識與華嚴成分。
棲霞寺的教派變遷也有類似表現。該寺為三論宗祖庭之一,但該宗除以《中論》《十二門論》《百論》立宗之外,也重視《華嚴經》;僧朗本人“華嚴、三論,最所命家”[24]。相似的,西安草堂寺,三論宗的另一祖庭(始于后秦鳩摩羅什),同時又是華嚴(源于唐代華嚴五祖宗密)、成實宗(同樣源于鳩摩羅什)祖庭。華嚴思想與各宗的融合值得關注。
(二)棲霞山舍利塔形制與華嚴
1.華嚴特征
(1)須彌座八相圖
棲霞山舍利塔下部為八角形須彌座,座上為三層仰蓮構成的蓮臺。八相圖位于須彌座束腰部分。梁思成認為,“棲霞寺舍利塔八相圖,手法精詳,為此期江南最重要作品。八相為①托胎,②誕生,③出游,④逾城,⑤降魔,⑥成道,⑦說法,⑧入滅”[25]。黃征依順時針次序定為“乘象入胎、王宮誕質、游四城門、逾城出家、悟道成佛、降服魔眾、轉妙法輪、示歸寂滅”,第五、六相順序與梁先生有所不同[26]。
“八相”相關內容,早期見于南朝真諦《大乘起信論》“從兜率天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轉法輪、入于涅槃”[27],內容與南唐有所不同,可見“八相”有一個流傳過程。從南朝宋釋寶云所譯《佛本行經》到隋開皇年間阇那崛多譯的《佛本行集經》,釋迦牟尼涅槃之前諸多“本行”數量遠遠超出“八相”,可能是“八相”不同構成的一個原因。
元代蒙潤《天臺四教儀集注》載八相為:“一從兜率天下、二托胎、三出生、四出家、五降魔、六成道、七轉法輪、八入涅粲。”并認為,“《華嚴》中列降魔相”,“以《華嚴》中,所列八相是大乘故。”[28]可見由南朝至五代,八相內容依大小乘之別確有所調整。棲霞山舍利塔之“八相圖”雖與《天臺四教儀集注》所列仍略有不同,但必然來自于《華嚴經》大乘“八相”體系。至于八相成道以浮雕來表現,則是隋唐以來佛教世俗化的結果。
(2)一層塔身浮雕
一層塔身較高,八面均為淺浮雕。若以正南為第一面,則順時針第一、三、五、七面為四大天王像,第二面(西南)為普賢菩薩像,第六面(東北)雕像殘毀,已被推定為文殊菩薩像,第四、八面為版門。普賢菩薩、文殊菩薩的成對出現,很明顯來自于華嚴三圣(文殊、普賢二菩薩以毗盧遮那佛的左右脅侍出現)的組合。
關于四大天王像,也有若干學者根據服飾差異認為是二天王、二力士組合的[29],并以龍門石窟奉先寺的九座大像的組成作為參照[30]。但即便是奉先寺之盧舍那佛(釋迦牟尼報身佛)、文殊普賢二菩薩、天王、力士的組合,也是反映華嚴世界的。另外,今天的棲霞寺舍利塔緊鄰毗盧寶殿(20世紀20年代所建),后者所供奉的就是毗盧遮那佛,似乎也在暗示著這座塔與華嚴世界的關系。
棲霞寺石窟存有南朝時期無量壽佛(阿彌陀佛)、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所組成的“西方三圣”雕像,那么單獨現于塔上的普賢菩薩、文殊菩薩,加上刻有八相成道的佛塔本身(象征佛陀)組成“華嚴三圣”也是自然之事。
2.《華嚴經》的可能影響
盛名于南朝的僧朗本為遼東人,兼修華嚴與三論,與僧朗淵源極深的棲霞寺,本身就有華嚴的底子。客觀來看,如果說華嚴宗對南唐佛教存在影響,則主要是由《華嚴經》的經典地位決定的。該經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為釋迦牟尼成道后為文殊、普賢等大菩薩所宣說。最早譯本為東晉佛馱跋陀羅所譯《六十華嚴》。唐代有兩個譯本,分別為《八十華嚴》與《四十華嚴》。華嚴宗以隋代杜順為初祖,認其為文殊菩薩化身。
華嚴宗在唐代得到廣泛傳播。山西交城縣萬卦山今存中唐晚期華嚴經塔六座,基座分八角形、方形兩種,塔身也相應為八角形和方形[31]。此外有兩點值得關注:一為三重仰蓮蓮花座,棲霞山舍利塔須彌座上也為三重仰蓮;二為塔檐雕刻飛天,與舍利塔一層檐下相似(圖二)[32]。
五代之時,華嚴思想影響廣泛。稍晚的北方遼朝,在今呼和浩特造八角七層樓閣式萬部華嚴經塔,一般推測約建于遼圣宗年間(983—1031年),略遲于南唐滅國之后。此斷代并非定論,但也可佐證那個時代華嚴思想的廣泛影響。
張馭寰認為“華嚴經塔的形制奠定了后期所謂‘幢式塔’的基礎”[33],本文無意討論“幢式塔”與棲霞寺舍利塔的關系,但華嚴經塔的形制可能會影響南唐舍利塔的構思,應是相對合理的推測。

圖二// 山西萬卦山華嚴經塔
(三)棲霞山舍利塔形制與密宗
棲霞山舍利塔是五級密檐塔。筆者曾在《外來密檐塔形態轉譯及其本土化研究》一書中詳盡討論了密檐塔形制與密宗(密教)的關系。北朝嵩岳寺塔與雜部密教密切相關,但總的來看,唐代以后,除了云南滇密與密檐塔形制的對應性較強之外,密檐塔僅僅是密宗寺廟的形制選項之一[34]。不過與五代時間上多有重疊的契丹政權(后來的遼)信奉密宗,佛塔也呈現為棲霞山舍利塔式樣的帶有須彌座的實心密檐形式,使得我們仍舊需要留意密檐之間隱含的密宗思想痕跡。此外,有學者認為在舍利塔八相圖之涅槃圖中(圖三),“在七寶床兩側各有一頂盔貫甲作怒目橫眉狀者,當系密跡金剛力士”[35],是為少量的與密宗直接相關的題材。
因為妙因寺教派流變與密宗無直接關系,所以對棲霞山舍利塔與密宗思想關系的關注主要來源于華嚴經與密宗思想的關聯性上。學界一般認為,《華嚴經》中的毗盧遮那佛(釋迦牟尼法身佛)即密宗中的“大日如來”,密宗的一些儀軌也在《華嚴經》中出現。“《華嚴經》作為與密教思想甚為接近的一部大乘經典,一直若隱若現地影響著佛塔建筑的傳承與轉化。”[36]鑒于前文討論的舍利塔華嚴特征和密檐形制,密宗思想也可能蘊染了建塔之時的宗教氛圍。

圖三// 棲霞山舍利塔八相圖之涅槃圖
(四)棲霞山舍利塔形制與禪宗
南唐妙因寺以禪宗為主流信仰。禪宗大盛之后,華嚴宗、密宗都是寓宗。南唐舍利塔出現之后,帶有須彌座的實心密檐塔主要流布于北方。雖然遼代主奉密宗,但金代則以禪宗為主,金代密檐塔分明是禪宗、華嚴、密宗形制的混合代表。
棲霞山舍利塔形制與禪宗的直接關聯見于一層塔身轉角倚柱鐫刻的經文,例如:《金剛經》四句偈,“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楞嚴經》贊佛六句偈,“□□□妙法,惚持不動□。楞嚴王世□,有消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護法身”;《法華經》,“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37]。《金剛經》四句偈,素來為禪僧所傳誦;《楞嚴經》《法華經》同樣被禪宗奉為經典。
總的來看,禪宗是最有可能導致棲霞山舍利塔多元教派元素混合呈現的宗派。
三、棲霞山舍利塔形制的其他影響因素
(一)佛塔建造者的佛教傾向
1.林仁肇與高越
林仁肇為南唐名將,除棲霞寺之外,任南都(今江西洪州)留守期間曾制有《龍興寺鐘款識》(《全唐文》收錄),但相關史料中并無其好佛的記載,推測林對棲霞山舍利塔的貢獻可能偏于工程的督造管理方面。
舍利塔的另一建造者高越原為北方高士,好佛,死后葬于棲霞寺(妙因寺)山外坡地[38],可見其對該寺的看重。高越應非常重視棲霞山舍利塔重建一事,曾寫有《舍利塔記》一卷,惜已失傳。據陸游《南唐書》,高越為幽州人,岳父盧文進同為幽州人,“娶虜公主”[39],也就是說高越岳父母為遼朝宗室成員。幽州為遼朝一部分,妻子有契丹血統,自己又來自幽州,那么高越之好佛,非常可能帶有遼地的宗派特征,進而影響到南唐舍利塔的形制選擇上。
2.南唐皇室
影響南唐皇室信仰的教派主要有禪宗與華嚴。華嚴宗遵《華嚴經》為至高經典,在唐武宗滅佛之后,該宗漸漸式微,但余緒仍在。南唐開國皇帝李昪在尊仰文益禪師的同時,亦曾接受僧人勉昌進獻、唐代李通玄所撰《新華嚴經論》,“令書十本,寫李長者真儀十軸,散下諸州”[40],可見其對華嚴的推崇程度。李昪之后,中主李璟喜歡禪宗經典《楞嚴經》[41],而后主李煜則曾召博學的幽州“酒禿”(元寂)和尚講解《華嚴·梵行》一品[42]。可見這種禪宗與華嚴成分的摻雜對南唐帝王均有影響。
前文判斷,棲霞寺舍利塔重建于后主時期。曾有北僧小長老勸說李后主,“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后主多造塔像”[43]。此小長老后來深得信任,深具華嚴成分的棲霞寺舍利塔或許正是此時所造。
(二)隋代舍利塔形制的可能影響
1.棲霞寺舍利塔須彌座及一層塔身的年代
黃征曾撰文提出,“一般認為塔的底座和第一級應該基本是原物,但也可能重修時嵌補過”[44]。從原文上下關系來看,“原物”似指隋代原物,但也未與肯定,作者又補充道,最晚至南唐,比較含糊。就筆者所查其他參考文獻來看,一般將塔基、一層塔身斷為南唐所建,例如邵磊將八相成道圖中的建筑形制與南唐建筑做對比加以證明[45],鄭立君通過舍利塔基角柱龍紋造像與南唐烈祖欽陵浮雕龍對比來證明[46]。在此稍作拓展,試論幾點間接理由。
(1)隋代密檐塔應為方形平面,目前八角形塔基過小,只適合實心石塔。
敦煌莫高窟有隋代密檐塔壁畫形象(圖四)[47],為方形平面,同時期其他佛塔類型也以方形為主。張馭寰推測舍利塔底邊達16米,即便沒有這么大,也遠遠超過目前仰蓮座直徑(略超4米)[48]。隋代王劭《舍利感應記》云“我興由佛,故于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49],說明塔身內部空間的存在。唐天寶進士蔣渙《登棲霞寺塔》[50],雖未直接描寫隋代舍利塔形制,但既然稱為“登”,則該塔也是有內部空間的,其大小無法安放在目前的基座之上。

圖五// 云岡第六窟東壁浮雕塔
但隋代舍利塔也有可能是有較高基座的。《舍利感應記》記有“皇帝皇后于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浮圖”[51]一句,推測是指塔基高出地面,在舍利塔總高度上占有顯著比例的情況,從而與塔身在形態上連為一體。其實隋代以前石窟壁畫中,多層木塔下設須彌座的情況很多,例如云岡石窟第六窟東壁浮雕塔(圖五)[52]。
(2)八角形當為后起之制,為五代江南多層佛塔的普遍趨勢。“八相成道”與八邊形匹配應屬同期現象。現存五代江南佛塔平面狀況詳見表一[53]。
由表一可知,南唐舍利塔八邊形平面確為五代江南磚石塔所常見。其中,五代早期的臨安功臣山塔仍有唐風,取正方形平面,但隨即八邊形開始流行。
一般而言,對“八相成道”或“七佛一菩薩”的表達會產生八邊形平面的需求,后者與北涼小石塔的發展脈絡有關,暫且不論。如前文所述,隋代佛經并未提供內容穩定的“八相成道”規制,而且各相平等的八相序列也不是隋代方塔適合表達的。
五代八邊形佛塔雕刻素材也有較明顯的華嚴成分。例如杭州靈隱寺雙石塔四層側面各雕一幅文殊菩薩和一幅普賢菩薩像,杭州閘口白塔形制與靈隱雙塔如出一轍。當然,這些佛塔形制中多雜有其他教派元素,如閘口白塔須彌座束腰部分“完全刻滿了《陀羅尼經》”[54],為密宗成分的體現。依本文推測,大多數五代佛塔早于棲霞山舍利塔的建造年代,其形制對后者必然有所影響。
2.隋代舍利塔形制相關推測
須彌座及一層塔身斷代還涉及到隋代舍利塔到底是何形制、何材質的問題。依照《廣弘明集》卷第十七載《隋國立舍利塔詔》,仁壽年間的舍利塔由“所司造樣,送往當州”[55],說明隋代舍利塔樣式是統一的。鑒于這些塔一座也未能留存至今,張馭寰推測這些塔全部是木塔,并對此塔進行復原——邊長16米的方形三層木塔(圖六)[56],但未過多考慮基座形制。曹汛對該塔層數有不同看法(認為是五層),但同樣認為該塔有統一式樣[57]。
多年來,她以超前的工作理念、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勤耕不輟的工作態度,勾畫著祥順鎮中心校發展的宏偉藍圖,致力打造鄉村教育閃光名片,用錚錚言行詮釋著新時期好校長形象,踐行著對鄉村教育事業執著的承諾,贏得了學生、家長、同仁以及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
近年對棲霞山隋代舍利塔形制討論比較深入的一篇文章是《隋仁壽舍利塔形制試探》,該文概括前人觀點為兩類:覆缽式塔(向達)與樓閣式方塔(梁思成、劉敦楨、小杉一雄、張馭寰),并提出自己觀點,認為應是“臺基上的覆缽頂單層方塔,中心有剎柱,頂上有相輪、寶瓶,其材質有磚、木,外表飾以金碧”[58]。

表一// 五代江南多層佛塔一覽表

圖六// 張馭寰復原隋代舍利塔
此文的一個重要論據是道宣《續高僧傳》所錄《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曇遷傳》“安置寶塔為三十道,建規制度,一準育王”[59]一句。該段文字確實說的是仁壽元年舍利塔之事,“育王”指的是阿育王,但“建規制度,一準育王”這一要求未見于《隋國立舍利塔詔》,分明是唐代道宣的轉述,文獻客觀性不同于《廣弘明集》所錄詔書內容,雖然后者也是道宣輯錄。即便隋文帝認可“建規制度,一準育王”這一原則,一來,印度本土佛教早已消退,阿育王時代(約公元前3世紀)的制度只能在八九百年之后中土傳說中體會;二來,六朝至隋的佛法儀軌早已融入太多的中國化內容,所謂“一準育王”,絲毫不會影響佛塔形制的本土化。所以筆者并不贊同過度關注隋代舍利塔對“阿育王塔”形制的繼承關系上。
作者在文中提到西晉太康二年(281年)越州出土小舍利塔,“梁武帝造木塔籠之”,倒似乎與隋代仁壽舍利塔的功能、形制有類似之處。關于此塔材料,也有其他間接材料有所暗示。明末清初道士張怡偈語《舍利塔》云“隋氏建塔,以奉舍利……劫火洞然,神力莫效”[60],似乎是說隋代舍利塔是燒毀的,但不知所據何來。總的來看,《隋仁壽舍利塔形制試探》的研究結論中對方塔、木材的認定仍有意義,但對磚木混合、中心有剎柱的單層塔結構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則缺乏有效論證,且中心剎柱與地宮的設置恐有違背。
3.《隋國立舍利塔詔》相關分析
還可以略作其他推測:隋代仁壽舍利塔共分三批建造。仁壽元年要求到達州境之后,“縣尉已上,息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剎等事。”“行道”應與進入州境后舍利迎送有關,“打剎”概指“嚴持香華,寶幢音樂”[61]之類,總共七日的期限,包含舍利入函,那么建塔立剎應在此前完成,舍利入函、封閉石函(或地宮)為整個儀式的結束,以示其森嚴與隆重。據隋代《慶舍利感應表》推斷,蒲州、嚴州舍利入函之前均已立塔,而京師大興善寺起塔之時,“先置舍利于尚書都堂”[62],說明下石函時塔應完工,一層塔身應有內部空間。
第一批下詔建塔時間為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要求當年十月十五日午時,“同時下石函”。時間共四個月零兩天,應包括護送詔書與舍利抵達州境的時間。之后才是招工備料、開挖地宮(磚壙)、立塔、裝飾的時間,只能一切從速,何況陰歷十月已是冬天,瓦作、灰作在北方尤其受到施工限制,木結構是最合理的選擇。隋代《舍利感應記》載“亳州開寂寺立塔,界內無石,別處三石,合而成函”[63],埋地的舍利函尚且如此,也說明塔身只能采用木材。第二批在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頒詔,四月八日午時,“同下舍利,封入石函”,間隔時間更短。從工期上說,預先加工好木構件、現場快速裝配更為合理,張馭寰也認為在短期內建塔只能選擇木結構[64]。
此外,雖說磚塔在隋代已很常見,但磚的燒制與應用仍不普及,成本和燒制條件、施工速度都受到一定限制。雖說是皇家工程,但全國同時起塔30—50座,各州均應有官窯(或鄰州可借用)才行,恐難辦到,莫說一共是三次建113座塔。
另外,詔書中應未涉及到雕刻細節。例如“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65]一句中,“法相”應指諸法真實之相,所以才與“解”相稱,此句應不是指佛像或塔身雕刻素材。雖然目前尚難以推測木舍利塔的具體裝飾情況,但塔內應有佛像。
4.隋代舍利塔的直接影響
討論隋代舍利塔形制,目的仍舊是探索南唐舍利塔的形制來源。南唐舍利塔可能直接受到隋代舍利塔形制影響,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基座、一層塔身與經變的表達
隋代舍利塔原為木塔,有內部空間,塔內很可能在不同樓層供有佛菩薩像及“神尼像”等,在轉換為實心佛塔之后,菩薩像、經變素材等變為塔身外觀上的雕刻。同時原塔可能存在的基座轉換為八邊形須彌座,成為“八相成道”的載體。一層較高的塔身也可能受隋代木塔影響。
(2)層數
明代葛寅亮《金陵梵剎志》記載“舍利塔,高七級,在無量壽佛之右,隋文帝造;高數丈,五級,鐫琢極工,南唐高越、林仁肇復建塔。”[66]“五級”為石舍利塔現有層數,“七級”之說按照向達的理解是“塔連頂共為七級”[67]。一般認為隋代木舍利塔就是五級,依據是《重藏舍利記》中隋代智泉寺“建木浮圖五級,安舍利于其下”[68],南唐塔層數是對隋代塔的繼承。
(3)仿木的密檐
南唐舍利塔仿木結構的檐部,是隋代舍利塔為木塔的一個較為直接的證據。以磚石仿木成為五代之后江南多層佛塔的普遍形制特點。
(4)塔剎
隋代《慶舍利感應表》記載隋代舍利塔有寶瓶(蒲州棲巖寺)、五色相輪(嚴州)[69],南唐舍利塔重修后的塔剎繼承性不明顯。
四、結論
對石舍利塔的形制來源略作總結(表二),可以看出舍利塔形制中并列華嚴成分與禪宗、密宗成分,并不矛盾,具有禪宗融合之下的時代特征。《華嚴經》也與禪宗、密宗思想皆有交融會通之處。基座與一層塔身雕刻來源于對《華嚴經》的表達,一層較高塔身、密檐則受到密宗和禪宗的影響。雖說本文強調教派來源,但就基調而言則更強調《華嚴經》,而非華嚴宗。

表二// 棲霞寺舍利塔形制成分來源表
密檐形制實為五代江南之特例,或許更應從北方(如遼對北朝的繼承)尋找理由。南唐對遼朝很重視,陸游《南唐書》有《契丹》一文,專記兩國交往。總的來看,南京棲霞山舍利塔應是在北方唐代單層石質華嚴經塔的基礎上,參考北朝型密檐塔形制并承繼隋代木舍利塔某些元素而造。而南唐舍利塔密檐之間“四層共刻六十四尊佛像”[70],很可能是對棲霞寺南朝千佛崖巖石窟的就近模仿。恐正是棲霞山舍利塔這種明顯的南北多元拼貼做法,所以未能在江南進一步流行。
反觀遼代磚塔的發展脈絡,相對于棲霞山舍利塔,倒可能是獨特的,例如直接承續唐代磚石塔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非從南唐而來。至于契丹是否早有此類密檐形制出現,尚不能確定。
[1]南京市棲霞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棲霞區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第121頁。
[2]張馭寰:《中國塔》,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頁。
[3]或作“高樾”,本文按兩種《南唐書》等多數文獻統一為“高越”。
[4]徐永利:《由嵩岳寺塔看密檐塔分型》,河南省文物建筑保護研究院編《文物建筑(第十輯)》,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63—67頁。
[5]a.鄭立君:《試析南京棲霞寺舍利塔天王、力士造像的特點與風格》,《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9期;b.柴劍虹:《南京棲霞寺飛天形象初探》,黃征:《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第61—70頁。
[6]邵磊:《南京棲霞寺舍利塔佛傳圖的內容暨所涉南唐建筑規制諸問題》,《形象史學》2017年第2期。
[7]薛政超:《五代金陵宗教發展研究》,《長沙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
[8]宋·陸游:《南唐書》,《南唐書(兩種)》,南京出版社2010年,第320頁。
[9]宋·馬令:《南唐書》,《南唐書(兩種)》,南京出版社2010年,第46頁。
[10]宋·歐陽修等:《新唐書》,中華書局2000年,第858頁。
[11]唐·釋道世著,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四)》,中華書局2003年,第1970頁。
[12]后晉·劉昫:《舊唐書》,中華書局2000年,第1308頁。
[13]同[10],第859頁。
[14]同[8],第280頁。
[15]同[10],第797頁。
[16]同[8],第280頁。
[17]同[10],第786頁。
[18]同[10],第785頁。
[19]同[8],第280頁。
[20]同[9],第98頁。
[21]又據《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六,“南唐高越林仁肇建塔,徐鉉書額曰妙因寺”(宋·馬光祖修、周應合撰:《景定建康志(四)》,南京出版社2010年,第442頁)。徐鉉為一代文宗,長期擔任知制誥,此外在保大元年(943年)曾任祠部員外郎,保大十年(952年)任祠部郎中,北宋乾德二年(964年)任南唐中書舍人,北宋開寶四年(971年)任南唐工部侍郎(趙文潔:《徐鉉生平詩文編年》,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第12—38頁),同年后主李煜去帝號,稱江南國主。徐鉉任工部侍郎雖然有利于幫助建塔,但屬后主去唐號的沒落之時,且建塔主持者也非徐鉉,故此建塔時間應該不會延宕至971年。另外,徐鉉素不喜佛而好神怪(趙文潔:《徐鉉生平詩文編年》,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第4頁),所以本文對徐鉉不做過多討論。
[22]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60頁。
[23]同[22],第362—363頁。
[24]梁·慧皎:《高僧傳(卷八)》,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中華書局1992年,第332頁。
[25]梁思成:《中國雕塑史》,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233頁。
[26]黃征:《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第20頁。
[27]梁·真諦譯、高振農校釋:《大乘起信論校釋》,中華書局1992年,第143頁。五代之前《大乘起信論》譯本有兩種,一是南北朝僧人真諦(499—569年)所譯一卷本,較為流行;二是唐代實叉難陀(652—710)所譯二卷本。參見該書第6—8頁。
[28]達照:《〈天臺四教儀集注〉譯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31—332頁。
[29]白文明:《棲霞寺舍利塔石雕》,《美術大觀》1996年第4期。
[30]同[5]a。
[31]張馭寰:《中國佛塔史》,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61—65頁。
[32]同[2],第124頁。
[33]同[31],第62頁。
[34]徐永利:《外來密檐塔形態轉譯及其本土化研究》,同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08—109頁。
[35]同[6]。
[36]同[34],第161頁。
[37]a.向達、鄭鶴生:《攝山佛教石刻補記》,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重慶出版社2009年,第383—384頁;b.鄭立君:《試析南京棲霞寺舍利塔裝飾設計的特點與風格》,《東南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38]許廷長、濮小南:《棲霞寺史話》,南京出版社2008年,第45頁。
[39]同[8],第281頁。
[40]同[8],第351頁。
[41]薛政超:《五代金陵宗教發展研究》,《長沙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
[42]同[8],第351頁。
[43]a.同[9],第176頁;b.同[8],第352頁。
[44]同[26],第26頁。
[45]同[6]。
[46]鄭立君:《南京棲霞寺舍利塔龍紋造像的特點與風格》,《南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47]傅熹年:《中國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1年,第508頁。
[48]筆者參考棲霞山舍利塔立面測繪圖,按塔高18.73米等比例折算。
[49]隋·王劭:《舍利感應記》,唐·釋道世著,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三)》,中華書局2003年,第1275頁。
[50]同[38],第114頁。
[51]同[49],第1275頁。
[52]筆者改繪,原圖見王大斌、張國棟:《山西古塔文化》,北岳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16頁。
[53]a.同[31],第86—101頁;b.王承:《五代杭州佛寺》,同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第36—38頁。
[54]梁思成:《浙江杭縣閘口白塔及靈隱寺雙石塔》,《梁思成全集(第三卷)》,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1年,第287—300頁。
[55]唐·道宣:《廣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20頁。
[56]同[31],第30—36頁。
[57]曹汛:《兩擔愁云——建筑歷史的困境和歷史建筑的悲哀》,同濟大學編《第四屆中國建筑史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增補輯》,2007年,第1頁。
[58]楊效俊:《隋仁壽舍利塔形制試探》,《唐史論叢》(第二十五輯)2017年,第23—40頁。
[59]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中),中華書局2014年,第666頁。
[60]同[38],第137頁。
[61]同[49],第1276頁。
[62]隋代《慶舍利感應記表》,唐·釋道世著,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三),中華書局2003年,第1280—1281頁。
[63]同[49],第1278頁。
[64]張馭寰:《關于隋朝舍利塔的復原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5期。
[65]同[55]。
[66]明·葛寅亮撰、何孝榮點校:《金陵梵剎志(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8頁。
[67]向達:《攝山佛教石刻小記》,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重慶出版社2009年,第358頁。
[68]同[58],第25頁。
[69]同[62],第1280頁。
[70]鄭立君:《試析南京棲霞寺舍利塔的設計藝術特點》,《藝術百家》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