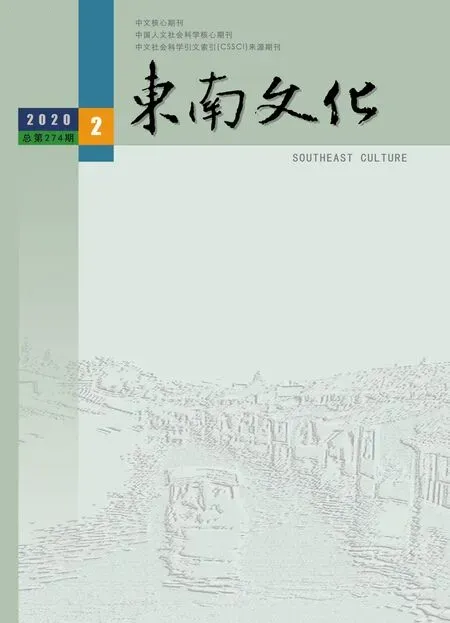南京獅子沖南朝墓出土散磚畫像研究:以鹵簿畫像為切入點
張 今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 江蘇南京 210023)
內容提要:結合獅子沖M1、M2出土散磚銘文和丹陽仙塘灣墓、金家村墓出土完整鹵簿畫像,可以對刻劃磚銘的含義展開討論,并復原它們在完整畫像中的位置,進而明確拼砌規則。借助這一方法,不難發現M1、M2散磚畫像與金家村墓、吳家村墓的部分畫像存在同一粉本現象,其來源可能是蕭齊末代帝陵級墓葬拼砌磚畫的剩磚,齊梁禪代后因無法繼續參與畫像拼砌,而被作為一般墓磚使用。
2013年1—6月,南京市博物館考古部(今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棲霞區新合村獅子沖北象山南麓調查并發掘了兩座南朝大型磚室墓,并于2015年公布發掘簡報[1]。兩座墓均未完全發掘,但在M1發現了由模印畫像磚拼砌而成的完整壁畫,其內容包括竹林七賢、羽人戲龍、仙人持幡等。此外,在墓室填土中還發現了大量散落的模印畫像磚,這些散磚的大面(模印畫像的磚面可稱為側面和端面)上多有刻劃文字,用以標識此磚對應的畫像內容和位置。2016年,部分散磚藉《南朝真跡》一書以五面拓印的形式刊布,是為本文展開討論的基礎[2]。
《南朝真跡》出版后,圍繞南朝拼砌磚畫的討論逐漸增多,其中以鄭巖先生(以下略去敬稱)和王漢的研究最重要,但他們多關注七賢畫像的制作,而對其他畫像探討較少[3]。本文嘗試以鹵簿[4]題材的拼砌磚畫為切入點,對這批散磚進行觀察。此前,丹陽的仙塘灣[5]、金家村、吳家村[6]三處南朝墓葬均出土了較為完整的鹵簿畫像,但磚面刻劃文字的情況不太明晰。獅子沖M1、M2的情況恰與之相反,我們雖無緣得見完整畫像,但憑借出土散磚得以掌握部分刻劃文字的信息。綜合兩批材料,我們可以對單幅畫像的拼砌方式有進一步的了解。此外,七賢畫像的傳承序列前人多有討論,甚至以此作為解決墓葬年代問題的關鑰[7]。筆者認為,同墓所出的其他畫像應當被予以類似關注,這對我們進一步了解粉本關系,特別是齊梁禪代之后帝陵畫像可能存在的內在變化很有幫助。
一、鹵簿畫像與刻劃磚銘
為便于討論,謹將獅子沖南朝墓出土鹵簿畫像散磚信息制成表一。

表一// 獅子沖南朝墓出土鹵簿畫像散磚信息匯總表[8]

續表

圖一// 騎馬武士畫像

圖二// 執戟武士畫像
首先,對于鹵簿畫像內容,特別是南朝磚畫中鹵簿畫像的構成,前人已有不少認識,此不復述。本節重點討論畫像內容與刻劃磚銘之間的關系[10]。
(一)騎馬武士
此類畫像對應的磚銘是“具張”,“張”與“裝”韻腳相同,可以互通,故“具張”就是“具裝”。具裝指戰馬所披的鎧甲,楊泓對其形制和實物資料的發現情況,已有完整論述。他認為,完備的馬鎧在三國時期雖已出現,但配備程度并不高,直到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馬鎧才在軍中普遍配備[11]。完整的“具張”畫像見于仙塘灣墓的西壁和金家村墓的東、西壁(圖一)。畫像主體為一人一馬,人戴冠,著裲襠鎧,肩背弓,胯下戰馬則配備成套具裝,英武矯健。《宋書·劉元景傳》載:“(安都)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12]其所述名物正與畫像對應。
(二)執戟武士
此類畫像對應的磚銘是“笠戟”,應即“立戟”[13]。完整的畫像見于仙塘灣墓西壁和金家村墓東、西壁(圖二)。畫中一人站立,頭戴外罩籠冠的梁冠,身穿廣袖長袍,手執戟,腰佩劍。仙塘灣墓執戟武士畫像上端殘缺,金家村墓畫像完好,長戟頂端還有兩段飄帶。

圖三// 傘扇侍從畫像
(三)傘扇侍從
此類畫像對應的磚銘是“迅繖”[14]。完整的畫像見于仙塘灣墓西壁和金家村墓東、西壁(圖三)。畫中兩人前后站立,頭戴介幘,穿上衣,著縛褲,分別執障扇與傘蓋。前人相關討論中以劉未所述最為完備,他從畫像流變和等級制度兩方面勾勒了傘扇儀仗在魏
晉南北朝時期的變化。劉文認為,傘扇組合流變的關鍵在于扇的形制變化,大致呈現了“無(曹魏至東晉早期)→桃形扇(東晉晚期)→上圓下方雉尾扇(南北朝)”這一趨勢[15]。對比畫像資料,可知在南北朝時期,傘扇儀仗畫像中的“扇”即上圓下方形雉尾扇這一觀點基本成立。

圖四// 仙塘灣墓出土“右迅苐一”磚銘
那么,“迅繖”磚銘何解?“繖”的字義較易理解,其與“傘”相通,指鹵簿中的傘蓋。而“迅”的含義不明。仙塘灣出土“右迅苐一”(圖四)磚銘為我們提示了最基本的前提,即“迅繖”兩字可以調換順序,屬并列關系的聯合短語。既然“繖”指傘蓋,那么“迅”是否就是與傘蓋搭配出現的雉尾扇呢?本文擬提出一種推測,以供討論。中古文獻常見“迅羽”一詞,泛指運動迅捷的鳥類,如張衡《西京賦》:“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薛綜注:“迅羽,鷹也。”[16]又如謝朓《野鶩賦》:“落摩天之迅羽,絕歸飛之好音。”[17]這類偏正詞語在使用過程中,可能會發生修飾成分替代主語進入習慣用語的情況[18]。也就是說,“迅”有可能表達“羽”的含義,與“繖”構成聯合短語進入刻劃磚銘的系統。當然,這一推測還需要更堅實的語言學證據支撐。
(四)騎馬鼓吹
此類畫像對應的磚銘是“家脩”。完整的騎馬鼓吹畫像見于仙塘灣墓東壁和金家村墓東、西壁(圖五)。畫中三騎相繼,上方環繞各種花卉,樂手皆頭戴冠,著廣袖長袍,由南向北依次演奏建鼓、排簫和笳[19]。關于“家脩”銘文,素無善解,近年祁海寧猜測“脩”或通“佾”,指樂舞,可備一說[20]。
二、刻劃磚銘位置的復原嘗試
前文介紹了散磚和完整畫像的基本信息,下面試圖通過獅子沖M1、M2所見散磚銘文復原丹陽二墓壁畫的拼砌,這也是借助完整畫像進一步探賾磚銘含義的嘗試[21]。如磚銘中的“左”“右”,是依據平面畫像還是墓室空間確定?磚銘中序號的排列規則又是怎樣?這些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圖五// 騎馬樂隊畫像
(一)騎馬武士畫像的拼砌復原
就騎馬武士畫像而言,我們可將圖一的三幅畫像與獅子沖M2出土“具張”磚銘散磚側面的殘存畫像進行比勘(表二)。
依據簡報披露的畫像磚拼砌方式,可以將表二的對應關系制成磚銘位置示意圖(圖六)。
雖然圖六所示大部分磚銘都是筆者推測補齊的,但依據能夠對應到畫像相應位置的磚銘推斷,其余磚銘的位置也是大致可靠的。通過圖六,我們已不難看出畫像磚的砌筑規律。一、磚銘中的“左”“右”,是依據墓室空間確定的,即當背靠北壁、面向墓門時,左手邊的東壁畫像即為“左”,右手邊的西壁畫像即為“右”;二、工匠只對構成畫像主體的墓磚進行編號,而主體以外用作補白的花紋磚則不予編號;三、順磚層是一個整體,由下往上進行編號;四、不論丁磚、順磚,一律由南向北進行編號。為了驗證這一規律,接下來討論騎馬鼓吹畫像的拼砌。
(二)騎馬鼓吹畫像拼砌復原
就騎馬鼓吹畫像而言,我們可將圖五的三幅畫像與獅子沖M1、M2出土“家脩”磚銘散磚側面的殘存畫像進行比勘(表三)。
依前文的方法,我們可以將表三的對應關系制成磚銘位置示意圖(圖七)。
雖然獅子沖M2提供的刻劃磚銘依舊很少,但已知的五塊散磚已足夠我們確定其余磚銘的位置,由此得到的圖七與上文所歸納的四條規律均吻合。參考這些規律,我們便可順利復原另外兩種畫像的拼砌。
(三)執戟武士與傘扇侍從畫像拼砌復原
與前文同理,我們將圖二、三的六幅畫像與獅子沖M1、M2出土“笠戟”“迅繖”磚銘散磚側面的殘存畫像進行比勘(表四)。
于是,我們可以將表四的對應關系制成磚銘位置示意圖(圖八)。
經過磚銘位置的復原,鹵簿畫像的拼砌規則已基本清楚。在復原過程中,筆者可確定金家村墓與獅子沖M2出土散磚的鹵簿畫像出于同一粉本,兩者在對應畫像磚上的人、物相對位置,以及線條細節幾乎一致,而與仙塘灣、獅子沖M1的鹵簿畫像明顯不同[24]。根據仙塘灣墓畫像推定磚銘位置雖也可行,但每塊磚上的畫像都存在較大差異,甚至個別畫像磚位置也與磚銘抵牾,同樣的情況在比勘獅子沖M1散磚畫像時同樣會遇到。曾布川寬早已指出,仙塘灣墓與金家村墓的羽人戲虎磚畫為同模制作,而鹵簿和七賢畫像均不同模[25]。借助本節總結的拼砌規則,我們正可以進一步考慮曾布川寬的觀察結果,并試析獅子沖墓出土所有散磚畫像與其他墓例的關系。
三、散磚畫像的來源與性質
比較不同的畫像,需要從拼砌方法和畫像樣式兩個角度切入,以下分別述之。

表二// 獅子沖M2出土散磚與仙塘灣、金家村墓騎馬武士畫像比勘表

圖六// 騎馬武士畫像磚銘位置示意圖(左為東壁,右為西壁)[22]

表三// 獅子沖M1、M2出土散磚與仙塘灣、金家村墓騎馬鼓吹畫像比勘表
(一)拼砌方式

圖七// 騎馬鼓吹畫像磚銘位置示意圖(左為東壁,右為西壁)[23]

表四// 獅子沖M1、M2出土散磚與仙塘灣、金家村墓執戟武士、傘扇侍從畫像比勘表
綜合《南朝真跡》和簡報公布的數據,可知獅子沖墓出土每塊鹵簿畫像磚預設的尺寸是大致相同的,即長33.5、寬14.5、厚4.5厘米左右。由此拼出的完整畫像尺寸可依據上節的復原結果計算得到,分別為:高32.5、寬33.5厘米(騎馬武士),高41.5、寬13.5厘米(執戟武士),高41.5、寬27厘米(傘扇侍從),高41.5、寬67厘米(騎馬鼓吹)。不難看出,單磚尺寸應當是基于對畫像的完整認識進行設計的,而由于長度略大于厚度的7倍,故七塊丁磚加上彼此間粘合的縫隙恰好與一塊順磚長度相當,這一設計的用意在金家村墓所見騎馬武士和騎馬鼓吹畫像中體現得最為清晰。仙塘灣墓與金家村墓的鹵簿畫像,除騎馬樂隊上行順磚拼砌方式不同外,其余畫像均與上節所繪的各磚銘位置示意圖一致[26]。騎馬樂隊的差異處,王漢已經指出,即仙塘灣墓該畫像上行順磚的正中位置是一塊整磚,而金家村墓該位置為兩磚接縫。根據這一特點和表三—4的對應關系,可知獅子沖M2的騎馬樂隊畫像拼砌方式與金家村墓同,這也對應了其畫像內容的異同關系。

圖八// 執戟武士(東壁)與傘扇侍從(西壁)畫像磚銘位置示意圖

表五// 出土南朝拼砌磚畫樣式對應表[34]
鹵簿畫像磚以外,獅子沖墓出土其他畫像磚的單磚尺寸也大致與此相同,由制坯、燒造導致的長、寬誤差不大于2厘米,厚度誤差不大于0.5厘米。所以,它們的拼砌方式也就不難按照前文所述進行復原了,本文于此不作展開。
(二)畫像樣式的來源與性質
依照上節比勘鹵簿畫像的方法,筆者將獅子沖兩座墓出土所有畫像可辨的散磚與其他墓例所見畫像進行比較,發現其與吳家村、金家村兩座墓的部分畫像存在同一粉本現象,且互有交錯,具體表現為:M1與金家村墓的直閣將軍畫像[27],并與吳家村墓的羽人戲龍、羽人戲虎、七賢畫像[28]出于同一粉本;M2與金家村墓的獅子[29]、直閣將軍畫像[30],并與吳家村墓的羽人戲龍[31]、羽人戲虎[32]、七賢畫像[33]出于同一粉本。于是,將町田章、曾布川寬、王漢諸家的觀察結果與本文結合,便可把幾處南朝拼砌磚畫粉本關系展現出來(表五)。
由表五可以看出,獅子沖M1、M2散磚畫像與吳家村、金家村墓拼砌磚畫關系最為密切。曾布川寬推測金家村墓墓主是齊明帝蕭鸞,吳家村墓墓主是齊和帝蕭寶融[39]。王志高、許志強、張學鋒推測獅子沖M1墓主是梁昭明太子蕭統,M2墓主為蕭統生母丁貴嬪[40]。筆者認同這些成果對墓主身份的推測。蕭鸞葬興安陵在永泰元年(498年),蕭寶融葬恭安陵在中興二年(502年),丁貴嬪葬寧陵在普通七年(526年),蕭統葬安陵在中大通三年(531年),雖然其間齊梁禪代,帝室陵區發生變化,但四座墓年代畢竟相隔不遠,出土同一粉本系統的畫像也很合理。
由獅子沖墓發掘簡報可知,這些散磚出土于墓室填土,原先可能作為普通墓磚用于磚室營建,其性質當為前代使用剩余的“廢磚”。通過本文注34、35、36也可獲知,散磚畫像并不同于正式砌筑在獅子沖墓室東西兩壁的完整畫像,而是另有來源,其與可能是興安陵、恭安陵的丹陽金家村、吳家村墓具有緊密聯系。進一步推測的話,這些散磚可能原本就是營建蕭齊末代帝陵級墓葬時的剩磚,蕭齊亡后,蕭梁帝室采用了新的墓室畫像粉本,故這些剩磚無法繼續參與完整畫像的拼砌,轉而被用作一般墓磚。這一推測是否可行?或許梁代的修禮行為可以為我們提供參照。
(三)齊、梁間墓室畫像的因革
齊梁禮制是一個傳承有序、逐漸完善的過程。齊永明年間開撰《五禮儀注》,終齊之世未成,梁天監元年(502年)重新開展這一工作,詔諸儒撰修五禮,至普通五年(524年)方才繕寫校訂完畢。《五禮儀注》以外,何佟之、任昉、明山賓等禮學家,甚至梁武帝本人都參與了諸多禮樂制度的修訂,禮制逐漸完善[41]。
墓室畫像雖不載于現存禮典,但其形式、內容皆與禮制關系緊密。考慮到南朝儀制遠較北朝精密,齊、梁又為其最成熟的階段[42],墓室畫像不可能孤立于這一時代特征,而僅在粉本系統內部傳承、損益、改動。筆者認為,帝陵級墓葬所用拼砌磚畫的樣式,應該和禮制在齊、梁間的因革關系大同小異,即保持由獅子、直閣將軍、羽人戲龍、羽人戲虎、七賢、鹵簿諸種畫像組成的基本配置不變,而單幅畫像粉本存在多種選擇的空間。在“五禮之書,莫備于梁天監”[43]的蕭梁初期,帝陵級墓葬改換一批新的畫像粉本是契合于禮制需求的,獅子沖墓的年代也正處在這一時期。其散磚畫像樣式在今丹陽、南京的存廢之別,恰好為觀察這一變化提供新的視角。
結語
本文中,筆者以獅子沖南朝墓出土鹵簿畫像散磚為切入點,復原了刻劃磚銘在完整畫像中的位置關系,并循此路徑,比勘全部散磚畫像與其他墓例所出拼砌磚畫。經過比勘,筆者發現獅子沖M1、M2所出散磚畫像與丹陽金家村、吳家村墓的部分畫像存在同一粉本現象,且互有交錯。考慮到散磚出土于墓室填土,并沒有參與完整畫像的拼砌,筆者推測其為蕭齊末代帝陵級墓葬拼砌磚畫的剩磚,在梁武帝時期被作為一般墓磚重新使用。
散磚用途的轉變,促使本文提出齊梁禪代之后,帝陵級別墓葬畫像粉本也可能隨之發生變化。而南京西善橋宮山、罐子山,以及石子崗M5、小村M1等蕭齊以后墓葬所見畫像與丹陽地區蕭齊帝陵畫像粉本完全不同也可佐證這一可能性的存在。若這一轉變成立,那么營建主持方對于墓室畫像粉本選擇的主觀性就有必要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中,南朝時期拼砌磚畫粉本的多樣性也就值得我們注意[44]。
[1]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棲霞獅子沖南朝大墓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5年第4期。
[2]南京市博物館總館、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編:《南朝真跡:南京新出南朝磚印壁畫墓與磚文精選》,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6年。
[3]a.鄭巖:《前朝楷模,后世之范:談新發現的南京獅子沖和石子岡南朝墓竹林七賢壁畫》,《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300—311頁;b.王漢:《從壁畫磚看南京西善橋宮山墓的年代》,《東南文化》2018年第2期;c.王漢:《論丹陽金家村南朝墓竹林七賢壁畫的承前啟后》,《故宮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3期。
[4]發掘簡報均以“出行儀仗”稱之,本文為行文簡潔,且更貼近時代語言,以“鹵簿”替代。“鹵簿”一詞出自蔡邕《獨斷》“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其中“鹵”指大楯,儀仗出行時執盾者居外側,而儀仗有部伍次序,皆著之簿籍,故曰“簿”。參見孫機:《兩唐書輿(車)服志校釋稿》卷一,《中國古輿服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32頁。
[5]南京博物院:《江蘇丹陽胡橋南朝大墓及磚刻壁畫》,《文物》1974年第2期。
[6]南京博物院:《江蘇丹陽縣胡橋、建山兩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
[7]關于西善橋墓年代問題的討論成果研究者多有羅列,搜羅較全面者見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市雨花臺區文化局:《南京雨花臺石子崗南朝磚印壁畫墓(M5)發掘簡報》,《文物》2014年第5期。
[8]表一中各磚的順序按鹵簿的順序排列。依據現今發現的完整鹵簿拼砌磚畫,從墓門到墓室后壁鹵簿的排列順序為:騎馬武士(具張)、執戟武士(笠戟)、傘扇侍從(迅繖)、騎馬鼓吹(家脩)。
[9]“訖”前疑有“行”字。
[10]〔日〕曾布川寬著、傅江譯:《六朝帝陵:以石獸和磚畫為中心》,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83—91頁。
[11]楊泓:《中國古代的甲胄(下篇)》,《考古學報》1976年第2期。
[12]南朝梁·沈約:《宋書》卷七十七,中華書局1974年,第1984頁。
[13]仙塘灣南朝墓出土相同刻劃磚銘,簡報釋為“右垣戟苐三”。細辨“垣”字形,亦可釋作“笠”,今據辭例改釋。
[14]吳家村墓的傘扇侍從畫像未見圖片,只有文字描述。金家村墓的磚銘亦未見圖片,整理者猜測其為“護迅”,今據辭例可知應為“繖迅”之訛。
[15]劉未:《魏晉南北朝畫像資料中的傘扇儀仗》,《東南文化》2005年第3期。
[16]南朝梁·蕭統輯:《文選》(宋尤袤刻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第178頁。
[17]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65年,第2920頁。
[18]類似者如“黃白”,本是對金、銀兩種物質顏色的描述,卻常常單獨出現以指代金(銅)、銀,如裴松之注引《魏略》“(王)修為司金中郎將,陳黃白異議。”(《三國志》卷十一《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中華書局1959年,第347頁)甚至引申為修煉行為,如“黃白術”“黃白事”等。
[19]關于第三名樂手所持樂器,丹陽三墓的發掘簡報和町田章均稱之為“塤”,曾布川寬稱之為“笳”,結合文獻,當以后者為是。
[20]祁海寧:《南京新出南朝磚拼壁畫墓價值初探》,《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5年第5期。
[21]吳家村墓的鹵簿畫像未見公布,故本節僅討論仙塘灣、金家村兩處墓葬。
[22]東、西壁磚銘位置示意圖均為面向墓壁時的視角。圖中磚銘位置僅為示意,劃線者為表二包含的磚銘,其余均為筆者為方便論述,依據墓磚砌筑規律補齊的磚銘,下同。此外,表二—6、7所示仙塘灣墓與金家村墓畫像位置不同,筆者依據金家村墓畫像確定圖六的磚銘位置,選擇原因將在下節說明。
[23]表三中有獅子沖M1出土的磚銘三種,但其磚側畫像難以與丹陽二墓的畫像對應。而M2散磚與仙塘灣墓畫像的對應情況與表二相似,故圖六仍憑借獅子沖M2出土散磚與金家村墓畫像確定磚銘位置。
[24]盡管表三—2的對應無法吻合,但僅此一例,不影響觀察結果。
[25]同[10],第135頁。原文“模”作“范”,為免歧義,本文替換表述。
[26]王漢對南京及周邊相關南朝墓磚畫的拼砌方式做過全面觀察,其中與本文相關的幾組畫像亦有所涉及,唯仙塘灣墓的騎馬武士、執戟武士和傘扇侍從畫像,作者認為拓片不清難以判斷。其實根據磚畫拓片,其拼砌方式是可以明確的。
[27]同[2]。明確了磚銘在完整畫像中的位置,我們便可以結合磚銘殘存筆畫對《南朝真跡》中的部分釋文進行訂補。M1的“直閤”銘文磚中(第359—365頁),M1︰Z353可補為“【左直】閤上四訖”,M1︰Z392可補為“【右】直閤下二”。另,M1︰Z36“左直閤中行四”的磚側畫像與金家村、吳家村墓皆無對應,但其磚銘風格也與其他磚明顯不同,可能另有來源。
[28]同[2]。M1的七賢畫像中(第409—415頁),M1︰Z200可補為“向下行卅【四】”。
[29]同[2]。M2的“師子”銘文磚中(第433—447頁),M2︰Z499可補為“某粘又銘中……左師子上行【五】”,M2︰Z136可訂為“右師子下行三”。
[30]同[2]。M2的“直閤”銘文磚中(第448—457頁),M2︰Z217可補為“右立閤【中行三】”,M2︰Z444可訂為“右直閤上三”,M2︰Z435可補為“右直閤中【一】”,M2︰Z135可補為“右直閤下【四】”,M2︰Z413可訂補為“左直閤下行二”。需要說明的是,《南朝真跡》一書中獅子沖M2的“直閤”銘文磚編號有誤,“M1”應統一為“M2”,此點承整理者許志強先生告知,謹致謝忱。
[31]同[2]。M2的“大龍”銘文磚中(第458—485頁),M2︰Z236可補為“大龍上行五十【二】”,M2︰Z421可補為“大龍中行十【九】”,M2︰Z226可補為“大龍中行卅【八】”。
[32]同[2]。M2的“大虎”銘文磚中(第486—516頁),M2︰Z153可訂補為“【大】虎中行卅九”,M2︰Z336可補為“大虎中行五十【九】”。
[33]同[2]。M2的七賢畫像中(第528—558頁),M2︰Z86可訂為“向上行卅【二】”,M2︰Z230可補為“向下【行廿二】”。
[34]出土拼砌磚畫的還有南京西善橋罐子山墓和鐵心橋小村M1,因兩墓出土畫像磚較少,且與表五所含墓例沒有對應,故不列入。參見羅宗真:《南京西善橋油坊村南朝大墓的發掘》,《考古》1963年第6期;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市雨花臺區鐵心橋小村南朝墓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5年第2期。另,表中獅M1、獅M2均指獅子沖墓出土散磚,與墓室兩壁發現的完整畫像無關。
[35]需要指出,獅子沖M1墓室西壁靠甬道處保存有完整的羽人戲虎畫像,但與散磚所示畫像并不相同,與吳家村墓七賢畫像同一粉本的是散磚。
[36]天人畫像在獅子沖M2東壁保存有“仙人持幡”部分,與M2出土散磚比較,并不相同,與吳家村也非同一粉本。
[37]和羽人戲虎畫像一樣,獅子沖M1墓室西壁留存的七賢畫像與散磚所示畫像并不相同,而與吳家村墓七賢畫像同一粉本的仍是散磚。吳家村墓西壁畫像殘缺不全,但參照東壁的情形,以及部分散磚如M2︰Z453、M2︰Z380等與殘存畫像相合來看,推測西壁畫像也和獅子沖墓散磚畫像同一粉本問題不大。
[38]石子崗M5發掘者認為,此墓與宮山墓出土“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畫像“不僅是同一粉本,而且是同一模范制作出來的”,參見《南京雨花臺石子崗南朝磚印壁畫墓(M5)發掘簡報》,第37頁。
[39]同[10],第21—28頁。
[40]a.王志高:《再論南京棲霞獅子沖南朝陵墓石獸的墓主身份及相關問題》,《六朝建康城發掘與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85—295頁;b.許志強、張學鋒:《南京獅子沖南朝大墓墓主身份的探討》,《東南文化》2015年第4期。
[41]a.閆寧:《中古禮制建設概論:儀注學、故事學與禮官系統》,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80—133頁;b.顧濤:《漢唐禮制因革譜》卷四《東晉南朝》,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第545—653頁。
[42]皮錫瑞以降的經學史家中,不少人視魏晉南北朝為“禮學中衰時代”,但事實并非如此。南朝學者尤重禮學研究,著作豐贍,其中以九世傳經的廬江何氏作用最顯,特別是何佟之在齊梁時期的修禮表現十分奪目。詳細辨析參見顧濤:《重新發掘六朝禮學:論何佟之的經學地位》,《國學研究》第39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37—264頁。
[43]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卷首第三“禮制因革上”,光緒六年(1880年)江蘇書局重刊本,第16頁。
[44]a.〔日〕町田章著、勞繼譯:《南齊帝陵考》,《東南文化》1986年第1期;b.謝振發:《北魏司馬金龍墓的漆畫屏風試析》,《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1期,2001年;c.同[3]b;d.同[3]c。相比之下,筆者更認同曾布川寬的說法,即這種變化并不一定發生在同一粉本系統內部,多種粉本系統的存在也是可能的。如《歷代名畫記》卷三《述古之秘畫珍圖》所記“諸鹵簿圖”,自注曰“不備錄,篇目至多”即為一證,見唐·張彥遠著、俞劍華注釋:《歷代名畫記》,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第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