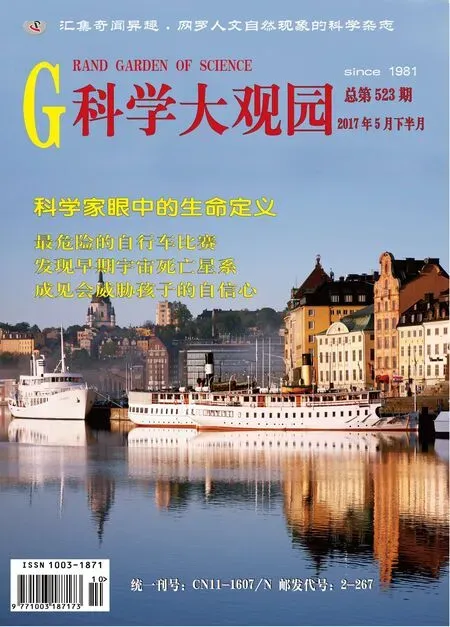《血疫》與惡魔共舞的普雷斯頓
徐琳玲
2020年的春節,被新冠肺炎疫情“封鎖”在家中的無數城市中青年通過各種網絡平臺,在現實和鏡頭雙重營造的驚悚氣氛中,觀看了這部講述人類和埃博拉病毒作戰的科學題材迷你劇——《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一只烏鴉在叢林上空盤旋,拍著翅膀,飛進一座富有熱帶風情的花園洋房。敞開大門的起居室,桌上擺設著精美的法式早餐,有牛角包、玫瑰色的開胃酒、果醬等等。烏鴉落在桌子上,開始肆無忌憚地啄食食物。桌旁一把打翻的椅子上——一名臉色蒼白的高個白人男子發出喘息聲,額頭上汗如雨下。
胖乎乎的黑人女仆不安地打電話催出租車。她吃力地攙扶著男子走出洋房,和司機一道把他塞進開往機場的出租車。在飛機上的衛生間里,男子看著鏡子里的自己,他的臉上此時長滿黃豆大的暗紅色丘疹,越來越密集,眼球血紅。
……
在內羅畢醫院的急診室里,男子呼吸越來越困難。主治醫生意識到病人可能被什么噎住了,拿起管子插進了他的口中。突然間,男子的口腔里噴射出大量黏糊糊的黑紅色液體,濺落在醫生的白大褂上、臉上、手上。醫生下意識地用手抹去濺在嘴上的血污,他的眼角四周星星點點。
在神秘病毒攻擊下,男子的內臟、肉體徹底“融化”成了一攤“肉湯”。
首播于2019年5月的大熱美劇《血疫》,改編自美國科學記者、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頓最負盛名的非虛構作品。1994年初版后,《血疫》(英文原著名為《高危區》)連續61周占據《紐約時報》非虛構類暢銷書榜首。25年來,已成為科學報道和寫作的經典之作。
普雷斯頓和高危病原體、公共衛生問題打了近30年交道,被公認為這一領域的“王牌”記者、作家,獲獎無數,成績斐然。他對潛在危機的洞察力和預見性,以及生動、精準的故事講述能力,甚至影響了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防御政策。
2020年2月底,我通過中間人把一份采訪提綱轉交給普雷斯頓,提及正在中國發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經歷諸多曲折,等他回復希望通過FaceTime接受采訪已到4月——此時,新冠肺炎已成為蔓延至全球的大流行病,美國成為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全球累計確診病例數、累計死亡病例數最多的國家。美國死亡病例最多的州是紐約州。
普雷斯頓和家人居住的普林斯頓小鎮,距美國頭號重疫區紐約市僅40英里,“我女兒一家住在紐約的布魯克林,我和妻子很為他們擔心。”
“我確實非常非常憂慮。”他談到了被疫情全然改變的日常生活、小鎮醫院的資源緊張、美國聯邦政府應對緊急狀態的糟糕表現、人類和病毒之間的戰爭與共存——“現在窗外很安靜,藍天空蕩蕩的,沒有一架飛機飛過。這種安靜,讓我想起了‘9·11事件之后的景象。”
“我一直在留心觀察,已做了很多筆記,但還不確定是否會寫一本關于新冠病毒的書。”
進入P4實驗室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一種被命名為“獲得性免疫缺乏癥”(AIDS)的怪異疾病在北美、歐洲、澳洲蔓延。1999年,病理學家和病毒學家把HIV病毒的源頭逐漸追溯到非洲叢林里的黑猩猩和某幾種猴子身上。
一種以非洲靈長類動物為宿主的病毒,最終跨物種地感染了人類,引發遍布全球的流行病。
1990年代初期,已在美國科學報道領域占有一席之地的普雷斯頓敏銳地預感到:來自非洲叢林的HIV病毒很可能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一些致命的病毒很快會從不再遙不可及的森林里走出來,入侵人類的身體,借助頻繁、便捷的現代交通,在全世界迅速蔓延開來,將人類的一部分“抹去”。
在與一位病毒學家的談話中,他得知就在距離美國政治心臟華盛頓不遠的雷斯頓市,美軍的科學家們發現一批商用的進口實驗用猴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為防止疫情暴發,科學家和士兵們聯手,撲殺了這一起美國本土的潛在疫情。結果證明:這是一種新型的埃博拉病毒,與史上最強的、致死率高達75%的扎伊爾埃博拉病毒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埃博拉病毒是人類已知最致命的病原體,屬生物防護四級。在P4實驗室,科學家們研究、擺弄著對人類最危險的病原體,包括埃博拉、它的姐妹病毒馬爾堡、炭疽熱病菌等等。大名鼎鼎的HIV病毒只是P2級,而SARS和正在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則為P3級——它們的病死率分別為10%和2%左右,雖然其傳染性極強。
采訪中,普雷斯頓最終獲得準許,可以穿著生物防護服進入美軍研究埃博拉病毒的P4實驗室。
他跟著一位年輕女科學家進入實驗室,經過一道又一道門,按步驟做清潔、消毒和隔離程序。最后,他們來到P3和P4之間的隔離區(也叫“灰色三區”)。女科學家從墻上拿下一件生化防護服,然后向他示范如何正確地穿上。等他穿上生化防護服后,一按氣壓閥,氣體就進入防護服。

普雷斯頓(右)和主演在首映式上。

“接下去,我們將要打開最后一道鋼質大門,進入到P4實驗室。她走過來,用雙手抓住我的肩膀,透過頭盔緊緊盯著我的眼睛,然后說——理查德,你感覺怎么樣?你還好嗎?我在觀察你的瞳仁收縮,看看你驚恐癥有沒有發作的跡象。”后來,他得知類似的驚恐癥有時會發生在第一次進入P4實驗室的人身上。
“你看到的這一劇情,其實是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我把它寫進了劇本里。”他在電話那頭說。Fox和美國國家地理一同買下《血疫》的影視劇改編權后,普雷斯頓也參與了部分編劇工作。
普雷斯頓把這個故事細節疊加到了女主角、美軍病理學家南希·杰克斯的身上。劇中,南希帶著新招募參與埃博拉項目的士兵進入P4實驗室。在進入高危區的最后一道大門前,這個平日總是刻意擺出男性氣概、愛用輕佻口吻和女上司說話的大兵開始出現呼吸困難。
防疫斗士獎
每進入一個艱深的專業領域,普雷斯頓對自己的要求是像去讀這個領域的研究生一樣鉆進去。幾乎每完成一部作品,他都會在這個專業領域收獲最高的認可和褒獎。
1984年出版的講述天文臺和天文學家的《破曉》,讓他獲得了美國物理學會獎。1994年的《血疫》,讓他拿到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頒發的防疫斗士獎——這是CDC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次把該獎頒給一個非醫學和公共衛生領域的人。
事實核查和對精準的追求,是普雷斯頓贏得科學家們深度信任的法寶。“初稿寫完后,我常常會打電話給他們,讀相關段落給他們聽,一次又一次地征求他們對準確表達的意見。但是,我從來不給他們發書面的草稿。”
1977年,23歲的普雷斯頓來到東海岸的普林斯頓大學讀研究生時,遇到了對他的職業和人生有著深遠影響的美國“非虛構寫作大師”約翰·麥克菲。
麥克菲被公認為是美國“創造性非虛構寫作”的開拓者,在半個世紀里培養了一大批杰出的記者、編輯和作家,弟子遍布《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紐約客》《時代》《國家地理》等各大主流媒體。
“麥克菲教我們詞句組成的準確性,要絕對尊重事實。把事實調查清楚很重要,如果一名搞技術或科研的讀者發現一個錯誤,那整個作品的可信度都被搞砸了。如果一部作品經過事實核查,甚至連一個普通讀者都能感覺得到。它會很嚴密,就像你關上新車的門時沒有嘎嘎的響聲一樣。”在和另一位非虛構寫作者的訪談中,他如此分享心得。
惡魔的拼圖
在《血疫》的開頭,普雷斯頓用冷靜、優美又令人毛骨悚然的筆觸,還原了1980年僑居于肯尼亞的法國男子夏爾·莫內(化名)生命中的最后15天,病毒如何一步一步把這名強壯的男子“融化”為一具不斷嘔出血水、血泥的行尸走肉,以及他究竟從何處感染上埃博拉的親姐妹——馬爾堡病毒。
當時,內羅畢醫院有一位醫生曾調查過莫內的病例,一位來自美國的病毒學家也曾調查過他的流行病史。這兩位專業人士和他們的調查,都成為普雷斯頓還原“惡魔拼圖”的重要線索。
對普雷斯頓來說,這些還遠遠不夠。最后,他進入了非洲中部的腹地。
“在肯尼亞,我去了莫內最可能感染上病毒的那個洞穴,我去了內羅畢醫院,到了他倒下的急癥室。在調查中,我一路上拍照,幫助自己更好地理解真實場景是怎樣的。我收集到了很多有關他的信息,譬如,那只棲息在他房屋頂上的鳥,所以我能夠描述這些。我寫的有關莫內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實的、精確的。”
經過詳盡的調查和摸排,醫生和來自美國的病毒學家相信:莫內和另一位“零號病人”的感染之地,很可能是在肯尼亞埃爾貢山上的奇塔姆洞穴。1988年,一位10歲的丹麥男孩也在出入洞穴的數天后出現可怕癥狀,很快暴死于馬爾堡病毒的攻擊。他的父母為肯尼亞的一家國際救濟機構工作,他們當時開車帶著孩子領略非洲大陸神奇而危險的美景,曾到奇塔姆洞穴探險。
1993年8月,在當地導游的帶領下,普雷斯頓來到隱藏著惡魔的洞穴。在洞口,他穿上生化防護服,準備好消毒藥劑、用具,為自己搭建起了一個臨時的“P4實驗室”。
5年前,為美軍工作的“病毒獵手”尤金·約翰遜鎖定奇塔姆洞穴后,曾帶著一支生物專家團隊對洞穴進行考察、取樣,他們帶來幾十只“哨兵動物”,又從洞穴里采集了幾萬只各種品種的昆蟲,最終一無所獲。
為普雷斯頓充當導游的當地獵人告訴他:他兒時經常進洞玩,當地一直傳說洞穴里藏著一種惡魔(疾病)——人若在洞里撞上了,就會化成肉湯,炸開,“(人身上)每一個洞眼都向外飆血。”相比之下,讓許多人感到毛骨悚然的艾滋病輕微得就像打了一個噴嚏。
在洞中,普雷斯頓穿著厚厚的生化防護服在黑暗中笨拙地行走、爬行。一路上,他看到了大象的骸骨、鐘乳石、蝙蝠、蜘蛛和形形色色的昆蟲,一邊留心著石頭上滑膩的果綠色泥漿——那是果蝠的糞便。
病毒學家們認為:把馬爾堡和埃博拉病毒感染給人類的中間宿主,很有可能是生活在洞里的果蝠。莫內、丹麥男孩在洞穴里接觸過果蝠的糞便,病毒通過皮膚上的傷口,進入到他們的循環系統。
在洞中,普雷斯頓忍不住琢磨起這些危險排泄物的形狀和顏色,覺得像一種牡蠣的烹飪做法,“有一瞬間我難以控制地琢磨起了蝙蝠糞便的味道。”他狠狠提醒自己——在最高危的生物四級區域,想吃屎的念頭是一種大腦的胡鬧。
“可以說,這是我的寫作原則——你要盡可能到事件發生的現場。你必須掌握一切可能掌握到的信息。”
大自然的復仇
但是,在這張真相的拼圖上,仍有許多他無法找到的空白——關于那些被埃博拉病毒“抹去”生命的人,譬如那位得知自己感染后想盡一切辦法辦理出國留學手續的年輕修女瑪英嘉,她到底在想些什么;譬如那位馬里迪鎮醫院之難中第一位死亡的當地教師,他到底是引爆這次疫情的“零號病人”,還是在醫院因共用針頭被其他人感染的?
HIV、埃博拉和馬爾堡都是來自非洲雨林腹地的“惡魔”。事實上,埃博拉原本是剛果境內一條河流的名字。
近半個世紀以來,源源不斷出現的新顯病毒——HIV、埃博拉及其姐妹馬爾堡、SARS、MERS(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和當下威脅全人類的新冠病毒,讓普雷斯頓越發確信一點:這其實是地球自身啟動的一種免疫反應,“甚至,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種大自然的復仇。”
“這些病原體也是大自然的力量之一。當人類這一寄生物種大量地繁衍,對生態系統毫不留情地破壞、摧毀,就使得原本遠離人類的病毒有越來越多機會和人類接觸,入侵人類,甚至會引發像今天這樣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對人類生命、整個社會系統造成摧毀性的打擊。”
“如果人類不從中吸取教訓,我確信未來這樣的大危機還會頻頻地重演。”他聲音沉重地嘆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