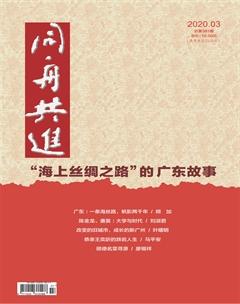1921年杜威的廣州之行
谷小水


1919年4月至1921年7月,美國著名教育家、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來華講學,在華活動兩年有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非常轟動的文化事件。杜威訪華時期,恰逢中國南北分立,南北兩大政權的對峙已經持續數年之久,但作為學者的他未為這種政治格局所囿:抵華之初,曾在上海與孫中山有過一面之緣;離華前夕,又踏足廣東政府治下的廣州。杜威與孫中山討論知難行易以及對廣東地區的實地考察,使他對中國問題有著更為全面的觀察和思考。
與孫中山討論知難行易
在中國知識界的邀請下,1919年4月30日,杜威偕妻女一行抵達上海,開啟了在華講學之旅。此時的孫中山正蟄居滬上,專心著書立說,經過長期的思考,他的“知難行易”學說業已成熟,《孫文學說》即將付梓,非常渴望能夠聽到第一流學者對自己理論的批評意見和建議。
與杜威晤談之前,孫中山接待了來訪的杜的兩位中國學生——胡適和蔣夢麟。胡、蔣此行赴滬專為迎接杜威而來。雙方談話的主題圍繞“知難行易”問題展開。胡適后來回憶道:有一天,我同蔣夢麟先生去看中山先生,他說他新近做了一部書,快出版了。他那一天談的話便是概括性地敘述他的‘行易知難的哲學。”這是胡適與孫中山的首次見面,這次晤面讓前者近距離地領略了這位名聞遐邇的革命領袖的魅力和風采,幾年后在討論青年學生是否應該干預政治問題時,為了論證讀書的重要性,他談道:“我去訪中山先生,他的寓室內書架上裝的都是那幾年新出版的西洋書籍。他的朋友都可以證明他的書籍不是擺架子的,是真讀的。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領袖資格,正因為他終身不忘讀書,到老不廢修養。”
5月12日,孫中山專程來到滄州賓館,拜會下榻于此的杜威先生,兩人共進晚餐。席間,孫中山以《孫文學說》即將出版相告,并重點介紹了自己在知行關系上的創獲。翌日,杜威在家書中詳細記述了知難行易說提出的緣起:“前總統孫中山先生是一位哲學家,這是我昨晚和他共進晚餐的時候發現的。他寫了一本書,就要出版了。他在書里說,中國人的柔弱都是因為他們接受了一位古老哲學家的話,‘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這樣一來,他們不喜歡行動,而是認為可以通過理論的方式得到一種全面的了解。而日本的長處正在于,他們即便在盲目的情況下也依然行動,通過試誤來向前推進,來學習。中國人則畏懼于在行動中犯什么錯誤,從而被束縛了手腳。因此,他寫了這樣一本書,要證明給人們看,‘知難行易。”
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與杜威重視行為經驗的實驗主義理論頗有相合之處,此次談話顯然使后者甚感愉快、難以忘懷,是以在第二年發表于《亞洲》的一篇文章中又再次提及。此外,孫中山關于中國人國民性的洞察以及中日兩國間的比較,也讓剛剛訪問日本的杜威心有所感,從而為其提供了一個觀察中國社會、分析中國問題的基本視角。此后當他思考中國、中日以及東亞問題的成因時,不時可見關于中國人精神面貌、心理特征、行事方式的鋪陳和解析。
杜威在華期間,足跡遍布十數個省區,大小演講200多場,還在北京大學、北京高師、南京高師等校系統授課。由于被視作“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化身,“正如鳩摩羅什一樣在適當的時候出現在中國”,杜威所到之處,聽者如堵,追隨者眾。對于杜氏對中國的影響,作為其訪華活動的推動者、參與者和見證者的胡適,當時即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時為浙江第一師范學生的曹聚仁,親耳聆聽過杜威的幾次講演,十余年后亦撰文指出:杜威先生在中國所得到的光榮,不僅遠過后來那些東來的學者,亦為中西交通以來所未有。”
在廣州的六次演講
1921年4月12日,在廈門大學校長鄧萃英的邀請下,杜威抵達福州。在閩講學期間,廣東教育界人士函托福建省教育廳代請杜氏順道赴粵。在廣東方面的催促下,23日晚杜威匆匆結束在福建的行程,與妻女自馬尾登輪借道香港前往廣東。
杜威訪粵之際,正是廣東各項事業銳意革新,蒸蒸日上之時。
1920年11月,援閩粵軍成功驅逐桂系,孫中山等返回廣州組建新政府后,在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長陳炯明的具體推動下,廣東的地方建設全面鋪開,如取消苛捐雜稅,設置廣州市政廳等。教育方面則成立權力很大的教育委員會,作為全省教育的最高領導機關,并聘任北京大學教授、新文化運動的巨子陳獨秀擔任首任委員長。陳氏履任后,對于全省教育事業銳意革新,積極推行義務教育,擴充師范教育,增強職業教育,又力邀國內學界名流齊聚羊城,共謀教育發展大計。整個廣東的教育和社會面貌煥然一新,與全國范圍內軍閥割據、萬馬齊喑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4月28日,杜威安抵廣州,由省教育委員會和省教育會安排入住亞洲酒店,隨即在美國駐廣州領事的陪同下前往拜會陳炯明。當日及隨后數日前來酒店拜訪者絡繹不絕。自翌日至5月上旬十余天的時間里,杜威先后演講六次。第一次是在小南門的國立高等師范學校禮堂,講題是《自動道德重要的原因》。其余五次,均在位于九曜坊的省教育會禮堂舉行,主題分別是學校與社會、西方對于東方的貢獻、自由權利問題、社會組織與社會發展、西洋社會發展之程序。六次講演的內容,在新創辦的教育會機關刊物《廣東省教育會雜志》上全文刊出。
這幾次演講,由于政治分裂、交通阻隔等原因,北方報刊普遍關注不多,僅有北京《晨報》和上海《民國日報》等少數報刊有所關注。從有限的報道看,演講在廣東引起的關注和轟動絲毫不亞于其它各省。報道稱,第一場講演于29日下午2時一刻開始,到場聽講者千余人,主要是高等師范學校及各專門學校的師生員工,“座無隙地”。首由陳獨秀介紹杜氏簡歷,并鄭重提請聽眾虛心領受講演內容。旋由杜威演講,韋玨擔任翻譯。4時許,演講結束。第二場講演于30日下午2時舉行,聽眾主要為各中學師生。當日上午9到11時,廣東女界亦邀請杜威夫人在省教育會禮堂發表演講。第三場演講在5月2日下午2時進行,聽講者來自社會各界,約千余人,“其中婦女及西人不少”,4時半始散。前三次演講,除第一次外,其余兩次皆由省教育會發給入場券,聽眾憑券入座。因省教育會禮堂約可容納千人,坐滿即停止入場,故因遲到而不得入者,大有人在”。
杜威在粵,為時甚暫,因慮及北京各校由于索薪而引發的風潮“解決在邇,未便久滯粵中”,于10日前后離粵北歸。對于這位世界著名學者的匆匆就道,“百粵人士甚為怏憾,百般設法阻止其行,大有板轅擋路之慨”。有報道感慨:教育界之明星,其得人崇拜如此。”
對廣東社會的觀察
杜威返京后,兩次集中談及訪粵印象。一次是在北京高師發表題為《南游心影》的演講。此次演講包括閩粵兩地的見聞和思考,因為聽眾多系中國人,政治方面固然“也有許多足以使之發生感想的地方”,但慮及“以外國人而談中國的政治,很有些不方便”,是以內容主要集中在相對不那么敏感的交通、教育等問題上。另一次是應上海《密勒氏評論報》所請而作的《廣東印象記》,該文6月11日于該報首載,上海《民國日報》當天節錄要點,16~18日北京《晨報》又刊出全文中譯本。由于主要是面向外國讀者,所以該文相對直言無隱,將訪粵過程的所思所想比較全面地予以揭示。
杜威南游,首先感受到的就是中國交通的落后。如從上海到福建的輪船班次很少,且由外國公司控制;而從福建前往廣東的行程中,他發現廣東這樣一個向來與外洋打交道的省份,因珠江口河道過淺,貨物的出入口必須轉道香港,廣州與香港間的貨物運輸只能使用小船。他感嘆道:“中國有許多省份所以和他省時常斷絕的原因,大半是由于交通事業之不發達。”而交通不便的影響,“不惟使旅客有行路難之嘆,并且及于政治、工業、智識等項。”
抵達廣州后,杜威與“許多新運動當中之政治的、官吏的、知識階級的領袖們”以及當地的外國人廣泛接觸,雙方的交往并不限于“形式上會面的客套”,而是能夠開誠布公地交換意見。同時,廣州街頭上不時上演的大規模群眾性活動,也吸引著他的眼球。杜威在粵的5月上旬,恰逢勞動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紀念日、五四運動、孫中山就任大總統、國恥紀念等多種紀念日及慶祝活動接踵而至,輪番上演。廣州市民冒雨參加活動的熱情,雖然令杜威心生奇怪,但為他提供了觀察廣東社會,“證明國民性質的大好機會”。經過多方面多渠道的交往、接觸與觀察,杜威對廣東的印象全然改寫,“與我初到廣東去的時候心中所有的完全兩樣”,一個全新的、與全國其他地區完全不同的廣東浮現在他的面前。
作為教育家的杜威,對教育問題自然有著特別的關注。來到廣東前,杜威見及各省“大宗款項多用于軍政,以致教育的經費不但不能保原有的數目,還要時時裁減”,中國的軍政和教育,“這兩個勢力相反的程度,已達到有彼則無此,有此則無彼的地步”,以致各地“各校近幾年來,不但沒有進步,甚至于不及從前”。到達廣東后,他驚喜地發現廣東政府治下的教育事業,正腳踏實地地邁步前進。廣州市政府啟動兒童強迫教育計劃,計劃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全市適齡兒童實現全部入學;還準備設立新式的高小和中學,強化職業教育,確保“畢業的生徒縱不能升入大學,而有相當的技能可以謀生”。他指出,盡管其他省份不乏教育計劃,但與廣東相比,更多像紙上談兵,“無裨于實在”。“廣東的行政機關要是能延長下去,中國教育前途或者有點希望。”“中國教育前途些微有點發展,只可望之于廣東政府。”
對廣東政府的各項新政,杜威同樣極表稱許,不吝贊美之詞。從禁止賭博、廢除賭捐,具有“現代精神”的市政府的設立,開通城市,建設市政,到省政府中官制和官吏的改革,公共衛生部的創設,教育委員會的組建,廣東政府“著實干了許多關于中國進步的事情,而且有許多也正如他們所說,是中國唯一的政治,真為人民的福利,不為官吏的權力和私囊,而且受治于大多數人,不但只有一點好意,而且也有關于政治的近世眼光和知識上的訓練的。”“廣東政府的一切設施,都是極誠懇地想著為人民造幸福。”
廣東政府正在推進的各項革新事業之所以不為外界所知,杜威認為,是因為有關的新聞渠道為北京政府和英國政府所掌控。由于“孫逸仙和他近旁的人都是向來反對英國的”,英國方面對廣東政府非常敵視,與廣東毗鄰的港英當局,“以他的財政上和政治上的利益,自然歡迎現政府的陷落,而希望腐敗的、無能的、不經訓練的舊政府之復來。”正是在它們的把持下,幾乎所有有關廣州的新聞,“都是純粹含有宣傳之目的的”,甚且帶有非常明顯的以丑化廣東政府為唯一目的的“搗亂”性質。對于北方報章慣常使用的廣東政府布爾什維克化的指控,杜威指出,陳炯明和孫中山二人“是很有社會主義者的精神的”,所以他們都想將自然富源和基本工業的所有權及管理權保留在政府手中,以免落入私人之手,這樣做的目的既是為了保障政府的收入,更是為了廣大人民的利益。
廣東政府的多種開新嘗試顯然使杜威眼前一亮,是以他認為,中國未來的統一和希望不在事實上缺乏“一種合理的仁慈的中立性”、動輒“用軍閥的勢力去壓人”的北京政府,而在廣東以及其它南方省份上。他相信:“倘若南方各省繼廣東之后,有好的省自治制度建設起來,將來必定能互相聯合,那才是真正的統一,不是紙上的或軍閥式的統一。”
(作者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