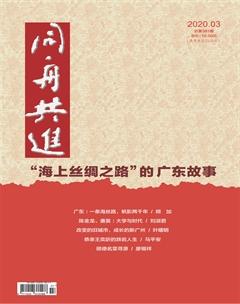吃主兒”王世襄
王學斌



“一個人的口味往往是愛吃而又未能吃夠的東西最好吃。某些大師傅做菜的訣竅之一是每道菜嚴格限量,席上每位只能吃一口,想下第二箸已經沒有了……”這段妙語,出自我國當代文博巨匠、收藏大家王世襄先生之手。
王世襄出身仕宦之家,高祖王慶云曾任兩廣總督、工部尚書。祖父王仁東曾任內閣中書,伯祖王仁堪為清光緒三年狀元,是梁啟超的老師。父親王繼曾是外交使節,一度擔任軍機大臣張之洞的秘書,清亡后在北洋政府擔任過國務院秘書長。母親金章是畫家,大舅金北樓是當時畫界領袖人物,創立了中國畫學研究會。這種身世背景,為王世襄后來成為“京城第一玩家”打下了基礎。
君子近庖,自古有之,何況像王世襄這般的奇士怪杰,喜好哪一種門類,就能玩得精通,甚至玩出些人生道理來,這才是大家。在眾多朋友心中,王世襄便是此等高手。
王世襄小時候就喜歡進廚房,看家廚做菜,這些家廚都是當時的名師。在這些名師的指導下,他很早就開始自己上灶做菜,煎炒熘炸,樣樣都行,還交了不少廚師朋友。汪曾祺在《食道舊尋》一文中就提到,京城諸位學問家,要說會吃、能吃且會做善烹,首推王世襄:“學人中有不少是會自己做菜的,但都只能做一兩只拿手小菜。學人中真正精于烹調的,據我所知,當推北京王世襄。世襄以此為一樂。據說有時朋友請他上家里做幾個菜,主料、配料、醬油、黃酒……都是自己帶去。聽黃永玉說,有一次有幾個朋友在一家會餐,規定每人備料去表演一個菜。王世襄來了,提了一捆蔥。他做了一個菜:悶蔥。結果把所有的菜全壓下去了。此事不知是否可靠。如不可靠,當由黃永玉負責!”
身懷如此絕活,但王世襄從不認為自己是正宗的美食家或具備承擔大宴能力的名廚。他曾發表文章《答汪曾祺先生》,認為汪曾祺此說來自傳聞,有點言過其實。他謙虛地糾正道:“又說我提了一捆蔥去黃永玉家做了一個菜,永玉說把所有的菜都壓下去了。這是言過其實。永玉夫人梅溪就精于烹調。那晚她做的南洋味的燒雞塊就雋美絕倫,至今印象猶深。永玉平日常吃夫人做的菜,自然不及偶爾嘗一次我的燒蔥來得新鮮,因此他才會有此言過其實的不公允的評論。”
王世襄始終自認是一位地道的老北京“吃主兒”。
【“春菰秋蕈總關情”】
王世襄先生治饌,確有其獨到之處,會買、會做、會吃,怎么好吃怎么來,不受所謂傳統菜譜、盛宴標準所限。
細究起來,“吃主兒”的稱謂其實涵義挺深。在如今社會,提及精于品嘗美味佳肴之輩,我們往往冠之以“美食家”的稱譽。然而在王世襄看來,“美食家”是個尊號,是不可以自稱的。況且精于美食的道行,也是頗深的,至少也要有豐富的閱歷,對飲食文化體會入深,同時還得見多識廣,對各地的名廚、名館、名菜、名人了如指掌,對于名饌的由來與淵源,前世與今世,能夠引經據典、如數家珍般地詳加考證,揭示出一道菜、一例湯、一桌宴甚或一碗面背后的深邃韻味,達致此步,才是大家風范,美食家”這頂桂冠方戴之無愧。
用王世襄先生愛子王敦煌先生的話來講,貌似“美食家似乎都可以稱之為‘吃主兒,并且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實不盡然,因為‘吃主兒必須具備三點,就是會買、會做、會吃,缺一不可”。
“吃主兒”怎么采購原材料呢?其中訣竅甚多,乾坤頗大。限于篇幅,我們不妨以挑選蘑菇為例。
蘑菇作為家常用菜,老百姓都十分愛吃。不過,這極其平常的菜,對于王世襄而言,可不簡單。1949年前,北京市面上的鮮蘑菇,品種較少,主要是雞腿菇和柳菇,后來出現了人工培育的白圓菇。20世紀70年代后,白圓菇幾乎一統江湖,但這品種顯然不入王世襄的法眼:
從外觀來看,顏色發黃,菇柄的底部基部都發黑了。新鮮是談不上了的。菇傘沒有閉合的,而且傘邊殘破不全。有的雖不殘破但也都裂了口兒了。這東西疑為制作罐頭時被剔除的等外品。品質好一點的不能說絕對沒有,但那可真是可遇不可求了。而且所謂好也不過是稍稍周正、稍稍新鮮一點兒而已。品質既然談不上,口感也好不了哪兒去,用它入饌只能用于做個雞、燉個肉借味用用。要真為食用蘑菇本身,就差點勁了。
其實王世襄心中最垂涎的,還是老北京當年的野生蘑菇。據他回憶,柳菇和雞腿菇,外觀和口感都不同。柳菇是叢生的,上市的柳菇有三四個頭的,也有十幾、二十幾個頭的,大小不一,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甚遠;而雞腿菇單個兒生長,菇柄長于菇傘數倍,其形狀像極了一把沒有完全閉攏的雨傘。據其烹飪經驗,這兩種野生蘑菇,是不可混用的。
柳蘑有點土腥味,但質嫩、易熟,烹制時多加點紹興老酒把土腥味殺下去,口感亦是極好的,或炒或燴都好吃,當然王認為燴勝于炒。倘若加點雞絲、嫩豌豆,燴制“雞絲豌豆燴鮮蘑”,則是上乘的佳肴——畢竟其品質上佳,怎么處理都是美味。雞腿菇則不然。它倒是沒有土腥味,可用它做菜確實沒有如柳蘑那樣滑嫩。因此,雞腿菇只適合炒食,不宜燴制。按老北京土話“它的質地偏艮,沒有那種柔滑勁兒”。
這兩種蘑菇的采購,也并非天天都有,往往看運氣。其主要貨源,通常由住在南郊的幾位善挖蘑菇的人那里提供。他們各自有挖蘑菇的去處,各行其道,互不干擾。采了一回之后,他們估摸著該采下茬的時候就再走一趟,也算是換點謀生的閑錢。然而到上世紀70年代后期,隨著市郊不斷拓展建設,永定河畔也在整治,野生蘑菇越來越難找了,所以這些人索性不采了,柳菇和雞腿菇隨之在市面上絕跡。
于是,王世襄動了自己去采蘑菇的念頭。他先是上菜市場找售貨員打聽,又按照指點騎著自行車出了永定門,在那邊的一所小學的傳達室里找到了以前往市場送蘑菇的張老漢,才知道了其中的很多內情。原來當初那些采蘑人大多住在永定門和右安門外,蘑菇生長的地點也位于永定河河沿一帶,堤坡處、林帶等處,都有野生蘑菇。
蘑菇屬于菌類,要想采蘑菇就必須會看“梢”。所謂“梢”,一方面指那些草木蔥郁的地方,一方面和埋在土內的菌絲有關。有“梢”的地方,會年復一年生長出蘑菇來。有經驗的采蘑人可以在未曾涉獵過的山野鄉間辨別出“梢”的所在。這位張老漢見到王世襄,頗有相見恨晚的感覺,兩人聊得很是投機,把他見過的各種“梢”一一介紹給王老爺子。后來王世襄按圖索驥,果然找到過野蘑菇。
說到這,恐怕有人會問:王世襄緣何對蘑菇如此鐘情?難道只是為了滿足口腹之欲?答案自然不是。很多人都了解,一個人味覺的養成與健全,其實在小時候就已經完成。所以很多人對某些食物的喜歡乃至貪嗜,實際上與童年或少年時的飲食記憶緊密相關。
十一二歲時,王世襄隨母暫住南潯外家。南潯位處太湖之濱,江浙兩省交界處。鎮雖不大,卻住著不少大戶人家。到這里來做傭工的農家婦女,大多來自洞庭東西山。服侍外婆的一位老嫗,就是洞庭東山人,每年深秋,都要從家帶一甏“寒露蕈”來,清油中浸漬著一顆顆鈕扣大小的蘑菇,還漂著幾根燈草,據說有清熱解毒的功效。這種野生菌只有寒露時節才出土,因而得名。其味之佳,可謂無與倫比。正因為它是外婆的珍饈,母親不許他多吃,所以才感到特別鮮美。
在燕京大學讀書時,王世襄常常騎車去香山游玩,而香山是以產野生蘑菇聞名的。經過訪問,在附近的四王府村結識了一位人稱“蘑菰王”的年逾六旬的老者。老漢見這位年輕的大學生好學又懂禮貌,便一手不留地傳授采菇秘訣,他告訴王,香山蘑菇有大小兩種:大而色淺的叫“白丁香”,小而色深的叫“紫丁香”。王先生自此初窺“蘑菇世界”之門徑。
建國后,王世襄仍不忘找機會品嘗各種美味菌菇。湖南的野生菌亦頗為人所樂道,在西南聯大上過學的朋友,往往談起抗戰時期長沙街頭小飯鋪的蕈子粉、蕈子面(就是湯煮米粉或面條上加蕈子澆頭)如何鮮美,九如齋的瓶裝蕈油也常被人帶出來饋贈親友。1956年,王世襄在中國音樂研究所工作,參加了湖南音樂普查之行,跑遍了大半個省。那一次的印象是長沙的蕈子粉趕不及衡陽的好,而衡陽的又不及湘南偏遠小鎮的好,看來,起決定作用的不僅在蕈子的品種好不好,采得是否及時尤為重要,柄抽傘張,再好的蕈子也沒吃頭了。
當年從湖南道縣去江華的公路尚未修通,要步行兩天才能到達。中途走到橋頭鋪,眼看一位大娘提著半籃剛采到的鈕子蕈送進一家小飯鋪,王世襄不禁垂涎三尺。普查隊的隊長是一位非常強調組織性、紀律性的同志,時時警告隊員要注意影響。王世襄自嘲道:象我這樣出身不好……她自然覺得有責任對我進行監督改造,如果我不進行請示批準,擅自進小飯鋪吃碗粉,晚上的生活會就不愁沒有內容了。”
好在一路上,王世襄走在最前面,隊長落在后頭至少三五里之遙,于是他乍著膽子進去吃了碗蕈子粉:哈哈!這是我在整個普查中吃到的最好的野蕈子!我很想來個第二碗,生怕被隊長看見而沒有吃,抹了抹嘴走出了小鋪的門”。
可見,作為“吃主兒”的王世襄,對于食材的要求,有多挑剔了。
【“一捆蔥”驚煞眾人】
會采購,僅是邁出了第一步,之后便是要顯示過硬的廚藝。其實廚藝高低,不在于原料是否價錢高昂名貴,而在于面前擺放的無論是飛禽走獸、山珍海味,還是稀松平常的蘿卜白菜、豆腐蔥蒜,“吃主兒”都能把它們的本味處理得恰到好處,活色生香,讓人吃后終生難忘。
王世襄是收藏家,他說自己搞收藏常用“直覺”的方法,有點類似書畫鑒定中的“望氣”(指書畫卷軸打開之后先觀望一下整幅書畫的氣勢),他做飯的風格也秉承此旨。王老自稱:“做菜不拘一格,勿論中外古今,東西南北,更不管是什么菜系,想吃什么就做什么,以意為之。”他的拿手菜有不少,其中僅香糟菜就有糟熘魚片、糟煨茭白、糟煨冬筍、糟蛋海參等,此外還有雪菜燒黃魚、火腿菜心、雞片燒豌豆、糖醋辣白菜、羊油麻豆腐、面包蝦……
精于烹飪的,對于原材料都格外看重,樂于在灶臺間舞弄而不跑菜場的,那是“假把式”。王世襄每天早晨去朝陽市場,在市場門口排隊,開張的鈴一響,就第一時間沖進去,一起逛菜市場的,有保姆,也有名廚。他從不愿意買反時令的蔬菜,總是什么季節吃什么菜,時令蔬菜既新鮮又便宜,而且“味兒對”。在王世襄看來,去菜場買菜,是人生僅次于“吃”的最大樂趣。
王世襄有幾道拿手菜。第一道是燉牛舌,這道菜是王世襄根據西餐罐燜牛肉的做法改良得出的。將新鮮牛舌除去外膜,切厚片,入砂鍋。先用猛火,后轉文火,燉燜6小時。期間依次加入黃酒、精鹽、醬油、姜片、蔥頭以及切成滾刀塊的胡蘿卜。
另一道拿手菜是“鍋塌豆腐”,這道菜分北京和山東兩種做法,是王世襄從北京一個小飯館學來而稍加損益的。其具體做法是用黃酒泡蝦仁,加醬油、精鹽、白糖,如果有高湯加一點更妙。南豆腐半斤,切三厘米見方薄片放入碗內。雞蛋三枚,打碎倒入豆腐碗中,加入少許煸熱的蔥花拌勻。炒鍋放素油,燒熱后將豆腐、雞蛋倒入,攤成圓餅,兩面煎成金黃色。待將煎熟時,倒入泡有蝦仁的調料,用筷子在餅上戳幾個小洞,令調料滲入其中,即可起鍋。
還有一道值得濃墨重彩記上一筆,即開篇所引汪曾祺老先生的話里之“一捆蔥”。著名的民俗和美食學家魯克才先生寫過一篇題為《莫道君子遠庖廚——訪著名學者、美食家王世襄》的文章,根據王世襄的口述,記錄了“悶蔥”的做法:黃酒泡海米,泡開后仍須有酒剩余,加入醬油、鹽、糖各少許。大蔥十棵,越粗越好,多剝去兩層外皮,切成二寸多長段。每棵只用下端的兩三段,余作他用。素油將蔥段炸透,火不宜旺,以免炸焦。待色已黃,用筷子夾時,感覺發軟,且兩端有下垂之勢,是已炸透,夾出碼入盤中。待全部炸好,推入空勺,將泡有海米的調料倒入,燒至收湯入味,即可出勺。
其實,這道菜準確的名稱是“海米燒大蔥”,是王世襄自創的叫法,只在為數不多的幾位老朋友中流行。更多的人,包括品嘗過這款菜的一些朋友,都把它叫作“燜蔥”。王老在介紹這個菜時還附加了兩條:如請香港朋友,海米須改為干貝,因為香港海味太豐饒,海米被認為不堪下箸之物,難免一個個拋出來剩在碟中。還有就是此菜只宜冬天吃,因為深秋蔥未長足,立春后蔥芽萌發,糠松泡軟,味、質均變矣。
不論是叫“海米燒大蔥”,抑或“燜蔥”,王世襄對蔥這種入饌原料,可謂情有獨鐘。在他的飲食觀里,蔥,確切地說是京蔥,占有很高的地位。不但在烹制不少菜肴中,作為必不可少的佐料,還在他的拿手菜中,作為主料使用。凡是了解他的老朋友,沒有一位不知道這段佳話的。比如著名學者張伯駒、朱啟鈐先生以及朱家溍、惠孝同、陳夢家、黃苗子等密友,更是吃過不止一回。就是王的同事,包括那些小字輩的小朋友也都吃過。
王世襄學會做這款菜有年頭了,還是在他二十多歲那時,由他的表哥金潛庵先生傳授的。金開藩,號潛庵,是金北樓先生的長子,湖社創辦人之一,也是集中西精湛廚藝于一身的著名吃主兒,當年譚家菜館的常客。
關于自創“燜蔥”的原因,王敦煌曾說:“說開了,無非也就是那些個好吃蔥燒海參的食客們,愛吃這個味兒,又嫌海參貴,光用佐料不用參。做的時候,又怕舍了海參,沒了海味的味兒,添上點兒小海米烹制而成的。”這些食客還有一點共識,他們沒有像某些老饕那樣,把大蔥的蔥香視為濁氣——任何蔬菜或者說入饌原料,都有它的本味,喜歡與否,也是人之常情,可品嘗過這款菜的人,沒有一位不認同大蔥之香的。
“海米燒大蔥”的做法,用料固然簡單,卻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烹制,這就和主料大蔥的選用,有密切的關系了。京蔥在不同的時節,生長狀態也不同。因此分為小蔥、溝蔥、青蔥、大蔥和羊角蔥。王世襄當年選用的,就是京蔥之中的大蔥。但是并非所有的大蔥都能入菜,必得是在霜降之后、上凍之前,從地里起出來的大蔥。因為只有在地里經了霜,蔥質才會變得脆嫩可口,也只有這樣的大蔥,才能稱得上是“上品大蔥”。即使是最優質的大蔥,優質期也只能延續到來年的正月十五,此后大蔥的品質,就日趨下降了。按吃主兒的選料標準,只有在大蔥的優質期,才會做這款菜。
然而世上的事,總保不齊遭遇時過境遷的變化,后來北京市場上,蔥的品質和以前相比,已大不相同了。一方面,由于北京的氣候比以前暖和,往往到了霜降的節氣并無霜降,另一方面,培育方式亦有不同。大蔥越長越茁壯了,可是蔥白的脆嫩感不復存在,就是在深秋霜降之后,最優質的大蔥亦是如此。用其入饌,剝皮數層之后,依然挺拔且韌。入鍋油煸,即使炸透,用筷子夾起來一段兒,入口仍有嚼勁,卻根本不能把它嚼爛,原來那種入口即化的感覺,蕩然無存了。也正是從那時起,王世襄再也沒做過這款菜了。
因此直到今天,隨著王世襄老先生的故去,海米燒大蔥這道菜,更多是留在了眾多讀者的腦海中,萬里風沙知己盡,誰人會得《廣陵》音”,成為大家記憶中的美味了。
【對祖國飲食文化有深沉之愛】
會買,會做,終極目的,恐怕還是要滿足腸胃之需。而會吃,吃出文化甚或是人生哲理來,這才是“吃主兒”的化境。
不妨先看看王世襄先生對中國飲食文化的整體態度。1983年,由國家商業部舉辦了一次全國烹飪名師技術表演鑒定會,作為顧問,王先生有過一段很是精妙的評點:
我國菜肴,講究色、香、味、形、器,五者都很重要,但其間仍有主次。最重要的還是味。色、香與味本有密切聯系。一般說來,味如果好,色、香也不會差。色敗香消,又安得有佳味!形則有原料本身的形(如全雞、整鴨、烤豬之類),一般刀工的形(如條、片、絲、丁、塊、方、筒、卷等)和特殊加工的形(即將菜肴做成種種物體形象)。其后者如運用得當,對精饌佳肴能起錦上添花的作用,但不可弄巧成拙,只有有助至少無損于味才是可取的。器是盛裝菜肴的容具,既適用又美觀自然最好,如未能兼備,則適用比美觀更為重要。因為不適用便會影響到味。總之菜肴供人食用,是舌根鼻觀美的享受,故自應以味當先。
珍味佳肴,自當色香味形器俱全,但其中關鍵之關鍵仍是菜之原質本味,否則無異于買櫝還珠、本末倒置。單單一個味字,又涵括味正、味香、味濃、味厚、味醇、味鮮、味純、味美、味清等等方面,也正因辨別如此精細,一種菜品自然有其一種獨具的味道,當然若能幾種化入一菜當中,更加上乘,其中之奧妙堪稱無窮。
這種意境往往是可意會而無法言傳的,但王世襄憑借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精準把握,竟筆下生花,將眾多菜品的精髓寫得傳神“到胃”,仿佛美味已躍出紙上,鉆進讀者的鼻中,誘惑眾人的味蕾,讓人垂涎三尺,化為饞蟲:
香濃味厚,色燦如金,保留著譚家菜風味的“黃燜魚翅”。原湯盡在,鮮美醇厚,裙邊腴而不膩的“氣鍋圓魚”。上桌才用上湯沏澆,毫無搭配,全憑本身的質嫩味鮮使人叫絕的“汆閩江海蚌”。雞白如雪,裝裹著晚霞似的紅糟,以細切蘿卜、蟄皮為佐,色能炫目,味促朵頤,香堪沁齒的“三絲伴糟雞”。蝦肉明透,宛如白色琉璃,清炒無汁,只灑上些鮮綠茶旗槍的“龍井蝦仁”。湯清如水,品之初淡而漸濃,乍薄而轉厚,但又不掩晚菘本味的“開水白菜”。羊腿瘦嫩,裹衣煎炸,卻渾然鼓起,薄如細輕紗,入口又酥松自化的新疆“帶泡生燒肉”……
身為“吃主兒”,既有美食,自當與君共享,并通過文字、活動廣為揚播。同時,如果美食遭遇江河日下、日趨蕭條之慘境,“吃主兒”也應當站出來為之呼吁鼓吹,王世襄先生便是如此。
在國外的時候,王先生與一位俄羅斯朋友比拼中俄兩國小吃,雙方爭執不下。各自歸國后,有一次這位俄羅斯朋友遠道來訪,在冬令時節,王世襄做了“南味的酥魚和羊羔,福州的炸油菜松和冬菇冒筍,北京的炒素菜絲和仿蝦米居的野兔脯,浙江的糟雞,南北都有的糖醋辣白菜墩和醬瓜炒山雞丁等”,并總結說“俄國小吃充實而濃厚,但缺少淡雅雋永之品,相形之下,就顯得粗了一點,這在中國的山水畫和俄國的古典的重彩油畫之間也能體會到它們之間的差距”,一桌菜、一席話令這位倔強的朋友口服心服。
1983年舉行的全國烹飪名師技術表演鑒定會,匯集了全國各地最出眾的大廚(其中有些后來成了國家特級廚師,如福建“雙強”),王世襄與王利器、溥杰一起成為大會特邀的品嘗委員,會后王世襄撰寫的總結文字亦可見其在飲食方面的理論素養和鑒賞力。
當時老北京市面上不少餑餑鋪,從店鋪外貌到柜內食品都很有特點,民族風味很濃,堪稱中國文化的象征。餑餑鋪字號多以齋名,金匾大字,鋪面裝修極為考究,如果不是牌樓高聳,挑頭遠跳,就是屋頂三面曲尺欄桿,下有鏤刻很精的掛檐板,用卷草、番蓮、螭龍、花鳥等作紋飾,懸掛著“大小八件”“百果花糕”“中秋月餅”“八寶南糖”等招幌。
從金碧輝煌、細雕巧琢的鋪面,已經使人聯想到店內的糕點也一定是精心制作,味佳色美的。老餑餑鋪還有一個特點,即店內不設貨品柜、玻璃櫥,因而連一塊點心也看不到。以當年開設在東四八條口外的瑞芳齋為例,三間門面,店堂頗深,糕點都放在朱漆木箱內,貼著后墻一字兒排開。箱蓋雖有竿支起,惟箱深壁高,距柜臺又有一兩丈遠,顧客即使踮起腳也看不到糕點的蹤影,只能“隔山買老牛”,說出名稱,任憑店伙去取。但顧客卻個個放心,因為貨真價實,久已有口皆碑。
可是時代在發展,北京的中式糕點一度卻停滯不前,上世紀60年代以來真是每況愈下。開始是干而不酥,后來發展到硬不可當,而且東西南北城所售幾乎都一樣,似一手所制。因此社會上流傳著一個笑話:汽車把桃酥軋進了瀝青馬路,用棍子去撬,沒有撬動,棍子卻折了。幸虧也買了中果條,用它一撬,桃酥出來了。這未免有些夸張,不過點心確實夠硬的,吃起來不留神,很可能硌疼了上膛。
對此情形,王世襄先生頗為擔憂,曾多次寫文章強調要重視中華美食的傳承,尤其是美食老字號的保護與弘揚。可喜的是后來北京的中式糕點有所好轉。
王世襄先生回憶1989年初的時候,他已能在東單祥泰益買到軟而不粘牙的薩其馬。之后《北京晚報》兩次報道東直門外十字坡開設了一家由四個老字號(寶蘭齋、桂福齋、致蘭齋、聚慶齋)聯合組成的薈萃園,力求恢復傳統風味中式糕點。王老特意前往觀光品嘗,品種相當齊全,味道也很不錯,翻毛和酒皮的大小八件、油糕、穰餅、狀元餅、桃酥等應有盡有,連過去桂福齋九月才應時的花糕也能買到,而且依然是老味。薩其馬色澤淺黃,果料齊全,入口即化,全無渣滓,只有調料、炸條、拌糖每道工序都掌握得很好才能做出來。老爺子一時欣喜,主動地為薈萃園做了一副對聯寫在一個小條幅上,其文如下:
卅載提防,糕硬常愁傷我顎!
四齋薈萃,餅酥又喜快吾頤。
這種喜悅之情,恐怕不只是源自于口腹之欲,更多的是他對祖國飲食文化的深沉之愛。
正是基于這種誠摯的深情,王世襄先生晚年曾對中華美食老字號的復興提出四點要求:
一是“實事求是”;二是“天下怕就怕認真二字”;三是“不打無準備之仗”;四是“樹立主人翁態度”。
這四項標準,誠可謂美食老字號掌門人應秉持的“至理名言”。筆者自忖,這也是一名合格“吃主兒”應具備的眼光和規矩。其實,對待飲食,如同對待我們平日其他事與物一樣,都少不了較真乃至挑剔的態度,如此才能從中摸到門道,做出成績。
斯人已去,新一代“吃主兒”的衣缽,吾輩理當勉力為之。
(作者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