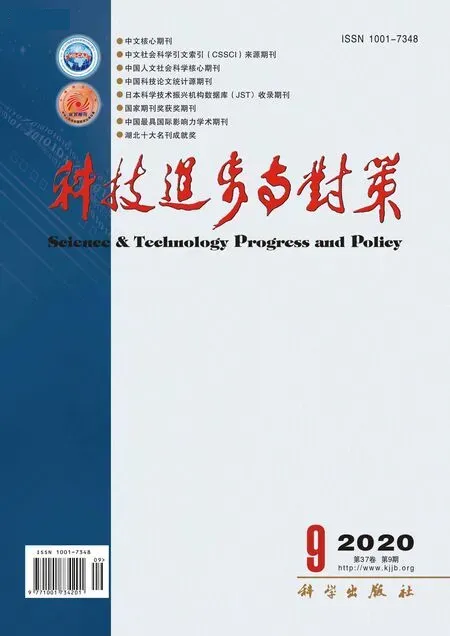考慮吸收能力的區域創新多維溢出效應
李 華,杜丹陽,吳愛萍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6)
0 引言
中國經濟已告別高速增長階段進入到高質量發展階段,創新驅動發展成為打造新引擎、增強新動力的國家戰略,創新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從《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2019》[1]可以看出,東部沿海省份及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是創新能力領先地區,東西地區差距在縮小,而南北地區差距則在拉大,各地區創新能力存在明顯差異。創新客觀存在區域梯次差異,強化創新能力領先地區的創新溢出效應,促進區域間創新聯動協同,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必然要求[2]。
衡量區域創新能力的核心指標是區域創新效率,區域創新能力提升的關鍵在于創新效率提高[3]。區域創新效率提高不僅可以通過改善區域創新環境實現,更可以充分利用創新溢出效應實現[4]。由于區域間存在技術合作和貿易往來等,創新過程涉及的人員、資金、技術等要素會相互流動即產生創新溢出,進而對區域創新效率產生影響[5]。
創新過程不是簡單的一次性投入產出過程,其中包含多階段和多要素,每個階段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共同構成創新動態過程[6]。本文將創新過程分為知識創新階段和產品創新階段。創新溢出表現為空間溢出和價值鏈溢出,空間溢出體現在不同區域之間,價值鏈溢出發生在創新過程的不同階段[7]。對空間溢出效應和價值鏈溢出效應的利用程度則受區域吸收能力影響[8]。在吸收能力不同的區域,同樣的創新溢出效應對創新效率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吸收能力較強的區域可以更好地實現創新效率提高[9]。
本文在對創新過程進行劃分的基礎上,考慮不同區域對創新溢出的不同吸收能力,研究在空間溢出效應和價值鏈溢出效應同時存在時,吸收能力對知識創新效率和產品創新效率的影響,從中得出政策啟示,為區域創新能力提升提供借鑒。
1 文獻綜述
區域創新在不同區域間和不同創新階段間均存在溢出。區域創新有顯著空間相關性,存在較強的空間溢出效應[7,10]。區域創新活動越活躍,空間溢出效應越顯著[11]。從創新價值鏈角度,創新過程可以分成不同階段,各階段之間存在價值鏈溢出效應[12]。創新價值鏈概念最早由Hansen等[6]提出,他們將創新過程視為包括創意產生、創意發展和創新傳播的三階段過程。基于Hansen等[6]、余泳澤等[7]、張貴等[10]的研究,考慮到創新主體差異,本文將區域創新過程分為知識創新(K)和產品創新(P)兩個階段。知識創新階段為了獲得新知識推動基礎科學技術發展而展開研究,初始投入(XK)經由知識創新階段形成中間產出(YK),其部分(Z(K,P))作為產品創新階段的投入,另一部分(D)則直接流入創新系統中,該階段的創新主體通常為高校和科研院所;產品創新階段將新知識引入商業應用領域,投入(XP)包括中間投入(F)和知識創新階段的部分中間產出(Z(K,P)),形成最終產出(YP),該階段的創新主體通常為企業。
一方面,各區域內知識創新階段可以通過其產出影響產品創新,產品創新階段又可以通過需求等途徑反向影響知識創新,知識創新和產品創新之間存在價值鏈溢出效應,如圖1所示;另一方面,創新要素在各區域間流動導致各區域之間存在空間關聯,各區域創新間會產生相互影響作用,稱為空間溢出效應[13],如圖2所示。任一區域知識創新與其它區域知識創新、產品創新之間存在空間溢出效應,同時與本區域的產品創新之間存在價值鏈溢出效應。同樣,任一區域產品創新與其它區域知識創新、產品創新之間存在空間溢出效應,同時與本區域知識創新之間存在價值鏈溢出效應。

圖1 價值鏈溢出效應

圖2 空間溢出效應
區域創新效率不僅受創新溢出影響,還受吸收能力影響,區域創新效率、創新溢出和吸收能力之間也存在交互關系。吸收能力概念由Cohen等[14]首先提出,多用于研究企業利用外部知識提升創新效率[15-16]。后被用于區域或國家層面的創新效率分析,發現吸收能力對區域創新有驅動作用[17],而吸收能力對于區域創新效率提升存在門檻效應[18]。對于創新效率、創新溢出和吸收能力之間的關系,趙莉等[19]發現,外商直接投資會產生創新溢出,吸收能力在創新溢出對創新效率的正向作用中起中介作用;上官續明(2018)發現,區域間技術流動產生的創新溢出是促進技術進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創新溢出與吸收能力之間的交互作用可以增強前者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對于區域創新而言,吸收能力決定著創新溢出在該區域能夠發揮多大作用[8]。當吸收能力足夠強時,可以對區域間流動要素有效加以消化利用[20]。本文將吸收能力定義為決定區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將空間溢出和價值鏈溢出轉化為本區域創新效率提升的能力。吸收能力作用如圖3所示,圖中以區域i的知識創新效率為例,區域i的產品創新階段對本區域知識創新階段產生價值鏈溢出,區域j的知識創新階段和產品創新階段對區域i的知識創新階段產生空間溢出,空間溢出和價值鏈溢出對區域i知識創新效率的作用則受吸收能力的影響。

圖3 吸收能力作用路徑
現有研究發現,由于區域吸收能力不同,創新溢出對各區域創新效率的影響也不盡相同。但在創新效率、創新溢出和吸收能力研究中,現有文獻忽略了創新屬于非一次性投入產出過程,此時創新溢出表現為空間溢出和價值鏈溢出,對空間溢出和價值鏈溢出的利用程度受吸收能力影響。將創新過程進行細分,在考慮空間溢出效應和價值鏈溢出效應時,吸收能力對知識創新效率及產品創新效率會產生何種影響仍需深入探討。因此,本文利用全國內地30個省域數據(西藏因數據不全未納入統計),在計算各省域知識創新效率和產品創新效率的基礎上,分別針對知識創新效率和產品創新效率構建基于吸收能力的創新溢出效應模型,從而分析空間溢出效應和價值鏈溢出效應下,吸收能力對知識創新效率和產品創新效率的影響。
2 研究方法
2.1 區域創新效率測度方法
在創新價值鏈視角下,創新過程分為知識創新和產品創新兩個階段。區域創新效率包括知識創新效率、產品創新效率和整體效率3個部分,分別反映知識創新階段、產品創新階段和整體投入產出關系。知識創新效率和產品創新效率是創新過程中不同階段的創新效率,整體效率是綜合考慮兩個階段所得的創新效率[10]。創新效率測度方法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以隨機前沿分析為代表的參數方法,另一類是以數據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簡稱DEA)為代表的非參數方法,現有文獻一般采用DEA方法對區域創新效率進行測度。
傳統DEA方法只能單獨計算出知識創新效率或產品創新效率,忽視了知識創新階段的部分產出會投入到產品創新階段。F?re等[21]提出的網絡DEA方法考慮了創新過程各階段間的關系,但該方法要求投入或產出按照相同比例調整以達到有效,與現實投入產出活動不符,使計算所得的創新效率缺乏可靠性[22]。在此基礎上,Tone等[23]提出NSBM(Network Slacks-based Measure,簡稱NSBM)方法,解決了要求投入或者產出同比例調整以達到有效的問題。NSBM方法中有投入導向、產出導向和非導向3種建模方式,為綜合考慮投入和產出變動,本文采用非導向方式建模,計算出各省域知識創新效率、產品創新效率和整體效率。


(1)
(2)

特定省域DMU0的整體效率為:
E0=min
(3)

(4)
特定省域DMU0的產品創新效率為:
(5)
2.2 基于吸收能力的創新溢出效應模型
基于前文計算所得的知識創新效率和產品創新效率,進一步研究吸收能力對知識創新效率和產品創新效率的影響。本文參考Jung等[9]對吸收能力的處理方法,構建了一個包括空間溢出效應、價值鏈溢出效應和吸收能力的空間計量模型。知識創新效率和產品創新效率既受空間溢出、價值鏈溢出及吸收能力的影響,也受區域內部環境因素的影響。區域i的知識創新效率表達式為:

(6)

區域i的產品創新效率表達式為:

(7)

由于各區域創新相互影響,本文將內地30個省域看作一個整體加以分析[7]。采用矩陣形式重寫式(6)和式(7)得到:
lnK=(α1I+α2M)WlnK+(α3I+α4M)lnP+(α5I+α6M)WlnP+lnC×β
(8)
lnP=(α7I+α8M)WlnP+(α9I+α10M)lnK+(α11I+α12M)WlnK+lnD×γ
(9)
lnK和lnP是30×1的向量,分別表示知識創新效率和產品創新效率;W是30×30的矩陣,代表30個省域的空間關系;M是30×30的矩陣,代表區域吸收能力;lnC是30×A的矩陣,代表知識創新階段的環境影響因素,β是A×1的向量;lnD是30×E的矩陣,代表產品創新階段的環境影響因素,γ是E×1的向量。
區域間空間關系采用距離空間權重矩陣表示,距離閾值設置為520km[12],當區域i和區域j的省會距離小于等于520km時wij取值為“1”,否則為“0”。考慮到存在兩個區域相鄰但是省會距離大于520km的情況,對此類關系wij也取值為“1”,最終得到省域空間關系矩陣W。
3 指標選取
3.1 創新過程投入產出指標選取
創新過程兩個階段的投入指標和產出指標各不相同,各指標相應數據需從國家統計局等權威途徑獲取[22]。本文在參考相關文獻[7]、[10]、[12]的基礎上,選取創新過程中投入和產出指標,如表1所示。

表1 創新過程中投入產出指標
知識創新階段的投入為人力和資金。其中,人力投入指標選用R&D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人員全時當量之和;資金投入中,由于以往R&D經費投入會對當期研發過程產生影響[25],故選定R&D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資本存量之和作為資金投入指標,采用永續盤存法把R&D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經費支出處理成存量數據(朱有為、徐康寧,2006)。產出為論文、專利和技術市場合同成交額,考慮到數據可得性,論文指標選用國外主要檢索工具(SCI、EI和CPCI-S)收錄科技論文數;專利指標選用專利申請授權數,考慮到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3種類型專利的創新程度,對3類專利分別賦予0.5、0.3和0.2的權重[22],加權平均后得到最后專利申請授權數;技術市場合同成交金額指標可反映科研成果被認同程度,能夠彌補只采用論文和專利表示知識創新階段產出的不足[22]。
產品創新階段的投入為R&D試驗發展人員全時當量、R&D試驗發展資本存量、新產品開發資本存量以及知識創新階段的部分產出(專利申請授權數和技術市場合同成交金額)。采用永續盤存法分別對R&D試驗發展經費支出、新產品開發經費支出進行處理,得到R&D試驗發展資本存量和新產品開發資本存量。作為研究成果形式的論文指標不作為產品創新階段的投入。產出包括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新產品銷售收入和高技術產品出口貿易額。
選取全國內地30個省域數據,數據區間為2011—2016年,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考慮到從投入到產出存在時滯性,選取滯后時間為1年[4]。為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對所有價格指標均以2011年為基期進行平減。其中,R&D經費支出采用研發價格指數平減[26],新產品開發經費支出采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平減,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新產品銷售收入和高技術產品出口貿易額采用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平減。
3.2 創新溢出效應模型相關指標選取
本文選用人力資本水平代表吸收能力。對于人力資本水平的衡量,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標(李亞玲、汪戎,2006),將受教育程度劃分為5類:未上過學、小學、初中、高中、大專及以上,對應累計受教育年限分別界定為2年、6年、9年、12年和16年[27]。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區域中人員工作能力或技術水平較高,能更加充分通過學習、利用其它區域的創新成提升自身創新效率。人力資本水平較低的區域無法有效利用所獲取的知識或技術等,或者說,創新溢出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參考相關研究,影響兩階段創新效率的環境因素如表2所示[7,10,22]。

表2 影響兩階段創新效率的環境因素
其中,人均GDP以2011年為基期,采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指數進行處理。市場化指數來源于《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其余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和《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
4 實證分析
4.1 各省域創新效率測度
采用DEA-Solver15軟件對中國內地30個省域的知識創新效率、產品創新效率以及整體效率進行計算,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全國內地30個省域知識創新效率、產品創新效率與整體效率(2013—2016年均值)
4.2 空間相關性檢驗
在運用空間計量模型前,首先利用Moran's I指數對各階段創新效率的空間相關性進行判斷[10],Moran's I指數可以用來判斷各省域知識創新效率間和產品創新效率間是否存在空間相關關系,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知識創新效率和產品創新效率的Moran's I指數值
注:***、**、*分別表示在0.01、0.05、0.1的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下同
從表4可以看到,除2016年產品創新效率的Moran's I指數值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外,其它數據均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兩階段創新效率均存在較高的空間相關性,各區域創新效率存在相互影響。2013—2016年知識創新效率的空間相關性均強于產品創新效率的空間相關性,表明知識創新效率在空間上的相互影響程度高于產品創新效率。
4.3 模型結果及分析
利用Matlab軟件對模型(8)和模型(9)分別進行求解,結果如表5和表6所示。
4.3.1 知識創新階段
從表5可以看出,在空間溢出部分,2013—2015年各省域知識創新階段的空間溢出對知識創新效率的影響(α1)顯著,此時吸收能力對知識創新效率有顯著正向影響(α2);當知識創新階段、產品創新階段屬于不同省域時,產品創新階段對知識創新階段的空間溢出對知識創新效率的影響(α5)只有2014年顯著,此時α6顯著為正,吸收能力對知識創新效率有促進作用。由此發現,空間溢出效應在部分年份顯著存在;當空間溢出效應顯著時,吸收能力提升可以促進知識創新效率提高。

表5 知識創新階段創新溢出實證結果

表6 產品創新階段創新溢出實證結果
在價值鏈溢出部分,2013年和2014年同省域內產品創新對知識創新的價值鏈溢出對產品創新效率產生了負向影響(α3),α3在2015年和2016年不顯著,同省域內產品創新對知識創新沒有產生顯著價值鏈溢出效應。此時,吸收能力對產品創新效率的影響(α4)不顯著或為負向影響,吸收能力提升不會對知識創新效率產生正向作用,還會因在提高吸收能力時產生的無效資源利用而導致知識創新效率降低。
從環境影響因素看,政府投入力度對知識創新效率沒有顯著作用,表明政府投入不會對知識創新效率產生影響[10]。高等教育投入水平參數只有兩年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高等教育投入沒有發揮應有作用,應提高經費使用和管理能力。企業經費支持參數并不顯著,說明企業經費支持對于知識創新效率沒有顯著促進作用,這與價值鏈溢出分析結果一致。經濟發展水平參數檢驗結果均顯著且為正值,表明經濟發展是科技創新的基礎,可以促進知識創新效率提高。
4.3.2 產品創新階段
從表6可以看出,在空間溢出部分,2013—2015年各省域產品創新階段的空間溢出對產品創新效率的影響(α7)顯著,此時吸收能力對產品創新效率有顯著正向影響(α8);當知識創新階段、產品創新階段屬于不同省域時,知識創新階段對產品創新階段的空間溢出對產品創新效率的影響(α11)在2014年和2015年顯著。同時,α12顯著為正,表明吸收能力對產品創新效率具有促進作用。由此發現,空間溢出效應在部分年份顯著,當空間溢出效應顯著時,吸收能力提升可以促進產品創新效率提高。在價值鏈溢出部分,同省域內知識創新對產品創新的價值鏈溢出對產品創新效率的影響(α9)均不顯著,表明同省域內知識創新階段對產品創新階段沒有產生顯著價值鏈溢出效應,知識創新階段和產品創新階段之間沒有形成互動。此時,吸收能力對產品創新效率的影響(α10)也不顯著,吸收能力提升不會對產品創新效率產生顯著積極影響。
從環境影響因素看,產學研合作程度參數只有兩年顯著且為負值,說明高校及科研院所和企業之間沒有形成良好互動關系,與價值鏈溢出分析結果一致。產業結構參數不顯著,第三產業產值提高不會對產品創新效率產生顯著影響。金融支持力度同樣不能影響產品創新效率,說明除資金支持外,金融服務水平等還需要進一步提升。經濟發展水平對產品創新效率呈現負向影響,原因是受到創新投入冗余的影響。市場化水平可以正向影響產品創新效率,市場化水平提高可以激發企業創新主體意識[10],促進創新產生,從而提高創新效率。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文將吸收能力引入知識創新階段和產品創新階段的空間溢出及價值鏈溢出效應中,并建立相應的空間計量模型,在利用NSBM模型測量內地30個省域知識創新效率和產品創新效率的基礎上,就空間溢出、價值鏈溢出與吸收能力對知識創新效率和產品創新效率的影響進行檢驗,結果表明:
(1)在空間溢出部分,空間溢出效應在部分年份顯著,說明省域間沒有形成穩定的空間關聯關系,存在某些年份各省域間創新活動關聯程度較低的情況。當空間溢出效應顯著時,吸收能力提升可以對知識創新效率和產品創新效率產生顯著正向影響;當空間溢出效應不顯著時,吸收能力不存在顯著作用。
(2)在價值鏈溢出部分,同省域內產品創新對知識創新的價值鏈溢出效應在2013年和2014年產生了負向影響,其余年份均不顯著;2013—2016年知識創新對產品創新的價值鏈溢出效應均不顯著,說明各省域內知識創新階段和產品創新階段相對獨立、缺乏互動。此時,提高吸收能力對知識創新效率和產品創新效率沒有顯著作用,甚至具有負向影響。
5.2 建議
(1)加強區域間協同合作與創新過程兩階段之間的融通,促進空間溢出和價值鏈溢出產生。打破區域間地理限制,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推動東部地區的先進技術向中西部地區擴散,促進知識等要素流動,促進區域間創新聯動協同;促進產學研用深度融合貫通,借助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實現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與企業實際需求匹配,強化和完善成果轉化體制機制,打通知識創新和產品創新兩階段間的融通瓶頸。
(2)注重區域吸收能力提升,促進空間溢出和價值鏈溢出轉化為區域創新發展動力。一個區域需要積極主動地利用空間溢出效應與價值鏈溢出效應,采取必要措施提升區域吸收能力,充分利用知識、技術等創新要素的溢出效應推動區域創新發展。
5.3 不足與展望
本文在知識創新階段和產品創新階段的空間溢出及價值鏈溢出效應研究中考慮吸收能力,給創新溢出效應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補充,但是仍存在不足之處,希望能夠在未來研究中予以解決。現有研究存在多種吸收能力衡量方式,未來可以對吸收能力衡量方式予以改進,使其更加準確;對于省域間空間關系的確定,距離閾值參考現有研究進行設定,可以進一步采用不同閾值,將距離因素的影響納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