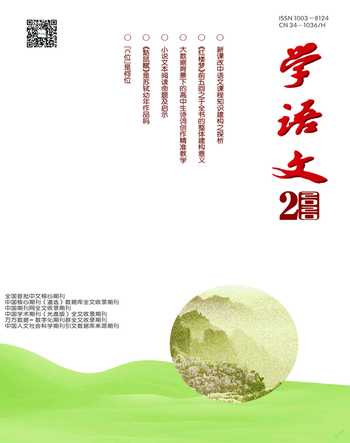《黠鼠賦》是蘇軾幼年作品嗎
陳文忠
摘要:蘇軾幼年詩文作品,流傳至今主要有三篇:一是十歲時應父命而作的《夏侯太初論》,二是十歲左右在學舍與同學合作的《天雨聯句》,三是十一歲時所作的《卻鼠刀銘》。《黠鼠賦》是蘇軾幼年作品嗎?這是誤解。原因有二:一是誤讀了《王直方詩話》的記載,誤以為“兩用”《夏侯太初論》語句的《顏樂亭記》和《黠鼠賦》也是“東坡十歲時”所作;二是缺乏對《黠鼠賦》全文完整深入的細讀。
關鍵詞:蘇軾;幼年作品;《夏侯太初論》;《卻鼠刀銘》;《黠鼠賦》
蘇軾《黠鼠賦》開篇“人鼠斗智”一段,被選入多種行銷甚廣的中學生文言文讀本。于是,網絡上照例出現了對這段有趣文字的種種注釋、翻譯、賞析;同時,不忘標明此文的寫作時間,或曰“相傳為蘇軾11歲時所寫”,或曰“蘇軾11歲時應父命而作”云云。網絡上有些介紹蘇軾童年經歷的文章,則對此作了進一步演繹。
《黠鼠賦》是蘇軾幼年作品嗎?這是今人的誤解!本文先說可信的蘇軾幼年詩文,再談今人誤解的緣由。
蘇軾幼年的詩文作品,流傳至今,可考可信的主要有三篇:一是十歲時應父命而作的《夏侯太初論》,二是十歲左右在學舍與同學合作的《天雨聯句》,三是十一歲時所作的《卻鼠刀銘》。
蘇軾十歲時應父命作《夏侯太初論》的記載,初見于北宋《王直方詩話》“東坡作《夏侯太初論》”條。其曰:
東坡十歲時,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其間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蠆”之語。老蘇愛之。以少時所作,故不傳。然東坡作《顏樂亭記》與《黠鼠賦》,凡兩次用之。
王直方(1069—1109)比蘇軾小33歲,生前喜從蘇軾游,可稱蘇軾的忘年交,也是江西詩社中人。此人無他嗜好,惟晝夜讀書,手自傳錄。棄官后,處城隅小園,嘯傲自適。晁公武《郡齋讀書記》稱:“蘇子瞻及其門下士……亟會其家,由是得聞緒言余論,因輯成此書。”書中直錄東坡山谷語頗多,所記應當可信。
夏侯太初何許人?老蘇為何命蘇軾為之作論?夏侯太初即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后為三國曹魏正始名士,推為正始玄學家的“宗主”,著有《本玄論》等系列玄學著作,對玄學名稱的形成和玄學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三國志·魏書》有傳。《世說新語》中《方正》《雅量》《賞譽》《品藻》諸篇載有時人和晉宋名士對他的贊頌:觀其人,“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賞譽》);論其學,“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方正》)云云。《世說新語·雅量》中的一則故事,最能傳神寫照: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面對“霹靂破柱,衣服焦然”的突發危急情境,夏侯太初的神色無變與賓客左右的跌蕩無狀形成鮮明對照。夏侯太初既是正始名士,也是曹魏集團的著名軍事家和政治家。在軍事上,正始年間曾任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負責防蜀重任。在政治上,他是正始改制集團的中堅人物。嘉平六年,與李豐合謀政變,事發被司馬氏所殺,時年46歲。《三國志·魏書·夏侯玄傳》寫其臨刑:“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蘇軾的《夏侯太初論》“以少時所作,故不傳”,只留下他后來反復引用的兩句:“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蠆。”
前句暗用了藺相如完璧歸趙的典故。寓理于象,兩相對比,兩句意思是,人激于義憤有時可以撞碎貴重的寶玉而在所不惜,有時卻因打壞一口鍋而失聲痛哭;人鼓起勇氣可以同猛虎搏斗而無所畏懼,有時卻因被毒蜂一蜇而猝然變色。這是常人狀態而非英雄本色。
蘇洵為何命蘇軾作《夏侯太初論》?莫非想讓蘇軾從小以夏侯太初為榜樣,將來無論在生活中遇到“霹靂破柱”的突發情境,還是為國為民必須“臨刑東市”,都能像夏侯太初那樣“神色無變,舉動自若”?同樣在蘇軾十歲左右,母親程氏夫人為蘇軾兄弟親授以書,以氣節勉勵二子。“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墓志銘》)蘇洵命蘇軾作《夏侯太初論》,程氏夫人親授以書,以歷史名人為榜樣,以氣節勉勵二子,目的是相同的。《夏侯太初論》僅剩兩句,但意味深長,極富想象空間。
蘇軾與同學合作的《天雨聯句》,《蘇軾文集》卷六十八《記里舍聯句》曾追敘其事。其曰:
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堯咨、舍弟子由會學舍中《天雨聯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楊云:“夏雨凄涼似秋。”余云:“有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吃饅頭。”坐皆絕倒,今四十余年矣。
蘇軾所謂“幼時”,孔凡禮《蘇軾年譜》系于蘇軾“十歲”。《欒城集》卷十五《送程建用宣德西歸》開首云:“昔與君同巷,參差對柴荊。”詩末自注:“君昔嘗稅居,與弊廬東西相望,武昌君見其家事,知非貧賤人。此語未嘗語人。俯仰三十年矣。”詩作于元祐元年。武昌君謂母程氏。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曰:“以子由聯句論之,要不出于十齡作也。”今從其說。
今讀四人聯句,程、楊謹守詩格,蘇軾轉而嘲戲,蘇轍則直取生活,然不免俚俗。眾人之所以絕倒者,正以蘇轍之句俗。蘇轍晚年比較兄弟詩文風格,有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二人幼年聯句,似已能見出某種傾向。
蘇軾幼年作《卻鼠刀銘》,事見蘇籀《欒城先生遺言》。其曰:
東坡幼年作《卻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修寫、裝飾,釘于所居壁上。公言,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
蘇籀是蘇轍之孫。《四庫全書總目》曰:“籀字仲滋,眉州人。轍之孫,遲之子也。南渡后居婺州,官至監丞。籀年十馀歲時,侍轍於潁昌。首尾九載,未嘗去側,因錄其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以示子孫,故曰《遺言》。”蘇籀所記,自當可信。《卻鼠刀銘》,孔凡禮《蘇軾年譜》系于蘇軾十一歲。今從其說。蘇籀是蘇洵之曾孫,“曾祖稱之”,即蘇洵對二子文章的稱贊。蘇轍《缸硯賦》,孔凡禮《蘇轍年譜》據其“序”系于蘇轍十七歲。此處不論。
《卻鼠刀銘》是蘇軾幼年詩文中,惟一完整保存的作品。全文如下: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劍鉞之馀。文如連環,上下相繆。
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
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終夕窣窣。叱訶不去,啖嚙棗栗。
掀杯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為兩門,窘則旁出。
輕矯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為怪妖。
晝出群斗,相視睢盱。舞于端門,與主雜居。貓見不噬,又乳于家。
狃于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盤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
物豈有是,以為不誠。試之彌旬,凜然以驚。夫貓鷙禽,晝巡夜伺。
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須搖乎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
是獨何為?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為畏,相率以逃。
嗚呼嗟夫!吾茍有之。不言而諭,是亦何勞。
南宋初彭乘《續墨客揮犀》卷五《卻鼠刀》條曰:“蘇子瞻有卻鼠刀,云得之于野老,嘗匣藏之。用時但焚香置凈幾上,即一室之內無鼠。”這段文字,除“用時但焚香置凈幾上”,似出于對蘇軾的仙化想象,顯然源自《卻鼠刀銘》。
蜀地民間或有一種習俗,在家中置放一把卻鼠刀,便可以驅趕老鼠。《卻鼠刀銘》以豐富的想象,奇幻的情節,流暢的文筆,贊美了卻鼠刀立竿見影的驅鼠威力。全文思路清晰,層層推進,跌宕起伏,首尾照應,可細分為四個層次:從“野人有刀”到“暴鼠是除”為第一層,簡要介紹了卻鼠刀的來歷、形狀、紋飾和“暴鼠是除”的功用;從“有穴于垣,侵堂及室”到“吾刀入門,是去無跡”為第二層,具體描寫了惱人的鼠患和暴鼠的狡黠。對鼠鬧場面和暴鼠行徑的刻畫,顯示出幼年蘇軾過人的觀察力和老到表達力;從“又有甚者,聚為怪妖”到“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為第三層,小蘇軾突發奇想,從現實到虛幻,描述了“聚為怪妖”的老鼠精的鼠鬧,文思更進一層,而“炊未及熟,肅然無蹤”,則再次顯示出卻鼠刀的超然威力;從“物豈有是,以為不誠”到“不言而諭,是亦何勞”為第四層,通過上述兩個場景的描寫,作者由敘述到議論,對“宛然尺刀”勝于“兇貓鷙禽”的威力表達了無以言表的佩服,也為擁有威力無比的卻鼠刀而感到得意和慶幸。
蘇轍晚年用一個“奇”字評此文。幼年蘇軾把得之于野老的一把卻鼠刀,以洋溢的才思,鋪采摛文,敷衍成一篇250余言的四言銘文,不能不令人稱“奇”。毋怪得到父親的稱贊,隆重地“命佳紙修寫裝飾,釘于所居壁上”,以示表彰。
考察了可信的蘇軾幼年作品,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問題了。《黠鼠賦》是蘇軾幼年所作嗎?回答是否定的。那么,為什么會流傳那種說法呢?原因有二:一是誤讀了《王直方詩話》的記載,誤以為先后“兩用”《夏侯太初論》語句的《顏樂亭記》和《黠鼠賦》,也是“東坡十歲時”所作;二是缺乏對《黠鼠賦》全文完整深入的細讀。
繼《王直方詩話》之后,南宋初吳幵《優古堂詩話》也有“蘇軾作《夏侯太初論》”的記載,并對殘句作了溯源。他在引用《王直方詩話》語之后,繼續寫道:
……以上皆王記。予按《晉書·劉毅傳》鄒湛曰:“猛虎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予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予意外故也。”乃知東坡意發于此。
經吳幵補充的這段文字,稍后為南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沿襲”類轉錄。從《王直方詩話》到《優古堂詩話》,宋人關于《夏侯太初論》的記述包含三層意思:一是蘇軾十歲時,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老蘇愛之”;二是此文為少時所作,故不傳,但有兩句在《顏樂亭記》和《黠鼠賦》中,“凡兩次用之”;三是吳幵發現,流傳的兩句并非全是蘇軾的原創,而是對鄒湛語融入己意的再創造。
那么,《顏樂亭記》和《黠鼠賦》作于何時?所謂《顏樂亭記》,其實是《顏樂亭詩并敘》中的“敘”。《敘》曰:
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顏氏久矣。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其上,命之曰“顏樂”。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于小者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之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用以自警云。
據清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卷十五考證,《顏樂亭詩并敘》作于蘇軾離開密州之后,亦即為蘇軾四十二歲后所作。《敘》中引文后,王文誥注曰:“以上四句,乃公十來歲時,宮師命作《夏侯太初論》語。后惟見于《黠鼠賦》及此敘中,其原文已佚去矣。”[1]王注明確告訴我們,《顏樂亭記》和《黠鼠賦》,均是蘇軾后來的作品。
細讀《黠鼠賦》全文,也可發現此文絕非“東坡十歲時”所作。《黠鼠賦》同《赤壁賦》一樣,是散文體的文賦,而非駢偶體的律賦,同樣是富于理趣的名篇。全文可分三層:第一層是敘述,通過蘇子與童子的對話,描寫了人鼠斗智的場面,掉在囊橐之中的老鼠,運用巧智,死里逃生,刻畫了黠鼠之“黠”;第二層是蘇子由此發出的感慨,“役萬物而君之”的智慧之人,竟然“見使于一鼠,墮此蟲之計中”;第三層由沉思而醒悟,蘇子通過同幻化人物的對話,恍然而悟,之所以“墮此蟲之計中”,是因為“不一于汝,而二于物”的“不一之患”,并再次引用《夏侯太初論》中的語句,予以論述:
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嚙而為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余俯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怍。
細讀全文,至少有三處表明,此文絕非十歲的蘇軾所作:一是十歲的蘇軾不可能稱自己為“蘇子”,并有一個“童子”相隨。十歲的蘇軾正從張易簡在學舍中讀書;二是蘇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十歲的蘇軾不可能自夸“多學而識之”;三是引語后明確寫道:“言出于汝,而忘之耶?”這是你自己說過的話,難道你忘了嗎?
詩文句意的自我重復,在文學史上并不少見。陸游即是一例。錢鍾書曾說:“放翁多文為富,而意境實少變化。古來大家,心思句法,復出重見,無如渠之多者。”[2]蘇軾的自我重復,亦非一例。北宋趙令畤《候鯖錄》卷一《東坡十余歲擬謝對衣并馬表》曰:“東坡十余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并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間有云:‘匪伊垂之帶有余,非敢進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仍益之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余;斂退之心,非敢進也馬不進。”趙令畤是蘇軾知潁州時的屬僚,過從甚密,所言當可信。不過,縱觀蘇文,像《夏侯太初論》《顏樂亭記》和《黠鼠賦》,在時間跨度如此之大的三篇文章中,一字不易地重復同樣的話,并不多見。
意象比喻是多義的。這兩句在三篇文章所起的作用也有微妙的差異:《夏侯太初論》或意在反襯夏侯玄“霹靂破柱”卻“神色無變”的鎮定;《顏樂亭記》用以闡明“古之觀人也,必于小者觀之”的道理,以正韓子之說;《黠鼠賦》則借以強調“不一于汝,而二于物”的危害。
《黠鼠賦》作于何時?《王直方詩話》把它置于離開密州后寫的《顏樂亭記》之后。文中“蘇子”僅有“童子”相隨,居處又有“黠鼠”為害,處境極為落寞。莫非寫于再貶黃州之后?待考。
參考文獻:
[1]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第三冊),中華書局1982年,第777頁。
[2]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中華書局1984年,第125至126頁。
(作者單位: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
[責編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