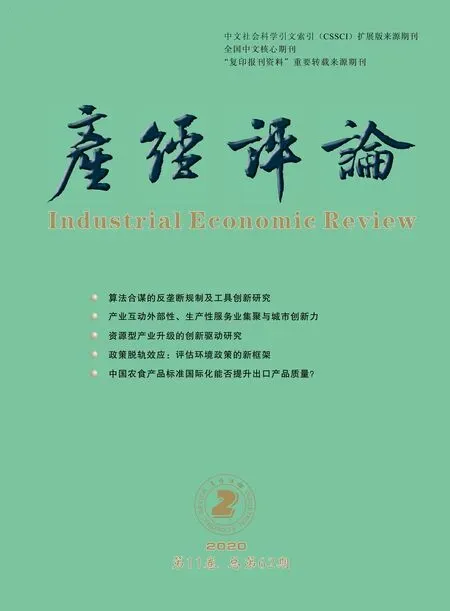產業互動外部性、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城市創新力
——對我國七大城市群的一項實證比較
一 引 言
在各大區域發展戰略推進下,我國區域經濟呈現出“均衡-非均衡-均衡”的倒U型結構。在這一過程,城市群發展和擴張,形成了十大城市群的區域空間格局。城市群經濟在我國經濟版圖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已經成為創新擴散的主要載體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從實踐層面驗證了區域經濟“在集聚中走向均衡”的重大理論意義(陸銘等,2019)[1]。然而,隨著跨國投資對各國經濟的不斷滲透,構建了一個以城市為節點的全球生產網絡,從而經濟全球化所加劇的企業與企業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演化為大城市群之間的競爭。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明確指出,以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動國家重大區域戰略融合發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領城市群發展、城市群帶動區域發展的新模式。因此,今后我國經濟空間分布的趨勢是在宏觀層面相對分散而在區域尺度上相對集中,跨區域的協同創新發展是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區域經濟研究的重要方向。
另一方面,由于產業結構在時間和空間上會產生知識擴散與互動效應,即動態外部性(Dynamic Externalities)(Helsley和Strange,2014)[2],產業協同升級通常作為跨區域協同發展的主要抓手。黨的十九大報告也強調,推動創新驅動和產業結構升級對中國經濟穩定增長至關重要。而生產性服務業是為商品或服務生產提供中間服務投入的產業,是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高級產業形態,具有附加值高、專業化程度高、知識密集等特點,且伴隨著全球生產方式從“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轉變,處于價值鏈高端的生產性服務業逐漸取代制造業成為“后工業社會”區域經濟增長和城市體系重構的主導產業,是城市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楊帆,2018)[3],甚至成為識別與解析世界城市體系、國家或區域城市網絡的重要工具(Ashworth,2011[4];路旭等,2012[5])。中國當前仍處于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中低端(任志成等,2017[6];陳明和魏作磊,2018[7]),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是各級政府推動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引領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提升、促進經濟提質增效的重要措施。那么,生產性服務業如何作用于區域城市創新?本文從產業集聚外部性與產業互動外部性(即產業結構動態外部性)著手,以城市群作為研究的空間尺度,分析各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在城市群內的相對集聚程度對該城市創新的影響,并分城市群探討這種影響的差異性,為促進產業更好更快更可持續發展、提升城市群區域創新競爭力提供參考。
二 文獻回顧與理論機制
1.產業集聚理論
集聚經濟理論認為,共享、匹配和知識溢出是產業集聚促進創新的主要途徑。集聚經濟的本質是分工經濟,產業集聚之所以能夠驅動創新發展,與其如下特性密不可分:(1)專業化外部性(即MAR外部性),有學者稱之為“產業關聯效應”,強調相同產業集聚形成更緊密更細化的產業鏈,通過專業化的勞動力池和“干中學”效應,促進產業內知識溢出和經濟創新增長(Romer,1990)[8]。(2)多樣化外部性(即Jacobs外部性),亦可稱作“產業互補效應”,認為不同行業廠商集聚帶來的跨行業知識溢出是技術創新的主要源泉(Jacobs,1969)[9]。Jacobs利用美國170 個城市的六大產業數據驗證了外部性理論,從投資組合理論的角度來看,多樣化集聚的城市擁有更有效的資源配置組合,創新成功的可能性及效率均會提高。(3)市場外部性(Porter外部性),或稱“產業競爭效應”。Combes(2000)[10]強調高度的市場競爭將導致企業強烈的研發投入動機,從而實現知識的快速積累和增長。(4)規模經濟效應或范圍經濟效應。對于制造業來說,集聚中的企業由于共享城市間基礎設施,具有更廣的生產需求和更低的交易成本,促進了生產率和創新效率的提高;而生產性服務業由于需求的差異化和多樣化,通過集聚可以擴大生產范圍和發展空間,降低經營風險,獲取范圍經濟效應(張天華等,2019)[11]。
專業化集聚和多樣化集聚都強調了外部知識對創新的重要性,其區別在于知識是否存在產業邊界(Beaudry和Schiffauerova,2009)[12]。相關研究表明,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對創新效率或經濟增長的影響有差異,可歸納為三種結論:一是MAR外部性比Jacobs外部性更有效,如Baptista和Swann(1998)[13]發現專業化集聚相對多樣化集聚更有利于企業創新;范劍勇等(2014)[14]構造了1998-2007年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企業面板數據,分析了產業集聚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影響及TFP變化的結構性因素,發現專業化經濟通過技術效率改善對TFP增長產生正面的顯著影響,多樣化經濟雖然能夠促進前沿技術進步,但是沒有顯著促進整體TFP增長;劉乃全等(2016)[15]通過研究專業化集聚、多樣化集聚對我國2003-2012年30個區域創新效率的影響,亦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二是Jacob外部性比MAR外部性更有效,認為知識的外溢更易發生在互補的行業而不是同行業的企業之間,因此城市中多樣化產業結構所帶來的雅各布外部性或者跨行業聚集經濟更容易促進企業的創新,Antonietti和Cainelli(2011)[16]利用意大利制造業企業數據的經驗研究結果即支持了這一觀點;賴永劍(2012)[17]利用2005-2007年中國制造業企業平衡面板數據集,研究集聚經濟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發現專業化水平與企業創新成功率及勞動創新產出率之間均存在倒U形關系;而多樣化水平對企業創新績效有最突出的正向作用,也驗證了多樣化最有利于企業創新。三是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分別在不同環境下有效,Andersson et al. (2005)[18]對瑞典進行實證分析認為專業化和多樣化集聚均有利于技術創新;程中華和劉軍(2017)[19]則從集聚外部性和城市規模角度分析了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工業效率提升的空間外溢效應,發現專業化集聚和多樣化集聚對不同規模等級城市工業效率提升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由此提出對于規模較小的城市,工業化水平較低,工業結構較初級,專業化集聚模式更適合;反之,多樣化集聚發展模式更適合。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設1:
H1: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具有空間外溢效應,專業化集聚與多樣化集聚兩種集聚模式的空間外溢效果不同。
2.產業價值鏈理論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創新力之間的聯系不僅體現在上述的產業結構動態外部性,也體現于生產性服務業本身的特殊性上。一方面,生產性服務業與消費性服務業及制造業相比,由于其消費替代彈性小,故消費者多樣性需求越強,在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的框架下,則越容易實現規模報酬遞增(陳建軍等,2009)[20];另一方面,生產性服務業主要為制造業服務,具有知識密集度高、產出附加值大的特性,扮演著知識源和技術源的角色,生產性服務業可以嵌入制造業價值鏈,與制造業形成良性互動以提高制造業產業結構的軟化程度。因而,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有利于形成基于結構軟化的動態比較優勢,進而提升產業競爭力和城市創新力(李福柱和李倩,2019)[21],主要表現為:科學研究服務業嵌入制造業帶來技術創新優勢,信息傳輸、計算機與軟件服務業嵌入制造業形成柔性制造優勢,商務服務業嵌入制造業產生營銷與品牌優勢,金融服務業嵌入制造業帶來融資優勢,交通運輸與倉儲服務業嵌入則形成運輸優勢等(于明遠和范愛軍,2019)[22]。而這一作用機理主要通過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實現,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設2和假設3:
H2:生產性服務業的相對多樣化集聚更能通過嵌入制造業獲取動態比較優勢進而提高城市創新競爭力。
H3:產業結構動態外部性表現出明顯的區域異質性,對于不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的城市群,其對城市創新力的影響有差異。
綜上,相對于現有文獻,本文創新之處可能在:(1)選取城市群為研究及測度集聚水平的空間尺度,以突出城市群在我國區域經濟格局中的作用,并充分考慮產業集聚的地域根植性和空間外部性兩個原生性特征。(2)以生產性服務業的行業集聚度為核心研究變量,而非常見的高技術產業集聚程度,相比高技術產業對創新的直接影響,生產性服務業對創新的影響及作用機制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和可探究性。(3)對于城市創新力的衡量,借鑒了大多數文獻中采用的發明專利授權數,但本文選取的是經過價值化、有效化、標準化等多步驟處理的創新指數,即已被授權的有效發明專利價值存量,以更準確地反映城市創新能力。

圖1 產業互動外部性、集聚外部性對城市創新產生影響的理論機制
三 實證研究設計
知識溢出是集聚外部性的一個重要表現,不同產業所產生的集聚外部性大小各有差異,而生產性服務業是典型的知識密集型產業,具有較高的技術進步水平及較強的凝聚力,是我國經濟高質量增長的新動能(李平等,2017)[23]。本文主要刻畫生產性服務業大類下幾大細分行業的集聚情況,研究其對創新產出的影響。根據“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和東部率先發展”這一區域發展總體戰略要求,考慮各城市群經濟發展水平及數據可得性,東部地區選取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中部地區選擇長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西部地區選取成渝城市群,東北地區則選擇哈長城市群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

表1 七大城市群主要城市構成
(續上表)

城市群組成成渝城市群重慶;四川省的成都、自貢、瀘州、德陽、綿陽、遂寧、內江、樂山、 南充、眉山、宜賓、廣安、達州、雅安、資陽。哈長城市群黑龍江省的哈爾濱、齊齊哈爾、大慶、牡丹江、綏化;吉林省的長春、吉林、四平、遼源、松原。
(一)模型設定
為更好地反映產業結構動態外部性對城市創新力的影響和兩者間的空間作用,本文基于Griliches(1992)[24]提出的知識生產函數,將兩種產業結構動態外部性作為技術因素加入,并充分考慮到研究變量的空間效應既可能存在于變量間的空間相關性,也可能是由地區誤差項在空間上的相關導致,建立了擴展型知識生產函數的空間杜賓模型:
(1)
為避免模型內生性問題帶來的偏差,將創新的時間效應納入考察,在式(1)基礎上構建動態空間面板杜賓模型:
(2)

θ1lnECOit+θ2lnINFit+θ3FINit+θ4GOVit+θ5INPit+θ6ENVit+εi+λt+μ
(3)
本文將重點考察系數β1、β2和ρ1、ρ2、ρ3,其中β1、β2用來考察本地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和多樣化集聚對該城市創新力的影響,ρ1用于捕捉鄰近城市創新對本地創新的影響,ρ2、ρ3用于捕捉鄰近城市生產性服務業的專業化集聚和多樣化集聚對本地創新的影響。
(二)數據來源與變量選取
本文采用涵蓋我國七大城市群的127個地級市的2003-2016年面板數據,且數據均經過定基處理和平滑處理,以2001年為基期。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價格指數統計年鑒》、各省統計年鑒和各城市統計年鑒,個別年份缺失的數據,用相鄰年份的平均值補充。根據最新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國家標準》(GB/T4754—2015),本文將服務業中行業代碼在51~60、63~63和71~75之間的行業確定為生產性服務業,具體為批發與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和軟件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等六個細分行業。模型中各研究變量的指標選取如下。
1.被解釋變量
城市創新力(IPV):由城市創新指數反映,不再以簡單的專利申請數或授權數表示,而是引用《中國城市和產業創新力報告2017》中的創新指數。這一創新指數將專利價值化,不僅在建立專利更新模型時剔除已過期的專利授權,得到有效專利授權存量,而且經過標準化處理,剔除了價格因素。其計算方法是以年終(12月31日)作為每年的觀測時點,選擇在觀測時點還有效的發明專利(已被授權并且還處于存續期),最后加總不同城市(或產業)的專利價值得到其專利價值存量;然后將2001年全國專利價值總量標準化為100,計算得到2003-2016年的城市創新指數。
2.核心解釋變量
以相對專業化集聚程度(SPE)和相對多樣化集聚程度(DIV)作為表征產業結構動態外部性的定量指標。測量專業化及多樣化集聚程度的常用方法有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香農威納指數、K-L散度、區位熵等,本文綜合比較各種測算方法后借鑒Duranton和Puga(2001)[25]在研究中所采用的相對多樣化指數來衡量城市的多樣化水平,利用區位熵指數來衡量某一地區產業專業化集聚程度。本文基于城市群這一空間尺度,重新界定產業集聚程度,提出“相對專業化集聚”和“相對多樣化集聚”的計算方法,意指某城市相對其所在城市群內其他城市的行業集聚程度,均以各行業的就業份額為經濟指標進行計算。
(4)
(5)

3.其他控制變量
(1)經濟發達度(ECO):用地區人均GDP表示。創新需求和強度與地區經濟發達程度聯系緊密,一般而言,經濟越發達的城市,創新需求越旺盛,創新要素投入傾斜得越多,因而創新活動更密集,創新成果轉化率也更高。(2)信息化水平(INF):由人均郵電業務收入表示。信息化有助于知識的擴散和創新要素的流通,可有效提升研發效率(余泳澤和劉大勇,2013)[26]。(3)金融發展水平(FIN):金融機構年末存貸款余額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該指標可在一定程度上測度地區金融機構的金融服務水平,金融發展水平越高,企業創新的信貸約束越小(Tadesse,2002)[27],融資渠道的暢通是企業開展創新的動力和保障。(4)政策效應(GOV):由科學技術支出與教育支出之和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表示,以考察當地政府對科技和教育的政策傾斜力度對城市創新力的影響。(5)環境效應(ENV):由單位面積二氧化硫排放量表示。環境規制是制約產業和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這里引入環境效應作為唯一預期對城市創新力有負向影響的變量。(6)投資效應(INP):由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采用永續盤存法對資本存量進行估算(假設平均滯后一年)。
Kit=Ei, t-1+(1-δ)Ki(t-1)
(6)
K0=E0/(g+δ)
(7)
其中,Kit、Ki(t-1)為i地區第t期和第t-1期的資本存量,Ei, t-1為i地區第t-1期的投資額,E0為基期(2001年)的投資額,式(7)為基期的資本存量計算公式,g為考察期內各地投資的平均增長率,δ為固定資產折舊率,本文取δ=15%。為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模型中所有價值變量數據均經過各城市所在省份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進行平減,得到基期為2001年的不變價格數據。
四 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全國總樣本空間回歸分析
針對上文中建立的動態空間杜賓模型,采用動態面板廣義矩(GMM)估計。為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還以靜態空間杜賓模型的回歸估計作為對比,依據隨機效應和固定效應模型的豪斯曼檢驗結果,拒絕隨機效應的零假設,認為固定效應模型更為合適。如表2所示,三種模型的回歸結果大體一致,而動態空間杜賓模型R平方顯著提高,具有更高的擬合度,因此動態空間杜賓模型GMM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和可靠性。

表2 基于127個樣本城市的三種空間回歸估計
(續上表)

變量靜態空間杜賓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動態空間杜賓模型Wx*SPE(ρ2)0.093***0.0140.008(2.68)(0.10)(0.15)Wx*DIV(ρ3)-1.123***-1.283***1.068***(-7.59)(-4.08)(8.77)Wx*lnECO3.997***0.9270.980***(9.12)(0.63)(2.78)Wx*lnINF-0.930***1.279***-1.103***(-5.13)(3.43)(-9.63)Wx*FIN-1.167***-4.668***1.974***(-4.76)(-3.69)(4.71)Wx*GOV-0.955-20.954***17.536***(-1.38)(-7.14)(10.54)Wx*INP2.203***-2.562***1.430***(10.15)(-2.66)(4.96)Wx*ENV0.0260.740***-0.498***(1.51)(6.16)(-11.72)Spatial rho(ρ1)-1.781***-1.600***1.730***(-6.45)(-4.07)(11.34)δe20.107***0.080***0.015***(10.04)(9.96)(10.20)Obs177817781651R20.91 0.570.96Hausman-test155.07***155.07***
注:L1為城市創新力的滯后一期變量,***、**、*分別表示1%、5%、10%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為Z統計量值,下表同。本文展現的結果均為穩健性回歸結果。
結果顯示:δe2和空間自回歸系數(rho)均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空間溢出效應顯著存在,本地城市創新水平的正向溢出有助于促進鄰近城市創新力的提高。滯后一期的創新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驗證了創新存在時間效應,即創新具有連續性,本期的城市創新力受上一年城市創新力顯著影響。生產性服務業兩種集聚類型的系數β1和β2并不顯著,表明城市在城市群內的相對專業化集聚水平和相對多樣化集聚水平對本地創新能力有正向影響,但影響較弱。考慮空間效應的Wx*SPE的系數ρ2不顯著,相對專業化集聚水平對鄰近城市創新能力未產生促進作用,而Wx*DIV的回歸系數ρ3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相對多樣化集聚則顯著地促進了鄰近城市創新能力的提升,驗證了假設1。這一結果與王春暉(2017)[28]的研究結論相互呼應,表明生產性服務業的多樣化外部性對我國整體創新能力的提高作出有益的貢獻,反映出生產性服務業在特定區域內為多樣化集聚提供了多樣化的服務環境,減少了工業企業的生產成本和搜尋成本,推動了生產性服務業和工業的融合創新。同時,生產性服務業的多樣化集聚使各產業關聯更加密切、互補性的知識交流更加頻繁,有助于產生更多的創新回報。
此外,經濟發達度、政策效應、投資效應的系數均顯著為正,對本地創新能力起顯著正向促進作用,而信息化水平、金融發展水平、環境效應對本地創新能力的影響不顯著。所有控制變量的空間權重系數均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其中本地經濟發達度、金融發展水平、政策效應、投資效應的溢出均對鄰近城市創新能力有促進作用,信息化水平、環境效應的溢出則顯著抑制了鄰近城市的創新力。
考慮行業異質性問題,參考史雅娟等(2017)[29]的做法,本文進一步將六大生產性服務業按照產業本身的技術性和與制造業融合程度劃分為高級生產性服務業和一般生產性服務業(見表3),以分別研究高級生產性服務業與一般生產性服務業的兩種集聚水平對城市創新力的影響,結果見表4。

表3 生產性服務業的行業劃分

表4 基于行業異質性的動態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
(續上表)

變量高級生產性服務業一般生產性服務業INP0.097***0.097***(5.18)(5.13)ENV0.0010.001(0.87)(0.78)Wx*SPE(ρ2)-0.350***0.745***(-4.55)(2.70)Wx*DIV(ρ3)-0.002***-0.019***(-3.45)(-2.93)Wx*lnECO-0.379-0.772**(-1.09)(-2.12)Wx*lnINF-0.451***-0.321***(-3.98)(-2.73)Wx*FIN0.426-0.154(0.98)(-0.36)Wx*GOV8.001***7.450***(5.37)(5.21)Wx*INP0.950***1.059***(3.39)(3.73)Wx*ENV-0.131***-0.172***(-3.07)(-3.96)Spatial rho(ρ1)0.0270.020(0.18)(0.13)δe20.107***0.015***(10.04)(10.53)Obs16511651R20.95 0.94
從表4可以看出,高級生產性服務業的相對多樣化集聚會顯著降低本地城市的創新力水平,但估計系數為-0.00001,影響微弱,一般生產性服務業的相對多樣化集聚對本地創新無顯著的負向作用,因此整個生產性服務業的相對多樣化集聚并未對本地城市創新產生顯著性影響,而高級生產性服務業和一般生產性服務業的相對專業化集聚均對本地創新力無顯著影響,這與表2生產性服務業整體的相對多樣化集聚與相對專業化集聚估計系數均不顯著相一致。空間權重系數中,高級生產性服務業的相對專業化集聚和相對多樣化集聚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即與鄰近城市創新力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一般生產性服務業則表現出因集聚外部性的來源不同而對鄰近城市創新力產生差異性影響的特點,其相對專業化集聚估計系數在1%顯著性水平下為0.745,表明相對專業化集聚程度每提高1單位將顯著促進鄰近城市創新力增長0.745個單位,而相對多樣化集聚每提高1單位,鄰近城市創新水平顯著降低0.019個單位。未考慮行業異質性的回歸結果表明整個生產性服務業的相對專業化集聚對鄰近城市創新力影響為0.008且不顯著,其原因可能是高級生產性服務業與一般生產性服務業所產生的作用相互抵消。值得注意的是,表2結果顯示整個行業的相對多樣化集聚空間權重系數為1.068,而高級生產性服務業的相對多樣化集聚空間權重系數為-0.002,一般生產性服務業的相對多樣化集聚空間權重系數為-0.019,三個系數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這一結果為假設2提供了充足的論證,說明單一的高級生產性服務業或單一的一般生產性服務業的相對多樣化集聚不足以完全支撐制造業產業體系,使其擺脫靜態比較優勢的束縛,形成基于制造業產業結構軟化的系統的動態比較優勢。只有當生產性服務業的各類“軟要素”適當地嵌入制造業價值鏈中,發揮產業聯動和空間協同的作用,塑造技術創新、柔性制造、營銷與品牌、融資、運輸等綜合比較優勢,才能提升城市產業競爭力和創新力。
(二)考慮區域異質性的空間回歸分析
結合理論分析中提到的我國以城市群為主體的經濟發展格局,本文將127個樣本城市按城市群分類,分別考察產業結構動態外部性對各城市群的城市創新力的影響,仍然采用動態空間杜賓模型進行GMM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表5顯示,生產性服務業相對專業化集聚和相對多樣化集聚對各城市群產生了差異性的影響,所有城市群的空間自回歸系數以及創新的滯后一期系數均顯著為正,創新的時間效應和空間外溢效應顯著存在,從而有效驗證了假設3。下面逐一分析各城市群的實證結果,考察生產性服務業相對集聚水平對不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的城市群影響的差異化狀態,并從產業結構動態外部性角度作出解釋。

表5 基于城市群異質性的動態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
(續上表)

變量珠三角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哈長城市群INP-0.435***0.182***-0.087**0.114***-0.0220.106-0.202***(-2.92)(4.92)(-2.00)(2.81)(-0.69)(1.19)(-3.02)ENV-0.029***-0.004*0.003-0.0030.005-0.002-0.174***(-9.10)(-1.65)(0.38)(-1.26)(1.26)(-0.29)(-12.73)Wx*SPE(ρ2)2.248***-0.217-0.4672.530***-0.1190.005-4.616***(5.38)(-0.65)(0.62)(17.60)(-1.28)(0.18)(-14.45)Wx*DIV(ρ3)0.031-0.414*0.0352.217***3.581***0.026-0.865***(0.15)(-1.87)(0.38)(7.58)(15.43)(0.31)(-21.03)Wx*lnECO8.494***0.308-0.533*19.956***5.399***-1.495-5.367***(13.73)(0.38)(-1.93)(11.52)(5.09)(-0.75)(-7.57)Wx*lnINF0.468***-0.643*0.339*-0.813***0.1650.3282.421***(16.07)(-1.83)(1.82)(-2.74)(1.20)(1.08)(13.65)Wx*FIN15.481***2.432***1.082*25.473***0.854***1.6315.865***(14.83)(2.70)(1.86)(21.31)(3.32)(1.46)(9.13)Wx*GOV4.043***109.030***3.647*54.580***155.580***-2.23810.718***(9.78)(32.16)(1.72)(14.58)(38.79)(-0.59)(3.92)Wx*INP-5.694***-0.218-0.598*-1.741***-6.547***-0.3593.423***(-5.10)(-0.50)(-1.98)(-5.45)(-10.87)(-0.32)(12.57)Wx*ENV-0.405***0.218***-0.015-0.182***0.024-0.1381.216***(-23.40)(3.30)(-0.28)(-4.14)(1.14)(-1.38)(28.01)Spatial rho(ρ1)7.776***6.263***0.399*1.598***0.802***1.499***46.355***(43.04)(44.17)(1.79)(7.28)(3.75)(10.53)(363.73)δe20.0010.011***0.003***0.010***0.018***0.013***-0.031***(1.09)(4.21)(5.86)(7.28)(4.57)(4.49)(-16.94)Obs117338130364364208130R20.68 0.50 0.590.94 0.030.15 0.01
對于珠三角城市群而言,相對專業化集聚回歸系數β1及空間權重系數ρ2為正值,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對本地城市和鄰近城市創新力均產生正向影響,且在七大城市群中對創新的貢獻率最大;相對多樣化集聚系數β2為負值,空間權重系數ρ3為正值,但都不顯著,說明珠三角城市群內城市創新能力主要來源于生產性服務業的專業化外部性,即驗證了馬歇爾外部性理論,不僅當地的生產性服務業相對專業化集聚能夠顯著提高該城市創新力,周邊城市的相對專業化集聚亦促進了本地創新力的提升,這體現出我國珠三角城市群發展的主導模式為專業化發展模式。由于珠三角地區是我國最大的輕工業基地,制造業基礎雄厚,城市群內中心-外圍城市間專業化分工明確,上下游企業協同配合度高,產業鏈條完整,從而形成良性競爭合作關系,創新的輻射效應大于虹吸效應。其他因素如本地經濟發達度、信息化水平、金融發展水平、政策效應對本地城市及鄰近城市創新力亦起到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環境效應同預期一樣對城市創新力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污染越嚴重,將直接抑制本地和周邊城市創新活動的開展,與預期不同的是投資效應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加大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會顯著降低城市創新力。
在長三角城市群中,生產性服務業相對專業化集聚對當地城市創新力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起到負向作用,對周邊城市創新力的影響不顯著,相對多樣化集聚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對本地城市創新力有促進作用而對周邊城市有負向影響,結果有效支持了雅各布外部性理論,長三角的創新發展更多地得益于相對多樣化集聚,符合一直以來長三角地區是我國最大綜合性工業基地的事實。同時反映出城市群內部的競爭強于合作,這與長三角所形成的多中心-外圍的發展模式有關,上海、南京、杭州以及次中心城市蘇州、寧波等發展差距較小,各城市產業特色鮮明。而本地經濟發達度、信息化水平、金融發展水平、政策效應、投資效應對本地創新力同樣產生正向推動作用,環境效應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對當地創新能力產生抑制性影響。經濟發達度和投資效應未對鄰近城市創新產生顯著影響,信息化水平對鄰近城市創新力有負向作用,可能與信息流動及信息獲取的便捷性增加了就業流動機率有關,金融發展水平、政策效應、環境效應均對鄰近城市創新力有顯著促進作用。
京津冀城市群與成渝城市群的核心解釋變量回歸結果基本一致,相對多樣化集聚對當地城市創新力的影響不顯著,且相對專業化集聚和相對多樣化集聚的空間權重系數均不顯著,表明在該城市群內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動態外部性溢出效應不明顯,不同之處在于京津冀城市群內生產性服務業相對專業化集聚對城市創新力的負向影響顯著而成渝城市群內該系數不顯著,可以概括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并不能驅動京津冀城市群與成渝城市群內城市創新,原因可能是產業集聚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如房價高企、交通擁擠、同業競爭等超過其帶來的知識共享、勞動力池等正面效應;另一種解釋是該城市群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水平相對較低,與制造業的嵌入程度有待加強,導致基于制造業結構軟化的動態比較優勢不明顯。結果中還需要注意的是對京津冀城市群而言,經濟增長和投資增加并不能提高本地創新水平,反而會產生反向作用。
對于長江中游城市群,隨著生產性服務業相對專業化集聚和相對多樣化集聚水平的提高,本地城市和鄰近城市的創新力亦會顯著上升,反映了在該城市群中馬歇爾外部性和雅各布外部性是有效的。對比兩種系數大小發現,相對多樣化集聚比相對專業化集聚對本地城市創新力的正向作用更強(β2>β1),相對專業化集聚比相對多樣化集聚對鄰近城市創新力的促進作用更大(ρ2>ρ3)。目前長江中游城市群處于工業化加速發展階段,對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和依賴程度高,因此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城市群內城市創新起著重要而顯著的作用,是城市創新的關鍵驅動力。控制變量中,信息化水平和環境效應對本地城市創新力無明顯影響,其余變量均顯著地促進了本地城市創新力的提高,信息化水平、投資效應、環境效應則對鄰近城市創新力產生明顯的負向影響,而經濟發達度、金融發展水平、政策效應通過空間外溢作用能夠推動鄰近城市創新。
中原城市群內生產性服務業相對專業化集聚對本地創新力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對鄰近城市創新力則影響不顯著;相對多樣化集聚顯著促進了鄰近城市創新而對本地城市創新力作用不顯著,說明該城市群內相對多樣化集聚比相對專業化集聚的空間溢出作用更明顯,但無論是相對專業化集聚亦或是相對多樣化集聚程度的增加,均能帶動城市群整體創新能力的提升。控制變量中除政策效應有助于顯著提升本地城市創新力外,其余變量均對本地城市創新力不產生顯著影響,對鄰近城市創新力產生顯著正向影響的有經濟發達度、金融發展水平、政策效應,投資效應則顯著抑制了鄰近城市的創新,信息化水平和環境效應無顯著影響。
與長江中游城市群截然相反,哈長城市群內生產性服務業兩種相對集聚對本地城市及鄰近城市創新力均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表現出馬歇爾外部性和雅各布外部性均無效;且除經濟發達度起顯著促進作用以及信息化水平無明顯影響外,所有控制變量對本地城市創新起顯著抑制作用;除經濟發達度對鄰近城市創新有顯著負向影響外,其余控制變量均顯著提高鄰近城市創新力。這一定程度上說明哈長城市群經濟發展相對緩慢、產業低端鎖定,工業經濟水平較為滯后,與達到“服務經濟”階段仍有相當一段距離的現狀,在這種情況下,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無法形成良性互動,且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成本大于其產生的正向外部效應。
(三)空間效應的分解及分析
以上實證結果反映了生產性服務業相對專業化集聚和相對多樣化集聚對城市創新影響的不同作用路徑和區域異質性。采用偏導數的方法可以捕捉空間內某一空間單元發生變化對自身因變量以及其他空間單元因變量產生的影響,對自身的影響稱為直接效應,對相鄰空間單元的影響稱為間接效應,兩者加總為總效應(Arnold和Pace,2011)[30]。空間計量模型的一個優勢便是可以定量測度出空間效應的大小。接下來,本文將對生產性服務業兩種相對集聚對城市創新的空間效應進行分解,其中,直接效應即表示某城市生產性服務業相對集聚對該城市創新力的影響,間接效應則指其他城市生產性服務業相對集聚對該城市創新力的影響,總效應為所有樣本城市生產性服務業相對集聚對該城市創新力的影響。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空間效應的分解
從直接效應來看,珠三角和哈長城市群內相對專業化集聚存在顯著的負向直接溢出效應,且珠三角的直接溢出效應強于哈長城市群,相對多樣化集聚影響則不顯著,表明珠三角和哈長城市群內生產性服務業相對專業化集聚能夠顯著抑制本地城市創新力的提升,這種抑制作用在珠三角表現更大。具體為珠三角城市群內某城市相對專業化集聚每提高1個單位,該城市創新力將下降0.205個單位;長三角城市群內相對專業化集聚存在顯著的正向直接溢出效應而相對多樣化集聚存在顯著的負向溢出效應,即長三角城市群內生產性服務業相對專業化集聚促進本地城市創新而相對多樣化集聚抑制了本地城市創新;其余城市群內不存在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直接溢出效應。就全國整體而言,相對專業化集聚和相對多樣化集聚的直接溢出效應不顯著。
從間接效應來看,珠三角和長江中游城市群內相對專業化集聚存在顯著的正向間接溢出,后者的正向溢出效應更強,而相對多樣化集聚的影響均不顯著,說明這兩個城市群內其他城市的生產性服務業相對專業化集聚對本地城市創新有顯著促進作用,且該促進作用在長江中游城市群內影響更大;長三角和哈長城市群內相對專業化集聚則存在顯著的負向間接溢出,前者溢出更多,即長三角城市群、哈長城市群內城市創新力受到其他城市生產性服務業相對專業化集聚的抑制作用;相對多樣化集聚的正向間接溢出主要體現在長江中游城市群內,負向間接溢出主要體現在哈長城市群內,換言之,長江中游城市群內其他城市相對多樣化集聚對本地城市創新起到明顯的促進作用,哈長城市群內其他城市相對多樣化集聚對本地城市創新產生抑制性影響。就全國而言,僅相對多樣化集聚存在顯著的正向間接溢出效應。
從總效應來看,生產性服務業相對專業化集聚水平每提高1個單位,全國層面的城市創新力無明顯變化,珠三角城市群中的城市創新力將上升0.371個單位,長江中游城市群內的城市創新力將上升1.687個單位,哈長城市群內城市創新力則下降0.102個單位,基本與間接效應的作用方向相同。而生產性服務業相對多樣化集聚程度每上升1個單位,全國層面的城市創新力將平均顯著上升0.658個單位,長江中游城市群內城市創新力將顯著上升1.498個單位,與間接效應有同方向的影響;長三角城市群內城市創新力會下降0.064個單位,與直接效應作用效果接近;哈長城市群中的城市創新力會下降0.019個單位,可以視為全部來自于間接效應的影響。以上結果進一步檢驗了前面實證結果的穩健性,即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主要是通過與制造業之間的良性互動這一間接渠道來影響城市創新力。
五 主要結論與政策啟示
生產性服務業是優化城市群空間關聯網絡結構的牽引力,是增強城市群競爭力并提升其國際影響力、引領力和控制力的重要引擎,而生產性服務業的空間差異是全球城市崛起、城市體系重構和城市內部空間塑造的主要推力(梁紅艷,2018)[31]。本文從產業結構動態外部性角度切入,將城市群作為產業集聚的空間載體,考察生產性服務業相對專業化集聚、相對多樣化集聚對城市創新力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在城市群之間的差異性。結論是:(1)各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在城市群內相對集聚能夠產生跨區域的影響,即生產性服務業相對集聚具有空間溢出效應;(2)就全國整體來看,對城市創新力有顯著持續性影響的主要是相對多樣化集聚而非相對專業化集聚,因此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生產性服務業嵌入制造業價值鏈中所形成的動態比較優勢來實現城市創新能力的提升,換言之,產業互動外部性的影響大于集聚外部性的影響;(3)生產性服務業相對集聚對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發展模式的城市群內城市創新影響具有差異性。相對專業化集聚對城市創新力有顯著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珠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以及中原城市群中,相對多樣化集聚對城市創新力產生顯著積極影響則體現于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
由上可得以下政策啟示:第一,應當充分運用產業結構動態外部性與空間的聯動機制促進城市創新,促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由過度集聚的地區向集聚不足的地區轉移,緩解由于過度集聚產生的擁擠效應。在城市群內建立疏散產業擁擠機制,加強轉出地區(中心城市)與承接地區(邊緣城市)合作交流,促進產業有效轉移,解決增長乏力和資源錯配的問題。第二,大力完善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產業聯動機制,提升產業價值鏈。通過一定的產業配套與市場引導,強化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嵌入互動效應,尤其是促進制造業與高端生產性服務業融合,通過提高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程度,實現制造業由低價值鏈環節向高價值鏈環節的升級。第三,科學規劃和合理制定異質性產業政策,積極推動城市群之間的協同發展。即使是同位于東部沿海地區的京津冀、珠三角、長三角三大城市群,其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也表現出不同的作用效果,因而應更多地立足于城市群的方位而非東中西部的行政視角制定差異化的產業政策,從而更好地推動區域協同創新發展。譬如對于珠三角城市群,應加強生產性服務業的專業化集聚發展,培養和引進專業技能型人才;對于長三角城市群,則需要借助政府政策以及市場機制,鼓勵和吸引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更好地促進制造業產業鏈的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