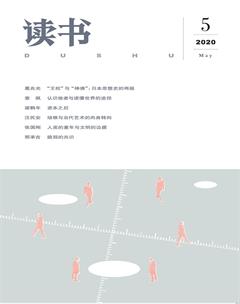特殊的年代、特別的地方和特別的學人
吳小安
一
饒宗頤很特別,是當代中國的國學大師,更是香港的文化符號;反過來,饒宗頤是香港的文化符號,更是當代中國的國學大師。饒宗頤成名成家,與歷史時代和政治變遷密切相關。海內與海外,國內與國際,始終是饒宗頤學術人生與心靈寄托的兩大維度。饒宗頤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僅是其對國學的深厚造詣,而且在于其作為通儒的赤子丹心。國學與中華情,海外華人與中國心,凝聚于一身。
在東亞,與當時國共海峽兩岸分離、東西方冷戰意識形態相對應,英國著名人類學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 把中國香港、澳門、臺灣和海外華人統稱為“殘剩中國”(Residual China)。國際冷戰背景下,“殘剩中國”被西方想象建構為一個分散與邊緣的地緣政治單元,而又成為統一的研討中國的歷史文化社會分析單元;由于當時中國大陸對外隔絕,西方漢學家無法實地進行研究,這些地區也成為西方漢學家替代研究整個中國的實地場域和樣板模型。在當時的政治語境里,相對于新中國而言,弗里德曼“殘剩中國”的概念主要指以意識形態為分野的地理板塊的邊緣性與碎片化的政治特征,以及私有化市場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特征。然而,幾十年后,這一概念所沒有闡發的當代涵義應該更包括中國傳統風俗習慣承繼的文化特征,即以后所發展類似的“文化中國”的概念。與“文化中國”去政治化的族群文化政治概念不同的是,“殘剩中國”概念背后長期被忽視的歷史文化傳統內涵卻很有鮮明對比的啟發性。
經過近百年現代性歷程和社會變遷,回過頭看,中國傳統文化特征,如今更是足見彌珍。港、澳、臺等地區各自擁有了一批來自中國大陸、具有深厚中國文化情結的杰出學者、國學家和文學藝術家,例如歷史學家錢穆、小說家金庸、歌詞作家莊奴和國學大師饒宗頤,他們各自融合了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的元素,成為引領各自領域風騷的社會文化符號。這一時期,與歐美大學留學背景的中國漢學學者在西方大學之間流動不同,一批受中文教育背景的漢學學者,主要集聚和流動在中國香港、臺灣、澳門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大學和科研院所之間。幾十年來,正是這些杰出的學人成為境外中國文化傳統傳承的重要臍帶和傳播的重要符號,其中饒宗頤作為香港的杰出國學大師而熠熠生輝,是當之無愧的。
在東南亞,反殖民主義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重塑了東南亞各國一系列重大內外權力關系版圖,東南亞華僑社會面臨著嚴重沖擊。一九五五年,南洋大學在新加坡正式宣布創辦,這是國外第一家以華文為教學媒介的大學,牽動著東南亞華人社會千千萬萬學子及其家庭的心。一九六五年,新加坡被迫離開馬來西亞宣布獨立,新加坡走上一條立足于自身國情和地區區情的獨特發展道路。一九六八年,新加坡政府成立東南亞研究院。幾乎同時,美越戰爭升級,地區安全政治形勢與新馬國內工運、學運、游擊戰,一外一內,給東南亞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與此相對應,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大批國際海外漢學與新興東南亞學者,紛紛云集新馬兩國。在中國大陸被封鎖的幾十年里,中國臺、港、澳與新、馬一直成為國際亞洲研究、國際漢學、國際資本流動和海外華人社會文化流動互動交匯的重要平臺和關鍵支撐點。這一時期,在區域內,作為華社族群語言文化符號的教育政策與去中國化歷史文化傳統政治的對外政策,相互交織,甚至沖突;在地化的東南亞華人的研究與中國中心的文史哲傳統漢學研究,開始分野,各自發展,前者越來越受到重視,后者顯得越來越落寞。與此同時,與漢學截然不同的發展局面是,東南亞研究則開始風生水起,地區內本土的東南亞研究與地區外的國際東南亞研究相互呼應,開始成為一道亮麗的學術風景。
在更廣闊的政治文化知識脈絡譜系中,歸納起來,至少四大維度的轉型進程,對理解把握饒宗頤,應該非常重要。其一,是中國從幾千年的傳統到一百多年的現代性轉型進程。其二,是中國自古至今對外文化長期交流互動進程。其三,是“二戰”后開始的冷戰、民族國家建構,以及中國對外重新開放、香港、澳門回歸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其四,香港與新加坡同為亞洲四小龍的兩個華人為主的耀眼城市,分別是東亞和東南亞的經濟與現代性的明珠,也是英聯邦內華人學者(無論英文教育還是中文教育)國際化互動與流動的交匯平臺。鑒此,作為偉大變遷的親歷者、承繼者、與時俱進者,饒宗頤恰好成為處于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國家與民族、海外華人社會之間交匯代表性的國家文化符號。而長期定居香港的饒宗頤,更使這種文化符號賦予歷史與當代特殊的意識形態涵義。這種國家文化符號人物包括北京大學的季羨林、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錢鍾書和中山大學的陳寅恪。
二
饒宗頤學術上的特殊意義卻遠不止于此。其一,他是自學成才的,沒有受過大學教育,卻飽讀經書,能成為國際學界承認的國學大師,本身非常具有勵志的社會效應。其二,饒氏精通古文字,甲骨文和梵文,金石、考據和敦煌學,樣樣都是絕學,不是一般學者能夠比肩的。其三,饒氏聚中國古典學者技藝于一身,是當代通儒,古琴、詩詞、繪畫、書法都有很高的造詣,更是罕見。作為漢學家的饒宗頤,成名始終卻在境外,他與印度、日本、美國及歐洲的漢學大儒聯系密切,一九六二年榮獲國際上聲譽極高的西方漢學獎法國“儒蓮獎”,更是奠定了其在學界的地位。在此背景下,一九六八年秋,饒宗頤正式抵達星洲,出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對饒宗頤在新加坡這段重要歲月的研究,對理解饒宗頤的整個學術人生和新加坡當時重要轉型時期的漢學教研狀況,很重要。楊斌博士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學系任教的十二年中,敏銳地捕捉了這個重要的文化與學術課題,在一個非常恰當的年份和地點推出了《上座傳經事已微—饒宗頤新加坡大學執教考》這部厚實而重要的專題著作,可喜可賀。
本書正文共六章,分別題為“南征”“著述訂補”“南洋史地”“南洋學案”“交游”“詩史”,關注饒宗頤在新加坡大學執教歲月的主要問題,涉及饒宗頤受聘的各個技術性細節,敘述了新加坡華文學界專業學術團體南洋學會和新社及其學刊的互動,考訂了饒宗頤在新加坡的漢學研究,特別是古史研究、華文金石研究的重要貢獻,還原了著名南洋學案“蒲羅中”論戰的全部經過,勾勒出饒宗頤在新加坡交游的社會文化脈絡,通篇富于歷史史料的扎實性和歷史學人的想象力,不簡單。饒有趣味的是,書中結語一章,作者以中華文史為經,以香港和星洲為緯,在饒氏學術人生長河的透視中,對饒氏在新加坡大學的五年聘期做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簡要述評,感嘆對比:“香港、香港”與“南洋、南洋”! 誠如作者言:“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八年這十年,前五年基本在新加坡,饒宗頤郁郁不樂;后五年在香港,饒宗頤又如魚得水。到了七十年代末,誰也無法否認,饒宗頤已經是一代宗師,是中華文化圈和國際漢學界的通儒”(345頁)。所以,就個人事業發展而言,如果說,饒氏從香港赴南洋是榮任;那么,饒氏從南洋回香港也很難說不是榮歸。回歸香港,就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無疑是一樣的榮光。作者言“蹩腳的雙城記”,雖欲言又止,而“上座傳經事已微”卻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直抒胸臆、直接點題,發人深省。
在已經出版的幾種饒宗頤學述與傳記著作中,作為專業的歷史學人楊斌的這本專業學術著作,應該是別具一格的。該書的學術重要性相信不僅是因為饒宗頤課題本身,而是因為時段與地域的重要性和專業的高質量。鑒于饒宗頤在新加坡大學并未留下檔案記錄,著述主要依據已經發表的饒著、《南洋學報》和《新社學報》《新社季刊》、其學生和同事的記述回憶,以及口述歷史和實地考察,生動而詳實地呈現了饒宗頤在新加坡大學的學術與社會生活的基本脈絡。有鑒于此,關于饒宗頤在新加坡大學的教學和系務的重要內容,很遺憾地無法涉及。同樣,關于饒宗頤在臺灣“中研院”和美國耶魯大學兩次客座訪問也幾乎不能專門記述,這兩次訪問一年半時間占據饒氏在星洲短短五年的近三分之一,同樣令人扼腕。究其實,除了資料匱乏外,可能與沒有利用新加坡官方檔案、報章資料和其他地方重要收藏史料有關,也與作者在短短兩年半時間內完成此論著有關,同時與作者主要是為了撰寫一篇長文而非專著的初衷應該不無關系。當然,由于時間倉促,編輯不到位,書中明顯出現有些語句重復和打字錯誤的地方。希望在本書再版的時候,作者能夠在背景拓展、事件分析、人物性格和主題彰顯上,進一步精雕細琢。
三
無論是香港,還是新加坡,都是很特別的地方;無論是饒宗頤本人,還是饒宗頤的時代,同樣地,也是很特別的;饒宗頤滯港、抵新與返港的時機,也同樣是機緣巧合的。一九四九年,因機緣巧合饒宗頤滯留香港,旋即受林仰山教授(F.S.Drake)賞識被聘任為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從此人生軌跡突變。一九六八年,饒宗頤赴新加坡大學履新,榮任中文系首位講座教授兼系主任,事業更是如日中天。實際上,從一九六六年饒宗頤接受新加坡大學聘書,到一九六八年他正式履新,雖然前后相差只有兩年時間,然而,新加坡國內與國際形勢卻風云突變,已然大不相同。與其說這是新加坡的國家學術任命,毋寧說更關乎新加坡華社族群文化政治。因為履新后新加坡形勢變化很快,這應該是我們理解饒宗頤當初接獲聘書時躊躇滿志、壯懷激烈的興奮與他抵達后的落寞、離開時的壯志未酬的挫折感的大背景。然而,無論如何,饒宗頤對新加坡華人金石碑銘研究與古史研究的開拓性重要貢獻,功不可沒。自其《星馬華文碑刻系年》(一九六九)開風氣之先以來,東南亞華人金石研究,無論是陳荊和、陳育崧的《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一九七0),還是傅吾康、陳鐵凡的《馬來西亞華文碑刻萃編》(三卷,一九八二、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傅吾康的《印尼華文銘刻萃編》(三卷,一九八八、一九九七),或是傅吾康、劉麗芳的《泰國華文銘刻匯編》(一九九八)、張少寬的《檳榔嶼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銘集》(一九九七)與《檳榔嶼華人寺廟碑銘集錄》(二0一三)、莊欽永的《馬六甲、新加坡華文碑銘輯錄》(一九九八),以及丁荷生、許源泰的《新加坡華文銘刻匯編(一八一九至一九一一)》(二冊,二0一六)等等,幾十年來都可以窺見學術一貫的脈絡和傳承。時過境遷,二0一四年,加拿大的丁荷生(Kenneth Dean)抵新就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首位非華人教授兼系主任,正是基于其對福建和東南亞華人廟宇碑銘的歷史人類學研究的重要貢獻。
長期以來,東南亞一直是所謂的邊緣地帶,沒有引起國人的足夠重視。幾十年來,由于政治分離隔絕,即使中國學人對東南亞也是陌生,如果不是故意忽視的話。當然,閩粵兩省與臺港澳地區總是例外,不僅因為長期歷史紐帶的緣故,也因為社會文化的密切聯系。然而,曾幾何時,無論是閩粵貧苦移民勞工,還是中國知識精英和青年男女,如同西洋、東洋一樣,南洋一直也是他們對外部世界與現代性心儀憧憬向往之地。雖然南洋淘金熱早已褪色,然而,永不褪色的始終是南洋熱帶的異域文化風情和南洋華人的不朽傳奇。雖然亞太地區歷經滄桑巨變,但是遠東的香港和南洋的獅城依然是兩顆燦爛奪目的明珠。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卻又驚人地不同;每個人都會有抵達與離開的時候,然而不同時間、地點的抵達與離開,卻會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何止是“雙城記”的上演。饒宗頤受聘赴新加坡大學與返歸香港中文大學的時機都是機遇。無論歷史如何巨變,一代通儒饒宗頤在新加坡大學執教的短短五年,都將始終是國際漢學史上中華巨儒投放在南洋的一抹異彩。對饒氏學術人生而言,是這樣;對中國與南洋歷史互動而言,也是這樣;對饒氏學術人生進一步拓展而言,仍是這樣。在這種意義上,楊斌博士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學術工作。我想,在該書修訂再版的時日,如果配以一章恢宏大氣的饒氏學術人生與饒氏學問述評的導論,該書將更加大放光彩,相信楊斌是有這份功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