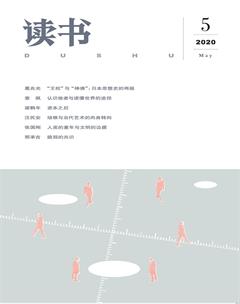“文化就是身體”
李熟了
一九八四年,當(dāng)鈴木忠志寫(xiě)下他那篇最重要的戲劇文獻(xiàn)—《文化就是身體》時(shí),他的劇團(tuán)從東京遷到深山里的利賀村已經(jīng)是第十個(gè)年頭。
利賀村地處日本富山縣,村里沿河修起兩條道路,成為連接外界的出入口。冬季積雪逾米,道路一旦被積雪或是滑坡阻斷,利賀村就會(huì)成為深山里的“孤島”。從一九七六年起,鈴木忠志將自己的劇團(tuán)遷移駐扎在此,迄今四十多年間在這里訓(xùn)練、演出、舉辦戲劇節(jié),并寫(xiě)下了長(zhǎng)長(zhǎng)短短的數(shù)十篇文章。這些文章又以其中最著名的一篇為名匯編成集,題為《文化就是身體》。此書(shū)譯為多國(guó)文字出版,中國(guó)大陸的版本則是二0一七年方成,二0一九年做了修訂。書(shū)中所錄,舉凡戲劇、社會(huì)、人生話題皆收入其中,這些文章貫穿鈴木的各個(gè)時(shí)期,從而勾勒出他的創(chuàng)作脈絡(luò)與思想軌跡,最終又匯流為他“文化就是身體”的核心思考。
然而,初到利賀之時(shí),日后文章中的許多認(rèn)知,對(duì)鈴木忠志來(lái)說(shuō)尚是朦朧的。彼時(shí)對(duì)于外人而言,這個(gè)導(dǎo)演和他的劇團(tuán)更是讓人難以理解—由于演員們每日最主要的事情除了尋找謀生之法,就是高強(qiáng)度的身體訓(xùn)練,如鈴木所述:“有些村民……一度懷疑我們聯(lián)合赤軍旅,借用合掌家屋作為基地,進(jìn)行秘密軍事訓(xùn)練。”(《孤獨(dú)的村落》)
二十世紀(jì)五十年代末,“安保斗爭(zhēng)”席卷日本全境,二十出頭的鈴木忠志亦投身其中。一九六一年,剛剛從早稻田大學(xué)畢業(yè)的鈴木忠志,與劇作家別役實(shí)等幾名大學(xué)同學(xué)共同組建了劇團(tuán),名為“新劇團(tuán)自由舞臺(tái)”。活動(dòng)了五年后,又與團(tuán)員們合力租下了東京一個(gè)咖啡館二樓的空間作為固定演出場(chǎng)地,并將劇團(tuán)改組為“早稻田小劇場(chǎng)”。“安保斗爭(zhēng)”作為鈴木前期創(chuàng)作的社會(huì)背景,雖很難斷言對(duì)于他造成了怎樣的直接影響,但這一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中的一些議題,的確可以在他的演出和理論中看到投射,并在日后的創(chuàng)作與思想軌跡中形成延續(xù)。
在《 文化就是身體》中所錄、成文于二0一一年的《鈴木忠志訪談》里,鈴木回憶道:“像易卜生、布萊希特、契訶夫等都想要改變社會(huì),都確信當(dāng)前的情況已經(jīng)不可忍受……六十年代日本戲劇藝術(shù)家—那時(shí)我剛剛起步—也類似如此。他們?cè)噲D通過(guò)作品傳達(dá)某種強(qiáng)烈的信息。我們說(shuō):‘在日本事情不應(yīng)該是這樣!……像寺山修司和我,我們基本上是把戲劇用作一種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從中可以看出,“戲劇—社會(huì)”這組關(guān)系在鈴木的創(chuàng)作生涯之初,是他的關(guān)注重點(diǎn)。這一時(shí)期的鈴木對(duì)“戲劇—社會(huì)”的強(qiáng)調(diào)實(shí)際上包含了兩個(gè)視角,其一,他認(rèn)為戲劇的發(fā)展并非單純的技術(shù)迭代,而是與社會(huì)深刻相關(guān);其二,戲劇與社會(huì)在關(guān)聯(lián)方式上,并不是以戲劇作為手段反映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那么簡(jiǎn)單。在鈴木看來(lái),戲劇與社會(huì)的連接點(diǎn),在于新的戲劇形式的創(chuàng)造。當(dāng)以新的戲劇形式來(lái)正面回應(yīng)新的社會(huì)問(wèn)題時(shí),形式才能得以持久、具備生命力,同時(shí)戲劇才能對(duì)社會(huì)形成持續(xù)性的影響。而形式創(chuàng)造一旦不去正視社會(huì)問(wèn)題,只能淪為一種景觀,很快就會(huì)被更新鮮的形式所替代。
“安保斗爭(zhēng)”帶來(lái)了那一代年輕人在戰(zhàn)后對(duì)于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的空前參與,也讓將戲劇形式與社會(huì)掛鉤看起來(lái)十分自然,但實(shí)際上,這種視角在當(dāng)時(shí)的日本戲劇界是居于邊緣位置的。日本將二十世紀(jì)初由西方傳來(lái)的、區(qū)別于歌舞伎等傳統(tǒng)藝能的演出形式稱為“新劇”,到五六十年代,“新劇”進(jìn)入發(fā)展的興盛期,從業(yè)人員、演出場(chǎng)次、觀眾數(shù)量都達(dá)到了空前的規(guī)模。然而在戲劇形式上,面對(duì)同時(shí)代巨大的社會(huì)動(dòng)蕩和變革,“新劇”舞臺(tái)卻固守著二三十年代沿襲而來(lái)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傳統(tǒng)。放在鈴木“戲劇—社會(huì)”的視角下來(lái)看,“新劇”的形式和社會(huì)問(wèn)題毫無(wú)關(guān)系,成為一種抽象的技術(shù)體系。對(duì)于整個(gè)年輕一代而言,戰(zhàn)后“新劇”已經(jīng)嚴(yán)重脫離日本現(xiàn)實(shí)卻又牢牢主宰著戲劇界。鈴木忠志的前期思想也因此帶上了對(duì)于“新劇”的反叛性,這種反叛又集中在對(duì)于“新劇”的寫(xiě)實(shí)主義美學(xué)和方法的批判上。鈴木完全不認(rèn)可“新劇”導(dǎo)演把現(xiàn)實(shí)主義理解為日常生活的再現(xiàn),在他看來(lái),契訶夫這樣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劇作大師并不是要將現(xiàn)實(shí)生活場(chǎng)景原樣搬到舞臺(tái)上,而是用一個(gè)在作家的民族文化里充滿詩(shī)意和隱喻的場(chǎng)景,把人物隱秘的心理狀態(tài)抽象外化出來(lái),把這樣的場(chǎng)景原封不動(dòng)地移植到其他民族的舞臺(tái)上,只能是拙劣和庸俗的。他的劇團(tuán)在七年時(shí)間里連續(xù)排演了別役實(shí)的《象》《門》《馬克西米利安博士的微笑》等五個(gè)荒誕劇,與“新劇”的寫(xiě)實(shí)傳統(tǒng)徹底決裂。
在鈴木這里,反寫(xiě)實(shí)作為一種藝術(shù)傾向的產(chǎn)生,一方面是基于在“戲劇—社會(huì)”的問(wèn)題上讓二者直接掛鉤,另一方面則是來(lái)自對(duì)“日本—西方”這組關(guān)系的自覺(jué)。“日本—西方”在“安保斗爭(zhēng)”的時(shí)代并不是一組抽象的對(duì)立關(guān)系,而是觸手可及的現(xiàn)實(shí)沖突:日美安保條約的簽署使得日本實(shí)際成為美國(guó)的附屬,民族本位思想亦在此時(shí)興起,加之駐日美軍犯罪事件頻發(fā),種種因素推波助瀾之下,日本社會(huì)形成了一個(gè)反美情緒的高潮。而此時(shí)的“新劇”界由日共掌握著領(lǐng)導(dǎo)權(quán),其背后的蘇聯(lián)則正試圖調(diào)整冷戰(zhàn)格局、緩和美蘇關(guān)系,于是“新劇”界在“安保斗爭(zhēng)”當(dāng)中不僅毫無(wú)作為,甚至譴責(zé)學(xué)生的行為,這讓年輕藝術(shù)家們對(duì)上一代劇場(chǎng)前輩變得極為失望并走向決裂。在六十年代,反寫(xiě)實(shí)即反“新劇”,反“新劇”又帶上了由日本出發(fā)抵抗美蘇霸權(quán)的政治意味。反美蘇的另一面則是對(duì)于日本自身文化主體性的尋求,“日本—西方”成為那一代年輕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中幾乎天然存在的視角。鈴木曾回憶:“六十年代的日本失去了自身的主體性,急于模仿西方事物,我希望能夠改變這樣的現(xiàn)象。”這種視角又為下一個(gè)階段的超越提供了準(zhǔn)備。
“當(dāng)日本社會(huì)面對(duì)西方影響,從一個(gè)農(nóng)業(yè)團(tuán)體網(wǎng)絡(luò)轉(zhuǎn)變?yōu)橐粋€(gè)現(xiàn)代工業(yè)化社會(huì)時(shí),一種新的戲劇形式也隨之產(chǎn)生。”(《關(guān)于表演》)由六十年代末進(jìn)入七十年代,鈴木從“日本—西方”的思考方式出發(fā),將之置換為“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并使之與戲劇形式掛鉤,從而生產(chǎn)出自己的一系列理論。
一九六八年,別役實(shí)退出“早稻田小劇場(chǎng)”。失去劇作家的鈴木不再以推出某類劇本為中心,轉(zhuǎn)而開(kāi)始以解構(gòu)、拼貼的方式進(jìn)行創(chuàng)作。他從西方當(dāng)代劇本、日本歌舞伎劇本、日本近代小說(shuō)截取片段,將之改編、并置在一處,以《關(guān)于戲劇的東西》為名創(chuàng)作了一部新戲,一九六九年完成演出。新戲?qū)⒀莩龅闹攸c(diǎn)由劇本轉(zhuǎn)移到了演員表演上,女演員白石加代子從此成為鈴木作品的固定主角。次年的續(xù)作《關(guān)于戲劇的東西Ⅱ》更使得鈴木與白石聲名大噪,鈴木被冠上“日本前衛(wèi)戲劇代表人物”等名頭,并帶著這個(gè)戲開(kāi)始參加各國(guó)戲劇節(jié)。同年,早稻小又推出了《關(guān)于戲劇的東西Ⅲ》。三連作的演出讓鈴木完成了自己創(chuàng)作中由文本中心向演員中心的轉(zhuǎn)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