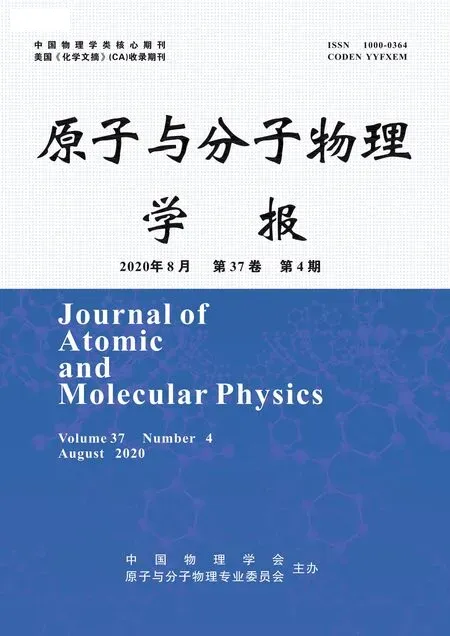表面活性劑單體引起的細胞膜失穩
王 平, 盛 潔, 雷一騰, 馬貝貝,朱 濤,蔣中英,
(1. 伊犁師范大學電子與信息工程學院 微納電傳感技術與仿生器械重點實驗室, 伊寧市 8350002. 南京大學物理學院 固體微結構物理國家重點實驗室, 南京市210093)
1引 言
表面活性劑是一類能夠顯著降低物質表面張力的雙親分子. 與細胞膜作用, 可實現細胞裂解、脂質體外排與膜組分搜集等. 常用的單鏈表面活性劑的物理性質主要由其帶電性、疏水鏈長度等決定[1, 2]. 需要選擇表面活性劑以實現特定的功能, 如陽離子型的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銨(CTAB)被用于提取負電性生物大分子[3], 吸附自促進的十二烷基硫酸鈉(SDS)被用于搜集失活的膜蛋白[4], 對氫鍵作用影響較弱的Triton X-100被用于提取磷脂筏結構[5].
高于臨界成膠束濃度(CMC), 表面活性劑可組裝為膠束. 聚集狀態的表面活性劑可將生物膜組分拔出原始的雙層膜結構, 使后者的完整性嚴重受損[6]. 但低于CMC, 以單體狀態存在的表面活性劑分子與生物膜的相互作用的機制與調控的認識仍存在很多不足.
Tamm等報道了表面活性劑單體可插入生物膜結構, 并考察了結合速率常數與疏水鏈長間的關聯[7]. 插入生物膜的分子可以顯著地改變了前者的側向流動性、剛性、主轉變溫度等性質[8-10]. 但變化的方向與程度由磷脂膜與表面活性劑的組分共同決定[9]. 同時, 插入分子產生的膜內外葉非對稱與過量膜面積是否會引起三維結構重組也是一個開放的問題. 在低濃度下, 月桂酸酯等表面活性劑插入產生了微管或出芽結構[11], 但多肽表面活性劑卻未引起相應的膜三維形態重構[12].
探索單體狀態的表面活性劑與生物膜作用是極其重要的課題. 即使在CMC以上, 仍存在以單體態存在的表面活性劑[2], 需要區分單體和膠束態對生物膜產生的差異. 在本文中, 我們采用了三種常用代表性表面活性劑與仿生磷脂膜作用, 分別是陰離子SDS、陽離子CTAB及非離子Triton X-100. 在CMC以下, 考查了它們的插入對膜形態、完整性的影響, 并進一步建立了與細胞毒性間的關聯. 我們的研究在分子水平深化了磷脂與表面活性劑的作用方式、調控手段的理解.
2實驗部分
2.1實驗材料
二油酰磷脂酰膽堿(DOPC)購于Avanti Polar Lipids. Hela 細胞株、DiI、DMEM 細胞培養液購于江蘇凱基生物技術公司. 其它化學試劑購于國藥集團化學試劑公司. 所有試劑均為分析純.
2.2支撐膜與表面活性劑溶液的制備
磷脂支撐膜(SLBs)通過DOPC囊泡在二氧化硅或玻璃襯底自發融合制備, 囊泡通過擠出法在Tris-HCl緩沖液中制備, 詳見我們之前的報道[13]. 表面活性劑以給定濃度(C)溶于Tris-HCl緩沖液(模型膜實驗)或DMEM溶液(細胞實驗)中, 在實驗前超聲并離心除氣. 本研究的所有實驗溫度均控制在37 ℃, 數據平均值和標準方差均為三次以上實驗的結果.
2.3臨界成膠束濃度的檢測
采用LS55熒光光譜儀(PerkinElmer)表征了1-芘甲醛熒光隨表面活性劑濃度的變化(激發波長365nm, 發射波長400 - 600nm). 當熒光發射峰(λpeak)為473 nm時表面活性劑以單體形式存在, 發生峰藍移則表示達到CMC[11].
2.4石英電子微天平及耗散系數表征(QCM-D)
QCM-D在E1(Qsense AB)上進行, 使用二氧化硅沉積的石英芯片. 通過共振頻率(Δf)、耗散系數的偏移(ΔD)表征了芯片表面吸附層的質量與粘滯性變化. Δf與質量成正比, ΔD與耗散性成正比.
2.5熒光顯微觀測
在DOPC囊泡中摻雜1 mol% DiI熒光染料, 使用IX73熒光顯微鏡(Olympus, 100倍油鏡)與控溫灌流艙(Warner)對蓋玻片襯底(Fisher)的SLBs、及其接觸表面活性劑溶液后的熒光圖像進行了表征.
2.6MTT實驗
表面活性劑對Hela細胞的毒性通過MTT比色法進行了檢測. Hela細胞在96孔板鋪板后24小時, 加入給定濃度的表面活性劑DMEM溶液. 培養6 h后再加入MTT溶液, 孵化4 h后, 將底部沉淀溶于DMSO進行紫外吸收檢測(Bio-Rad 680, 檢測波長570 nm). 每個樣品進行了五個重復實驗.
3結果與討論
首先, 基于疏水探針1-芘甲醛在水相與膠束中的熒光發射峰差異, 熒光光譜表征了三種表面活性劑的CMC. 如圖1所示, 當CTAB在低濃度以單體存在時(CCTAB0.7 mM), 1-芘甲醛的λpeak為~ 473nm. 當CTAB濃度提高形成膠束后(CCTAB> 0.8 mM), λpeak逐漸藍移. 由圖1可得, CTAB、SDS與Triton-100的CMC分別為0.8, 5, 0.2mM. Triton X-100的CMC低于前兩者, 與早先報道一致[14]. 因此本研究將C限制在180 μM以下, 確保表面活性劑均以單體形式存在.
隨后, 通過QCM-D表征了三種表面活性劑與DOPC磷脂膜的相互作用. DOPC是生物膜中常見的雙電性磷脂. 許多研究基于該磷脂, 考察了模型膜與雙親分子相互作用, 發現能雙親分子能引起DOPC膜的三維空間形態變化[11, 15]. 而QCM-D能夠敏感地捕捉此動力學過程. Δf、ΔD分別反映著吸附層的質量和粘彈性變化. 實驗步驟如圖2A所示, 首先在二氧化硅襯底表面沉積囊泡以形成SLBs. 沉積平衡時的Δf~ -25 Hz和ΔD< 10-6表明形成了完整的SLB結構. 之后泵入表面活性劑溶液(C= 100 μM).
三種表面活性劑產生的膜響應具有顯著區別. 對于Triton X-100, Δf大幅降低, 說明大量表面活性劑進入吸附層; ΔD顯著增高, 說明表面活性劑引發磷脂膜明顯的形態變化. 同時, 緩沖液漂洗后, Δf、ΔD可回落到初始值, 說明高耗散的結構與吸附層并非緊密相連, 可被溶液環境中的機械擾動分離開. 而對于CTAB與SDS, Δf、ΔD僅有小幅偏移, 表明僅有微量表面活性劑插入磷脂層, 造成了很低的膜耗散性提高. 在15 min的作用時間內, Triton X-100、CTAB、SDS引起的平均Δf偏移分別為-6.4、-1.2、-0.1 Hz, ΔD偏移分別為2.4、0.28、0.1510-6. 因此, 非帶電性Trition-100能夠誘導最為顯著的膜變化.
隨后, 改變了三種表面活性劑的溶液濃度, 在C= 10 - 100 μM范圍內, 發現QCM-D的測量偏移量是與C直接相關的(圖2B). 較高的C產生了較大的Δf、ΔD偏移, 說明表面活性劑物質的量是誘發磷脂膜形態變化的決定因素. 而當C10 μM, Δf、ΔD的偏移基本消失.

圖2 QCM-D表征表面活性劑與SLBs的相互作用. (A) Δf - t 與ΔD - t 圖. (B) 在SLBs與CTAB (紅)、SDS (綠)、Triton X-100 (藍)作用15 min后, Δf、ΔD的偏移.Fig. 2 QCM-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etergents and SLBs. (A) Δf - t and ΔD - t curves. (B) Shifts of Δf, ΔD after 15 min interaction between SLBs and CTAB (red), SDS (green), and Triton X-100 (blue).

圖3 SLBs與表面活性劑作用前后的熒光顯微表征. (A) 完整SLB, 及其與(B) CTAB、(C) SDS、(D) Triton X-100作用15 min后的熒光顯微圖. 示意圖中黃色、綠色、紫色、藍色分別表示DOPC、CTAB、SDS和Triton X-100. 比例尺長度為10 μm. Fig. 3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imaging of detergent-induced membrane morphological responses. Fluorescence images of (A) intact SLB; 15 min aft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embranes and (B) CTAB, (C) SDS, (D) Triton X-100. Yellow, green, purple, and blue represent DOPC, CTAB, SDS, and Triton X-100, respectively. The scale bar represents 10 μm.
進一步在DOPC磷脂膜中摻雜1 mol% DiI染料, 熒光顯微技術表征了表面活性劑作用前后SLB的形態變化. 如圖3所示, SLB是一個均質的磷脂膜結構. 在與Triton X-100作用后, 膜表面形成了大量微泡出芽結構, 該結構可以被緩沖液漂洗除去. 而SLB與CTAB作用后, 表面出現了明暗光強不均的分布, 表明膜結構可能出現了非均的高度差異, 這在pH誘導的膜在組裝中也被觀察到[15]. SLB與SDS作用后變化最小. 因此, 熒光顯微觀測與QCM-D的結果一致, Triton X-100可誘發最為顯著的膜形態變化.
我們對不同表面活性劑產生的效應差異進行了分析. CTAB與SDS分別帶正電與負電, 而Triton X-100不帶電(圖1). 一方面, 由于自身分子間的靜電排斥, 初始插入磷脂膜的SDS或CTAB會抑制進一步的表面活性劑進入, 從而使磷脂膜內的表面活性劑濃度限制在較低水平(較低的Δf偏移). 但插入分子產生的過量膜面積會造成膜彎曲[15], 形成高低不均的分子層結構(熒光非均質). 這使得分子間過量壓力得以釋放, SLB下側的高耗散水增多(ΔD略增大). 另一方面, 由于自身分子間不存在靜電排斥, 初始插入磷脂膜的Triton X-100不會抑制進一步的表面活性劑進入(較高的Δf偏移). 在過量膜面積與分子自發曲率誘導的富集效應[16]下, 更容易形成高曲率的高耗散出芽結構(較高的ΔD偏移和熒光出芽點). 這種出芽結構能夠在外力的作用下失穩并脫離底面, 破壞磷脂膜的整體完整性.
最后, 考察了表面活性劑的模型膜響應行為是否影響到了細胞的正常生理功能. 在Hela細胞的DMEM培養液中加入了10 - 180 μM表面活性劑, 基于MTT實驗表征細胞的活力. 發現Triton X-100在100 μM的濃度即可對細胞活性產生影響. 當CCTAB= 180 μM, 細胞活力下降(Vc)至80.2%. 而在實驗濃度范圍內, SDS與CTAB并未對細胞正常生理行為產生負面效應. 因此, Triton X-100產生的生物膜三維結構的再組裝可能影響了細胞膜的穩定性與功能.

圖4 MTT表征表面活性劑溶液環境中的Hela細胞活力.Fig. 4 MTT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effects of DDG and GML on human cell viability.
4結 論
在CMC以上表面活性劑與生物膜的作用與調控機制已經被深入研究了. 但以單體存在的表面活性劑如何與生物膜相互作用仍是一個開放的問題. 在本文中, 我們考察了三種不同離子型的表面活性劑與生物膜的相互作用. 研究發現, 在CMC以下, 非離子型Triton X-100能誘發最為顯著的膜形態變化, 并引發細胞活力的異常. 機理分析表明, Triton X-100具有較弱的分子間靜電排斥, 使得它更易大量地插入生物膜, 從而誘導形成高曲率的非穩出芽微泡結構. 而帶電的CTAB或SDS由于分子間靜電排斥, 限制了表面活性劑分子的大量插入, 從而降低了對膜形態和完整性的負面影響. 我們的研究深化了表面活性劑與生物膜作用機制的理解, 對表面活性劑在生物醫藥、膜組分萃取等領域的深化應用提供了指導與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