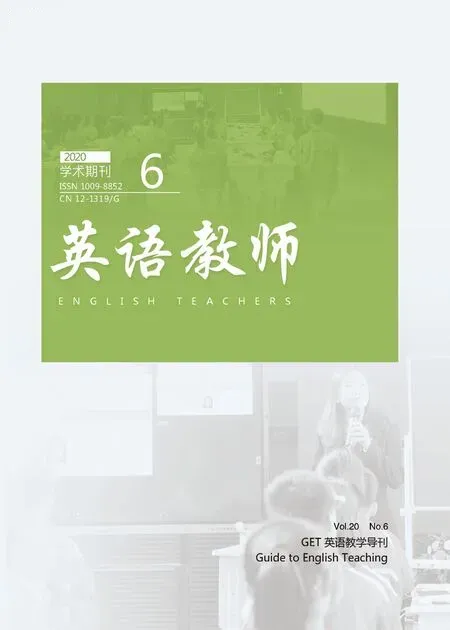初中學習者英語詞匯提取模式效應研究及其對基礎英語教學的啟示
韓玉強 趙夢雨 張運橋
一、研究問題
二語學習者往往在聽覺詞匯辨識上存在較大困難,視覺狀態下能夠識別的不少單詞在聽覺狀態中卻無法辨識的現象非常普遍(Goh 2000)。在國內,劉思(1995)驗證了英語學習者“閱讀詞匯”和“聽力詞匯”的不同,研究結果表明,與閱讀詞匯量相比,其聽力詞匯量明顯不足。陳曦(2003)認為應該充分重視這兩種詞匯之間的差距,并首先采用了“視覺詞匯”與“聽覺詞匯”的提法,這樣,二語學習者的詞匯視聽差異被提升到了不同感覺通路下的模式差異問題上。孫藍、許秋敏等(2006)認為詞匯性效應、詞頻效應、語義性效應、語境效應等影響心理詞匯提取的因素都無法解釋該差距,遂以兩種模式下的詞匯判斷作業為基礎提出了詞匯提取模式效應加以闡釋。不過,張淑靜、陳曉扣(2009)通過看寫法和聽說法兩種不同模式探討英語學習者的心理詞匯,得出結論:兩種模式的結果基本一致,不同模式不會對實驗結果產生太大的影響。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質疑了二語詞匯模式效應。
蔣楠(Nan Jiang,2000)的二語心理詞匯表征與發展模型認為,二語詞項在其最初詞形發展階段幾乎沒有任何內容信息,而只有其語音和拼寫等形式表征;到了母語詞目中介階段,詞目結構就會由母語對應詞的語義等內容來填充;最后再發展到詞匯整合階段,二語詞匯的詞形、語義、句法等信息高度融合進心理詞項,這構成二語詞匯發展的理想狀態。由此模型可知,二語心理詞匯的形式和語義在整合階段之前是分離的,且不少詞匯在最終整合之前就已停止發展,因此形義融合無從完成。很多英語學習者都經歷過聽到一個詞時,感覺很熟悉,卻不知其為何義的階段,也有過大聲朗讀英語,卻不知所云的經歷,這些現象也說明部分英語心理詞項音義分離,不具備語言符號的透義性特征。語言符號是由聲音和思想構成的“雙面體”,其真正的獨特之處在于其“透義性”。作為能指的“聲音”和作為所指的“思想”在自然狀態下形成一個特定的有機整體,在交際過程中,只要不發生某種障礙,如不是說話人的口音難懂或者音調特殊,人們的注意力就總是能集中在了解對方所傳達的思想上,而不去注意聲音的物理性質,“當我們感知到語詞指號的時候,那么,不同于所有其他的嚴格指號,我們并不感到它們的物質形狀似獨立的東西,恰恰相反,這個形狀似和它的意義混同到這樣一個程度,以致非在知覺失調的情形下,我們是不會去理會語詞指號的物質方面的存在的”(沙夫1979)。
認知心理學家安德森(Anderson)和鮑威爾(Bower)的雙過程理論(dual-process hypothesis)將長時記憶信息提取區分為再認和回憶兩個過程。再認是指事物再度呈現時仍能認識的心理過程。回憶是指過去的事物以形象或概念的形式在頭腦中重新出現的過程,通常以聯想為基礎。再認只需判斷測試項目在記憶中是否存在,而回憶不僅需要在記憶中搜尋某一項目,還要對其進行精確提取。相對來說,再認比回憶更容易。個體即使回憶不出來,仍可對某些刺激項目正確再認。因此,詞匯真假判斷即確認該詞是否真實存在,屬于再認范疇。而詞匯翻譯測試則需要通過詞匯語音或拼寫形式激活并提取語義,屬于回憶范疇。二者之間存在明顯差異。人們說母語時處于十分自然的心理狀態,進行詞匯判斷時一般能夠自動激活單詞的語義信息,而由于語言水平、母語干擾等因素限制,往往使二語詞匯難以達到形義相透(透義性),語義的提取往往需要顯性意識控制,即使詞匯判斷正確時也未必能夠充分激活或提取其語義信息,因此通過詞匯真假判斷作業考查二語詞匯的語義提取情況就不像在母語研究中那樣可信,而詞匯翻譯需要被試對詞匯語義充分提取。正是基于以上考慮,韓玉強、張素瑩(2017)并未采取詞匯真假判斷作業的方法,而是運用詞匯翻譯法,對非英語專業大學生進行詞匯聽譯和筆譯測試,分別通過語音和書面(視覺)形式充分提取語義,比較兩者得出詞匯語義提取的模式差異,結果表明,大學階段非英語專業學習者詞匯提取模式效應顯著。
然而該研究還沒有在基礎教育階段的英語學習者中展開,二語詞匯提取模式效應究竟從什么時間開始這一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因此,擬運用詞匯翻譯法探討初中學習者的英語詞匯提取模式效應,目的是驗證在此階段是否已經出現模式效應,從而對基礎英語(詞匯)教學有所啟示。
二、實驗過程
(一)確定對象
目前我國基礎教育階段英語課程(包括義務教育和高中兩個階段)按照國際上通用的分級方式被分為九個能力水平等級。在這個九級目標體系中,課程級別和基礎教育階段的各個年級不完全對應。義務教育階段(1—9年級),在小學從3年級開始開設英語課程的學校中,其學生需要完成一至五級目標要求,3—4年級對應一級目標,5—6年級對應二級目標;進入初中后,7—9年級分別完成三、四、五級目標。高中階段三年則要完成六至九級目標(教育部2012)。
本實驗計劃選取基礎教育中間階段的九年級上學期開始后的學生為研究對象。他們多從小學3年級開始正式系統學習英語,已經完成八年級四級能力目標的學習,目前正在學習五級目標要求的內容,正好處于九級能力水平目標體系的中間階段。因此選取江蘇省徐州市某中學八年級某一自然班進行測試,該班共有50名學生。
(二)選詞試測
為了測試學習者已經掌握的(4級能力目標)詞匯,本實驗從他們所用教材譯林版八年級英語教材(上、下冊)中的單詞列表中選取單詞。在選詞過程中,首先排除了帶*號即“只要求會讀,聽得懂,不要求拼寫”的單詞,以及語義不明確的單詞,如語氣詞等;其次排除了在不同單元以不同詞性或詞義出現的一詞多義詞,共得到600個單詞;最后以5%的比例進行系統抽樣,最終確定30個測試詞。
在正式實驗之前,隨機挑選5名學生進行預測,以確定正式測試所需的時間。筆譯單詞事先直接打印在測試卷上,其單詞發音采集自牛津詞典中的真人發音,并用Adobe Audition CC軟件進行降噪處理,效果清晰,適于播放測試。由于聽詞和看詞的用時存在差異,因此聽譯測試先期進行的5名受試聽譯所需的時間均多于筆譯。綜合5名受試的情況,最終確定聽譯每詞用時8秒,筆譯每詞用時6秒。
(三)正式測試
除去5名預測學生之外的45人參加了正式測試。測試分兩次進行,先進行筆譯,后進行聽譯(因為預期筆譯成績比聽譯成績好,先進行筆譯測試,如果聽譯成績受筆譯影響有所提高,只能說明實際情況比實驗結果所表明的差距更大)。為最大限度地減少影響,筆譯測試結束后兩個星期再進行聽譯測試,且受試事先對測試并不知情。兩次測試所選單詞相同,但呈現順序不同。測試前,明確告知受試測試僅用于學術研究,與其學習成績無關,同時要求他們在看到或聽到英語單詞后,根據第一印象在測試卷上快速寫出其所對應的中文詞義。測試過程監考嚴格,紀律良好,共獲取44人的有效答卷。測試結束后,課題組成員依照統一標準批閱試卷,每個單詞詞義正確得1分,錯誤不得分,成績為正確翻譯詞數。最后使用SPSS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三、結果分析

表1:聽譯、筆譯成績分析
從表1可以看出,在測試成績方面,筆譯得分率為70.1%,而聽譯得分率只有48.8%,而且聽譯成績標準差大于筆譯成績標準差,這說明被試在筆譯視覺模式狀態下對單詞的熟悉度較高,成績相對穩定,而在聽覺模式狀態下差異較大,成績不穩定;聽譯、筆譯成績的SPSS配對樣本t檢驗表明,兩種模式下的詞匯提取差異顯著(P<0.01)。
為充分說明這一差異,進一步將成績按照低、中、高三個層次及5分一檔劃分為六個分數段,對聽譯和筆譯測試成績在這六個分數段內的人數分布進行了統計(見表2)。如表2所示,兩組人數均呈正態均衡分布,表明測試數據有效,可信度高。在10分以下(含10分)的低分區間內,聽譯人數為9人,占20%,而筆譯人數僅為1人;在11—20的中間分數區間內,筆譯人數為19人,聽譯人數為31人,聽譯在中間分數段人數的占比超過66%;在21—30高分區間內,聽譯人數只有4人,而筆譯人數卻有24人,筆譯在高分段人數的占比超過50%。聽譯人數峰值(17人)出現在中下分數段(11—15),而筆譯人數峰值(17人)出現在較高分數段(21—25)。在較低的前三個分數段中,聽譯人數均高于筆譯人數;而在后三個分數段內,聽譯人數又均低于筆譯人數,聽譯與筆譯差距明顯。

表2:聽譯與筆譯測試成績區間人數分布
為了進一步證明聽覺詞匯和視覺詞匯之間的差距,還統計、分析了受試“聽譯對,筆譯錯”即純聽覺詞匯,以及“筆譯對,聽譯錯”即純視覺詞匯的數量對比(見下頁表3)。結果顯示,純聽覺詞匯的數量為34個,人均只有0.77;純視覺詞匯的數量為342個,人均為7.77,即受試平均約有8個純視覺詞匯,占全部30個測試詞匯的27%;而純聽覺詞匯人均不到1個,不足全部30個測試詞匯的3%,SPSS數據配對樣本t檢驗表明二者存在顯著差異(P<0.01)。如果將這兩組數據相減,就可以基本得到純聽覺詞匯和純視覺詞匯的差額,即在這30個隨機選出的英語詞匯中,受試視聽詞匯的均值差為7.7,比重約為23%,這就意味著在受試所掌握的閱讀詞匯中,至少有超過23%的詞匯無法在聽覺狀態下被識別,初中英語學習者詞匯的視、聽差距由此可見一斑,這嚴重制約了其英語聽說能力。

表3:受試“聽譯對,筆譯錯”及“筆譯對,聽譯錯”兩組單詞數量對比分析
綜合測試成績、成績區間人數分布、錯誤詞匯數量對比等三個方面的分析結果可知,受試聽譯、筆譯同一組英語詞匯的表現差異明顯,其英語詞匯聽覺能力嚴重不足,初中英語學習已經出現了顯著的詞匯提取模式效應。
四、研究啟示
本研究對基礎英語教學有以下幾方面的重要啟示:
首先,實驗結果表明初中生英語詞匯提取模式效應顯著,“單詞看得懂但聽不懂”的現象較為普遍,這一現象須引起廣大基礎英語教學工作者的注意,從而著手預防和解決該問題,否則將嚴重制約和影響初中生英語聽說能力的發展。
其次,初中生英語詞匯提取模式效應的深層次原因值得思考。語言介質的物質形態結構不同,語音形式在時間上展開,書寫形式在空間上分布,二者維度不同,其所分別依賴的語言聽覺、視覺信號在其感知與處理方式上也有著很大不同:語言聽覺信號是稍縱即逝的、多變的,且語流中信號之間的界限模糊;語言視覺信號則具有停留性、穩定性和邊界清晰性等特點。前者的干擾因素較多,沒有絕對不變的或標準的語音形式,音素和其實施不是一一對應關系;后者受筆跡影響,考慮到印刷文本在二語學習中占有絕對優勢,這種影響可以基本忽略。所以,語言聽覺和視覺信號加工的難易度應該會有所差異。
視覺、聽覺詞匯識別的接入代碼差別很大,前者為字法表征的起始音節,后者則為單詞語音的起始音素(Taft 1986)。語言的腦神經機制研究表明,不同模式的詞匯會經由不同的感知通道進入大腦,然后再由不同的腦區負責加工處理,語言知覺表征有著顯著的通道特異性。它們構成了詞匯提取模式效應的基礎。然而母語模式效應并不凸顯,不受研究者重視。這是因為雖然詞匯的輸入方式是特定的,但在某一層面上,詞匯系統所表示的項目卻是中立于輸入方式的,即“不管哪一種輸入,心理詞庫中的意義表征是統一的”(桂詩春2000)。更為重要的是,母語詞匯的透義性特點凸顯了其語義的本質,其物質形式多為無意識的自動加工,從而使詞匯輸入層面的差異在母語加工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
然而很多二語詞匯無法實現形義相透,并且其正字法和語音也很難做到充分,所以感覺通道的差異就會對這些詞匯的加工提取產生重要影響。再加上課堂環境下的二語學習一般很難將詞匯的口頭和書面形式學習安排在不同的學習階段,這與母語詞匯習得中的音義結合的第一性、拼寫表征的后起性完全不同(韓玉強2017)。這種“共時性”決定了語言介質的不同特點及其所依賴的語言視覺、聽覺信號加工的難度差異會對二語詞匯產生重要影響。而且由于二語輸入的主要來源是書面文本,以應試為目的的教學模式又長期重讀、寫,輕聽、說,這就使學習者通過視覺通道獲取語言輸入的機會要遠多于聽覺通道,詞匯純語音刺激和輸入的機會少、頻率低,致使學習者腦中所建立的詞匯形象多以視覺為主,正確的聽覺形象相應缺失,語音能力明顯不足。而中國學生因受其母語漢字學習經驗的制約,詞匯學習更加依賴視覺特征,特別是部分學生基于對26個英文字母加工提取的高度自動化,主要依靠拼讀字母記憶單詞,從而將單詞建構為詞義與字母串的結合體,這既忽略了語義與正確語音的結合,又忽略了字母與正確語音的形音對應,致使詞匯提取模式效應愈加顯著。
再次,從解決策略方面看,基礎英語教學宜及早采取相應的措施,指導學生正確學習英語,從而降低乃至克服這一效應。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1)要培養中小學生良好的英語語音能力,使他們能夠正確辨識和說出單詞發音。(2)要特別注意英語學習過多依靠視覺輸入的問題。當學習者缺乏足夠的語音能力時,視覺輸入方式的弊端尤其顯著。而二語學習的特點決定了這種局面難以避免,所以只能將其有效控制,并加以利用。一方面,英語教師必須反思二語教學語音、拼寫的教授時機,改變主要依靠文字輸入的二語學習傳統,堅持聽覺先行的多元化呈現策略,從而凸顯語音環節,避免其他感覺通道對語音的壓制。學習者在詞匯學習過程中宜遵循聽、說優先,讀、寫跟進的原則。所學的單詞要盡量做到聽后重復和聽后拼寫,在正確發音的基礎上,充分進行語音加工,并實現字母與語音的結合,然后再獲取其語義、語法和語用等信息,這樣既能夠實現語義與語音整體直呼的結合,又能夠實現分析式語音與拼寫字母的音形對應。另一方面,英語教師可以適時進行英語直拼法(Phonics,還有不同譯法,如自然拼音法)教學。英語直拼法正是利用表音文字語言的形音對應優勢,讓學習者通過分析/合成方式依照字母或字母組合發音直接寫出/讀出單詞,從而逐步內化其形、音對應規則,最終能夠“見形知音,聽音知形”。英語直拼法能夠幫助學習者在詞匯拼寫形式的基礎上,通過有效的形音聯結將視覺詞匯轉化為聽覺詞匯。由于學習者往往有著更大的視覺詞匯量,因而對詞匯提取模式效應問題的解決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另外,在英語學習的初始階段,英語教師還須慎重使用字母拼讀記憶、漢語拼音標音、漢字標音等對英語語音有著不良影響的詞匯學習方法。